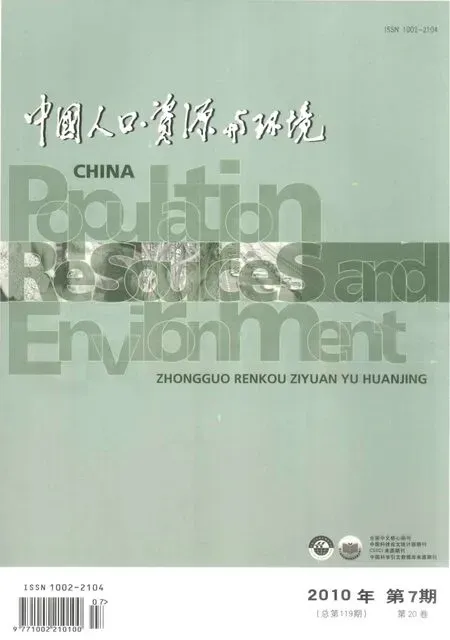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与完善*
2010-02-17邓海峰王希扬
邓海峰 王希扬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与完善*
邓海峰 王希扬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使这一权利作为财产,在市场上自由流转,我国于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已经为此创造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初具雏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仍然存在着外部的制度缺陷。其中,户籍制度作为一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管理制度,严重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至于使得这一制度所应发挥的基本功能被抽空。因此,本文提出以现行户籍制度为核心对当前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造,从而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扫清障碍。最初通过“以土地换社保,变农民为市民”的方法,允许进城农民在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下,有资格加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进而逐步过渡到取消基于户籍限制的城乡二元化模式,逐步构建覆盖全国范围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制度的基本功能。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全国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公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一编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将这一权利明晰为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用益物权,结束了几年来对其根本属性的争论,进而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走向商品化和资本化。法律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繁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级交易市场的形成理应指日可待。
但是,在现实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如立法者所愿,通过市场交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种种制约因素的掣肘,致使其实践成效大打折扣。其中,户籍制度便是诸多亟需克服的制约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户籍这一形成并发展于计划经济时期,以稳定社会、保障经济建设为目的而建立的旧制度愈发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的社会趋势。然而,现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却阻断了作为农民工进城务工配套制度出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致使我国出现了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低效率的双重不利局面。因此,我们需要在认识和分析户籍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建议。
1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现状
理论上,土地流转包括土地归属关系的流转与土地利用关系的流转两方面。其中,土地归属关系的流转,是指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如土地的买卖、赠与、征收等;土地利用关系的流转,是指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关系在主体之间发生转变[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不存在土地私有的现象。因此,我国土地权利交易市场的客体为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实际上仅指土地利用关系的转变。具体到农村土地权利交易而言,主要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二级交易市场上发生的权利主体的转变,包括转让、出租、入股、互换、抵押等多种形式。
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已经初具雏形并日渐成熟,但近年来,这一市场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预期之繁荣顺畅。事实上,虽然我国的法律与各项配套政策已经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依据与基础,但现实中各种制约因素仍然在对这一过程发挥着制约作用。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完全走入交易市场,真正作为生产要素供给手段的功能难以发挥,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资本性收入的预期难以达到。因此,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减少上述阻碍因素,使土地使用权能够充分发挥投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显示出巨大威力。
2 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
2.1 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管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常规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及管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和迁徙等方面[2]。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社会身份与经济身份相包容的城乡户籍差异在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中国在建国初期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所普现的城市贫民问题[3]。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所取代,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始活跃起来。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之下,城市居民脱离了国营、城市大集体单位,其依托于国营、大集体单位的经济身份自然而然地随之消失,成为了不受所属经济组织形式约束的自由人。与此同时,城市居民能够基于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获得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使其在自主地选择职业、居住地的同时毫无后顾之忧。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还原经济自由为导向的经济身份改革未能在农民身上得以实现,同时,社会身份又决定了他们在离开土地、脱离集体经济组织后没有新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土地维系生存,无法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可以说,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犹如一道无法跨越的藩篱,束缚着城乡各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换,由此引发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走向。
2.2 户籍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户籍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通过农民所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发生联系。
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承包方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交易仅局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内。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取得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参与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其二,从发包方处直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要受到严格限制,“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也就是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只有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才能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别是想要承包农村土地的城镇居民,只能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四荒”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次分配的过程中,如果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受让方则不受限制,而受让方非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取得集体经济组织一定数量以上成员的同意,并经乡或镇政府批准。对于农村人口来讲,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身份决定其有资格作为承包方,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对于非农人口,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就要受到严格限制。
2.3 现行户籍制度制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原因
农村土地对农民具有生存保障与投资的双重作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功能的长期趋势将呈现为从生存保障走向投资[4]。在此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际上具有多重功能:其一,打破原有的静态财产权分布格局,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刺激土地投资价值的实现,促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进一步市场化;其二,为打破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奠定经济基础,为农民的自由流动创造制度可能;其三,为实现土地所承载的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货币化创造制度支撑。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城镇居民的经济自由,但对于亿万农民来讲,社会身份和经济身份都没有随之改变,他们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土地提供最根本的保障、需要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行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根本制约就在于:这种身份差异所引发的更为深层次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别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项功能难以实现。分述如下: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引发的二元就业制度阻碍农民的自由流动。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民工们挥汗如雨的工作场景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居民的社会身份没有得到转变,很多工作岗位都将农民工拒之门外,想要在城市中找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难上加难,例如很多收入高、待遇好的岗位在招工的范围上有严格限制,唯有城市居民才属于被招用的对象,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只能望而兴叹[5]。在市场化改革下,城镇居民在经济身份上摆脱对国营单位的依赖,获得职业选择的自由。但对于农民工来讲,他们进入城市却仍然属于农村村民,社会身份没有能够转变为城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农民的流动创造了制度可能性,但现行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无法自由选择职业,使得这种可能性难以成为现实。
第二,现行户籍制度制约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货币化。对于农民来讲,一方面,土地上之权利作为一种动态财产权,能够通过市场化流转的途径实现价值,促进土地投资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作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依靠,负有生活、就业、养老三重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能够使土地的投资与社会保障双重功能的价值实现货币化。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农民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后,只获得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部分资源性价值,土地的级差地租远远没有在土地流转的对价中反映出来[6];另一方面,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货币化未能得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社保功能货币化实际上是农民进城后基于身份转变而应当取得的城镇社会保障,而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区别化使得农民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无法完成由农民身份到城镇居民身份的社会身份转化,从而导致农民在退出集体经济组织,丧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会身份后,无法取得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从而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待遇的社会保障。这一项对于农民安身立命至关重要的功能无法实现必将造成两重后果,并且该后果将根本制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其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价值应当囊括土地的两项基本功能:生存保障和投资,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是这两项功能转向货币化的过程。然而,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货币化无法实现,直接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的市场价值大幅减损,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货币价值降低,使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性价值被制度性压低。长此以往的交替循环就造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值钱的怪现象。
其二,对于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早已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却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走进城市之中,却无法成为城市的主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意味着将丧失土地这一自然的社会保障基础,同时他们又无法像城市人那样享受各种社会福利性救助,一旦遭遇失业将毫无生存保障。而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发生,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约有2 000万外出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而在这些返乡农民工中,有1 000万早已没有“承包地”[7],他们正面临着失业又失地的生存问题。严峻的现实状况加重了农民的“惜地”心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想法愈发根深蒂固,他们宁愿“撂荒也不转让”的保守态度,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明显制约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可见,现行户籍制度是直接造成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货币化无法实现的重要根源,也是间接压低土地资源性价值的重要根源。它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后两项功能落空,即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受阻,土地社保功能货币化无法实现。而建立动态土地资产的第一项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的自由流动以及土地社保功能货币化的实现。由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本应发挥巨大作用的三项功能基本被抽空,而其弊害则是深远的。
其一,违背建立平等、自由的共同体成员关系的正义伦理。这里所说的社会共同体,主要表现为国家。平等意味着一国之内的所有公民应当享受最基本的权利和受到最基本的保护,国家不应根据人们的出身、职业、居住地等在政策和制度上区别对待公民,而应当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8]。很显然,现行户籍制度无形中造成了户口身份的高下、贵贱之分,进而引发制度歧视。
其二,阻碍生产要素在市场间的合理流动。市场经济要求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依靠价值规律的调节在市场上自由流动,现行户籍制度却极力限制土地、劳动力在体制内的流动和转移,而且继续为各种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执行提供依据和条件[9]。这一制度早已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不相协调,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背道而驰。
其三,侵害了国民于城乡间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阻隔不仅表现在阻止农民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同时还表现在阻止城市居民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基于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享有成员权的可能。
长远来看,这种制约将造成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由形式矛盾走向实质矛盾,成倍放大未来改革的成本。
3 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
根据以上所述,针对现行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为了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有效发挥,本文提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建议,根本目的在于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扫除障碍。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需要以新的社会保障方式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使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货币化得以实现;
第二,城镇市民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当避免出现既享有城镇社会保障,又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超级公民”待遇。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转让权利后如何办理城市社保接续和城镇居民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如何实现社保关系的转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此,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对策:
其一,彻底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体制,实现全国户籍的统一,进而实行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国外户籍管理的经验来看,户籍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作为公民身份的证明以及国家统计人口的工具。而自19世纪形成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偏离了其原初的功能。其实,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不在于制度本身,恰恰在于它承载了太多原本不应当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改革户籍制度的根本目标在于恢复户籍制度的单一功能,取消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种种附加值,使其从区别公民待遇的手段转变为纯粹的公民身份证明和政府人口统计工具。只有建立功能一元化的户籍制度,才能保证城乡居民具有统一的公民身份,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事实上,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最主要体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化,依据城里人或农村人的不同,享有的社会保障也不相同。目前,我国城镇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级统筹,有些地方是地市级统筹[10]。由于农民工普遍在其居住地以外的省市打工,他们无法取得工作地的城镇户口,该省市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就完全将户口不在本省市的农民工排除在外,造成了农民工无社保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并设立覆盖所有公民的普遍社会保险金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这种普遍性的社会保险,公民均有资格成为投保者,并且只要投保达到一定年限,同时符合该项社会保险对领取者的要求就可以享受社会保险金。这种打破旧体制而重新建立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减少不同地区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成本,有助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将从根本上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障碍,以新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取代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充分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货币价值。当然,这种较为激进的破旧立新式改革,显然需要付出较长的准备时间方能实现。
其二,维持现有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仅将城镇的社保体系加以改造,使其不再设置户籍限制而向农民开放,即“以土地换社保,变农民为市民”的改革方法。城市居民“有社保无土地”、农村居民“有土地无社保”的现实状况是由城乡居民不同的生活条件决定的。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生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比农村居民要大,因为城市居民一旦失业,将会完全失去收入来源,而农村居民尚有土地可以依赖。这种原本相安无事的局面随着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被打破,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身份实质已由农民转变为工人,但却无法以城镇居民的身份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由此引发出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民没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即“放弃土地以换取社保”或“放弃社保以换取土地”的选择模式没有形成。
因此,在维持现有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下,进一步改造城镇社保体系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对于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工,应当允许他们通过缴纳一定社会保险费用的形式加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也就是说,进城农民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真正转变为城镇市民,有资格参加城镇的社会保障。这样做便于操作和管理,可以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保障问题[11]。而对于那些想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城市人,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当放弃城市给予的社会保障,由城镇市民转变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 结 语
在市场经济迅猛如潮的今天,我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与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之的遭遇截然不同:如今,农村经济已经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12],许多农民已经不再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为生存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改革将更多的中国农民与市场而非土地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命运是与市场化紧密联系的。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使这一权利成为财产,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转,而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人,可以通过理性的风险评估和分析,选择保有权利或者将其让渡,从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现行户籍制度及其所引发的问题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顺理成章地通过市场化实现其价值,法律所构建的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就无异于是纸上谈兵,无形中浪费了立法资源、增加了适法成本。因此,以破除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主张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模式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允许农民通过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加入到城镇的体制中来,变农村户口为城镇户口,并有资格取得城镇社会保障,而对于城镇居民,也可以在放弃城镇生活条件的前提下,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份子享有成员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过渡至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再以户籍作为公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建立以身份证为核心的统一公民身份制度,最终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编辑:田 红)
References)
[1]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4.[Meng QinGuo,et al.Study on China’s Rural Land Circul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9:44.]
[2]陆益龙.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Lu Y iLong.Beyond the Household:to Analyse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4:1.]
[3]Tiejun Cheng,Mark Selden.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9:650.
[4]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8.[Meng QinGuo,et al.Study on China’s Rural Land Circul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9:18.]
[5]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40.[Yu DePeng.Urban and Rural Society:From Isolation towards Openness:Study on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w[M].Jinan:Shandong People’s Press,2002:140.]
[6]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8.[Meng QinGuo et al.Studyon China’s Rural Land Circul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9:108.]
[7]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外出劳动力返乡问题日趋严重对土地承包关系的影响初步显现[EB/OL].2009-03-03,[2009-03-29]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03/110111348.html.[Rur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Ministry of Agriculture.Increasing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and the Beginning Impact to L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EB/OL].2009-03-03,[2009-03-29]
[8]刘翠霄.天大的事——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25.[Liu CuiXiao.Study 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 Farmers[M].Beijing:Law Press,2006:125.]
[9]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02.[Yu DePeng.Urban and Rural Society:From Isolation towards Openness:Study on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w[M].Jinan:Shandong People’s Press,2002:302.]
[10]刘翠霄.天大的事——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95.[Liu CuiXiao.Study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 Farmers[M].Beijing:Law Press,2006:295.]
[11]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课题组.以土地换社保变农民为市民——改革户籍制度的基本思路[J].四川改革,2007,(10):29.[Research Group in Sichuan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Changing Land Rights for Social Security,Making Peasants Become Citizen:the Basic Idea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ation[J].Sichuan Reformation,2007,(10):29.]
[12]刘翠霄.天大的事——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8.[Liu CuiXiao.Study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 Farmers[M].Beijing:Law Press,2006:198.]
AbstractBeing usufructuary right,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as a kind of property can be traded in the marke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perty Law”,which was promulgated in 2007,has created the solid protection to this trade system.However,the emerging trade market of this land rights still has external system problems.As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which is a product of the planning-market economic system,hinders the market circulationof this right seriously.Therefor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focusing on the exis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we need to reform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which is basedo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o as to clear th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At the beginning,through the wayof“changing land rightsfor social security,making peasants become citizen”,rural migrant workers can get social security on the premise of giving up their rural land rights.Finally,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a new nationwid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functions of 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nationwid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strictions to 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fro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DENG Hai-feng WANG Xi-yang
(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F301.1
A
1002-2104(2010)07-0097-05
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6
2009-12-07
邓海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自然资源法。
*该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环境法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自然资源物权创新制度研究”(编号:2007JJD820166)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