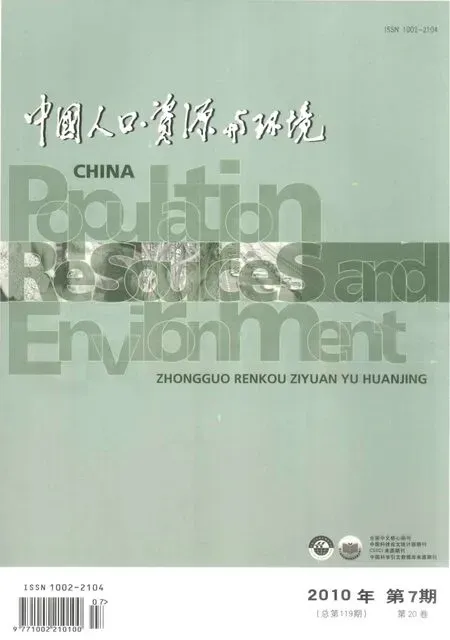“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解读3
——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冷静观察
2010-02-17王小钢
王小钢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解读3
——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冷静观察
王小钢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最大的立场之争可能是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政治辩论。“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哲学基础。历史责任、矫正正义和“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体现了“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理念。人均排放权和平等参与权则体现了“给平等者以平等”的理念。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视域中,不是中国,而是丹麦和美国劫持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从中国的立场看,国际社会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之后理应在“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理念基础上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国际社会应将历史累积排放量和人均GDP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参考标准。其次,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律令和后代人的正当需要,国际社会应将人均累积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参考标准。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按照平等参与原则开展将来的国际谈判。
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历史责任;人均标准
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落下帷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各缔约方均不太满意,尽管缔约方会议同意“注意到”(taking note of)《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由于苏丹、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的反对,缔约方会议没有通过《哥本哈根协议》。在联合国条约中,“注意到”的术语意味着缔约方会议没有批准也没有通过,不持肯定态度也不持否定态度。哥本哈根会议中最大的立场之争可能是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的政治辩论。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BASIC四国)在多次谈判场合重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甚至在12月18日领导人会议上发言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修改为“共同但有区别的回应”(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es)[1]。在气候正义的视角下,全球气候体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视域中,究竟是哪些国家劫持了哥本哈根会议?从中国的立场看,国际社会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又应如何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哲学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徐以祥博士认为,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中,适应气候变化所适用的哲学原则是矫正正义,减缓气候变化所适用的哲学原则是分配正义[2]。芝加哥大学波斯纳(Eric A1 Posner)教授与孙斯坦(Cass R1 Sunstein)教授从经济分析和道德哲学的角度主张,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减排上花费大量资金并不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合理方式,更合理的方式是直接向穷国的穷人支付现金;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矫正正义的论辩错误地将国家视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历史排放的前代人已经逝世,由当代人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受害者还没出生,没有过错的当代富人却被迫向没有受到这些富人排放行为损害的当代穷人做出赔偿[3]。剑桥大学拉加马尼(Lavanya Rajamani)博士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哲学基础是“给平等者以平等”(equality for equals)、“代内公平”(intra2generational equity)和“恢复性平等”(restoring equality)[4]。
1986年8月30日,国际法协会在汉城通过的《关于逐渐发展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宣言》(简称《汉城宣言》)宣布,平等(非歧视)原则“是指对同等的情况应同等地对待,对不同等情况应该按照……不平等给予相应的不同等待遇”。《汉城宣言》在“3.1公平原则”中还宣布,“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应依符合公平原则的条约和国家实践发展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公平协调各种相同和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本文看来,“给平等者以平等”(equality for equals)和“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inequality for unequal)构成了全球气候体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哲学基础。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睿智地写道:“给平等者以平等,不平等者以不平等,才是正义的真正呼声;由此可以推出,永远不要平等对待不平等”[5]。徐以祥博士所谓的分配正义属于“给平等者以平等”的哲学范畴。拉加马尼博士所谓的“代内公平”和“恢复性平等”和徐以祥博士所谓的矫正正义都属于“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哲学范畴。
1.1 “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
《汉城宣言》中的平等原则也可以称为比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义并不是算术中的平等,而是一种相互关系中的平等,合乎比例的平等[6]。在全球气候体制中,平等原则并不要求美国和图瓦卢排放一样多的温室气体,而是要求各国在承认既有事实性差异基础上达致某种合乎比例(比方人口比例)的平等。因此,在全球气候体制中,“差别待遇合乎比例地体现了既有事实性差异”[4]。因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历史排放而造成的适应气候变化问题,至少应根据两个既有事实性差异适用“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哲学理念。根据“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理念,“区别的责任”可以表现为历史责任(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与能力有关的责任”甚或矫正正义。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既有的事实性差异的第一个表现为历史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根据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全球CO2排放数据库,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CO2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哲学理念意味着发达国家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承担历史责任。历史责任遭受发达国家质疑的两个主要原因是:①当代的穷人遭受的损害实际上来自过去世代的排放行为,而不是来自当代的富人;②过去的世代在排放温室气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威胁气候系统,因而他们并没有任何过错。如果一项国际条约要求发达国家为其历史排放承担历史责任,那么这实际上是通过一项溯及既往的法律要求发达国家为其在过去根本没有任何过错的排放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进而言之,这项国际条约的惩罚对象不是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人,而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诚然,当代人不应为前代人的不当行为负责。然而,当代人从前代人透支地球环境吸收能力的不当行为中受益,因此当代人必须为前代人不当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7]。按照一般观念,当一人死亡以后,他的债务随着他身体的消亡而消灭。然而,当他的继承人继承了他的财产时,他的继承人就必须以他继承的财产来清偿的债务。在全球气候体制中,道理亦应如此。发达国家的当代公民从他们民族的历史排放中继承了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各种物质财富,因此他们要对因他们民族的历史排放而遭受损害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责任不仅源于“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s pay principle),而且源自“受益者补偿”原则。“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补偿”原则都是“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哲学理念的体现。其中,“污染者付费”主要处理在世的当代人在过去和现在的排放问题;“受益者补偿”原则主要针对过去的世代在过去的排放问题。
过错并不是承担补偿责任的必要条件。正义的全球气候体制旨在改变当前糟糕的气候变化状况。这种糟糕的气候变化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造成的。虽然发达国家的过去世代在排放温室气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威胁气候系统(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没有过错,不是坏人),但是他们当时排放的温室气体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一直累积到现在,造成了当下糟糕的气候变化状况。然而,发达国家承认它们的累积排放,但不承认它们有任何过错。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Todd Stern)博士在哥本哈根会议中说:“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的绝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充满喜悦却不知道排放会导致温室效应的事实……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排放(温室气体)到大气层的历史角色——这些温室气体现在仍然在大气层中。但说到内咎感(the sense of guilt)或罪责(culpability)或补偿(reparations),我绝对不同意。”从气候正义的视角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虽然发达国家在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排放中没有过错,但是根据“受益者补偿”原则它们对其历史排放负有补偿的责任。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既有事实性差异的另一个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力(财力和技术资源)的不同。“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哲学理念意味着每个人、每个机构和每个国家都有责任根据其能力解决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个经济实力强的个人、公司或国家应当比那些经济实力弱的个人、公司或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发达国家并不是绝对否认这种“与能力有关的责任”,它们只是倾向于把这种责任理解为一种恩惠、慈善活动或福利援助。芝加哥大学波斯纳教授与孙斯坦教授认为,财富从富国富人向穷国穷人的再分配是极其可欲的,这种再分配可以很好地增加总体社会福利[7]。然而,他们否认这种福利主义考虑与历史责任的联系。
诚然,“与能力有关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源自福利主义考虑。相对于富人而言,穷人的一美元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事情恰恰如此。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国家往往是那些财力和技术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例如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一美元不能为富国富人带来多少福利,但是可以为这些穷国穷人适应气候变化带来更多的福利。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不能将“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与历史责任完全割裂开来。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在财力和技术资源方面的能力优势恰恰源自于它们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的工业化进程。如果没有巨大的累积排放量,发达国家就没有今天的财力和技术资源优势。因此,与历史责任一样,“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不仅源于“污染者付费”原则,而且源自“受益者补偿”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与能力有关的责任”和源于累积排放量的历史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发达国家无法否认能力优势与累积排放量的联系,也不能否认“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与历史责任的联系。
矫正正义是另一个与历史责任相联系的哲学理念,尽管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微妙的区别。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补偿的或矫正的正义(diorthotic justice)适用于这种情况:某人不当地损害了另一个人的利益,作为其结果的损失必须得到补偿[8]。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矫正正义与个人自由意志密切相关:一方面侵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另一方面侵害者的行为侵害了受害者的自由意志(欺诈或胁迫)。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和芝加哥大学波斯纳教授与孙斯坦教授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反对在气候变化领域适用矫正正义。然而,如果我们把“矫正正义”理解为被侵害的财富、荣誉和权利的恢复和补偿,那么发达国家缔约方从1992年缔结《公约》,尤其是从《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生效到当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理应适用“矫正正义”的哲学理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伯(Daniel A1 Farber)教授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1992年缔结了一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条约;由于国际社会已经明确认识到温室气体排放会造成巨大损害,在1992年以后的任何温室气体排放者都至少知道他们的排放行为的损害性质;现在断言排放者具有罪责可能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没有采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谨慎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过失侵权(negligent)[9]。《公约》要求附件1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回复到其1990年水平。然而,据《公约》秘书处的统计,从1990-2005年,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2516%,加拿大增加了2513%,美国增加了1613%。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发达国家的额外排放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侵害。按照“矫正正义”的要求,发达国家理应补偿发展中国家的损失。
1.2 “给平等者以平等”
在气候变化领域落实“给平等者以平等”理念的第一个命题是,地球的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大气空间的权利。人均排放权原则构成“共同责任”的另一个重要面向。由于担心需要花费巨额美金购买排放许可证,美国坚决反对人均排放权的概念。芝加哥大学波斯纳教授与孙斯坦教授认为,基于“公平”(fairness)的人均排放权论辩将会遭受严肃的反对;如果将“公平”理解为平等地或者合乎比例地分担气候条约的成本,按人均分配的方案因其没有考虑这项条约的所有效果而显得很不“公平”——任何一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条约都将使一些国家受益比其他国家更多,使一些国家受损比其他国家更多;在这种情形下,人均排放权只是貌似公平,实际上并不能带来公平的结果[10]。波斯纳教授与孙斯坦教授反对人均排放权的论辩只考虑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分担,而忽视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分担。减缓气候变化主要关涉在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分配基础上的大幅度减排;适应气候变化主要涉及在历史上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基础上的损害补偿问题。在波斯纳教授与孙斯坦教授看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不能根据历史责任和矫正正义主要由发达国家分担,只能计入到各个国家因缔结气候条约而遭受的损失——这种损失的不平等分配只能归因于按人均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方案。如前文所述,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分担是另外一个问题,它适用“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哲学理念——适用历史责任、“与能力有关的责任”甚或矫正正义原则。
印度目前在人均排放权方面的立场是,各缔约国人均排放量在将来的趋同是建构公平的全球气候协定的唯一基础。印度的长期趋同立场接近于目前广为国际社会接受的“紧缩与趋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方案。按照这种方案,人均排放量高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大幅度减排,人均排放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适当增长,各国在某个目标年度(例如2050年)的人均排放量大致“趋同”;然后各国继续共同减排,通过“紧缩”在远期年份(例如2100年)实现全球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按照这种方案,由于中国人均排放量已经接近或很快超过世界人均排放量,中国绝对排放量在未来几十年中必须持续缩减。因此,中国目前在人均排放权方面更倾向于“两个趋同”的立场,即各缔约国的从基准年到目标年度的过渡期内人均累积排放量和目标年度人均排放量的双重趋同。双重趋同的概念早先见于清华大学何建坤教授等的论文[11]。2008年12月,作为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的何建坤在波兰波兹南《公约》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COP-14)中正式提出了“人均累积排放”的概念。如果把IPCC发表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1990年作为分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基准年,各国可以实现在目标年度(例如2100年)人均排放量大致“趋同”,并在从基准年到目标年度的过渡期内人均累积排量也大致“趋同”。中国和印度都坚持,地球上的每位公民平等地分享这个星球的大气空间。因此,中国理解的“大气空间”包括未来的大气空间和过渡期内的累积性大气空间。印度理解的“大气空间”主要是未来的大气空间。鉴于地球的每位公民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度都应平等地分享大气空间,所以现在和将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分配理应坚持人均排放权原则。
在气候变化领域落实“给平等者以平等”理念的第二个命题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家平等地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汉城宣言》宣布了平等参与原则:“所有国家法律地位平等,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均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国际决策过程以解决世界经济、金融及货币问题;在国际组织内,这一原则应促成建立一种能公平地兼顾所有有关利益的决策制度”。显而易见,平等参与权原则根源于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在气候变化领域,平等参与权原则构成“共同责任”的一个重要面向。爱丁堡大学波义尔(Alan Boyle)教授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要是指“一种在形成国际法的过程中进行合作的义务”,“它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一种公平基础,发展中国家有权在谈判达成应对全球环境关切方面的新法过程中依赖这种公平基础”。波义尔教授接着写道:“而且,这个原则在设定参照标准方面也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在随后谈判达成进一步的实施协议中或在解释现有条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正是依据这些参照标准而定”[12]。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权容易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遭受发达国家的侵犯。
2 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审视哥本哈根会议
2.1 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会议吗?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发达国家及其媒体纷纷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哥本哈根协议》中的各种缺陷承担责任。12月20日,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 Miliband)在《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哥本哈根之后的路》的文章,指责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会议——“我们未能就2050年以前全球减排50%或发达国家减排80%达成协议。这两个提议均被中国否决,尽管得到了发达国家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3]。中国果真“劫持”了《哥本哈根协议》了吗?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提议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吗?它们符合“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的哲学理念吗?
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的《公约》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最终目标)。根据“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的哲学理念,《公约》还具有第二个目标——“生态空间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the ecological space)[4]。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当前提出的“气候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临界点。根据气候变化科学数据,如果要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的概率限制在50%之内,那么在2000-2050年之间全球排放的CO2不得超过5 000亿t。因此,第一个目标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前半部分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5 000亿t。第二个目标意味着必须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平分配CO2的排放空间(生态空间)。由于拥有较少人口的发达国家却占据了绝大部分生态空间,它们必须大幅度降低其在全球排放中的份额。为了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公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必须率先大幅度强制减排,并且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以促使其适应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的上述两个提议至少在两个方面违背了“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的哲学理念,偏离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要求。首先,发达国家的提议强调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轻视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进而很可能促成发达国家掠夺性地继续占据发展中国家应得的“生态空间”。为了将21世纪前50年的全球排放总量控制在5 000亿t CO2以下,仅仅强调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远远不够。因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仅与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有关,而且与发达国家在2010年之后40年的减排路径有关。我们假设可以为发达国家设计两种减排路径:①发达国家在2045年以前小幅度减排,然后持续减排并在2050年以前实现减排80%;②发达国家在2020年以前大幅度减排至40%,然后持续减排并在2050年以前实现减排80%。显而易见,第一种减排路径虽然也可以实现“发达国家在2050年以前减排80%”的目标,但是发达国家在2010年之后40年间的排放总量远远高于第二种减排路径。如果接受发达国家的上述两个提议,在《哥本哈根协议》中只写入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不写入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那么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选择近似于第一种减排路径的减排方案。实际上,如果发达国家实际履行其当前分别做出的政治允诺,那么它们很可能要比第二种方案多排放1 000亿t CO2。于是,拥有较少人口的发达国家在将来的40年间仍然会占据远远超过其在全球排放总量中应得份额的排放空间,违背了“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理念和《公约》的第二个目标。反过来说,由于拥有世界人口19%的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近75%的排放空间,“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哲学理念要求发达国家必须按照接近于第二种减排路径的减排方案率先大幅度强制减排。
其次,发达国家的提议可能将“2050年以前全球减排50%”和“发达国家减排80%”捆绑在一起,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发展中国家根据人均排放权利理应享有的“生态空间”。这两个提议捆绑在一起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在2050年以前将绝对排放量减少20%,将人均排放量至少减少60%”;“在2050年以前,美国等发达国家获许的人均排放量将比发展中国家高2-5倍”[14]。IPCC的科学建议是,发达国家在2050年以前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减排90%(而非8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50年前后的人均排放量应大致趋同。实际上,根据这两个提议,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降低2050年的减排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放慢未来40年间的减排速率——这样必定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排放量的不平等,导致无法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在2050年前后大致趋同的预定目标,从而违背了“给平等者以不平等”的哲学理念。
正因为发达国家关于“2050年以前全球减排50%或发达国家减排80%”严重偏离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要求,中国才在哥本哈根会议中拒绝了发达国家的这两项提议。发达国家的这两项提议试图加重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负担,把按照《公约》本应由发达国家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严重违背了“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的哲学理念。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提出了自愿性减缓承诺,即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础上主动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开展自愿性减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没有“劫持”哥本哈根会议,相反为发展中国家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且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2.2 丹麦和美国“劫持”了哥本哈根会议吗?
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看,尤其是在“给平等者以平等”理念(平等参与权和人均排放权)的视角下,丹麦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试图“劫持”哥本哈根会议。
2.211 平等参与权
12月 14日,哥本哈根会议主席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提出建议,先谈《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草案文本,希望在2010年达成“单一协议文本”。非洲集团反对这种弱化《京都议定书》的程序,反对“单一协议文本”和“双轨合一”,进而退出会议。非洲集团首席谈判代表宣称,《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主席在没有征求非洲国家意见的情况下就提交了工作组草案文本。因此,非洲集团反对这种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洲国家在谈判中被边缘化,平等参与权遭受侵害。为了支持非洲集团的行动,“77国集团与中国”也威胁集体退出谈判。在这种情形下,赫泽高同意先谈AWG-KP草案文本,再谈AWG-LCA草案文本。12月16日,丹麦首相拉斯穆森(Lars L 12月18日凌晨,丹麦邀请26位政府首脑举行了一次小型秘密磋商会议,试图形成一个协议。第一,这些与会的政府首脑完全是主席国遴选的,没有经过《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同意。第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接到邀请,被扔在一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据此指责这种排斥性的会议只能导致一份秘密协定,宣布委内瑞拉不会接受这份秘密协定。第三,主席国甚至没有公布,哪些政府首脑被邀请,与会的政府首脑将要谈些什么。由于这种会议违背了包容性、透明度和平等参与原则,这种会议的成果也被认为带有偏见和排斥性、缺乏合法性,因而很难在缔约方会议上以协商一致的形式获得通过。当拉斯穆森最后将这份命名为《哥本哈根协议》的秘密协议提交给缔约方(全体)会议讨论时,很多政府谈判代表严厉批评了这种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惯例的秘密磋商程序。 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作为主席国的丹麦在程序上过于偏向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的平等参与权。会议主席拉斯穆森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协调和听取发达国家的意见,并试图将丹麦准备的一份协议草案和26国政府领导人秘密磋商会议形成的协议草案强加给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经常遭受轻视甚至是忽视。这种违背平等参与权的程序一方面浪费了很多时间,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用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相不信任,导致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小公分母”(lowest2common2denominator)的《哥本哈根协议》最后也没有获得缔约方会议通过。 2.212 人均排放权 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英国《卫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份从哥本哈根会议泄露出来的《丹麦文本》(Danish text)。这份由丹麦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草拟的《丹麦文本》严重背离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宣布发达国家在2050年以前的人均排放量上限为2167 t,发展中国家为1144 t。“77国集团与中国”小组主席迪阿平(Lumumba Di2Aping)回应称:“《丹麦文本》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对大气空间的正当、公平和公正的份额。该文本试图平等对待富国和穷国。我们不会接受一份导致世界80%人口陷入更深痛苦和不义的协议”[15]。通过宣布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为2167 t CO2和发展中国家为1144 t,丹麦和美国试图将这种不平等写入《哥本哈根协议》作为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丹麦和美国的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给平等者以平等”的哲学理念,而且直接违背了普通人的正义感。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这份无视人均排放权的《丹麦文本》提出了抗议和不满,《丹麦文本》后来并没有提交给缔约方会议进行讨论。 此外,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博士在哥本哈根会议中提出,中国在2020年以前将比美国排放多得很多的温室气体——“你只需做一道算术。这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道德问题,或者一个其他问题。这只是一个算术问题”。这种纯粹建立于效率基础上而完全忽视公平问题的观点,不仅违背了人均排放权原则,而且直接违背了普通人的正义感。由于从1992年开始一直没有减排甚至后来还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62142亿t CO2当量持续增长到2005年的72162亿t。由于在这15年间的人口持续增长,美国温室气体年人均排放量却一直没有多少起伏。这个数据也说明,如果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强制实施减排,那么其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将一直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美国每年人均排放20 t CO2当量,大概是中国人均排放量的4-5倍,印度的10倍,非洲的20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8倍。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尤其是根据人均排放权原则,美国理应率先大幅度强制减排,以期其人均排放量在某个目标年度(例如205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法律哲学中的“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理念,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遭遇无情和霸道的权力政治。《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际谈判中也总会遭受冷酷和专横的暴力劫持。传统的国际政治在气候变化领域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于是,社会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语出惊人:“在当前时期,我们还没有气候变化的政治。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一套如要我们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就必须做到的政治创新”[16]。吉登斯不幸言中,哥本哈根会议确实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吉登斯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被他称为“吉登斯悖论”的难题——“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言中,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16]。 《哥本哈根协议》第1段宣称:“我们强调,气候变化是我们世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强调,我们拥有强大的政治意志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的能力来加急应对气候变化。”当美国坚决反对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权时,当发达国家侵犯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权时,当发达国家不全面履行历史责任和“与能力有关的责任”时,国际社会如何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加急应对气候变化呢?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或者说,为了解决“吉登斯悖论”,国际社会确实需要政治创新。然而,任何政治创新都不能抛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现实政治终究不能长期远离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为了弥补现实政治和法律哲学的鸿沟,本文从中国的立场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三个参考标准。 首先,国际社会应将历史累积排放量和人均 GDP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参考标准。历史累积排放量是指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按照历史责任,一个发达国家的历史累积排放量越大,它承担的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负担就应越重。按照“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越高,它承担的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负担就应越重。这些负担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和支持能力建设。其次,国际社会应将人均累积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参考标准。人均累积排放量是指《公约》各缔约方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温室气体的人均累积排放量。国际社会在未来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额度时,必须同时考虑人均累积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不考虑人均累积排放量,就很难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律令(development imperative)。不考虑人均排放量,就很难照顾到后代人的正当需要。如果双重趋同方案可行,那么它可能是契合中国立场的最公平方案之一。最后,国际社会在哥本哈根之后必须按照平等参与原则开展国际谈判。 References) [1]President Obama’s Remarksat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2full Text[EB/OL]1[2009-12-25]1 http://page1politicshome1com/uk/article/4633/1 [2]徐以祥.气候保护和环境正义[J]1现代法学,2008,(1):187-1931[Xu Yixiang1 Climate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J]1 Modern Law Science,2008,(1):187-1931] [3]Eric A Posner,Cass R Sunstein1 Climate Change Justice[J]1 Georgetown Law Journal,2008,96:1565-16121 [4]Lavanya Rajamani.Differentia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1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50-1551 [5]Friedrich Nietzsche1 Twilightof the Idols[M]1Trans1 by RJHollingdale1 Harmondsworth,UK:Penguin,1968:1021 [6]Ruth Lapidoth1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J]1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1987,81:138-1461 [7]Lavanya Rajamani1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Balance of Commitments under the Climate Regime[J]1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000,9(2):120-13.1 [8][英]杰弗里·托马斯1政治哲学导论[M]1顾肃,刘雪梅译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11[Geoffrey Thomas1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M]1 Trans1 by Gu Su and Liu Xuemei1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6:1511] [9]Daniel A Farber1Basic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of Climate Change[J]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2007,155:1605-16421 [10]Eric A Posner,Cass R Sunstein1 Should Greenhouse Gas Permits Be Allocated on a Per Capita Basis[J]1California Law Review,2009,97:51-931 [11]何建坤,刘滨,陈文颖1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平性分析[J]1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6):12-151[He Jiankun,Liu Bin,Chen Wenying1 Analysis on The Equit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4,14(6):12-151] [12]Patricia Birnie,Alan Boyle and Catherine Redgwell,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M]1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Chapter 31 [13]Ed Miliband1 The road from Copenhagen[EB/OL]1[2009-12-25]1 http://www1guardian1co1uk/commentisfree/2009/dec/20/copenhagen2climate2change2accord1 [14]Martin Khor1 Blame Denmark,not China,for Copenhagen failure[EB/OL]1[2009-12-25]1 http://www1guardian1co1uk/commentisfree/cif2green/2009/dec/28/copenhagen2denmark2china1 [15]John Vidal and Dan Milmo1 Copenhagen:Leaked draft deal widens rift between rich and poor nations[EB/OL]1[2009-12-25]1http://www 1guardian1co1uk/environment/2009/dec/09/copenhagen2summit2 danish2text2leak1 [16][英]安东尼·吉登斯1气候变化的政治[M]1曹荣湘译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1[Anthony Giddens1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M]1 trans1 by Cao Rongxiang1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9:51] The“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Principle:An Observation on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WANG Xiao2gang The political debate on the principleof“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isprobably themost importantone at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Both“inequality for unequal”and“equality for equal”comprise the philosophical basisof the principleof the CBDR principle.The idea of“inequality for unequal”is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lating to capabilities1 The ideaof“equality for equal”is reflected in rights to per capita emissionsand rights to equally participate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BDR principle,Denmark and US,rather than China,hijacked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complywith the CBDR principle based on both ideasof“inequality for unequal”and“equality for equal”after Copenhagen.First,it should consider Historical Cumulative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GDP as essential parameters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Second,given the development imperative of development nations and legitimat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it should consider Per Capita Cumulative Emissions and Per Capita Emissions as essential parametersof climate changemitigation.Last,it should obey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rticipation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climate change;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inequality for unequal;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per capita standards X22 A 1002-2104(2010)07-0031-07 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05 2010-01-11 王小钢,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学和法哲学。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7JC820003)。 (编辑:田 红)3 哥本哈根之后
(School of Law,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