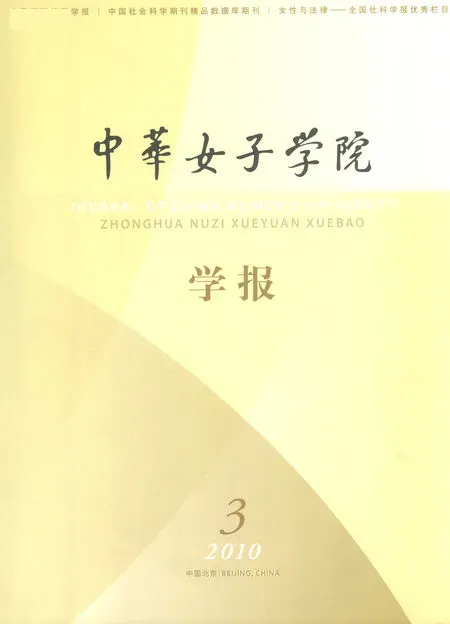论明代闺秀词人的“女性书写”及其词史意义
2010-02-17薛青涛
薛青涛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乡 453007;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 文学系,北京 100102)
论明代闺秀词人的“女性书写”及其词史意义
薛青涛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乡 453007;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 文学系,北京 100102)
明代闺秀词人书写了其在男性世界中为人女、为人妻以及为人母等不同身份的多元情感体验,表现了明前词中所不曾有的真正的女性情思与女性美感特质。同时,也从理论上提出“诗故非大丈夫事”这一新的观点来肯定女性的写作权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书写”。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明前女性词主题单一、性别色彩不够鲜明的局面,把女性词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女性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闺秀词人;女性书写;女性情思;女性词
所谓“女性书写”,主要是指女性作家表达女性真实生存体验,反映女性意识的一种写作方式。在西方女性主义者那里,“女性书写”更强调女性抛弃男性话语系统,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全新的写作,如埃莱娜·西苏的“身体书写”理论。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我们这里无意照搬西苏的理论,因为中国女性所走的道路和西方完全不同,古代女性更是如此。正如叶嘉莹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女性词人所完成的,却原来并不是破坏和颠覆,而是一种融汇,并且要在融汇中完善和完成一种女性的自我表述”。[1](P46)这种通过融汇男性话语来完成女性自我表述的方式,可以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书写”。明代闺秀词人虽然生活在男权势力非常强大的封建社会,身受各种限制,但他们依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仅在词作中表现了前代所不曾有的女性情思与女性美感特质,而且还在理论上提出“诗故非大丈夫事”这一全新的观念,体现了封建时代女性的历史性进步,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书写”。
一、“诗故非大丈夫事”:女性写作热情的高涨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的闺秀词人,除了李清照和朱淑真之外,大都是“不以舞文弄墨为能事”的,仅偶尔染指而已。明代的闺秀词人则不然,他们对诗词很是热衷,有很多人可以称得上是“以舞文弄墨为己任”了。张长文写自己“夜永衣单风露冷。诗骨癯癯,好似春来病。写得新诗还细咏。远山老树苍烟暝。”(《蝶恋花·夜坐》)夜深还在“细咏”“新诗”,大有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之意。沈宜修诸人更是“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纟壬而工子墨”。[2](P753)屠瑶瑟与沈天孙“相与征事纟由书,分题援简,纸墨横飞,朱墨狼藉。……屠长卿诗云:‘封胡与遏末,妇总爱篇章。但有图书箧,都无针线箱’”[2](P748),可见他们对诗词创作的热衷与痴迷。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作品流传后世,欲因“立言”而不朽。如会稽一无名女郎,遇人不淑,死前题诗于驿壁,其序云:“嗟乎!余笼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没无闻,故忍死须臾,候同类睡熟,窃至后亭,以泪和墨,题二诗于壁,并序出处。庶知音读之,悲余生之不辰,则余死且不朽。”[2](P761)很有司马迁那种追求“立言”不朽的意识。还有项兰贞,“临殁,书一诗与卯锡诀别,曰:‘吾与尘世,他无所恋,惟云、露小诗,得负名闺秀后足矣。’”[2](P752)临死前念念不忘的,不是子女家事,而是自己的诗稿,可见诗词在她内心的分量。
他们不仅在行动上孜孜以求,还从理论上肯定了女子的写作权力。陆卿子在为项兰贞《裁云草》作序时说:“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胜响而为诗;诗故非大丈夫事业,实我辈分内物也。”[3](P176)顾若璞在其《卧月轩稿》自序中写道:“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着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3](P208)两人不约而同在不否定妇职的前提下,肯定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实在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明代闺秀诗词创作风气之盛,我们还可以从反面得到印证,那就是当时的卫道士对他们的指责。理学家吕坤就斥责这些舞文弄墨的闺秀:“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4](P1409)可谓深恶痛绝。词人程公远《西江月》(戒女子从师)词云:“识字女人休羡,知音乖巧非奇。这般伶俐女孩儿。父母反身干系。野史经心作怪,淫词入目跷蹊。牵情惹绪意痴迷。此病最难医治。”视女子吟诗填词为“顽疾”,简直是痛心疾首。一般说来,一种社会现象,人们批评得越激烈,越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从这些非难者激烈的批评中,也可以说明当时女性诗词创作之盛。正是由于这种对诗词的沉溺与痴迷,他们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词作。据笔者统计,《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共收闺秀词人280余人、作品1970多首,远远超过了明前仅90余人、100多首的局面,可以说仅从数量而言,就已经由涓涓细流变成浩浩江河了。
二、“心声心画总是真”:女性多元情怀的书写
在唐宋词中,无论是男性词人笔下,还是闺秀自己词中,女性都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满怀愁怨的思妇。这些思妇既没有明确的身份,也没有具体的年龄,仅仅是一个“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5](P242)这种情况到明代闺秀词人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有一部分女性在模仿男性的口吻重复那古老的闺房恋曲,表现没有性别的相思,但大部分闺秀词人还是令人欣慰地写出了女性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他们“对景思亲,衔杯忆弟”(冒德娟《念奴娇·五日》),把自己各种人生情怀都写进词中。可以说“女性三部曲”中,他们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等各种角色的情感体验都形诸笔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静态仕女画的一角,而是一幅动态立体的女性人生画卷。
首先是深闺女儿的闲适与寂寞。“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的生活在以前的女性词中很少被表现,故而这些词就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轻松的阶段,因为尚未进入社会,所以没有深沉的哀愁,他们有时静静地学画:“凭湘几,匀银管,画绡屏。印出些些花样粟纹轻”;(王虞凤《相见欢·雕栏笼鸟无声》)有时尽情地嬉戏:“匀面罢,呼女伴,坐氍。又向绿窗深处赌抟捕”;(王虞凤《相见欢·新兴蛾髻如盂》)有时又略感烦闷:“小院闲无事。步花阴、嫩苔雨渍。弄明光、几迭琴弦腻。曲槛畔、情何似”;(叶小鸾《凤来朝·春日书怀近作》)有时又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如柏叶《生查子》所记录的一次“艳遇”:
停绣唤双鬟,随我园林耍。为折海棠花,行过秋千架。墙外少年郎,潜驻青骢马。欲觑又含羞,躲入花阴下。
这里的场景有点像宋词《点绛唇》(蹴罢秋千)中的那一幕,只是女主人公没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那般顽皮,而是十分害羞,想看又不敢看,“欲觑又含羞,躲入花阴下”。这种少年男女偶遇的场景,在女性这里,完全不是男性词人所拟想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或者“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温庭筠《南歌子·手里金鹦鹉》)那般一厢情愿,痴情热烈,完全是一种女性自己的立场与感受。
其次是为人妻的多重体验,有愁怨,有欢喜,也有悲伤。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男性外出为生计奔走,女性在家留守,守望是他们人生的主要内容,相思怨别在所难免。不过在女性词人笔下,他们并不是一味的被动等待,有时也有自己的“怨”言,如顾姒《鹊桥仙》:
乍拂征鞍,才归故里,忽又驱车东去。笔花生就赋离情,偏凭是、离情难吐。往岁燕山,今年甬上,羞杀镜中眉妩。天边牛女较争些,应不似、朝秦暮楚。
其词前小序云:“客冬幼舆归自京师,今春复游甬上,作此寄怀”,可知此词作于丈夫才归家不久又要远行之时。女词人对丈夫“才归故里,忽又驱车东去”常年不着家很是伤感,把自己的处境与不幸的织女相比,认为织女虽然不幸,尚且能一年和牛郎定期相会一次,而自己显然连织女都不如,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顾之琼则对男性执著的功业追求提出疑问:“春去速、蝶空忙,芳草映斜阳。又恐伊、封侯未稳,误了凝妆。”(《意难忘·寄外》)担心丈夫既不能实现理想抱负,又白白浪费夫妻相对的大好时光。可见在她心目中,“封侯”并不比“凝妆”重要多少。
正因为离多聚少,夫妻团聚的欢乐就更值得珍视。如陈玉娟写其夫功成归来之喜:“喜杀功名成就。准备玉箫双奏。拟定夜深时,相与从容话旧。非谬。非谬。月上柳梢时候。”(《如梦令》)长久的等待与期盼忽然有了满意的结果,她在欣喜之余有点不敢相信,“非谬。非谬”,两句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重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这种十分惊喜却又难以置信的心理,和晏几道“今宵剩把银杠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样精彩。此外,他们笔下还出现了夫妻夜话的场景,如张长文《小重山·与外夜话》:
秋草深深叫砌蛩。树林凋欲尽、吼悲风。吹来山寺几声钟。林间月、又入小窗中。秉烛傍熏笼。待君看史竟、话从容。古今阅历几英雄。千载后、试与断蛇龙。
在万木凋敝之时,屋外寒风怒吼,室内却暖意融融,夫妻“傍熏笼”秉烛夜话,谈古论今,和苏氏兄弟十分向往的“夜雨对床”一样温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种“惟酒食是议”的生活保姆,也不仅仅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式的风流点缀,而是可以和丈夫进行对话、交流的一个知心朋友。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女性在男性世界中所处地位的一种细微变化。
另外,还有不幸者的怨怀悲歌,如陈洁,字香石,监生孙安石之妻,后以无子归母家。其《菩萨蛮》词云:“今生浪拟来生约。从今悔却从前错。腰带细如丝。思君君不知。五更风又雨。两地侬和汝。着意待新欢。莫如侬一般。”离别之际,百感交集,内心的凄苦不言自明。又如冯玄玄,字小青,武林冯千秋妾,因见嫉正室,被迫徙居孤山别墅,抑郁而终。她在《天仙子·写怀》下片中写道:“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衣又捻裙双带。”词人这里掩去内心的悲伤,故作宽解语,语愈淡而心愈苦,比正面的呼喊更动人心弦。
再次,我们看为人母对儿女魂牵梦系的牵挂,以前的女性词从未表现过这个主题。先说对游子的牵挂,如张令仪《忆萝月·夜坐忆儿》:“寒风瑟瑟。正是愁时节。灯晕残花红泪滴。旅雁数声凄切。可怜游子天涯。短衣匹马胡沙。异国依人远去,须眉料结冰花。”词人寒夜独坐,思念远在塞外的爱子,想象他所饱受的风霜之苦,很是心疼。尤其是“须眉料结冰花”一句,写尽母亲对游子的悬想、思念、心疼、爱怜之情,现在读起来仍令人恻然。不过他们词中表现最多的还是对远嫁女儿的思念,如杨彻的《阮郎归·忆女》:
灯前梳裹带娇啼。牵衣难别离。犹闻兰麝在深闺。几回错唤伊。风日淡,暮云微。凄凉泪湿衣。梦中惊喜汝来归。觉回依旧非。
这首小词虽然只有47个字,但构思之精巧、情感之深沉、思念之殷切却极为感人,读来催人泪下。词人选取了脑海中最为深刻的几个片断展开:首先从离别时女儿的“带娇啼”落笔,挑起伤心之情,接以女儿走后,衣香犹在人不在的失落场景进一步渲染着思念之情,这是追述过去;下片回到现在,写自己因长久思念而“泪湿衣”的情景,紧接着插入因刻骨思念而产生梦中女儿归来的惊喜之情,使情感荡起,感情达到最高峰;最后又回到现实,以“觉回依旧非”的残酷现实来反衬梦中的惊喜,感情骤落,戛然而止,在万般惆怅中结束。尤其是“犹闻兰麝在深闺。几回错唤伊”这一生活错觉,写出母女之间那种长期“绕膝依依,晨昏举止相携伴”(杨彻《点绛唇·送女》)的亲密与依恋,一旦分离,竟然情不自禁照常呼唤女儿的情景,真实感人。她甚至因思念而入病:“病入人心,药石炉空沸”,幻想“千遍思量千遍泪。何时得汝欣欣至”。(《蝶恋花·忆女》)语直情深,大有周邦彦“天便叫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新绿小池塘》)的质直之美。这样魂牵梦绕的眷念,难免导致词人“镜影非前,人情异昔,怎禁心摧折。凭谁诉得,一宵满鬓华发”(王凤娴《念奴娇·寄女文妹》)的伤感与憔悴。另外还有对女儿去世之后的悼念,如沈宜修《菩萨蛮·对雪忆亡女》《踏莎行·寒食悼女》,王凤娴《忆秦娥》(月夜忆亡女引庆)二首等,更加深切感人,令人不忍卒读。
三、“曲细纤婉自风流”:女性词美特质的强化
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邓红梅概括为“纤、婉”,她说:“纤者 ,细也 ,微也。笔致之细 ,心思之微,是其大要。婉者,优美也,柔曲也。意象之轻约,抒情之曲折,是其大要。”[6](P4)可谓切中要害,概括非常准确。这种“纤而婉”的美感特质和女性独特的感悟能力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妇女在审美实践活动中,一般能对审美对象进行细微观察,能够保持稳定集中的注意力,这种静观默察,就可以收集有关审美对象的大量信息,就会把握审美对象的一些细枝末节。”[7](P101)这主要是因为女性的视觉与听觉发展一般比男性好,故而对外物的刺激更加敏感细腻。他们的词,也因此更具美感。明之前的女性词由于数量有限,这一美感特征还不明显。到了明代闺秀词人的笔下,这一“纤而婉”的女性词美感特质就十分明显了。关于这一点,读他们的词作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这里我们再举一例略加分析,如沈宜修《南乡子·晓起感怀》:
细雨寂疏栊。绣帐熏篝翠影重。娇鸟数声香梦杳,芳红。一片烟丝弄晓风。小蕊长茸茸。嫩柳轻桃染渐浓。又是春愁萦不了,忡忡。减尽容华玉镜中。
这是一首伤春词,词中所用的意象体现了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 ,如“细雨”、“娇鸟”、“烟丝”、“微风”、“小蕊”、“嫩柳”等,都非常细美、轻灵,读来给人一种如梦、如幻般的感觉。这时候还是初春,柳眼初绽,桃花微红,一切事物都还在蒙蒙细雨的笼罩中尽情享受春的暖意。可是女词人那颗敏感的心,早已感受到了青春行将逝去的伤感,心头萦绕着挥不去的春愁,在花与人的对话中品味无尽的悲感。词中既有春已来的喜悦,也有春将去的悲伤,情感委婉曲折,令人回味无穷。
另外,他们的词中还有一种男性词中极少见的纯粹的审美境界。因为封建时代的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有太多的社会道义要承担,有那么多“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需要寄托。他们偶有所会意,信笔写来,反而更具一种淡然悠远的意境,如,冒德娟《望江南》(晚步):
闲晚步,綦迹印苔深。蕉响疏风来别院,烟迷宿鸟语幽林。明月出花阴。
这首小令虽只寥寥数语,却能给人带来一种纯粹美的享受。词人在傍晚信步闲走,感受飒飒清风,倾听悠悠鸟语,沐浴皎皎月光,完全沉浸在自然怀抱之中。这里完全没有诗词中常见的“日之夕矣,牛羊下来”那种日暮时分女子异常浓烈的怀人念远之情,只有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那种“闲人”式的对美的领悟。其他如王凤娴《浣溪沙·郊行》、黄媛介《蝶恋花·西湖即事》、孙兰媛《感皇恩·鸳湖泛月》等皆属此类。这些作品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女性词的美感特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明代闺秀词人创作热情之高,远超前人。他们不仅沉迷于诗词写作,而且相当一部分人还有着十分明晰的写作意识以及流传后世的欲求。他们用词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从闺中少女的闲适与寂寞,到为人妻的欢喜与愁怨,再到为人母的牵挂与思念,“女性三部曲”中各个阶段、各种角色的情感体验都形诸笔端,抒发了真正的女性情思,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女性人生画卷。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特有的美感体验强化了女性词“纤而婉”的美感特质,改变了明前女性词主题单一、性别色彩不鲜明的局面,把女性词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女性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叶嘉莹.良家妇女之不成家数的哀歌[J].中国文化,2008,(2).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吕坤.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叶嘉莹.从女性主义文论看〈花间〉词之特质[J].社会科学战线,1992,(4).
[6]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7]任平安,赵艳屏.妇女心理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张艳玲
D442.9
A
1007-3698(2010)03-0089-04
2010-03-28
薛青涛,男,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8级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