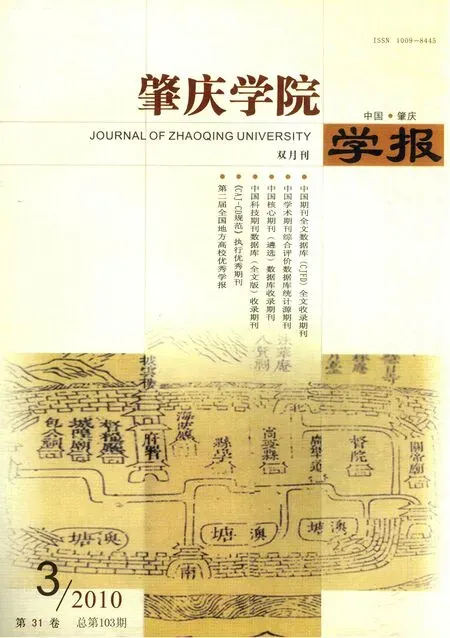“和而不同”:池田大作与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观比较
2010-02-16陈爱香
陈爱香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和而不同”:池田大作与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观比较
陈爱香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日本的池田大作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在探索人类的生态伦理问题上成了同路人。他们均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源主要在于科技异化,理性发展失衡;他们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视为实现人内部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外部自然世界和谐的有效方式。他们的生态伦理观是二人宗教情怀的折射。但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上,池田大作比较倚重人类悲悯苍生之情;而艾特玛托夫则偏重表现动物的灵性。
池田大作;艾特玛托夫;人与自然;生态伦理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极速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现代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由此,一门新兴学科——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主要探讨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支配着这些关系的伦理原则决定着我们对自然环境和栖息于其中的所有动物和植物的义务、职责和责任。”[1]有学者认为,对生态伦理来说,“重要的确实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主要方向将不是改造和征服外界、使自然界适应于人类,而是改造人类自身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生活方式、使人类适应于自然界,而与之保持和谐。”[2]池田大作先生作为日本当代著名的宗教领袖、思想家和国际人道主义者,对人类生存境况做了孜孜不倦的探求。他在与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对话录《伟大心灵的诗》中,专门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艾特玛托夫是前苏联管辖的吉尔吉斯地区一个著名作家,他创作了《白轮船》、《永别了,古利萨雷》、《一日长于百年》和《断头台》等叙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小说,并获得多枚国家荣誉勋章。池田大作与艾特玛托夫分属日本与吉尔吉斯斯坦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在探索人类的生态伦理问题上却成了同路人。本文拟对二者生态伦理观的异同加以分析比较,并探求其内在的精神文化根源。
一、科技异化与生态危机
池田大作和艾特玛托夫两个人都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症结主要在于理性发展失衡,即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价值理性日益式微。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忧虑之情。在与意大利学者奥锐里欧·贝恰的谈话中,池田大作指出了物质文明发展和人类生存状态改进的矛盾:“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从环境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并利用这种力量,在物质上实现了富饶、优裕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现代的人类,却把这种物质的力量用作可怕的武器,互相威胁,而且在现实中已经杀伤了大批的人。人们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却丧失了人生的生活意义,或者由此而走向杀伐的犯罪,成为一种绝望感的俘虏。”[3]174而导致这一状况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异化,工具理性膨胀。池田大作认为:“所谓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这种欧洲式的征服精神的一种表现;所谓发达国家,概而言之,就是对它们征服、排除自然而使其极度人工化所给予的一个称呼。”[4]227-228池田大作认识到人们应该从技术的膜拜和迷信中醒悟过来,认真思考技术的合理开发和使用,端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至今天,对于利用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来‘征服自然’的办法,我认为已被迫作大幅度的修正”[4]228。池田大作认为科学技术应该用来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毁灭性灾难的产生。
艾特玛托夫也清醒地认识到科技革命的消极影响。他在多部作品中反映了科技异化导致人性沦丧的悲剧。在《一日长与百年》中,人类运用高端科技探索到了外太空,但为了维护私利,人为地截断了地球与外太空的联系,将两位宇航员遗弃在外星世界。在《断头台》中艾特玛托夫描写了人类运用高科技疯狂奴役大自然的场景。作者匠心独运,通过狼的视角来观照人类的疯狂行为。人们开着直升飞机、手拿自动步枪在莫云库梅大草原进行围猎。飞机在母狼眼中成了“钢铁巨怪”。面对人类的大屠杀,母狼阿克巴拉觉得十分可怕。“在这如同世界末日来临的沉寂中,母狼阿克巴拉看到一张人脸。那么近,那么可怕,又那么清楚,以致母狼大吃一惊,险些落到车轮底下”[5]34。狼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凶狠的,让人畏惧的。在小说中,艾特玛托夫突破常规,写狼眼中可怕的人的形象。“野兽看见了野兽”[6],艾特玛托夫在一次与《文学报》记者关于《断头台》的谈话中这样说道。通过狼的视角观照人丧失理性的疯狂与可怕,更具批判意味。在人类堂而皇之的“开发资源”的活动中,母狼失子,伤心的狼叼走人子(波士顿之子),波士顿开枪杀死母狼的同时误杀自己的儿子。这预示着人类毁灭大自然的同时,也就毁灭了自身。作者以第三人称母狼为叙述视角,用它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实际上就是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裁剪”和“评判”世界。他认为现代世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野兽而是掌握现代科技工具丧失人性的人。
池田大作与艾特玛托夫目睹当今人与自然日趋恶劣的关系破坏了宇宙的和谐,威胁着人类的安宁生存。本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描绘出一幅幅生态战争与人类战争的惨剧。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惨剧的勾画,促使人们认识到地球的有限性和人类建立理想家园的紧迫性。除此以外,他们理性地分析这一切悲剧发生的根源,并努力探寻人类摆脱这一生存困境的有效方式——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二、道德的自我完善与生态和谐
池田大作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不平衡乃是一种人类心灵不平衡的表现。他指出:“不论是环境中的不平衡或社会中的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是人自身,其根源显然是在于我们人类内在自我的不平衡。”[3]177人以自然的统治者自居,这是人的贪欲的表现。人的贪欲无限膨胀,造成了全球生态困境。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不应该把科学技术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手段,而应另辟蹊径,即他所倡导的“人的革命”。“我们相信,在人们的内部实现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革,是紧急而必要的;所以我们一向呼吁,只有进行人的革命而别无其他的办法。”[3]186在池田大作看来,人类只有进行真正的“人性革命”,才能确立与自然调和的和睦态度,“才能面对自然的破坏——可以说是现代文明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筑起一道根本的防线。”[3]153人性革命的完成是从“一个人的内心革命”开始的。不能靠社会外部力量完成‘一个人的内心革命’,只能靠人的主体性,内发性,也就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规则性’和‘内发性’两者并存才能成为优秀的人格。”[7]池田大作主张通过人性革命,克服人的魔性欲望,实现人自身内部精神的和谐。
艾特玛托夫则以一部部震撼心灵的作品,直戳人类破损的精神世界。在《白轮船》、《断头台》等小说中,他探索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即人不断地进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艾特玛托夫希望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内在的道德需求。《白轮船》中无名小孩的悲剧,表明人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急迫性。小孩生活在大森林中,特别喜欢听爷爷讲长颈鹿妈妈的故事。在他眼中,长颈鹿是人的保护神。但是他的姨夫为了口腹之欲残忍地杀掉了长颈鹿。小孩失望之余,投水自杀了。小说通过孩童世界的纯洁凸显成人世界的污浊。在《断头台》中,他塑造了一位“劝恶向善”的殉道者阿夫季。阿夫季看到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人的道德的沦丧,信仰的丧失,……他不愿对社会的丑恶视而不见,而把宣传善行看作自己的使命。他认为“每个人都面临着一场革命,哪怕是在自己心灵的范围内”[5]92。面对罪犯,他“不想用说教的方式,不想用指责和审判的方式,而是想通过个人的参与、亲身的经历向他们证明,摆脱这种危险处境的唯一出路,只能通过本人的觉醒。”[5]92阿夫季通过自己的传道、受难,不被人理解,遭人唾骂,上十字架的苦难历程去拯救邪恶。阿夫季自觉担负起拯救人类、构建和谐宇宙之重任,他把自己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忧虑,对世界前途的不懈思考,对美好未来的永恒期待,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精神探索中。阿夫季这个形象很好的诠释了艾特玛托夫通过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达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想望。
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大自然,导致人与自然的严重疏离。池田大作和艾特玛托夫二人都认识到这一现状,他们也认识到这同时也是人处于精神危机状态的折射。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人自身。人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是对自身生命的戕害。人性沦丧导致人类精神家园失守与文化精神生态的失调。他们试图通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最终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内部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和谐。
三、悲悯苍生与视人如己
池田大作和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观是二人宗教情怀的折射。池田大作是日莲宗的领袖和虔诚信徒,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思维脉络建立在佛学理念(特别是《法华经》思想基础)之上。池田依据佛法原理,认为“我既宇宙”、“宇宙即我”,合理地阐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出了“自然与人都是有机关联的‘有生命的存在’,‘人领有自然,自然也领有人’”的结论[8]。“佛教的所谓‘佛’,就是指生命内在的尊严,因此可以说,所谓佛法就是生命的内在法则,在包含生物和非生物的自然界中,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生命之线’,这些线巧妙地调和了整个宇宙,织出了精巧的‘生命之布’。必须把生命的尊严的思想作为我们人类生存的旗帜,高高地举起,这就是保持自然协调的必不可少的条件”[9]111。正因为自然生物和人类一样都是“生命的存在”,所以人和其他生物平等相处,和谐共生。池田大作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上他宏扬了佛教的悲悯情怀,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生命的作用变为美好的东西,去怜悯一切其他生命,不做损害他人的丑事,才能使人的生命在事实上成为尊严”[10]。可见,池田大作生态伦理观的重心落在人的身上,“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命而宰杀、食用其他生灵,虽因多走其他生灵的性命而造下罪孽,但维持自己生命的努力却是善,如果能把这样维持下来的生命,用于使其他更多的人获得幸福,则被视为更大的善。因此,即使允许宰杀生灵,也完全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通过维持下来的自己的生命,做有价值的事情,那么罪孽将得到饶恕。”[9]84可以看出,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上,池田大作比较倚重人类悲悯苍生之情。
艾特玛托夫是个宗教情结颇深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或许不相信具体的安拉和耶稣,但他深受吉尔吉斯文化和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影响,他的多部作品都浸润着浓浓的宗教思想。在《断头台》中,他甚至选择了宗教人士阿夫季作为主人公。面对前苏联评论界的争论,艾特玛托夫曾向记者解释过他选择阿夫季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原因:“阿夫季是俄罗斯人,但我把他看得更广泛些,看作一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我试图通过宗教来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5]409艾特玛托夫试图解构传统宗教中的上帝,依托上帝之名,将外在的道德约束内化为人的内在需求。与池田大作从人的悲悯情怀出发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的是,艾特玛托夫立足于动物,他写了动物对人的怜悯之情,甚至将动物塑造成人类的祖先与保护者。在《白轮船》中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涉及了吉尔吉斯人中的布吉族的起源。长角鹿妈妈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该族最后两个孩子,从而使布吉族能够繁衍下去。在小说《断头台》末尾处,阿克巴拉与鲍斯顿的儿子肯杰什遭遇,“它走到孩子身边,添了添他的小脸蛋……母狼对他倾注了全部温情,不断吸着那孩子的气息。它觉得,如果人的小崽能住在它那岩石下的窝里,那该多么舒心啊”[5]397-398。动物对人的怜爱之情跃然纸上。身为吉尔吉斯人的艾特玛托夫深受本民族图腾文化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柯尔克孜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把鹿、骆驼、蛇、鹰和熊等作为图腾崇拜,因而十分重视与某些动物的精神血脉关系。艾特玛托夫从小生活在吉尔吉斯的群山与草原之间,吉尔吉斯文化完全溶化于其血液之中,这些影响折射到他的生态伦理观上,表现为他擅长描写动物所具人类之灵性。
总之,池田大作和艾特玛托夫虽深受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精神上却有着共通之处,即推崇众生平等、万物有爱的精神。他们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生态的保护与人类心灵家园的守护问题联为一体。他们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是自然生态悲剧的根本原因。池田大作和艾特玛托夫认为,人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必须走道德的自我完善之路。他们本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着力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力图唤起人们重建精神家园的意识。
[1]TAYLOR P W.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3.
[2]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4.
[3]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4]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选集[M].卞立强,编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5]艾特玛托夫.断头台[M].冯加,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6]严永兴.艾特玛托夫谈《断头台》的创作[J].外国文学动态,1987(3):25.
[7]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M].创价学会,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72.
[8]池田大作.人生箴言[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197.
[9]池田大作,狄尔鲍拉夫.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431.
Sharing but Different——comparing the eco-moral views of Daisaku Ikeda with Aytmatov’s
CHEN Aix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Daisaku Ikeda of Japan and Aytmatov of Kyrgzstan become companions on the way of exploring the eco-moral problems of human being.Both Daisaku Ikeda and Aytmatov have found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result of technology alienation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enses.They take the self-improvement of human moral a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spiritual harmony within human world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the external natural world.The eco-moral views of Daisaku Ikeda and Aytmatov is a reflection of their religious pursuits.Between man and nature,Daisaku Ikeda puts more emphasis on human emotions and sympathies for other lives in nature,while Aytmatov on the spiritualities of animals.
Daisaku Ikeda;Aytmatov;man and nature;eco-moralities
I106.4
A
1009-8445(2010)03-0021-04
(责任编辑:杨杰)
2009-12-20
陈爱香(1977-),女,湖南益阳人,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