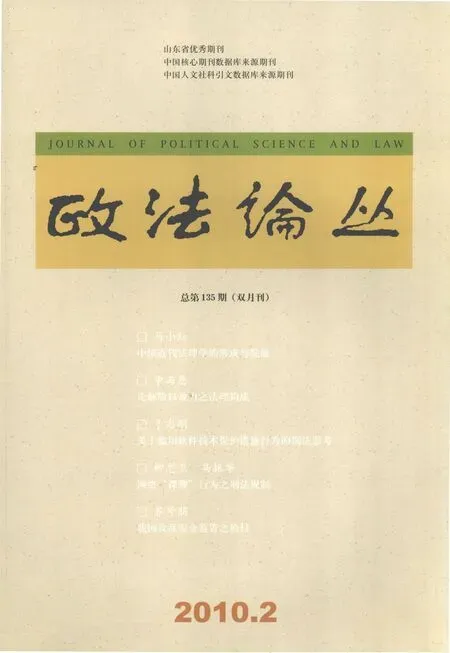论解除权效力之法理构成*
2010-02-15申海恩
申海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北京 100024)
论解除权效力之法理构成*
申海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北京 100024)
解除权效力的法理构成,历来为理论上的重大争论。作为对违约救济路径的救济手段,解除权的行使使得遵守合同一方当事人得以从原合同关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作为违约救济体系的重要元素,解除权担负着协调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使命。基于此,使得解除权发挥变更原合同关系为返还性债务关系是十分合理的,同时足以彰显其作为形成权之一种的基本权利属性。
解除权 效力 形成权 违约救济
私法以“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其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1]P245为其鲜明旗帜,此之谓私法自治原则。当私法自治原则所针对的主体为两个以上的人时,则“其法律关系内容的形成自应由其当事人以一致之意思表示共同决定 ”,学者称之为“契约原则”。[2]P76-77然而,意思表示之合致,何其困难,在发生契约义务违反的情事时,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情形更是凤毛麟角。个中缘由大致在于,当事人之意思表示所以能够一致,必以各方利益取向完全契合时方为可能;而一方有违反契约义务情事时,多意味着各方利益取向之完美契合已经破裂,于此种场合,要求当事人达成协议,实属困难。但是法律终须为当事人提供违约时的救济路径,此即引发了解除权的产生。
一、解除权效力的论争
从德国民法典以来,解除权作为违约的救济途径得以普遍存在,但是解除权的效力究竟如何,始终聚讼纷纭。学说上主要形成了直接效力说、间接效力说、折中说、债务关系转换说以及清算关系说。
(一)直接效果说
该说认为,合同的效力因解除而溯及既往地消灭,尚未履行的债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发生返还请求权。至于返还请求权的性质究竟为物上请求权抑或基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则各有不同的主张。该理论最大的弊端在于,合同既因解除权的行使而自始消灭,则发生类似于合同绝对无效之法律后果,债务人违反合同所致损害之赔偿请求权即成无源之水,从而导致解除权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冲突。作为违约后果的损害赔偿责任之承担应以有效之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为其前提,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在丧失其基础,从而导致行使解除权的同时不能请求损害赔偿,德国债法修订前即处于这种尴尬局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在理论实务奉行直接效果说的情况下,对其直接效力说加以改造,这说明我国学者早在民法典制定之初,即意识到德国直接效力说所存在的问题。从理论逻辑而言,契约自始消灭则无请求权基础,是完全自洽的。台湾地区立法、理论与实务于奉行直接效果说的同时,主张“解除权的行使,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其前后之矛盾也已为台湾学者所诟病。[3]
黄茂荣先生曾经考察了解除契约与损害赔偿的关系[4]P75-84,并认为,“第 260条与第 226条、第 232条间之适用关系,应该是选择的,债权人可以依其选择,或者解除契约请求信赖利益之赔偿,或者不解除契约,请求履行利益之赔偿。”[4]P80从而,“主张解除权人依第 260条得请求履行利益之赔偿并无意义。”据此分析,黄茂荣先生并不否认台湾地区关于“契约虽解除,其原依据契约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失其存在”的基本主张,而是主张“坚持请求履行利益者,不得解除契约”。[5]P285
直接效果说中,依是否承认物权行为,而又区分出“债权的效力说”与“物权的效力说”,前者坚持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原则,认为契约解除仅生债权的效力,不能发生物权的效力,故只能发生原状恢复请求权,而不能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6]P335后者则主张合同的解除必然导致物权效果之消灭,已经履行的部分,履行人享有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在前者,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必然导致物权效果与债权效果之区分,合同的解除仅发生干涉债权债务关系之形成权的效果,在其理论体系中,尚能成立。但是此种理论下,必然导致已经履行之债务应按照不当得利返还现存利益,对于合同关系当事人之保护未免不尽周全。合同解除当事人最根本的目的即在于,尽可能完全消除因对方违约而对其所生之不利影响,而如若仅返还现存利益,则无疑限制了合同解除权利人利益状态的恢复。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才有 259条之特别规定,使返还的范围不以现存利益为限,而以恢复原状为原则,构成规则上的例外。此种法制之下,对于债权人之救济固然得以周全,然而于学理上之解释却颇费周章。在后者也有问题,解除权的行使是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不仅仅需要意思表示,而且需要相当的公示形式。据此,解除权的行使不仅需要其意思表示到达对方,而且需要具备相应的形式要件,方能发生物权的变动。因此,在未为交付或变更登记之前,解除权人尚不享有已交付标的物的所有权,何来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而言呢。另外,所有使解除权具有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都无法就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同时)享有提供合乎逻辑的解答。
(二)间接效果说
该说认为,合同并不因解除而归于消灭,解除只发生阻却合同效力的功能。结果是,对于已经履行的债务发生新的返还义务,对于未履行的债务发生拒绝履行的抗辩权。根据该说,合同解除场合发生的恢复原状义务,并非基于合同溯及既往的消灭,而是基于解除的本质,特别是有偿双务合同上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价交换的均衡,合同上的债权关系并非因解除而消灭,而是变形为恢复原状的债权关系 (山中康雄、三宅正男主张)。恢复原状请求权被视为一种居于物权的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中间的、混合的特殊权利(铃木禄弥主张)。
关于“解除权的行使,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效力的消灭”的主张,避免了直接效果说面对损害赔偿问题时的尴尬,实为其优势。然而该说关于“解除权的行使,仅发生对合同效力的阻却”的主张,导致解释方向的迷失。对合同效力的阻却,仅仅在于使解除权行使之时起,不再向后发生约束当事人之效力,然而却根本无法解释何以应当对已经履行之债务发生返还请求权的结论。盖此前的合同效力既未消灭,其给付自有法律上的原因,使其发生返还请求权,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此其一。
其二,就解除权行使之目的论,权利人在于追求一劳永逸地从债权债务关系中解放出来,而非仅仅获得一种抗辩权。同时由于此种抗辩权并不能导致对方请求权的消灭,当事人双方仍然处于债权债务关系之中,这必然为新的交易关系埋下隐患。
再次,解除权为一种形成权,其特色之一在于使“法律关系发生、内容变更和消灭”。[1]P97间接效果说的主张,实质是对当事人赋予一种拒绝履行的抗辩权,事实上将解除权的效力限制在抗辩权的范围内,导致权利类型体系上的混乱,为其又一弊端。
(三)折中说
该说主张,解除权仅使合同效力向将来发生消灭,未履行的债务当然消灭,已经履行之债务,发生新的返还请求权。此种主张为当前众多学者所主张,[7]P618惟笔者认为,此种主张仍有改进的余地。
首先,合同效力向将来消灭,当然可以成为未履行债务消灭之原因。但是,却无法为已经履行之债务发生新的返还请求权提供合理的法理依据。
其次,对于损害赔偿而言,解除权使合同效力向将来发生消灭的规则,将导致因未履行债务对于债权人所造成之损害无法请求赔偿或仅能请求信赖利益之赔偿。原因即在于,合同自解除权行使时已经向将来发生消灭,履行利益之赔偿请求权不存在法律基础。
(四)债务关系转换说
该说认为,解除使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变形,转换为原状恢复债权债务关系。原债权债务关系中已经履行的给付,转化为恢复原状债权债务关系之未履行债务部分;未履行部分作为恢复原状债权债务关系中已经履行的部分。
至于债务关系转换说之优势在于,将原债权债务关系转换为恢复原状债权债务关系,一方面避免了使合同效力消灭时不当得利规则的适用,另一方面使得合同得以继续存续,则损害赔偿之基础仍然存在,要求履行利益之赔偿,于法理仍有根据。与此优势并存之弊端则在于:“将未履行的债务转换成所谓既履行的债务,纯属人工拟制,工于机巧”。[7]P618
(五)清算说
该说认为,合同解除的效果并非根据法律而是根据解除之单方法律行为而生;解除权之效力,于双方的给付已经履行时,则建立起返还义务,解除权并不使合同效力消灭,而是使债之内容变更为“清算关系”(Abwicklungsverhltnis)。该说现为德国通说。[8]P530此种主张优越于此前各种主张,主要在于不消灭债之关系,因违反合同义务所发生的各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均得以成立,此点与前述债务关系转换说相同。
面对诸种关于解除权效力法理构成之学说争论,笔者浅见以为,非借助解除权之发生动因、解除权之制度目的及先进法制之设计的考察,则无以做出客观、中立的评价,对于解除权制度亦无从深入把握。那么究竟解除权如何得以发生?其制度目的究竟是什么?解除权效力之应然的法理构成究竟如何?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必要从整个合同的救济体系中寻找基本的线索。
二、违约救济的救济:解除权发生之动因
(一)历史的考察
在罗马法上,对于违约的救济主要是通过损害赔偿来实现的。以迟延为例,其法律效果在于债务持续和损害赔偿。债务持续之意义主要在于“使迟延债务人承担迟延期间标的物意外灭失的风险”,[9]P222契约应当严守乃是罗马法上的一条“铁律”(an iron rule of Roman law),即使当事人之间以新的合同解除先前的合同,也并非理所当然成立的事情。例如罗马法上的协议解除,或者称之为相反合意 (contrarius consensus),即要求必须是“在债的履行之前”或“尚未给付”(re adhuc integra)前由当事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取消已经缔结的债的关系。[10]P272此外,即使有罗马法学家主张可以在部分履行之后协议解除,但这也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例外情形。当然,如果双务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方当事人即可以拒绝对待给付。[11]P801就此而言,虽然罗马法上的“铁律”并非如其所被宣称的那样“铁”,但是契约应当严守原则的主体地位并未受到大的影响,针对违约的一般意义上的解除权从未为罗马法所承认。[11]P802但是,从违约的救济方式角度考察,在罗马法上损害赔偿仍然占据着最为主要的地位。
中世纪时,某些合同,特别是买卖合同的债权人被授权拒绝迟延履行、请求损害赔偿并解除合同,这一权利为法国民法典所继受、推广。[12]P526-527中世纪德国南部,就已经有由当事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享有解除权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contract)。[12]P524买受人的债务不履行情形下,许多城邦法 (town law)也明确授予 (expressly granted)买主以解除权。[12]P525但是这些解除合同的权利主要都是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合同规范之中的,一般的、概括性的解除权在此时仍然没有被承认。这与罗马法中的情况相同,基本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法国法上对合同解除的规范主要表现为民法典1184条第一款的规定:“双务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时,应视为有解除条件的约定”。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被视为法律有关合同解除权的一般规定”。[13]P346但是,这一规定被称之为“默示的解除条件”更为合适,虽然都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但是二者绝不是同一范畴。解除条件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根源于当事人自身对于其法律行为所做的限制,在合同中的解除条件,则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对合同效力所做的客观限制,客观条件的成立,直接导致合同的解除;而在解除权,即使是在约定解除权场合,除有解除原因之外,尚必须有解除权人解除合同之意思表示,方能实现合同解除的目的。[7]P592法国法对于合同的解除,虽然较之于罗马法有所进步,但仍然局限于通过拟制解除条件实现其规范目的。
虽然日尔曼法“认可由于交易只完成一半而产生的返还义务:向他人转移了财产所有权的一方有权获取其交付的买价或者其他等价物”,这一制度非常类似于解除制度,但是伯尔曼并不认为这就是现代意义“契约”所言的契约救济。[14]直到 19世纪,在严格限定的狭窄范围内的单方解除权才得到承认,根本性的突破乃是由那些德国民法典之父完成的。[11]P802德国民法典原 325、326条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定解除权,在 346~356条规定了约定解除权及其规则。
无论是在罗马法上、还是在罗马法复兴之后法制上,契约应当严守原则都未成为僵死的信条;但是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其仍然是契约法的指导思想。这就导致了首先是对合同解除的限制,其次是在契约解除时仍然以合意解除、解除条件、拟制解除条件等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解说路径。
藉此可以发现,合同的解除大致经历了这样一条演进的路径:从罗马法以契约应当严守为由的不承认解除的原则和一定范围的例外,到法国法在此基础上对默示的解除条件的承认,再到德国民法将解除视为独立的法律范畴,承认单方意思表示即生效力的解除权。[6]P326的。正是基于契约应当严守,对于违反契约之行为的制裁才具有合理的基础,但同时也正是这一原则根本地导致了合同固有救济路径的困境。
伴随着违约而产生了各种违约责任,违约方受到来自法律或约定的第二次义务的约束,但其已经从契约逃逸,不再受到固有契约关系的约束了。手持承担违约责任的罚单,违约方可以自由出入于契约关系,但是对于守约方来讲,无论何种制裁,都是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其基本前提,从而在通过种种途径对守约方予以救济时,守约方仍然必须严守契约,否则将同样承受法律否定性评价。虽然守约方可以获得各种抗辩权,以抵御违约方的履行请求,但是这些抗辩权都仅使其契约义务处于停止状态,一旦抗辩权所有发生的情事消灭,守约方之契约义务则苏醒过来。也就是说,即使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使守约方获得抗辩权,守约方依旧处于契约关系的约束之中,而违约方则在实质意义上,以违约责任的承担为代价,脱离了契约关系的束缚,进入新的交易环境。在此种情形下,违约方当事人占据绝对的主动,固有救济路径只能被动地予以救济,并无积极解放守约方的任何有效途径。如此尴尬的制度实效,与契约严守原则所倡导的交易精神全然相反,当为固有救济路径的基本制度困境。
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固有的救济路径所能提供给债权人的仅仅是一种未来的、不稳定的填补,而债权人为了获取此种微弱救济,则必须以可能丧失现实交易利益为其代价。固有的违约救济路径从契约应当严守原则而来,以有效契约为前提,在对债权人提供救济的同时,要求债权人严守契约,而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此即使守约方面临如下困境:接受固有救济,即受契约约束,不得违背契约,不得利用新的交易机会,但固有的救济并非绝对可靠;利用新的交易机会,则必然违背契约应当严守的原则,导致违约,从而无法获得固有的救济,且要承担违约责任。此外,固有救济路径为守约方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债权请求权,其得否实现尚系于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状况,从实际效果来看,对于守约方的保护并不周到。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守约方当事人面临的困境,更是违约救济的困境。
基于此种利益衡量,固有的救济路径最终必然使
(二)理论的反思
对于契约的违反的处理,无论是采取“原因进路”抑或采取“救济进路”,都必然面临着如何设计契约违反的救济路径的问题。我国合同法总体上采取“救济进路”,①这也是各国合同救济进路的基本框架。解除合同作为救济途径,特别是解除权的发生,更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晚近德国民法典诞生时,才得以全面确立。虽然从罗马法到教会法再到近代法,契约的基础并不相同,各种固有救济途径也并非同时出现,但是各种固有救济途径都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契约应当严守 (pacta sunt servanda)。
在这一原则下,合同双方不遵守合同的约定,即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此种责任是以契约有效存续和违约行为的发生为条件的,是以契约应当严守为基础理性的、本欲遵守合同的债权人放弃契约应当严守的理想,自力寻求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新的路径。从契约严守出发的制度设计,最终导致了鼓励违约的实效,可见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制度困境之中。伴随着交易的日渐频繁,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困境日趋彰显,对违约固有救济路径的救济,则成为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了。而解除权的产生和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则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
三、解除权效力之再构成
就解除权而言,赋予其何种效力,必将影响其规范目的之实现,亦即确定解除权具体应当具备何种效力,必从其权利赋予之目的考察。解除权究应具备何种效力,并非一个先验的问题,而必须是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实践问题。什么样的效力,有利于合同解除目的之实现,则在解除权可能负载之范围内,就应当赋予其什么样的效力。此外,解除权与其他救济途径的协调、与其发生效力前后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影响解除权效力构成的因素。基于此,以下首先结合前文关于解除权产生之动因的研究,从目的论的角度,考察解除权就应具备何种法律效力。
(一)制度目的考察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考察,解除权制度的发生机理在于对固有救济路径的救济;从最终的制度目的来考察,对于固有救济路径的救济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但是,解除与固有救济路径毕竟不同,从整个制度体系来考察,解除承担着救济固有救济路径的重任,这必然使解除在救济当事人的功能方面表现出与固有救济路径所不同的特点。事实上,对于债权人的实体救济主要还是通过各种固有的救济路径来实现的,而解除权仅仅是使守约方摆脱合同约束的手段而已,以使其不至于陷入因遵守合同反而遭受不利的尴尬境地。基于此种制度创设的取向,恐怕不宜赋予解除权过多的效力,只要能够使解除权人得以摆脱原合同的不必要的约束即可实现解除权的目的,除此之为的对于当事人的救济,当非解除权制度之本分了。就此而言,经常与解除权联系在一起的恢复原状,无论是否将之归入民事责任的范畴,②都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救济路径,而绝非解除权的效力内容。
就使解除权人得以摆脱原合同的不必要的约束的目的而言,解除的效力自然以消灭合同效力最为直接,也最符合解除权之文意了,这恐怕也是众多直接效力说支持者的逻辑吧!然而,此种逻辑明显过于简单,个中弊端前文也已经多次述及,此处不赘。毕竟合同的解除作为整个救济体系的一环,必须与违约救济体系形成体系上的合力,否则必然造成违约救济体系的不和谐,直接效力说的弊端恐怕也就正在于此吧。
总体而言,违约救济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当事人恢复到如同未有违约一样的状态,此种制度目的之实现必须借助于恢复原状及损害赔偿来实现。原因在于,欲使当事人之利益状态恢复至未有违约时的状态,最理想的就是使双方按照合同的内容适当履行其义务(此即为强制履行),但理想模式的实现受到种种条件限制,并非违约救济路径的典型。除此之外,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使双方当事人互相返还已经履行之给付,若能全部恰当返还,则当事人之利益状态必然能够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此即为恢复原状),此后,只需补足合同履行可获得的增益 (此即为支付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即可实现违约救济的目的。就此而言,违约救济体系不过就是的恢复和扩大的恢复构建起来的有机体系。所谓固有的恢复是指实际的对已经履行部分的恢复,而对于因不能履行或不履行部分的赔偿即为扩大的恢复,固有的恢复与扩大的恢复共同协力,即可实现违约救济的目的。而所谓固有的恢复主要是通过恢复原状来实现的,扩大的恢复主要是通过损害赔偿来实现的,故此违约救济目的之实现,端赖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之共同协力。而解除权作为违约救济之一部分,必须与恢复原状、损害赔偿形成协调的关系,否则不利于解除权人得到全面的合同救济,从而解除权制度自身目的的实现也就失去既有的意义了。
(二)解除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之协调
然而,当前在解除权、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之间却存在着理论上的冲突,难以协调。例如在中华民国时期及后继之台湾地区民法上,学说与实务通统认为:“契约经解除者,溯及订约时失其效力,与自始未订契约同”;③史尚宽先生更谓:“既已有履行时,因解除而欠缺法律上之原因,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得请求其返还。”[15]P555可见,由于返还请求权之成立仰赖不当得利法理之运用,故首先必须是以合同效力之溯及消灭为其前提的。此为一典型案例。实际上,合同解除所必须借助之返还请求权之发生,排除约定者外,只能为法定之返还请求权。此种法定之返还请求权,在民法上主要来源有二:其一为作为物上请求权之一种的返还请求权,其二为不当得利之效果。如欲以物上请求权为返还请求权之基础,则必须以解除权人享有物权为前提,而对于已经履行之给付而言,物权必定已经移转于受领人,解除权人无从行使物上请求权。如以不当得利为返还请求权之立论基础,则必须符合不当得利之基本要求,即“没有法律上之原因”。但是解除权相对人取得解除权人之给付,乃是基于有效之合同,为有法律上原因之取得,欲达请求返还之目的,则必须使该合同自始失去效力。而且事实上,根据立法例的考察,除了构造“准合同”、“默示解除条件”外,援用最多的也就是不当得利法理了。然而这样的理论构造,必然引起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困难。
债务不履行而引发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过是原债权的转变或者扩张。如果原债权因合同解除而丧失其效力,则以该合同为基础由原债权转化而来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实无继续存在之基础。[4]P77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存在,必须以合同之有效存在为其前提。如此,则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二者因其存在之前提截然冲突,难以共存。债法改革前的德国民法典,即为严格贯彻这一法理,而使债权人必须在解除合同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选择其一,由此导致所谓解除陷阱 (Rücktrittsfalle)[16]P131的发生。至于学者所主张的“已经发生的以赔偿迟延损害或不良给付的附带损害为内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得以保持”,[17]P399除了由于附带损害赔偿请求权乃是由于其与合同效力无关之外,迟延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只能说是在事实面前对于理论的迂回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在解除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之间形成和谐法理结构,此即为具有形成权属性的解除权发挥其优势之所在。
“得为契约解除之权利,谓之解除权”。[15]P537其实,解除权之根本特征尚在于,只需解除权人一方之意思表示,即可引起合同关系效力状态之变动。因此,解除权之为一种典型的形成权为德、日及台湾地区民法所普遍承认。[1]P98
然而,形成权按照其内容,可以划分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内容变更、消灭三类,[1]P97-98芮沐先生更分别称之为:产生法律关系之形成权、变更法律关系之形成权与消灭法律关系之形成权。[18]P10-11我国台湾地区理论几乎一致认为,解除权为消灭法律关系之形成权,此固然是以台湾地区现行民法为实在法依据而提出的解释论观点。然而,从立法论角度考察,究竟解除权应具有何种效力,为形成权之何种类型,将对合同解除制度目的能否实现发生多大影响,实有必要予以深入探讨。
前文所作之考察使得试图通过解除权消灭合同效力的主张之不合理性暴露无疑。笔者认为,可以借助解除权“赋予权利主体以单方面干预他人之法律关系的法律权力”[19]P79的特性及其“发生、变更、消灭法律关系”的形成权效力,来实现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共同构筑和谐的合同解除法理构成。
由于解除权因素的介入,返还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再限于不当得利一种途径,也就不必须使既有债权债务关系溯及既往地失其效力,从而引发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对立。从其形成权属性出发,解除权的效力可能涵盖的范围乃是对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由于消灭原合同关系的设想并不成功,因此,赋予解除权变更原合同关系为返还性债务关系 (Rückgew hrschuldverh ltnis)之效力,从而既维护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得以行使之前提,同时使得返还请求权得以有效成立。从诸多方面来考察,赋予解除权以变更法律关系——使原债权债务关系变更为返还性债务关系——的效力,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从解除权所属之权利系统考察,其上位概念为形成权,是使法律关系发生、内容变更、消灭的法律权利。赋予解除权以变更法律关系内容之效力,并未逾越其作为形成权之基本属性范畴。
从权利所服务之目的考察,解除权服务于当事人利益状态之恢复的目的,而非仅仅消灭当事人当前之利益关系。赋予解除权变更原债权债务关系为法定的返还性债务关系的效力,直接实现了当事人利益状态的积极恢复,同时也避免了在整个系统上与作为利益状态消极恢复之手段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冲突。传统的直接效力说也是以此目的为解除权之服务宗旨的,不过在解除权之外,尚求助于不当得利制度进而达到恢复当事人利益状态之最终目的。其实质上是对解除权之根本属性欠缺深入的了解,抑或仅仅是局限于解除表面的、终局的、静态的追求,而弱化了解除权之效能,忽视了解除权作为当事人利益状态恢复之原动力的角色,而错误地使不当得利制度充当这一角色,这一角色定位实质上也超出了不当得利制度效力所及的范围,从而导致了理论与实际上一系列的不妥。
就解除权人的主观意图考察,其所追求者当不限于消灭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在于消除此债权债务关系所带来之影响,至于此债权债务关系在消除影响过程中以何种样态存在,则非其关注之点。就此以观,赋予债权人以解除权,必以达到债权人此种目的为宗旨,否则权利配置之目的无从实现,解除制度的目的势必也要落空。“他所真正需要的,是重新获得对其财产自由处分的权利,并能够从其他方面满足自己的需求。”[20]P118
此外,从其形成权属性出发,解除权的效力范围可能涵盖的范围乃是对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从文字解释“解除权”,其效力自然应当是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似乎也与权利所追求之目的相吻合。事实上,这是对解除权 (Rücktrittsrecht)这一最终形成于德国民法的权利类型的误解!从解除之德文文字构成来考察,Rücktritt乃是来源于动词zurücktreten,后者乃是由由动词 treten与前缀 zurück复合而成,其词义亦正是建立在这两个词之上。treten具有“踢、踩、踏”之义,更有“举步、迈步走向”之义,而 zurück则有“回去、回转、返回、回到原处”之义;由此复合而成之 zurücktreten即具有“向后退,退后”之义。此外,作为从德国民法发展起来的解除权(Rücktrittrecht)并不等同于 termination,前者更应该是在 termination之前寻求依合同而为之给付返还的过程。[21]P79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对解除权的法效构成予以重塑:解除权的行使,其效力即在于将原合同关系转变为返还性债务关系。返还性债务关系的目的即在于通过相互返还,清算当事人之间基于原合同关系所为的给付和所收取利益。
四、结语
根据本文的考察,严格从解除权的违约救济体系元素性质出发,从违约救济体系的和谐一致出发,将解除权的效力范围确定为变更原有合同关系为返还性债务关系,是对解除权形成权性质的重新确立。直接效力说对解除权为消灭原合同关系的效力定位并未超越其形成权属性范围,但事实上是对于解除权的形成权属性的违反。原因在于,依直接效力说的主张,解除权一经行使,即消灭原有合同关系。但是考察直接效力说的主张,此处并非终局地使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而使其负有返还的义务。考察合同关系的消灭制度可知,其无非是为合同权利义务的不复存在,双方当事人不因合同关系而存在任何联系。而直接效力说一方面使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另一方面使其直接发生尚未履行的部分免于履行,已经发生的部分发生返还请求权的效力,从而在解除权的形成效力上出现了严重的自相矛盾。
在此,笔者赞同清算关系说,使解除权发生变更原合同关系为返还性债务关系的效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解除权作为违约救济体系的元素的体系功能要求,另一方面如此的效力构成有利于彰显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属性。以变更法律关系为其效力,不仅使解除权充分协调了违约救济体系内部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冲突,同时也使得解除权作为原有合同关系和返还性债务关系的媒介,彰显了其作用于法律关系层面的特性。
注释:
① 韩世远先生将这五种救济途径统一称之为“违约责任”(参见: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 680页;崔建远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 232页),笔者认为将解除合同定性为违约责任的观点值得商榷。就其性质而言,合意解除乃是双方法律行为,其民事责任的性质无从谈起;单方解除时,主要是具有形成权性质的解除权的行使,是对于非违约方的赋权,本来的目的主要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韩世远书,595页),而不在于课于违约方以作为民事责任的第二次义务。另外,与违约责任相对应的均为非违约方当事人的请求权,而单方解除合同时,非违约方享有的是单方意思表示即生效力的形成权,违约方处于服从(Unter werfung)的地位,与普通违约情况下有重大的不同。凡此种种,不可不察。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解除合同视为独立于违约责任之外的救济途径。
② 关于恢复原状是否为民事责任,有争论。郑玉波先生将其作为依责任的内容为区分标准与履行责任、赔偿责任相对应的民事责任类型。(参见:郑玉波《民事责任之分析》,选自《民商法问题研究(一)》,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三),1991年版第 116页。)而韩世远先生认为,其不是直接基于不履行合同债务而成立的,而是解除时必然的法律效果。并非强制履行合同的手段,也不是履行合同的担保,从而也不能将其归入民事责任及违约责任的范畴。(参见: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 685页)。
③ 参见:1934年上字第 3968号判例。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555页;邱聪智著《新订民法债编通则(新订一版)(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360页;黄茂荣著《债法总论(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76页》。
[1] 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 黄茂荣.债法总论(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 叶启洲.附抵押权条款之保险契约的解除与不当得利——最高法院相关判决综合评释[J].月旦法学,2003,92.
[4] 黄茂荣.债法总论(第二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 Esser.Shuldrecht,2.Aufl.,1960.
[6] 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陈荣隆修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8] 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9] 丁玫.罗马法契约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0] 黄风.罗马私法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1] 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12] Rudolf Huebner.A History of Ger manic Private Law.London:JohnMurray,Albemarle Street,W.,1918.
[13] 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14] [美]哈罗德·伯尔曼.契约法一般原则的宗教渊源:从历史的视角看 [A].郭锐译.清华法学[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
[15] 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6] 杜景林,卢谌.德国新债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8] 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9]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0] [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21] Hugh Beale,Arthur Hartkamp,Hein ktz and Denis Tallon Cases.M aterials and Text on ContractLaw,Oxford and Portland,Oregon,2002.
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he Effect of Recession
Shen Hai-en
(The Seco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Beijing 100024)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effect of recession has been a hot issue.As the remedies of relief of breach,the exercise of recession,as a kind of right of formation,release the observant party from the tie of the obligation;as an essential factor of the system of relief under contract law,recession assume the mission to harmonize the rightsof claim based on reciperare and damages.Accordingly,the exercise of recession should modify the obligation from the original contract to reverse transaction.
recession;effect;right of formation;relief of breach
词】DF418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1002—6274(2010)02—013—08
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民法典背景下的形成权基本理论研究》(09CFX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申海恩(1979-),男,陕西蒲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