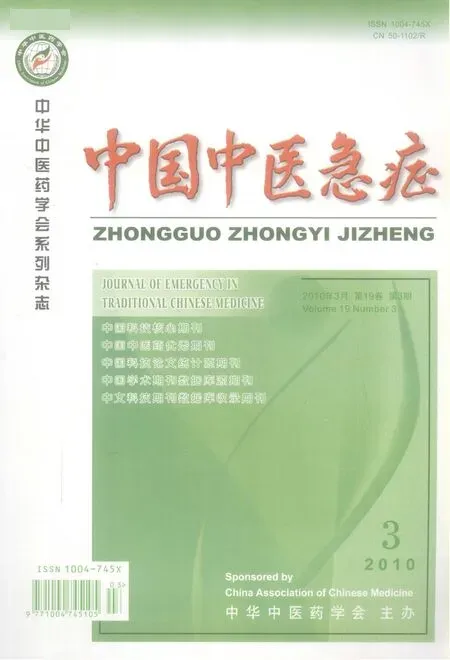《伤寒论》真武汤方证浅析
2010-02-10侯兆辉侯志敏
侯兆辉 侯志敏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医院(通辽 028000)
真武汤为治疗脾肾阳虚、水气内停的主要方剂。《伤寒明理论》谓“真武,北方水神也,而属肾,用以治水焉”;《伤寒来苏集》谓“真武,主北方水也。坎为水,而一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是阳根予阴,静为动本之义”。
真武汤全方5味药物[1],方中附子熟用,大辛大热,为君药,温肾暖土,峻补元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助阳行水以治本,盖水之所制在脾,水之所主在肾;臣以茯苓,甘淡渗利,健脾渗湿;生姜之辛散,散水宣肺走上焦,既助附子以温阳祛寒,又助茯苓以温散水气;佐以白术之健脾祛湿补中焦,健运中土,则水有所制;而尤重在芍药一味,既可益阴以复脏腑功能,又可制约附子、生姜温燥之性,引附子入阴散寒,防白术、茯苓祛湿伤阴之弊,益阴以和阳,可使阳药更好地发挥作用。体现了张景岳之“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阳得阴助,则生化无穷”的配伍原则。纵观全方,一是温阳药与利水药配伍,温补脾肾之阳以治其本,利水祛湿以治其标,标本兼顾,扶正祛邪;二是补阳药与养阴药同用,使温阳而不伤阴,益阴而不留邪,阳生阴长,刚柔相济,阴平阳秘,则诸症可愈。
《伤寒论》所载真武汤主证共2处,一是《伤寒论》第82条:“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目闰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本条是太阳病过汗,汗出过多损伤了阳气,失却“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的功能,故出现头眩,身目闰动,振振欲擗地;其里阳虽虚,然表邪未去,故仲景谓“仍”发热;其心悸一证,既有阳虚失于鼓动,又提示肾阳虚后,以至不能镇水气,使水气凌心所致,但毕竟阳虚轻,病程短,只是无形之水气凌心,尚不至于有形之水饮泛滥。二是《伤寒论》第316条:“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本条的真武汤证,则是由于病程较长,阳气久虚,水饮停滞所致。外则留滞于皮肤肌肉筋脉,致其失于温煦,经气不畅,而见四肢沉重疼痛;内则阳虚寒滞,脏腑失温,故一腹皆痛;且水饮上干肺气而咳,中伤胃气而呕,停滞下焦则下利、小便不利并见。可见其表里内外,上中下三焦皆受其害。
两者虽然同用真武汤,但其病因不同,而病证也存在较大差异。肾藏真阴真阳,为一身元气的根本;肾主水,是人体水液代谢的主要器官,肾中的阴阳之气,是肾水代谢的基础和动力,而肾水又是肾中阴阳之气的源泉,肾中阴阳的不足,必然导致肾水的代谢失常,肾水的不足和潴留,也必定影响肾阴肾阳功能的发挥,但肾阴肾阳的不足有轻重的不同,肾水的代谢失常,也有或多或少的区别,若肾阳先虚而病程短,肾水代谢尚未至潴留,则多表现为阳虚;若肾阳久虚且重,肾水代谢失常,则多表现为水停。总以无形之阳虚先见,有形之水停后现。阳加于阴谓之汗,汗生于阴而出于阳,故汗出过多既可伤阴,亦可伤阳。
2条真武汤证自是不同,然而在治疗时,仲景用同一方剂,其在第82条真武汤证是过汗伤阳,阳气易伤而难复,水湿易停而难消,在肾阳损伤之初,即早补阳气,杜绝水患,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意。若以真武汤重在“治水”言,则第82条所列病证用真武汤是为“防汛”,第316条所列病证用真武汤则是“抗涝”[2]。
真武汤证的病因病机为久病伤阳或太阳病误汗伤阳,少阴寒化阳虚,甚至寒水反而侮脾,土不制水,致脾肾阳虚,不能化气行水,水湿内停,或为痰饮,或为水肿,水气凌心射肺,或悸或咳,从而导致多脏器疾病发生。
由此可见,临证但凡见此证者,均可考虑真武汤为主方,在其基础上加减化裁,以治疗多种因阳虚而致的虚寒性病证。临床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素体虚弱者,外感汗出不解,同时出现阳虚水泛诸病;心阳虚复感外邪致心阳虚症状加重,水气泛溢者;脾肾阳虚,感邪后诸症加重,导致水气泛溢周身,出现肢肿尿少等症状者;慢性病中出现水气停留于全身或局部,有阳虚表现者[3]。在临床具体应用时,可不必拘泥于《伤寒论》原文所述的症状。
[1]李培生.伤寒论讲义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61~62,168~170.
[2]梁华龙.真武汤及其辨证[J].河南中医,2005,25(10):3~5.
[3]曹雯,董正华.真武汤探微[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27(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