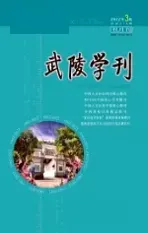昌耀:诗的抵抗史
2010-01-20张光昕
张光昕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昌耀:诗的抵抗史
张光昕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中,昌耀是一位命运多舛而诗艺独步的写作者。他的作品立足于对中国西部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景观的个人化体认,在趋之若鹜的时代创作风尚面前,昌耀坚守了自己独立的精神家园,让他的诗歌气质具有自我完成性。外部境遇的长期压抑,使得昌耀诗歌中埋伏下四条抵抗线索:在不同层面的生命体验中,他力图分别以诗歌写作中秉有的“羔羊情结”来反抗“雄牛情结”,用空间赋形来反抗时间速逝,用个体意志来反抗命运围剿,用诗意内核来反抗现实荒诞。这四条反诘线索交融杂陈,也同时充当了诗人尝试突围的解救之道,让昌耀诗歌呈现出砥砺、狰狞的美学特征。
昌耀;诗歌;美学特征

张光昕博士
昌耀是中国当代独树一帜的诗歌写作者。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他经历了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纠结在一起。昌耀的作品立足于对中国西部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景观的个人化体认,在趋之若鹜的创作风尚面前,他坚守了自己独立的精神家园,让其诗歌气质具有自我完成性。生存境遇的长期压抑,使得昌耀在多重生命体验中写就了一部诗的抵抗史,并且沿着以下四条线索得以展开。
一 “羔羊”反“雄牛”
昌耀素来以酷爱描摹噩梦的结构著称于世,但这个偏居西域的名字却没能与中国当代押上韵。从小怕鬼的他考入湘西军政干校后,因为不敢起夜而常常尿床,不得不被校方勒令退学①;但他并不肯善罢甘休,又瞒着父母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8军114师文工队,开始了日夜与军鼓、曼陀铃和二胡为伴的戎马生涯,随后随军开赴朝鲜战场;负伤回国后,他进入河北荣军学校,因为从保定城里买来的一张名为《将青春献给祖国》的藏地风情宣传画而倍受鼓舞,毅然决定投身大西北建设,从此入赘青海②;1957年的昌耀年纪尚轻,热爱创作,对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不太积极,并且刚好有人揭发他写了“歪诗”,青海省文联理所应当地把分配下来的“右派”指标划归给他,让他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到牧区后,他在尊严问题上屡次顶撞村支书,并听从房东的建议,装病不出工,在“家”里摆弄乐器,终于被一辆吉普车带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囚徒③;这一走就是二十余年,历史烟云散去后,他依然顶着剧烈的高原反应登上了太阳城参加诗会;与他的土伯特妻子离婚后,他横下一条心把住房留给子女,自己搬到摄影家协会的办公室独居,沦为大街看守;感情无所归依的他苦恋着远方的梦中情人SY,一日突发奇想,在信中煞有介事地向后者索求“长长的七根或九根青丝”;后来生病入院,因无法忍受病房里的吵闹,执意要求医院在走廊为他增设一张病床;直到万念俱空,他拖着沉重的病体艰难挪向病房的阳台并一跃而下……④就这样,昌耀被抛进了长达一生的噩梦之夜中:
每于不意中陡见陋室窗帷一角/无端升起蓝烟一缕,像神秘的手臂 /予我灾变在即似的巨大骇异,毛骨悚然。/而当定睛注目:窗依然是窗,帷依然是帷。/天下太平无事。⑤
(《噩的结构 》)
在昌耀那些沙砾般的文字中,无论是公认的佳作还是古怪的文体,即便是最为雄浑、热烈、昂扬的诗句岩层之下,孤独、隔绝、幽愤的心绪都会像一脉脉流动的地下矿泉汩汩渗出,为每一个受难的词语施洗,带领它们飞向苍穹。昌耀的诗歌呈现着砥砺的、狰狞的美学特质,在距离噩梦的“蓝烟”不远处,昌耀用他独有的方式艰难书写着自己苍凉而悲壮的生命体验。
昌耀对自己的诗风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的诗是键盘乐器的低音区,是大提琴,是圆号,是萨克斯管,是老牛哞哞的啼唤……”[1]雄浑的低音区奏响了沉潜在人性深处的健朗音符,昌耀关注的是人类精神基座上的生存事件,偏重低音的声学特征也使他的诗歌具有了风化和沉淀的力量,形成一种坚硬的质地,一种劳作的美学,一种雕塑感。雕凿是一次赋形的演奏,也是写作的隐喻:
雕凿一部史论结合的专著。/雕凿物的傲慢。/雕凿一个战士的头。
(《头像 》)
昌耀渴望在铿锵有力的敲击声中雕凿出一颗永恒的头颅,它带着意味深长的粗线条、石器时代的光环、英雄般的桀骜、古道热肠中浸润着坚韧的灵魂和冰冷的意志,以及一切逝去岁月里的荣耀。因此,不论在诗人的现实“离骚”中,还是在他的语境梦魇里,这类坚硬的形象会天然带有一种惰性,一种回归根部的梦想,它作品中大量积淀的惰性气质,孕育了倾注历史因子和情感细胞的语言聚合体,是诗人错乱而迷幻的个体身份的产物,是昌耀发明的诗意容器,它忠实记录了梦想中生命的勃起与阵痛:
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投影大地。/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垂布天宇。/午夜,一百种雄性荷尔蒙穆穆地渗透了泥土,/血酒一样悲壮。
(《一百头雄牛 》)
雄牛,是昌耀在西部高原上耳濡目染的生灵,这里的一百头雕塑感十足的雄牛形象,正是由他的惰性气质派生而出,也足以蕴藉他充溢着澎湃生命力的、粗线条式的、低音区的语言特征,因此它更易演化为一种诗学情结,以充足的精神能量支配着诗人的创作。于是,我们或许可以认定,昌耀的深层诗歌写作心理中具有一种雄牛情结,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一种昌耀式的英雄情结,暗自统摄了诗人的写作风貌,深深地契合了西部地理原始浩瀚的美学性情,同时,这一刚性的英雄逻辑也彰显着诗人无边的焦虑意识。作为昌耀作品的阳性原则,雄牛情结可以为我们解释,他的诗歌在精神向度上的超拔、坚忍和向善,在遣词造句上的坚硬、生僻和涩滞,也可以在写作之外解释昌耀在处世为人上的诚恳、憨实和倔强,这些都或多或少受到他潜意识中雄牛情结的驱策。我们可以在昌耀众多的诗篇中迎头撞见雄牛及其同类的身影,如水手、船工、驭夫、父亲们、挑战的旅行者、穿牛仔裤的男人、牛王、高车、木轮车队、金色发动机、堂·吉诃德军团……这一系列阳性物象驮载着诗人与日俱增的内心能量一路奔腾,并且,借助这种蓬勃有力的雄牛情结及其体现者的生命合力,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赞美和焦虑。
雄牛情结要将诗人的梦想带到何方?它是否可以在诗中一劳永逸地拯救失落的人类精神?这种过剩的阳刚气质果真能独霸昌耀的诗歌帝国吗?在雄牛军团狂飙而过的尘埃渐渐飘落之际,一个似曾相识的沉默形象却将我们带进一片迥然异趣的天地:
感受白色羊时的一刻/音符与旋律驱动将黑夜荡涤漂卷。/倦意全然扫却,顿觉心底多日之苦索 /瞬间丰满成形,眼前豁然开朗洞明。
(《感受白色羊时的一刻》)
黑夜中的白色羊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宗教意味十足的场景当中,它几乎等同于一只上帝的羔羊,一个耶稣基督的化身,一个平静的受难者的形象。这里的音符和旋律绝非锉刀和石像撞击时迸发而出的铿锵声响,它们如同羔羊的啼唤那般温柔轻盈,如丝如缕,绵远悠长。在昌耀站立的雪域高原,在人迹罕至的西部荒漠,本土的藏传佛教气息教会了这个充满血性的、颠沛流离的诗人一种安静的艺术,它通过这个神圣的生灵向诗人施展了一种超验的灵魂按摩术。羔羊是娇小的,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具有一种消解困顿的作用,正是每一种危险自身包含的拯救可能性。诗人把这一形象深藏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会发现,它不时地幻化成了牧人、少女、天鹅、蜘蛛、蚂蚁、车轮、陶罐、织机、丝竹、炊烟、泥土、贝壳、雪……它象征着那些默默受难的、具有温柔气质和理疗功能的、能够召唤出人类意念深处的悲悯情怀的弱小事物,正如昌耀所说:“我是这土地的儿子。我懂得每一方言的情感细节。”(《凶年逸稿》)
我们不妨将昌耀的这种写作心理称为羔羊情结,它是诗人作品中的阴性原则。如果说昌耀诗歌写作中激奋昂扬的雄牛情结是屋顶垒砌的坚硬砖瓦,羔羊情结就是砖瓦缝隙间长出的一根根青草;雄牛情结构成了昌耀诗歌的硬朗骨架和健硕肌肉,羔羊情结则融化进其体内安静流淌的血液和广为分布的细小神经,两者都来源于西部高原图腾般的生灵物象,共时存在于昌耀的诗歌体系中。羔羊情结犹如雄牛情结在水中的倒影,是每一个物种心灵的本质还原,它标识了一种存在的孤独状态,点染了词语的忧郁色彩。两者在诗歌中的交相互动,体现了诗人面对写作的复杂心态。澎湃的雄性荷尔蒙渗入午夜的泥土,白色羊的音符和旋律将黑夜荡涤漂卷,羔羊情结在语言中驯化着雄牛情结,这一规律让诗人总是保持精神上的胜利姿态。然而,雄牛情结和羔羊情结绝不是幼稚的二分法思维的产物。在诗化语境里,一加一通常要大于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就等于一切。
“自从看到某君画的那头倒毙的奶牛,我才发现自己懂得了奶牛的一生……她的骨架仍然粗实、高大、强而有力,现在仅撑着一张多皱的皮,像是风雨里坍塌的幕帐。”(《内心激情:光与影子的剪辑》)奶牛,似乎可以看做昌耀内心里雄牛情结和羔羊情结交汇下的典型对象。粗壮的牛性价值上叠加了哺乳的母性价值,这头奶牛便是阳性与阴性的象征合体。从终极意义上看,这种阴阳合体其实也存在于每一个事物、每一个词上。随着这头奶牛的倒毙,我们目睹了一场危险的降临,一个希腊式肉体迅速切换为一个犹太式肉体,雄牛情结和羔羊情结终结于这片慈爱的大地,不论奶牛身上的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孰多孰寡,它终究要纳入母性大地的怀中,陷入一场永久的梦幻。在这纯粹的梦想里,作为梦想者的奶牛,甚或任何一件事物,它们都要沿着梦想的斜坡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带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诗学惰性,它们才能回到原初的摇篮,回到大地,在那里将获得最终的拯救,找到内心的和谐与安宁。这是事物的梦想,也是词语的梦想。就像那头倒毙的奶牛一样,昌耀就这样沿着梦想的斜坡走向大地的深处、世界的深处、词语的深处。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在羔羊情结对雄牛情结的点化过程中,我们能够意识到他赋予诗歌语言以梦想的磁力,以及为实现这种梦想所付出的努力。
二 “空间”反“时间”
作为现实世界里的一只受难羔羊,昌耀在白色的噩梦中获得了他对所处空间的最初体验:“他走出来的那个处所,不是禅房。不是花室。/为着必然的历史,他佩戴铁的锁环枯守栅栏 /戏看蚂蚁筑巢二十余秋。”(《归客》)在流放荒原的二十多年间,昌耀与一种阴暗的、狭小的、被囚禁的空间体验朝夕相伴,这也成为他有意识地感知空间的漫长开端。他在痛苦乏味的监禁生活里通过观看蚂蚁筑巢展开对自我的定位和对世界总体空间的勘测,学会了一种“认知测绘”⑥的本领。也就是说,他在一间极端狭小封闭的囚室内探明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也渐渐充满了感知总体空间的精神能量,他领悟到了“必然的历史”的伟大逻辑,懂得了运用空间的观念来认识世界。
空间观念的萌生使昌耀以一位建筑师的眼光来参与诗歌形象的遴选和描摹,并为每一组空间形象注入物质想象的激素。“不是无端地记起了刨具和斧斤。/是匠人铁的啄木鸟和木的纺织娘 /为我留下了世间独有的韵致。”(《建筑》)构造诗句和构造房屋似乎具有相同的建筑学元素。保罗·雷比诺(Pau lRabinow)借采访福柯之际提到:“建筑的知识,部分属于专业的历史,部分属于营造科学的演化,部分属于美学理论的重写。”[2]建筑无疑是美学的爱子,它在昌耀的作品中不但指代着人工建筑,还指代自然建筑 (如山川河流)。诗人以他独到的美学判断力通过物质想象的翅膀实现了他的空间蓝图,并且开始了他对诗歌语言形式方面更有力的探索和实验:
戈壁。九千里方圆内 /仅有一个贩卖醉瓜的老头儿:/一辆篷车、/一柄弯刀、/一轮白日,/伫候在驼队窥望的烽火墩旁。
(《戈壁纪事 》)
和华莱士·史蒂文斯 (W allace Stevens)放在田纳西州的那只著名的坛子一样⑦,这个由篷车搭建的简陋瓜摊也获得了一种建筑物的尊严,它屹立在烈日之下、大漠之上,成为戈壁的一个生命地标。昌耀成功地动用了他在囚徒时代自修来的“认知测绘”能力,让这片中国西部的典型空间瞬刻显形。瓜摊定义了这片空间,为那些围绕着大漠飘忽不定的现实经验赋形;它也命名了这种戈壁经验,并将它们安放在人们对西部空间的物质想象和期待视野之中。这个九千里方圆内的瓜摊之于戈壁的意义,接近于梅洛 -庞蒂 (M aureceM erleau-Ponty)提到过的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就像在荒野中的原始人每时每刻都能一下子确定方位,根本不需要回忆和计算走过的路程和偏离出发点的角度[3]。按照这种神奇的认知序列,我们找到了一处瓜摊,就等于拥抱了整个大漠,这种地标式的建筑物身上,诗人可以径直阅读到雪藏在那里的众多经验和记忆。
作为一种有灵性的建筑物,戈壁瓜摊可以看成是诗人对整个西部空间的一个写意式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之下,昌耀开始了他对西部空间排山倒海般的阐释工程。作为一个前现代形态的传统社会,中国西部基本保持着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文明样式,当昌耀怀着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愫身临其境之时,中国文化上千年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积淀如同高原之风扑面而来:
历史太古老:草场移牧——/西羌人的营地之上已栽种了吐蕃人的火种,而在吐谷浑/人的水罐旁边留下了蒙古骑士的侧影……
(《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
这是昌耀在寻找黄河正源途中再现的奇幻历史景观,是民族记忆的出神状态。在沿着黄河河道逆流而上的水源寻根行动中,诗人也同时展开了他的文化寻根想象。对于中国 20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界来说,这股内心激情是与之合拍的。但我们同时可以觉察到,昌耀的激情更多地来自他对西部空间原发性的生命体验,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对自己发起的文化寻根。这种梦游般的出神状态几乎成为了昌耀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癖好。我们可以明显分辨出诗人欲将“时间空间化”的倾向。T.S.艾略特 (T.S.Elio t)提醒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4]。这种过去的现存性以建筑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以对空间形式的构造来传达它的价值。卡斯腾·哈利斯 (Karsten Harries)主张,建筑不仅仅是定居在空间里,从空无到空间中拉扯、塑造出一个生活的地方,它也是对于“时间的恐怖”的一项深刻抵拒。“美的语言”是一种“永恒现实的语言”。创造一个美的物体,就是去“连接时间与永恒”,并据此把我们从时间的暴虐中救赎出来。空间构造物的目的“不是阐明时间的实体,使我们或许可以更适意地悠游其中,而是……在时间中废除时间,即使只是暂时的”[5]。于是,我们发现了昌耀寄情于空间书写、讴歌奇伟建筑的一条潜意识:他正是希望以这种“时间空间化”的方式,释放他笔下空间形象的能量,让那些矗立在深层记忆中敦实的、凝滞的、牢固的建筑物成为一根根中流砥柱,让它们抵挡住时间洪水的无情流泻,让时空双方对峙的一刻闪现出更多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昌耀以空间抵抗时间的潜意识让他对一切空间构造物怀有好感。这一创作倾向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比兴”传统和“田园山水”情结;另一方面,在诗人深层的观念结构中,这意味他在仰仗空间的方位性有意制衡时间的绵延性。这条潜意识不但让昌耀对历史空间予以追思,而且向现实建筑空间投来赞美:“我不是朝圣者,/但有朝圣者的虔诚。/你看:从东方栈桥,/中国的猎装 /升起了梦一样的 /笑容。”(《印象:龙羊峡水电站工程》)198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思潮让“建设”成为了一个深受欢迎的时代主题,由此我们相信,昌耀对现实建筑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歌颂冲动源于他在创作中长期坚持的理想主义。早在 1959年,他就曾创作了一首歌颂“大炼钢铁运动”的民歌体叙事长诗《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将它统摄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名下,成为他一度崇尚的“高炉美学”的滥觞。多年以后,诗人有过这样的反省:“我欣赏的是一种瞬刻可被动员起来的强大而健美的社会力量的运作。是这样顽健的被理想规范、照亮的意志。这种精神终于在被导向极端后趋于式微,而成为又一种矫枉过正。”[6]可以认为,这种“高炉美学”在昌耀流放归来的诗歌中达到空前繁荣,也在日后社会价值转型过程中遭遇到艰涩的瓦解。
三 “头颅”反“墙壁”
一个诗人写作生命中的每一次意味深长的转向,其实都是与魔鬼达成契约的结果,都是一次魔鬼化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 (Haro ld B loom)认为:“使一个人成为诗人的力量是魔鬼的力量,因为那是一种分布和分配的力量 (这也是‘魔鬼’一词的原始含义)。它分布我们的命运,分配我们的天赋,并在取走我们的命运和天赋而留下的空缺里塞进它的货色。这种‘分配’带来了秩序,传授了知识,在他所知道的地方造成混乱,赐予无知以创立另一种秩序。”[7]同诗人流放归来后兴起的空间观念相类似,他在《斯人》之后写作风格的骤变不妨视为“另一种秩序”的诞生,它象征了昌耀诗歌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魔鬼化过程。以《斯人》为界,长期盘踞在昌耀作品中那种惯性十足的“高大全”式写作思维宣告终结,尽管这种“高炉美学”长期被诗人视为一种“顽健的被理想规范、照亮的意志”[6],并曾经在昌耀以及同时代的写作者和艺术家那里获得了它无与伦比的光环,但它本质上依然是由理想主义操刀下的魔鬼化产物。
骚动如噪声。你一声长叹,/以头颅碰撞梦墙。/可你至今不醒。
(《噱 》)
魔鬼化的引入让受虐的诗人燃起一团暴虐之火,让他在胸中迅速积聚起一股激愤的能量,昌耀决定用它来改造令人窒息的现实处境⑧。为了击溃多年来在自己认知谱系中盘根错节的“高炉美学”,为了拯救自己痛苦不堪的命运,昌耀适时调用了这股魔鬼化的力量——他要以头颅碰撞梦墙——这被认为是一种最为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在魔鬼化外衣的包装下,碰壁不再是弱者在现实境况里的可怜遭遇,而变成了一种英雄式的反抗姿态,在昂起的头颅上掠过了一丝豪迈的幻影。在这场以头撞墙的激战中,诗人的头颅成为带上钢盔的大脑,充当了整个身体的急先锋。头颅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御驾亲征,用尽浑身解数希望在密闭的意识形态高墙上撞开一个缺口。
“东方游侠,满怀乌托邦的幻觉,以献身者自命。/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是万能的魔法又以万能的名义卷土重 /来。”(《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骑士无疑是以头撞墙的杰出代表,也是昌耀自诩的对象。诗人炙热的肤体内部充溢着火一样的破坏力,他坚硬的头颅同样渴望着坚硬的墙壁。一道魔鬼化指令让诗人立即执行以头撞墙的行动,以期实现一种“去魔鬼化”的目的。诗人以声音形象量度着这一系列撞击的效应:“静夜。/远郊铁砧每约五分钟就被锻锤抡击一记,/迸出脆生生的一声钢音,婉切而孤单,/像是不贞的妻子蒙遭丈夫私刑拷打。/之后是短暂的沉寂”(《人间》);“骤然地三两声拍击灵魂。情结诡谲。/空荡荡是影子,黑黢黢僵仆,倒地急促”(《听到响板》)。在这种局促不安的基调中,昌耀从的撞击声里敏锐地捕捉到了细微的现代感受,这是头颅和墙壁之间展开的犀利对峙,诗人体内火一样的破坏力让碰撞时不断迸溅的火花成为了两者交流的产物,成为了诗人炙热而焦虑的文字,炮制了一种狰狞之美。以头撞墙是用自虐的快感来抵消、麻醉受虐的疼痛,几番撞击之后,身心麻醉的诗人获得了神经病人般异常敏感的听觉:“那时即便一声孩子的奶声细语也会如同嚎啕令男儿家动容”(《悲怆》);“难怪一声破烂换钱的叫卖就让你本能地忧郁”(《僧人》)。与其说这是以头撞墙的后遗症,不如说诗人实际在进行着一种声学自虐。在昌耀的秘密耳道里,“孩子的奶声细语”、“破烂换钱的叫卖”和诗人以头撞墙的声,都源于他的羔羊情结,属于羔羊式的声学体系,它们都是与各自命运之墙撞击时发出的音节,是生命的呻吟,是弱者的武器。昌耀通过这种声音的传递,找到了自己撞击墙壁的回声。神经敏感的诗人在忍受这种声学自虐的过程中,也把它改装成一种声学自慰,享受着从肉体到精神的多重体验。“淘空是击碎头壳后的饱食。/处在淘空之中你不辨痛苦或淫乐。/当目击了精神与事实的荒原才惊悚于淘空的意义。”(《淘空》)
悖谬的现实体验让撞墙本身成为一个自反性概念。墙成为一个象征围困的符号,它以真实的身躯出现在诗人被流放的年代,又以一种空间伦理填充着他的建筑学狂想,如今它以另一幅虚拟的面孔进驻了诗人对现实境况的真切感知。描述过“狗鱼实验”的舍斯托夫 (Lev Shestov)将以头撞墙视为“惟其荒谬,故而力行”的哲学赞词:他把人比作放养在玻璃器皿一侧中的狗鱼,另一侧则是狗鱼的猎物,它们中间有一道玻璃隔板,无所察觉的狗鱼一次次向猎物发起冲击,都狠狠地撞在了透明隔板上,几番尝试之后,狗鱼安静了下来。即使把隔板去掉,狗鱼依然无动于衷。昌耀在付出以头撞墙的代价之后,在体验了撞击中的自虐和自慰之后,貌似浑然不知地中了墙壁的木马计。墙壁并不固然强大,但昌耀以头颅相撞的正是这种游击主义的墙壁,后者每得逞一次便在火光的掩护下悄悄将海德格尔 (M artin Heidegger)所谓的“畏”的基本情态偷运进诗人的头颅内部,不动声色地解除了他精心布置的魔鬼化武装,致使昌耀的突围计划最终破产。
心源有火,肉体不燃自焚,/留下一颗不化的颅骨。
(《回忆 》)
头颅的魔鬼化不敌墙壁的木马计,以头撞墙预示了昌耀人生的失败,然而这一堂·吉诃德式的壮举却宣告了我们在认识论上的胜利。在头颅与墙壁的猛烈碰撞中,就像诗人记住了那些聊以自慰的声音一样,他也仿佛看到了迸溅出的火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撞击产生的火花不论来自幻觉还是真实的迸发,它们都被诗人误认为是他内在火焰的发泄,是外界对内心产生的共鸣。如果用阿伦特 (Hannah A rendt)评价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头颅与墙壁撞出的火星面前,昌耀正是“用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⑨,他就这样沉迷于这一假象之中。不论围困诗人的墙壁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永远存在,昌耀都像那条狗鱼一样慢慢安静了下来,失败后的昌耀已经不在乎是否还有墙壁了,他默认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思想者的圆颅顶驰去虚无的车马。”(《洞》)
昌耀已经与墙壁融为一体,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有麻木体验掩护下的自虐与自慰。当痛感和快感渐渐退潮,昌耀发现与魔鬼的契约实际促成的是自己与世界的象征性和解。昌耀很可能真的经历了创作的魔鬼化,他是一位试毒者,以此来达到免疫和自救。就像他描写过的一种含有毒素的植物那样,利用这种致命武器,为着个体生存向蚕食它的昆虫发起复仇:“以恶抗恶:植物可怖的宗教神话,魔力无边的咒语。”(《复仇》)不论魔鬼的力量带给昌耀的是幸运还是磨难,在接受辩证法领导的同时,与魔鬼签约的代价是让生命走向衰老,时间或许是一个最大的魔鬼,衰老是这个惊心动魄的魔鬼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正如昌耀所说:“世间自必有真金。/而当死亡只是义务,/我们都是待决的人。”(《浮云何曾苍老》)
四 “内火”反“外焰”
昌耀的诗歌中暗藏着一团双重火焰,它以一个诗意的原点为焰心组成同心圆。外层高温炙热,是一种热感型火焰,它与日常生活的氧气相接触;内层明亮炫目,是一种光感型火焰,它包裹着诗意的中心。外焰具有氧化作用,它隔绝了诗意的浸润,让诗人成为“天地间再现的一滴锈迹”(《听候召唤:赶路》);内焰具有还原作用,它毗邻诗意的源头,让诗人从此化作“一部行动的情书”(《慈航》)。双重火焰以相反相成的形式在昌耀作品中燃起,它们彼此间张力十足,又共存于一个文字空间;它包裹着昌耀全部的生命信息,并将它们以一种狰狞之美折射进那些逐渐成熟的诗行中。双重火焰展示了一幅充满吊诡、紧张和斗争的命运图式,联步呈现、整理和调解着现实生活与诗意之间的关系。内焰与外焰间的砥砺厮磨不仅勾勒出昌耀以头撞墙的创作心态,而且也导致了他作品中英雄情结的分裂和衰变。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昌耀在现实境遇上一系列悖谬体验不断升级,日常生活的外焰大有吞噬诗意内焰的趋势,企图让诗人的单纯内心世界全部氧化、变色、生锈,将审美空间焚毁成灰。在这团狰狞之火的威胁面前,昌耀体会到了自身的真实处境:
面对一种冷场,朝觐生命寒射的光照,/如在烧红的铁板感应蹦起的鱼。
(《场 》)
“烧红的铁板”远远要比“寒射的光照”来得更为紧迫和猛烈,热感型的火焰以绝对的优势要挟、遮盖住了光感型火焰,这也预示了日常生活有足够的力量击败诗意的存在。这种趋势让一贯秉承古典主义英雄观的昌耀开始对他笔下的形象做出一定的调整,以此为他难以为继的英雄逻辑铺就道路。在现实主义外焰的连年烘烤之下,在“烧红的铁板”上“蹦起的鱼”成为昌耀塑造出的一个另类的英雄形象,即使刀俎皆具,也不忘做一次绝望的反抗。“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悲壮啊,竟没有一个落荒者。/悲壮啊,实不能有一个落荒者。”(《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不论是“蹦起的鱼”,还是“丧家之狗”,昌耀将这类形象都注入一种反英雄的元素,日常生活以烘烤的方式邀请它们在昌耀创作的中晚期现身。反英雄形象的出现,促使它们与以往昌耀笔下的英雄形象分庭抗礼,成为了对古典英雄形象的戏仿:“堂·吉诃德军团的阅兵式。/予人笑柄的族类,生生不息的种姓。/架子鼓、筚篥和军号齐奏。/瘦马、矮驴同骆驼排在一个队列齐头并进。”(《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塞万提斯(Cervantes)创造的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本身就具有反英雄的色彩,这个迷恋骑士小说以致于走火入魔的伪骑士,终于在与现实之墙的无数次喜剧性碰撞之后,承认了一种悲剧性的命运。昌耀如同堂·吉诃德一般,同样付出了以头撞墙的惨痛代价,他终于承认:
没有硬汉子。/只有羊肠小道。/命运跳板的尖端/容不下第二种机缘。
(《嚎啕:后英雄行状 》)
嚎啕是诗人内心情感淤积的强烈爆发,也是对他长期赏识的抒情系统的一次格式化。尽管这里喷发出的消极见解仅仅是诗人情绪波动时的过激之词,但经过此番格式化处理之后,昌耀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认知模式和情感结构中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在昌耀众多的诗篇中,英雄一直是一个或一群“硬汉子”,是日夜奔腾、摧枯拉朽的一百头雄牛,是青藏高原上恣意挥鞭的牧人,是滚滚黄河里搏击湍流的水手,是开国元勋,是草莽豪侠,是水坝工地上牺牲的浇筑工人……英雄张扬的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是自然的原欲。然而,在诗人的嚎啕声中,不断失衡又持续升温的双重火焰显出了狰狞的面孔,仿佛施了某种巫术,硬汉子式的英雄们瞬间化为乌有:“大男子的嚎啕使世界崩溃瘫软为泥。/……硬汉子从此消失,/而嚎啕长远震撼时空。”(《嚎啕:后英雄行状》)如果把昌耀诗歌中遍布着“硬汉子”的创作阶段想象为一个“英雄时代“,那么如今这种嚎啕之声便意味着英雄时代已然“崩溃瘫软为泥”,而宣告另一种昌耀所谓的“后英雄时代”的登场。与“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形象的指令不同,“后英雄时代”创造的正是反英雄的形象,在这类形象身上,我们找不到丝毫整体感的光晕,找不到对正面宏观价值的讴歌,找不到乐观积极的抒情元素,它们被燃烧在“后英雄时代”里的狰狞之火统统消解、焚化,变成了对没有英雄出现的平凡人间的片段式记录,变成了一种灰烬中的叙述,变成对生存本身的赤裸相见。
“后英雄时代”对“英雄时代”的覆盖和消解是现实主义外焰对诗意内核虎视眈眈的结果:“如果必要的死亡是一种壮美,/那么苟活已使徒劳的拼搏失去英雄本色”(《一天》);“后英雄时代”在现实中的胜利者姿态驱散了诗人以往施加于“英雄时代”的种种梦幻,妄图解体昌耀创作心理中的英雄情结,将他带进了世俗、琐碎的现实生活。昌耀说:“日子是人人遵行的义务。”(《圣咏》)“后英雄时代”正是由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构成,这里“没有硬汉子,只有羊肠小道”,它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直面眼前这个并不完美的生活世界,让不能做英雄的人们成为苟活者,让耽于梦幻的人们嗅出人间的烟火。
昌耀就是这样一个怀有英雄情结的苟活者。在他中晚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从“英雄时代”向“后英雄时代”的转轨过程,这种转轨也包含着时代基本命题的转换,即从前者的“像英雄一样生活 (思考、说话、写作、恋爱……)”转变为后者的“像人一样生活 (思考、说话、写作、恋爱……)”。这种命题转换,彻底消除了昌耀以及他的同代人对英雄的崇高幻想,将自己还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感知世界,感知他人,也让他此间的作品中充满了叹嘘、疲惫和累累伤痕。现实主义外焰拼力扑灭诗意的焰心,但却无法将其焚烧殆尽,只能将它逼入中心的孤岛,如同锁入一间世外的牢笼,那里是昌耀内心里冥顽不化的诗意中心,它像一豆永远燃烧的灯火,为诗人保留着对英雄的梦想。因为昌耀的英雄情结内核尚在,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苟活者的名号;又因为英雄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昌耀不得不在“后英雄时代”的基本命题下成为一名苟活者。
观念与境遇的厮磨也正是双重火焰之间的抗衡,这让诗人的内心徒生出旷日持久的烘烤感和离奇的悖谬体验,但值得庆幸的是,生活对诗意的压抑反而促成诗意的再生。在昌耀的创作历程中呈现出一条英雄情结的衰变轨迹,这个过程面目狰狞,充满心灵的历险和意志的修炼。昌耀的诗歌在抵挡消极命运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一个诗意的内核,让我们能够穿透生活的迷雾洞悉灵魂的底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昌耀诗歌中的生命体验也构成了我们揣测生活的一个不老的神话。
注 释:
①参阅昌耀《昌耀的诗 ·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19页。
②参阅昌耀《艰难之思》,载《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03-405页。
③昌耀在 1962年撰写的对自己“右派”问题复议的《甄别材料》中称:“我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不愿过问旁人的事。我将生活划分为哪一种对我的创作是有利的,哪一种是无益的。比如:我觉得逛庙会,去草原对我的创作有好处,能启发我写作的灵感,而开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琐事似乎只对创作小说的积累素材有好处……我对政治与艺术的理解是幼稚的。这也表现了我的不成熟。”参阅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75-76页;章治萍《雨酣之夜话昌耀》,《中国诗人》(季刊)2007年第 1期。
④参阅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39-344页、第 467-468、第 380页、第 486-487页。
⑤本文引用的昌耀作品均出自《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参阅[美 ]詹姆逊《认知的测绘》,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 (1):新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93-307页。
⑦参阅[美 ]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陈东飚、张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65页。
⑧“以头撞墙”的生命姿态可以看做是昌耀从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社会体制、民生态势、感情生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一种形象化的心理反应。昌耀越发显得与自身处境格格不入,性格越发孤独伤感。这种受虐体验让诗人在心理上积聚了大量难以释放的窒闷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以头撞墙”即是诗人企求宣泄、找回心理平衡的一种消极自救手段。
⑨此语最初是瓦伦哈根对历史学家根茨的评价,阿伦特引用它来概括对海德尔格的看法。转引自[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9页。
[1]昌耀.宿命授予诗人荆冠 [M]//昌耀诗文总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589.
[2][法 ]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M]//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6.
[3][法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8.
[4][英 ]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 [M].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
[5]转引自[英 ]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M]//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97.
[6]昌耀.一份“业务自传”[J].诗探索,1997(1).
[7][美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修订版)[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02.
Changyao:H istory of Poetic Resistance
ZHANG Guang-xin
(Schoo lof L iterature,Journalism and Comm unication,M 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In the dom ai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Changyao is a superexcellent poetwho suffers m uch in his life.H iswo rks baseson hi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al environm ent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westChina.Against creation style of hisage,he keeps independentpersonality and voice,whichm akeshispoetry fullof a nature of self-comp letion.Because of long opp ression from externalworld,Changyao’shides four resistant c lues in hispoem s:He tries to use“lam b comp lex”to resist“bull comp lex”,fixed space to resist flying tim e,individualw ill to resist fate,and poetic content to resist realistic absurdity.The four cluesare interlaced and serve as thew ay for the poet to save him self.They give hispoem s an encouraging and ferocious aesthetic feature.
Changyao;poetry;aesthetic feature
I206.7;I207.25
A
1674-9014(2010)06-0086-08
栏目主持人:肖学周博士
主持人导语:昌耀,原名王昌耀,1936年 6月 27日出生于湖南桃源,2000年 3月 23日在青海西宁辞世,后魂归故里。由他亲自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在他去世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湟源县建立了昌耀纪念馆。如今,昌耀被公认为中国当代大诗人。骆一禾认为“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韩作荣认为“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作相比,也不逊色”。有关昌耀的研究性论文在其生前就已经出现,他去世至今十年来,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但比较分散,总体上与其大诗人地位还不相称。因此,《武陵学刊》特设“昌耀研究”专题栏目,集中刊发研究昌耀的论文,以期推动昌耀研究的深入发展。
2010-09-12
张光昕(1983-),男,吉林蛟河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