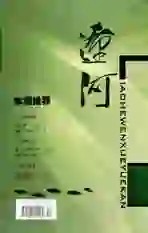飞鹤飞了
2009-12-25董连柯
董连柯
他,飞鹤,五花大绑的被押进了刑场。人们一下子骚动起来,不住地往前涌。那些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拄棍子的、抱孩子的,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奇、疑惑、迷惘、像看马戏团里的大猩猩,不,像看一头雄狮。他这个让最哭闹的孩子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住了声,让药山四周村庄一遍遍贴满布告悬赏缉拿的惯匪,竟有这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行。冷丁看到这黑压压的人群,他感到一阵眩晕、恶心,甚至要呕吐。是的,他有些窝囊,有些颓丧,但旋即又平静下来。自被捕以来,他一直沿用一种方法,背诵邓司令的绝笔:七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土几时收!一想到邓司令,一背他的诗句,就感到亲切,就感到温暖,身上就有股劲儿!一个山里娃娃,蒙您知遇之恩,教诲提携,才渐渐地像个抗联首领。邓司令你大义凛然地走了,小日本偷偷地杀了你,还不如我飞鹤,今天有这么多人来送行,他禁不住笑了。过一会我随你而去,到阴间还做你的马前卒。他笑了,更因为毕竟救下了三妹,让她毫发无损,这比什么都强,一想到三妹,他就会有种冲动,这个人生的小老师,是你的点拨,我才活得像个人样儿!但他的心又渐渐地沉下去,越来越黑,坠入一种悲苦凄绝的幽暗中。其实他也想活,跟三妹一块儿活,人家九井开出的价码够说的了:只管养伤,不必带兵打仗,和三妹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生活,只要给抗联首领写封信……自己投降,还要劝别的抗联头领投降,我飞鹤的骨头还没那么贱!
远处几个日本士兵正用枪托打人,飞扬跋扈到极点,他不由得闭上眼睛。四省丢失几时收啊,这是邓司令就义前的呐喊!如今,邓司令不能收了,自己也不能收了。他习惯地去摸枪,但手不能动了,我那百发百中朝夕相伴的水连珠啊,今生再也摸不到你了!他心里一阵酸楚。他把眼光移向远处,还是看看风景吧,看那最山巅的四花顶,多看一眼是一眼吧,这个养育他二十余年,让他魂牵梦绕的药山啊!他感谢刘虎臣,能让日本人同意他在父亲圆寂的日子,在药山脚下结束自己二十四岁的生命。
父亲,应该郑重叫他父亲了,二十岁前一直叫他义父,他的一生见证了药山的兴衰,他给他讲的第一个故事也是药山。那是唐代,元帅薛礼率二十万大军东征高丽,来到辽东,不料众将士水土不服,跑肚拉稀闹肠炎,薛帅一夜愁白了头,独自一人登上一座奇山,只见:天地苍茫渤海浮,松涛百里入云头,浮屠绝顶青霄半,俯见云雾似水流。薛帅哪有心思赏弄风景,对准山顶一块巨石,仰天长啸,挥剑劈成十字,只听轰然一声,那巨石化作一朵莲花,从中飞出一只白鹤,这白鹤飞呀飞,引薛帅来到半山腰一个平坦地,那儿到处长着中草药,三军一下得救,薛帅便赐名此山为药山也。
时光荏苒,到了清代,药山已成为辽宁四大名山,半山处,楼阁参差,金碧错落,规格巍然,尤以清华观、碧霞宫为最。僧道合住几十人,香火鼎盛。没想到那一天,突然闯进一队老毛子兵,那个头儿,急三火四的连说带比划,他越想说明白,主持越听不明白,凭什么让我们两个小时内离开?僧人见了兵,有理讲不通。不通就要动手,可怜老主持被刺刀活活挑死,众僧人吓得恨不得借两条腿逃命。
第二天夜晚,父亲一人潜回观内,飞身跃上檐头,观内人迹不见。走遍所有寺观,还是没一点动静,一直走到半山顶的玉皇阁内,他不由得大吃一惊,阁内藏着一大批枪械子弹。父亲明白了,老毛子兵急急忙忙藏这些东西,又急急忙忙逃走了。这日俄战争,他们不是小鼻子对手。
偌大一个药山,只剩父亲一人。香火早已中断,只好下山化缘。父亲就是那次化缘结识母亲的。他敲开一个庄户人家的大门,迎出来的是个少妇。他们一下子都愣住了,母亲几次到山上进香,父亲曾给他指点迷津,丈夫早逝,只能修来世吧。母亲笑了,笑得一定很好看,是那种嫣然一笑,不待父亲开口,母亲回身取出许多钱米。父亲哪肯受用,两个推来搡去,母亲早已红了脸,不知怎的说了一句,家里人都下地去了,只有我一人看家,到屋里喝口水吧。后来母亲便生下了他,按律随母亲前夫的赫姓,认父亲为义父,说是为了好养活。
人们还是冒漾似的往上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有脚下垫块石头,没等站稳又被挤下去了;有爬上小树的,又一个人爬上来,小树被压倒了。人们哟,你们看什么?说我是神枪手,那不假,说我有蹲式飞功,那也不错,但说我有三头六臂,能飞檐走壁那就是讹传了。蓦地,他看见了胖墩儿,胖墩儿眼巴巴地看着他,就是挤不到跟前。胖墩哭了,胖墩儿你别哭,不是你第一个叫我飞鹤的吗?我死后变成一只白鹤,在药山间飞来飞去,那有多好!
和胖墩是十六岁那年成为好朋友的。那年的四月十八庙会也没有今天人多,其实胖墩多少次要跟他玩儿,他不肯,还有很多孩子要跟他玩儿,不就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他这个野种啥模样吗?但那次他无法拒绝了,胖墩走了那么远的路,带的好吃的一口没动全给了他,头天晚上还把奶奶藏了半年多的一根天津十八街大麻花也偷来给他。“胖墩儿你快走,我等你五、六气儿了,你咋那么熊?要不,你在这儿坐着,我到四花顶给你取一样东西,别人爬上去得半天,你数一万个数,慢点儿数,我就回来了。”胖墩儿没数上一万个数,光顾看他爬山的样子,他简直如一只白兔一般,不,他飞的一般,白家织布一扇一扇的,多像只白鹤啊!“赫飞,你这名儿多咬嘴,你就叫飞鹤吧,你多像一只飞鹤啊!”“胖墩儿,你看,枪,真家伙!你掂掂,老沉了,老毛子的水连珠儿。”胖墩瞪圆了眼睛,两只手才擎住枪。“我告诉你了,你可要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那是我八岁那年,我到四花顶下面那个洞里玩儿,天哪,那里藏着那么多枪和子弹!我也像你似的,两手端起枪,顶上子弹,呯的一声打了出去,吓了我一大跳,老半天才回过神儿。从那以后,我天天跑来练枪,连做梦都在练。这些子弹壳给你玩儿,可别说我给你的。我可不吹牛,我现在的枪法老准了,我都能在夜间打香火头儿。你起誓,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要报仇,赫家堡子那个无赖,我妈是他逼死的……”“妈呀!”胖墩大叫一声,“不好,我妈找不到我,不知怎样着急呢,我可得走了!”“胖墩儿,你可发誓了,说话不算数是小狗!”
人群又是一阵骚动,铁桶般的密硬是挤开条缝。黄家大院的大炮手大胡子领着那位算命先生挤到近前,拎着酒和肉。大胡子,我的好哥哥!还有那位老交通,劳你们来送行了。
父亲总以为四花顶人迹罕至,他藏的枪鬼都不会知晓。那天,他看到堆成小山似的子弹壳,吓得晕了过去。佛家子弟,怎能鼓捣杀人的玩意!容不得自己分说,送他到黄家大院当炮手,方圆百里,哪个不知,黄家的规矩极严,只有送到那里父亲才放心。他一步三回头啊!药山,童年的摇篮,少年的乐园,只好拜拜了。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一遍又一遍,慈悲为怀,不要杀生……
上岗的第五个夜晚,夜朦胧,月朦胧,丑末寅初,人们正酣睡中,他和大胡子都抱着枪打盹儿,人家大胡子长着一双顺风耳呢!一激灵醒了,他也醒了,只见有五、六个胡子正在半里外一个土坎儿下面坐着,一个人还抽着烟,他手起一枪,打飞了那人烟袋锅子。第二天,黄家大院上百口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连大小姐都不住地对他飞眼儿,他不会飞眼儿,只管龇着一对小虎牙笑。大当家的还特地摆了酒席,他没敢喝酒,跑回到西厢房住处,那个常到黄家的算命先生也撵来了。被大胡子他们一下子围住了,都想算算何时能讨到老婆。算命先生满脸堆笑,“想算命不难,在下分文不取,但须猜对我出的一个谜语:一个小伙长得苗,五个姑娘搂他腰,三个姑娘扒裤子,底下露出一撮毛。”一语刚了,大胡子他们笑得在炕上打滚儿,他也笑了,这位先生,穿大衫戴礼帽的,大当家奉为上宾的人能跟他们混唠,这么热乎人儿,便有几分好感。“是毛笔吧”。先生也笑了,“刚才是蠢破素猜,再说一个。一大口两小口,品字模样,三皇留到今天,遮阴挡阳。君也用臣也用,君臣一样,富也用,穷也用,万古流芳。”大家面面相觑,哪里猜得到。又过了半天,他才说道,“是裤子吧”。众人半天才解开,又一齐笑起来。先生没笑,“我给大家讲一个没法遮阴挡阳的故事。在我们尖山窑一带,驻有一队日军,队长叫提茂,每天都得找一个妇女陪他过夜,天天换人儿,不知被他糟践多少良家妇女。这还不算,那天他抓来三十来个青年男女,关在个空房子里,强令男女各站一排,脱光衣服,对面站立,眼看对方,不从者便用皮鞭抽打。可怜那些妇女,极力用手去遮阴挡阳,提茂用刺刀乱扎其手,不时发出怪笑,折腾够了,留下两个漂亮点的由他轮着发泄兽欲……”禽兽,更是个禽兽!像撞翻了五味瓶,那酸水,那苦液,翻江倒海般在胸中涌动。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噢的一声叫了起来,大胡子他们吓了一跳,一开始他还只是抽抽搭搭哽哽咽咽,后来,跑到门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那尘封的记忆啊,他愿永远藏在阴暗处,扔在旮旯里,锁在抽屉里,如今却像决堤的水一下子宣泄开来。
他刚刚记事,睡梦中隐隐约约听见母亲和一个男人小声讲话,那男人还亲他的脸。父亲也有七情六欲,喜只喜得今宵夜,怕只怕天明又离别。别离后,相会不知哪一夜,听一听鼓打三更心更切,月照纱窗影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恨天,为何闰月不闰夜?赫家骡马成群,父亲来时,轻轻跳进院内,学一声驴叫,母亲便穿上长衫,把父亲裹在衣内的。自己越长大,赫家越沉不住气,族人找上乡邮去找父亲问罪,撵他离开药山,但佛门圣土早已鲜血染地,哪个主持愿来?最后允许父亲留在了药山,但再也不准踏入赫家堡子了。
忽一夜,又传来驴叫声,母亲急忙披衣迎接,进屋才知来的是本村无赖。母亲厉声质问,无赖嬉皮笑脸,“和尚来得,我为何来不得?”母亲高声呼救,半天,赫家大小人等,没一个上前。母亲和无赖厮打,他从睡梦中惊醒,也来帮母亲,那无赖拎起他如同拎一只小鸡儿,母亲屈服了。后来他睡了,睁开眼时,母亲的眼边儿红红的,还没事似的对他笑着,笑得很勉强。到了傍晚,那个无赖竟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进来,倒在炕上就睡。天亮时,母亲叫醒了他,母亲穿戴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立立整整。母亲要领他上药山,他乐得一蹦老高,他最爱上药山了!到了山脚,母亲好像凄惨地笑了笑,“你腿快,给你干爹送个信儿,说我一会儿就到。”他像个小燕子似的飞走了,他要和干爹一起来接母亲,他要一只手拉着干爹,一只手拉着母亲上药山,他是哼着小曲儿跑上山的。
母亲没上山,她向山脚的珍珠潭一步步走去,珍珠潭水又清又凉,她一遍遍默念着那两个让他牵挂的人的名字,作为女人,她没枉来到世上一遭,她不管珍珠潭的水是甜是苦,一口口地喝下去。
他与算命先生风尘仆仆来到尖山窑抗日联军住处时,太阳已偏西了。邓铁梅司令亲自迎到大门口,一把拉住他的双手,“我得飞鹤如得赵子龙也,老交通,你辛苦了!”两人哈哈大笑,他这才弄清先生的身份,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轻易地说服了自己,他也跟着嘿嘿笑。邓司令又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遂委任他为连长,说是连长,也就是管四十多人,一个个胡子拉碴,抱条烧火棍般破枪,就是这样,副连长刘虎臣还想争这个连长的位置呢,竟然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向自己发号施令,气得直喘粗气。第二天出操,集合哨子吹了三遍,人还没到齐。半天刘虎臣提溜着裤子跑了过来。“报告小连长,我拉箭杆稀,屁股还没揩就来了。”还使劲挤出一串响屁。哇的一声战士们全笑开了,有咧开大嘴可劲儿笑的;有捂着嘴偷偷儿乐的,他也跟着笑个不停。长这么大,自个儿管自个儿,哪管过这一大帮老爷们?他像一捆秫秸竖在那里,不知干什么是好,昨晚睡觉前温习多少遍的动作、口令全跟着众人的笑声溜了。他真是呆若木鸡了。这时,邓司令远远地向这边走了过来,刘虎臣他们急忙立正站好,他也如梦初醒,下令演习冲锋,从一个山头下来再冲上另一个山头。刘虎臣看得真真的,他飞鹤下了命令自己不动窝儿,瘸子打猎坐子喊,今天老子冲个样子给你看看,等他喘着大气儿爬上山顶时,发现这个小连长笑吟吟地站在那儿多时了,真他妈神了!到了全连从药山开回来时,全都换上了新武器,战士们一个个美滋滋的,胸脯挺得老高,刘虎臣也别上了老毛子的水连珠儿。这个娃娃连长,那是刚刮倒的庄稼,不扶(服)也得扶(服)。
他选好地形,让战士们砍伐树木堵塞道路,就近埋伏起来。老交通送来密信,提茂率一小队鬼子一小队伪军傍晚要经过这条路。他的每个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听得见心脏怦怦直跳。自己初来乍到,寸功未建,便委任为连长,今天又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人家邓司令想得多周到啊!亲自参加战前动员后,还请来吴三妹控诉提茂的罪行,那小丫头片子,讲得绘声绘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许多战士也跟着掉泪,求战欲望像开水壶里的热气腾腾直往上蹿!他似乎听见那许许多多被蹂躏的妇女在呐喊:打死提茂,今天一定要打死他!
太阳卡山的时候,果然有两辆汽车突突着开了回来,遇到堵塞树木,汽车慢了下来。这时刘虎臣瞄准汽车挡风玻璃就是一枪,他顺着刘虎臣的枪眼儿又是一枪,那司机一歪脑袋不动弹了。汽车一横歪,一车人全扣了下来。全连战士一齐开火,第一辆车上果然是提茂带的一个小队,他们还没见过义勇军有这么猛的火力,一下子死伤四五个,“八格,八格!”提茂恼羞成怒,连声怒骂。有两个鬼子架起机枪一顿猛扫,义勇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紧急关头,他蹲下身来,嗖、嗖、嗖,一眨眼工夫绕到鬼子身后,当当两枪,两个机枪手全倒下了。刘虎臣他们又得了把,乒乒乓乓一阵猛打。伪军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的几个鬼子也跟着逃了。提茂没有逃,他的小腿正在流血,只好趴在地上。他爬到机枪手旁边,端起机枪转过身就是一梭子。他意识到遇见了对手,他这一招足以压制住对手。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对手又绕到了他的背后,乒的一枪,他的左手中了一枪,机枪掉在地上。他本能地去摸手枪,乓,右手又挨了一枪,“八格牙鲁!”他暴怒了,眼珠子血红,他不知道对手是谁,让他浑身的本事无法展开。他看清了,是个穿白褂子的娃娃,露出一对小虎牙对着他笑,是那种蔑视的笑,两手各握一支枪,输给了一个娃娃,这不可能!他去摸战刀,但手不听使唤,他努力站得奔儿直,他要保持帝国军人的威严。当,又是一枪,他哆嗦了一下,他感到钻心的疼,他那糟蹋人家的家什儿少了半截儿,他感觉特别明显,眼前这个娃娃在嘲笑他,在戏弄他,他不能倒下,当,当,他知道那豁害人的东西抹根被掐去了,是麻,是木,是疼,他都感觉不到了,他没了底气,他乞求对手痛痛快快给他几枪,但对手就那么轻蔑的笑,过了一会儿,他一头栽倒了。
咣,咣,咣,几声锣响,人们安静下来,刘虎臣带着几个会兵,穿戴整齐耀武扬威地走进刑场,这个刘虎臣,今天还穿了日本人的呢装,你他妈的甘当人家的狗了?
两年前,邓司令和苗可秀相继被日本人杀害,义勇军一下子散了。有的北去通化投了杨靖宇;有的流落关内;有的小股上了山;刘虎臣被俘,投靠了日本人。
咣,咣,咣,又是几声锣响,又押上一个人,三妹,三妹!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刘虎臣,九井,你们这群王八蛋,三妹犯了哪条,一个弱女子,也要处死,你们这群野兽!
打死提茂的第二天,义勇军特地杀了一口猪,摆席庆贺。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邓司令敬酒他能不喝吗?他一个人悄悄溜回住处,正想眯一会,忽然,银铃般声音响起来,“赫连长,我们的大英雄,给我写几个字吧。”他赶忙坐起来,眼前站着一位姑娘,天生丽质,楚楚动人,手中拿个笔记本。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三妹,本来在凤城中学读书,日本人来了,书读不成了,参加了义勇军,在宣传队。”姑娘落落大方,快人快语。她离他这么近,扎实、温暖的香味儿直扑过来,哪像自己一身汗酸味儿,他真怕肮脏了人家,不由得向后躲了躲,但他有些发昏,心里黏糊糊的,如沐春风。她不会是个狐仙女吧?他被她的美色吓破了胆。要提写字,他犯难了,当初干爹教他认字,一遍就会,可就是不爱写,他的心思全在玩打枪上了。他早涨红了脸,稀里糊涂接过本本儿,半天下不了笔。“赫连长,词儿我替你想好了,岳飞是精忠报国,你就写杀敌报国吧。”这杀敌报国四个字,哪个他也安排不圆全。三妹干脆把着他的手写完了字。姑娘的手好细发哟,把在手下,酥酥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动人心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每句话都发着光,带着电。他一时呆了。“赫连长,你一来我就喜欢你,你看那些营连长,一个个胡子拉碴了,抽烟喝酒说粗话,还不讲卫生。连那些绰号也很粗俗,什么盖辽东,老北风,哪有飞鹤文雅啊。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你是根据这句诗起的号吧?”姑娘滔滔不绝,他真长了不少知识。“我哪有那些闲情逸致,胡乱叫的,以后,若能多跟你学学就好了。” “那好,说定了,我教你写字,你教我打枪。”三妹常来教他习字,他可不愿教他打枪,姑娘家家的,打什么枪,那是男人的事。可是他这个连长偏让这个女兵指挥得滴溜溜转。他的行李底下还不时压着几个梨,藏着一把枣儿。那是三妹偷偷留给他的。
端午节的早晨,队伍不出操。他和三妹起大早到老黑顶拔艾蒿。如果在药山,哪儿有细辛,哪儿有人参,他闭上眼睛都可采到。现在,他只好飞开双腿绕山跑。他拔了一大捆艾蒿时,才看见三妹嘟着小嘴儿生气呢。他太粗心了,把三妹扔了,他不会说客气话,不停地搓着手,露出一对虎牙讪讪地笑,“赫连长,人家肚子疼了。”“好好的,怎么肚子疼?”“我们女孩儿,每月都有三四天肚子疼。”天哪,多亏我是个男孩,否则,要耽误多少时间练枪!“赫连长,你把我背回去,就背到沟口,到沟口我就下来,”那小鸟依人的模样,没法儿拒绝,他蹲下身来,三妹那柔软充满弹性的胸脯紧贴在他的后背上,暖絮絮的,让他晕乎乎的,“赫连长,你慢些跑嘛,颠得我肚子更疼了。”他轻抬脚慢落地,三妹趴在他的肩上要睡着了。他往上踮了踮,三妹的头发搭在他的耳朵上,脸也贴在他的脸上了。他在感觉的海洋里美妙地漂流着。他停了下来,闭上了眼睛,真希望能睡上一觉,直到地老天荒。这时,三妹把他贴得更紧了,猛然间他感到心脏发起了疯,他完全醉了。后来,他像火山般爆发了,他放下了她,把她拥在怀里,要吃了似的看着她,那眼神儿一定是块烧红的炭!三妹,你教我的吕字我知道怎样写了。
九井粉墨登场了。慢条斯理地走过来,脸皮是亲切的笑,中国话说的蛮可以。他请飞鹤再考虑一下,自己可以耐心等待。
他仍望着药山,没理会九井。
时值早春,桃花水流,遍地泥泞。刘虎臣领着一队人来到药山,一个个狗乏兔子喘,哪像剿匪来的。刘虎臣连枪都没拿,他最清楚不过,他飞鹤回到药山那像是龙归大海,虎入山林。他知道,飞鹤早把他们的行踪看得真真的,要他的命是小菜一碟。“飞鹤兄弟,下山来吧,九井对我们很好,我们隔几天就能吃一顿粳米饭,不像在义勇军。九井很敬重你,决不亏待你……”嗖,一颗子弹打在他裤裆中间,屁股下的石头迸了一块,险些学那提茂,宝贝被掐了去,当时就尿了裤子。他只好推出那个无赖,这个狗一样的东西,缩在人群中间高喊,“飞鹤,当年你妈跟我,现在吴三妹也跟了我,我就住在于家上沟,”没等喊完,连滚带爬地跑了。他把银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恨不得咬成碎渣儿!两只脚钉子般钉在地上,直到挤出两个坑。一双大手要把枪捏扁,只一会枪柄上全是汗水。他的脑子异常清醒,他突然想起三妹讲的故事,黄雀捕蝉,螳螂在后。他没有追赶。过了几天,他侦知了情况,那个无赖还有个光棍弟弟,两个身边各放一支土枪,三妹就睡在他们中间,他一直没敢动手,刘虎臣他们就埋伏在上院。
到了七月,青纱帐起,杨靖宇得到他的口信儿,十分欢迎他入盟,并派人来接他。走前那天深夜,他潜入无赖室内,将他废了,留条小命。拉起三妹就跑,还是惊动了伪兵们,他们打着火把追赶,他回手一枪打落火把,若在平时,早已无影无踪,如今拉着三妹,速度显然慢了下来。第二个火把亮了,刘虎臣举起枪,他不敢要飞鹤的命,那样的话,九井会要他的命。他瞄准了吴三妹。飞鹤是什么样的?奋力扑向三妹,不幸受伤被俘。
时辰已到,正待行刑,远远一骑飞来,老远就喊,“枪下留人——黄家大当家的稍刻就到。”大当家的要救下三妹,积点阴德,再把三妹许给大胡子,积点儿阳寿。大当家的面子九井哪能不给,他要联络四方乡绅呢。遂有人拉三妹出刑场,三妹把头一甩,坚决不走,向众人高喊,“乡亲们,乡亲们啊,我吴三妹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日本人来了,我才失了学,与赫连长一起并肩抗日。我们不是胡子,更不是马贼,大家伙别以为飞鹤是杀人的强盗,他这个神枪手,除了杀日本人,没一个中国人伤在他的枪口下,这一点刘连长可以作证啊!”众目睽睽之下,刘虎臣不住点头。“赫连长,我们不能同生,但能同死,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只可惜,我们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此时,飞鹤已是涕泪沾巾,一向不善言词,竟也侃侃而讲,“三妹,你讲得好!有你这样的情义,我死也瞑目了。你还年轻,人生还长,大当家的会帮你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吧。以后逢年过节,能在我坟前烧几张纸,也不枉夫妻一场。不要管我,赶快走吧!”“不,不!咱们一起走,到阴间过日子去,活着我没给你留下一男半女,到阴间,我要给你生孩子,生很多孩子!刘队长,你枪杆直溜,送送我们,活儿利索点儿,不要让我们遭罪。”
四周群众,早已一片啜泣,渐渐有人嚷嚷起来。九井没法斯文下去。他原想,这个小姑娘会向他求饶,那时他便笑吟吟地走上前去,给飞鹤松绑,这一永恒的瞬间一登上报纸,那一个个抗联首领,哪个不步飞鹤的后尘?想不到又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他手一挥,人们急忙转过头去。三妹不顾一切地扑向飞鹤,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爹,娘,我们在药山地下相会吧!”
几声枪响,地下留下海棠一样的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一个老者高喊:“飞鹤飞走了!”人们抬头时,天边一片彩霞,有一只白鹤直插天际,正向四花顶飞去,瞬间不见了踪影。
飞鹤飞了,飞鹤飞了!很多人都说看见了,连黄家大当家的也这么说。药山一带老人都这么传说,我年过古稀的堂兄连威动情地跟我说,他让我写下来,于是我实录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