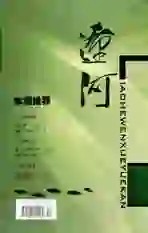二大爷
2009-12-25冯德斌
冯德斌
这下咱可发财了!“胖砣三”兴奋地说。
恐怕这钱也不是好要的。“凹抠脸”皱得像一块抹布,说有钱人吝啬得很,让他出钱如割肉挖祖坟。
“精句鸟”说,咱得找一个能说会道,能降住他的帮我们出头不就得了。
此话一出,立即得到大伙的赞同。大伙说找谁呢,谁能呢?
有人说,嗨,这还用想,二大爷呗!
二大爷就住我对门。说不清从何时起,大伙都管他叫二大爷。也不问老的少的,见面就称二大爷。
发生在二大爷身上许多经典故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二大爷年轻时候当过小队会计。有年冬天,乡里举办小队会计培训班。天气说冷又不是太冷,不冷,大伙又都把双手交互着插在袖窟窿里。那个时候,我们这里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摩托车,更别说小车了。能见到个毛驴车都是件稀罕事。
村子离乡政府有十来里地。一村八九个小队会计,中午,大家聚在一起,凑些份子,下馆子随便吃点,下午继续参加培训,同时也省得来回背路债。
二大爷有点另类,也就是大伙说的,不跟人家共吃一棵葱。他每天早晨从家走时,让妻子给他做两块饼,就是玉米面中间掐些芋干面的那种。妻子用笼布包上,给他放在一个发了色的黄挎包里。中午,别人在馆子吃饭,他则一个人蹲在馆子的一角吃杂面馅饼。起初,大伙看他一个人蹲在那儿,啃着又凉又硬的杂面饼,噎得眼珠子一骨碌一骨碌地往外凸,心里有些不忍,就想叫上他一起吃,但一想到他的家庭并不困难,比他们中许多人过得都要好。如果真是穷得拾不上把,那又另当别论了。这么一想,大伙不仅不觉得他可怜反而可憎,也就不愿再叫他一起吃。
培训班临结束的那天中午,大伙很快吃过了,走过来对二大爷说,桌上还剩点汤,你去就饼趁热喝了,也好暖暖身子。二大爷感激连声说好好。就过去把凉饼掰碎了泡在汤里,一边吭哧吭哧地吃饼,一边吸溜吸溜地喝汤,还不时地用袖子揩不知是被冻出来的,还是被辣出来的清水鼻涕。完了,他意犹未尽地抹抹嘴角,起身想走,店小二把他叫住了,说你还没付钱呢?二大爷说我只喝了点他们吃剩下的汤。小二说那油水都在汤里呢。二大爷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汤他们付过钱了。小二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宴,他们走的时候特地交待说留下你最后一个吃过付账的。
二大爷本来认为是天上掉馅饼,没曾想哎哟一下掉厕所了。呛得一个咕噜一个咕噜地往外打。
二大爷明白了。明白了的二大爷很憋气,很懊恼,也很无奈地,极不情愿地付了钱。
有次妻子从街上买菜回来,二大爷让妻子一笔一笔地报支出。算来算去少一毛钱。二大爷说你好好想想,这一毛钱到底弄哪去了。妻子想啊想,忽然“哦”了一声,说,想起来了,买韭菜时少找了一毛。二大爷说这就对了。你现在就去找那卖韭菜的,把一毛钱要回来。妻子不肯,说不就一毛钱吗,还够这么劳神费心的吗?二大爷不乐意了,说,你讲得轻巧。一毛钱那要多少粒麦子才换来的啊!妻子说那你一碗汤喝了二十块,你怎么就不心疼是多少麦子换来的?二大爷被妻子戳中了软肋,就不再说什么。但又不甘心,最后只好自己跑去,等二大爷雨布汗淋地赶到那儿,卖韭菜的已经走了。二大爷扫兴得如刚被阉过的老牛,虾嗒虾嗒地往回走。
去年,那是一个让人充满畅想的清晨。满天朝霞为碧绿的原野披上一层淡淡的戎装,啁啾的鸟儿歌唱着平安祥和。农人们早早地起来,开始一天的劳作。突然,有早起的村民不经意间发现河里泛起白银银的一片光亮,走近一看,傻眼了。那闪着白光的并非白银,而是大伙辛勤养殖的鱼儿全都肚皮朝天翻死在水面上。
看着满河大大小小肚皮朝上的鱼儿,大伙止不住心痛地落下了泪。只有二大爷没有落泪。有人见他鼻子翕动了两下,便沿河向上游走去。
事情的原因很快查明,是上游的一家企业趁夜色向河里排放污水所致。那家企业的老板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又是乡里招商引资过来的重点保护企业,便不把二大爷他们放在眼里。
不错,水是我排的,你能把我怎么地。有本事到法院告去,我等着!老板态度有点横。
告你?二大爷说,我明白,想通过法律扳倒你,很难!所以我不告你。转而,二大爷不屑地说,我不告你,但我一样会让你乖乖地,一个子不少地给我们送上!
你做梦吧,老板鄙夷地说,你以为你是谁,扁担插裤裆,自抬自高。也不撒泡尿照照,想从我这拿钱,门都没有!
二大爷说,那咱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今天你若不答应,就别想生产!
对,不赔偿就别想生产!大伙齐声喊道。
见此阵势,老板有点心慌,但更多的是恼火。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泥腿子在他的厂里,竟然对他指手画脚,还竟敢让他停产!这是绝无仅有的。他感到自己在职工面前颜面丢尽。这让他不能容忍。
他说,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二大爷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违规排放污水,将我们辛辛苦苦喂养了快一年的鱼全部撂倒,我们找你索赔难道还有错不成?难不成你欠债的还有理了,我讨债的反倒犯法了?
老板气急败坏说道,你这是破坏改革,破坏招商引资,是要负法律责任,是要坐大牢的!
二大爷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至于负什么责任,坐不坐牢,我想你说了也不算。再说,监狱也不是你家开的,想让谁坐谁就坐!
老板眼都红了,你等着。
二大爷说既然来了,我也没打算就这么着离开。
老板愤愤地掏出手机拨通了派出所,喂,是刘所长啊,我是星河灿烂企业老总杨辉。我这里有一帮刁民聚众滋事,导致全厂生产瘫痪,损失不可估量。请火速出警,严惩肇事刁民!
收起电话,老板说有种你别走。二大爷说我是吃粮食长大的,不是被吓大的。
同来的人怕事情闹起来对大伙不利,拽一下二大爷的衣角,算了,咱们还是走吧,别到时候赔偿没弄到反把人给抓进去,那就不值了。二大爷说谁怕谁走,不过到时赔偿钱一分也别想要!大伙迈出的步子又缩了回来,毕竟那钱对他们还是有诱惑力的。不过他们多了一个心眼,就是看似无意地跟二大爷拉开了一段距离,一旦有事好迅速开溜。
二大爷当然也看到了,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一会儿工夫,派出所的警车拉着警笛到了。
老板指着二大爷对那个刘所长说,就是这老家伙带的头。
刘所长手一挥,上去俩警察就要拷二大爷。
大伙都为二大爷捏把汗。
二大爷一边往后退一边说,你们别过来啊!
老板当下心中大快,不无幸灾乐祸地说,上啊,上啊,后退干啥,刚才你不是最能的吗,现在怎么装起孬种来了。说着放声大笑。可笑声还没结束,他傻眼了。
只见转眼间,警察已来到跟前,伸手去拷二大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二大爷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可把攥的酱色玻璃瓶高高举起。一警察眼尖嘴快,炸弹,快躲开!
一瞬间,人们仿佛闻到了刺鼻的火药味,听到了嗞嗞作响的火苗声,看到了渐趋浓密的硝烟。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像绷紧了的橡皮筋,一触即断。
二大爷想去拧瓶盖。
所长惊慌失措地喊道,别拧!有话好说!
二大爷说只要老板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就不拧。
这时,所长才想起自己还没有了解这些人到底为什么闹事。
他回转身去问老板,却早没了老板的踪影。原来,老板正幸灾乐祸放声狂笑时,突然听说有炸弹,当时就哑了。等回过神来,吓得屁股一拍,溜了。
所长有点不悦,说这王八羔子,真不够意思。于是差人把他找来,问明了事情的原委。
所长发话了,这就难怪人家了。你排污药鱼,先错在前,我看你还是先答应给他们赔偿,这事也就自然平息了。怎么样,老板,你看我这意见行吗?
老板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但嘴上还不敢说,不过他又不甘心。于是小声嘀咕道,我要是想赔,还叫你们来干什么,一群窝囊废。所长说,什么费不费的?老板怕所长不高兴,忙解释,我是说都是我不对。所长说,既然知道不对,还不抓紧给人家赔偿?老板说我这就赔,这就赔。
二大爷心里格外高兴。像你那高兴就放在心里不就完事了,偏要往脸上摆,而且还得意忘形的,显得没有度量。这就怪不得所长了,因为所长和老板说完回过头来想和二大爷说的,见二大爷这副德性,不免生气。你也不要太得意,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身携炸药,危害公共安全。要不是我们及时制止,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命丧你手!还不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二大爷说好,我坦白。伸手一拉瓶盖,一股浓烈的药味笼罩在工厂的上空。直呛得老板一个劲地打喷嚏。
所长赶紧用手去捂鼻子,想挡住那股刺鼻、呛人的怪味渗入。但终究没能挡住。嗓子里犹如吃入一只苍蝇,不上不下的,想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他的脸憋得像秋天的高粱。全身像被麦芒刺的一样疙疙燎燎的。
所长有种被耍弄的感觉,他很恼火。有心要修理二大爷一下,但见二大爷身后站着一大帮人,像一堵铜墙铁壁。这些农民,别看平时像一盘散沙。甚至于常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互相吵闹、打斗。但当他们中的一人抑或他们的共同利益遭到外来的侵害时,他们不需要任何人召唤,就会抱成一团,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
所长知道,这个时候修理二大爷,势必造成混乱不堪和难以收拾的结局。他狠狠地瞪了二大爷一眼,你别太得意。等哪天一旦落入我的手里,有你好看的!不过所长只是在心里这样想的,嘴上没有说。
但所长走时,还是说了一句,神经病!才掉头上车。
原来二大爷是想用喝农药来要挟老板以达到赔偿的目的。
老板无奈地摇摇头,让财务科赶紧赔钱走人。
我们村的二牛,早些年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走投无路之下,外出谋生,不想这倒成就了他的富翁梦。
受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二牛决定回到家乡办厂创业。乡里村里的干部一听说二牛要回乡办厂创业,那乡长、村长乐得抬头纹就像开锅的水,一圈一圈地向四面八方绽放开来。那几天,乡里的小车带着,好酒好菜招待着,好言好语笑脸相陪着。终于选定村东的那块地作为二牛的公司的厂址。
大伙听说这事之后,连夜在那些土地上栽上了“速生树”,盖上了“速生房”。这可是一笔数目不菲的赔偿款啊!这笔赔偿款大伙能不能拿到,拿到多少,这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头人为大伙说话撑腰,不然大伙辛苦搞起来的“速生树”、“速生房”那岂不就白搭了?
由于二大爷有着多次不俗的表现,大伙自然就想到了他。
尤其是二大爷被占的那块地,不仅被他的儿子栽上了“速生树”,还建上了“速生房”。他被占的地最多也最好。二大爷一直视那块为宝地。有人曾以三亩兑一亩想换取二大爷的这块地,他都没答应。现在有人要在上面投资办厂,二大爷岂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不乘机狠狠地捋他一把。除非他傻,何况他又不傻呢。
二大爷听了大伙的意图,蹙了蹙眉,你们真的让我领头?
大伙说那还有假,这事二大爷不领谁领,别人也没那资格啊!
那你们愿意听我的?
大伙说那当然。
你们不后悔?
大伙说不后悔。
二大爷的脸渐渐地严肃起来,他左臂环抱于胸,右手在下颌处轻轻抚动。大伙知道这是二大爷每次做出重大决定前的先兆。一般做大事的人都有自己特立独行的行事方式。就像有人遇事爱闷头抽烟,有人爱踱来踱去走个不停。二大爷跟他们不同,他是抱胸抚颌立在那儿不动。那次渔场索赔,二大爷就是现在这种姿态和神色。他们仿佛看到二大爷已从二牛手里接过成捆成捆崭新的钞票,正大把大把地往他们手里发,所有的人都心花怒放,笑逐颜开。
约莫过有半袋烟的工夫,二大爷说,大伙还记得吧,去年,在南方打工的二窝头在工地从十三层楼上摔下来,当场断气。他媳妇疼不过,疯了,至今不知去向。剩下婆婆守着三岁的孙子艰难度日。杏花外出打工,经不住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不到一年就回来和椿树离婚。牯牛小两口出去打工,把两个孩子丢给外公外婆照顾。老人眼神不对,小孩掉进门前的水塘里竟没有察觉……说到这,二大爷神色黯然,语气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村里能走的都走了,留下老的老小的小守着这一亩三分地,真是吃肉也不香啦。听了二大爷的话,大伙也不无伤感。
二大爷轻咳了两声,土地包产到户三十年了,大伙的日子已今非昔比。可我们跟城里相比毕竟还不发达,甚至还很落后。
大伙点头说就是。还假意地说,要不,我们也就不要这赔偿了,都乡里乡亲的,谁好意思伸手要那钱呢。
二大爷好像一点表情都没有,依旧往下说,我弄不懂什么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也搞不明白什么经济发展规律。但我想,如果村里再多几个像二牛这样的工厂,大伙也就不用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地讨生活了。
二大爷停下话头,摸出烟锅,有人给他递过一支香烟。二大爷说吃那家伙没劲。便有人给他上了火。
二大爷深深吸上一口,咂咂嘴,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更不是要摆什么高姿态。我只知道做人要讲个信义。二牛从小没了爹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些年在外打拼赚了一些钱,但也吃了不少苦头。为了回报乡亲,先后给我们铺了路,盖了学校。人家是一分钱的回报也没向咱们要啊。
有人说是啊是啊。有人就拿眼挖那人,你什么意思,你想充好人,做顺水人情,这钱你给啊。其实这人嘴上没把这些话说出来,但那人就不说了。
二大爷又吸了一口烟,不错,生活是离不开钱,有钱当然好。可钱也不是万能的。世界再变咱庄稼人的善良醇厚的本色不能丢。现在二牛回乡办厂创业,说到底是为了解决村里剩余劳力就业,让咱们不出村就能像城里人一样上班、生活。就能共享天伦,不需再为谋生而受分离之痛。再说了,二牛也按政策给我们作了赔偿。
有人情不自禁地说,二牛心地善良、厚道,是个好人。
二大爷说,好人就该有好报。二牛是为咱大伙着想。占咱点土地,咱能好意思向他要额外的赔偿吗?
大伙没有说话,但心里却嘀咕开了,二大爷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二牛对大伙不薄,怎么好意思向他张嘴要这钱呢。
话题一开,大伙就想起二牛的好来,想起二牛的好来就不免心有些酸。可好归好,这和赔偿是两码事。那可是一笔数目不菲的钱啊,够盖一栋两上两下的小洋楼。种一辈子的地恐怕也攒不到那么多呢。可若是拿了这钱又总觉得心里疙疙瘩瘩地不自在。庄稼人虽然生活质量不如城里人,但有自己的活法。活的就是图个自在。一个人活在世上纵然衣食无忧,富如金山。如果活的得整天窝心,那还有啥意思。
现在这钱反倒成了烫手山芋,要还是不要?大伙一时半会难以决断,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了二大爷的脸上,希望从二大爷的脸上找出答案。
二大爷将烟锅里最后一口烟吸完,躬身在鞋帮上将烟灰磕去,把烟袋往腰上一别。走进厨房拿出一只碗和一个茶杯放在桌上,又将一包黄豆放在桌旁。大伙不解。二大爷抓起一把黄豆说,这钱要还是不要,由大伙自己决定。不过我有一个提议,如果要,你就从袋中抓上一粒黄豆放在茶杯里。如果不要,就放一粒在碗里。说完二大爷将手中的一粒黄豆放进碗里。
那粒黄豆在碗里,像一个优美的音符,欢快地舞蹈着。又仿佛在呼唤着同伴,来呀,快来呀!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建设美好的新农村!
大伙互相看了看,也学二大爷的样子,走到桌边,抓起黄豆向碗里丢去,流畅出一首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