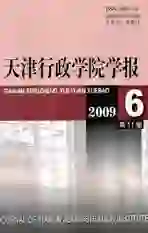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 经济资源建设的思想与现实启示
2009-12-15蒯正明
蒯正明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思想是:“剥夺”剥夺者是经济资源建设的基础;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是经济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济资源建设的制度保障;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经济资源建设的终极目标;注重分配问题是经济资源建设的重要方面。其启示主要是:坚持党经济资源建设的重心地位不动摇;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注重党经济资源建设的平衡性。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经济;资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6-0022-07
对执政党而言,凡是在经济领域内部对政党执政具有支持性的实体型要素和制度型要素都属于经济资源。实体型要素主要是指执政党执政期间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包括宏观国民收入的增长或衰退和微观经济的公民个人的收入状况,如GDP、人均GDP,等等。制度型要素主要是执政党执政主导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政策及其相关社会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济资源还包括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从执政资源的系统看,作为目的型资源的合法性资源是执政资源系统中各资源要素“合力”的结果。但在执政资源系统内,经济资源对合法性资源获取、执政地位存续的贡献要优于其他资源内容。经济资源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作用体现得快捷并且直观,它不需要意识形态资源的原始认同感,也不同于组织资源的复杂构成。因此,执政党经济资源的储量状况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
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行经济资源建设的具体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包含这些思想,也不意味着这些思想不值得珍视和认真发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设想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经济资源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今天研究这些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思想既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也源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纵观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多部著作中都阐述了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思想。
(一)“剥夺”剥夺者是经济资源建设的基础
马克思思格斯依据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实质,他们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并指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1)劳动产品和工人相异化;(2)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3)人和人类本质相异化;(4)人和人的关系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是一种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尤其造成了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因此,要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没有私有制、没有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p120)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2](p293)这段话集中表明:(1)无产阶级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使资本及其运作不再作为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力量,真正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素;(2)无产阶级的国家要掌握运作生产资料的全部生产工具,即建立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2](p283)因此,“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p285)“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2](p30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是真正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阶级,因此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国家政权集中在无产阶级阶级手中,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是经济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思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p86)在之后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也指出:“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2](p238)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移居伦敦以后,把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工业发展的“典型地点”,从而更加深刻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例如,在50年代初期,马克思说,大不列颠的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3](p134)。“英国工业创造了现代工业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实现了他们解放的第一个条件。”[3](p134)后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以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被扬弃的前提,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10](p45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并发展起来的,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它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在客观上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前提。
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特别是过渡时期,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远达不到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5](p314)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实现并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生产力将会高度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得到充分涌流,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将会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分析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科学地说明了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在完成过渡阶段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6](p135),进而为无产阶级政党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提供物质支持。
(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济资源建设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思格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要求出发,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唯物主义原理,提出未来无产阶级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制度保障,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历史上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277)然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表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2](p278)“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p277)另外,“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p286)。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揭示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原始积累剥夺小生产而得以确立后,又通过资本的积累而获得迅速发展,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又加剧了资本集中的过程。少数资本家通过剥夺多数资本家,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资本巨头的手中,这就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然而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集中,生产资料却日益掌握在数量不断减少的资本巨头手中,他们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在竞争的压力下竭力扩大再生产,但又使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相对过剩人口的规律使工人更加附属于资本,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这样势必会造成劳动人民购买力的衰退,从而引发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7](pp831832)因此,要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就必须在事实上承认社会化生产的“本性”,也就是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社会化生产资料、产品及其管理生产的权力,转变为归全社会占有和管理。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从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出发,从解决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产品被资产阶级占有的意义上,提出未来新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实质或方向,即公有制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可以改变广大人民受剥削的状况,同时也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5](p754)因此,“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7](p754)。“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5](p757)
(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经济资源建设的终极目标
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思格斯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即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经过三大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4](p104)。
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为个人从属于原始共同体;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为对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在这一阶段,由于人的能力还相当软弱,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依靠人群、氏族或其他社会组织来战胜自然。这样,个人不可避免地成了群体的附属物,只能依靠族群获得力量。在这一时期,个人被束缚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自由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部分人有条件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时,社会出现阶级与阶级对抗,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人的依赖关系。
第二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主要发生在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摆脱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人可以利用和开发自然以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生产力也由此得到极大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摆脱了束缚的人们取得了自由独立的人格,建立了平等的关系,“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5](pp746747)。但是,这种平等尤其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表现为进入劳动市场的无产者有权自主选择职业或是否出卖劳动力。但在存在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前提下,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出卖劳动的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被迫接受劳动的义务。所谓人身自由实际上是被迫出卖其劳动力的自由,而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8]。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相对过剩人口的规律使工人更加附属于资本。
第三阶段,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自由和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空前发达,从而为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物质条件。在这一时期,“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pp757758)。
(五)注重分配问题是经济资源建设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是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现实提出来的,也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平的现实进行科学反思的结果。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二分性和二元性,即资产阶级的“有产性”和无产阶级的“无产性”,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日益对立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控诉的那样:“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为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1](p93)
马克思在揭示资产阶级分配不公的同时,也阐述自己关于分配的思想,这集中体现在1875年他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所谓“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的观点,阐发了他的按劳分配思想,马克思表明了他在公平效率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以劳动为尺度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每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上领取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多少劳动,而凭着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备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由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和从社会取得个人消费品,劳动者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按劳分配是历史上分配方式的重大进步和伟大变革,它终结了人与人之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马克思也同时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5](p304)“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5](p305)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上,人与人之间在劳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还仍然存在着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p305)这种弊病,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了按需分配才能消除。由此就决定了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不可能在事实上享有如拉萨尔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平等的权利”,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事实上实行“公平的分配”。
由此马克思认为,为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无论自身条件如何都有同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社会产品就不应当不折不扣分配用于个人的消费,在消费品分配给个人之前,必须从总产品中做以下六项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第四,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五,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第六,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社会总产品在做了这六项扣除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用来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数额。其中,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就是国民收入所含剩余价值中用于社会救济的部分。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每个社会成员无论自身条件如何,都有同等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利的思想,认为每一个劳动者都有享受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带来福利的平等权利,对于那些遇到不幸事故、自然灾害以及由于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社会必须给予关注并设立专门基金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利。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经济资源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建设理论是今天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指南。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经济资源的储量状况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今天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经济资源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坚持党经济资源建设的重心地位不动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本身应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经济资源极为匮乏的现状,本应将执政资源开发的重点放在经济资源的开发上,但由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时还没有完全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没有较好的把握,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党却将执政资源开发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上。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目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从而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行转移的战略部署。但是,由于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国内出现极少数右派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由于主观上对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党开始越来越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虽然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对提升党执政合法性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结果不仅没有把人民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也使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受到很大的损害。“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上,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就必定要求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改造、斗私批修、灵魂革命,来形成一种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价值,使人超然于世俗物欲之外,不为衣、食、住、行所拘。很显然,毛泽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客观实际,走向了空想和错误。”[9](p12)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过分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政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建设,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思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我们必须将党执政资源开发重点放在经济资源的开发上,只有这样党的执政资源才能得以不断拓展,执政地位也才能得到有效的巩固。
(二)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资源建设与西方政党经济资源建设的本质区别。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进行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丰富党经济资源的储量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能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经济资源建设也必然会迷失方向,从而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等于公有制的形式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而是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过早地建立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生产关系,使党的经济资源建设受到挫折。过分“追求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而不了解社会主义只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并不要求经济基础的唯一性”[10](p159)。“这一理论的逻辑是:变革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地会引起敌对阶级和党内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人的反对和抵触。为了在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强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用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一理论的出发点虽然是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它没有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6](p135)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因此,我们既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公有制的优越性,更不能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盲目地追求扩大公有制的范围和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条件下的历史选择。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用以指导整个执政活动的根本原则,直接反映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奋斗方向和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党的经济资源开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但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部分领导人的错误举措,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发生了偏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导致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航船偏离了正确轨道,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文革”期间,由于执政理念的偏差,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职工年平均工资由于高积累而难以提高,相反却由1965年的625元下降到1976年的605元,降低7.5%,实际工资的下降更大。10年间,只有1971年调整过一次,低收入职工的工资,调整面仅为28%。而农民的平均收入,在10年间也基本上没有增加,相当一部分贫困低产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10](p382)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党一次深刻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深刻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看人民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答不答应。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了“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中心任务,对党的执政理念作了高度的概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求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既是对党执政理念的总要求,同时也是对党经济资源建设的要求。
(四)注重党经济资源建设的平衡性
马克思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实质上就是注重经济资源建设的平衡问题。经济资源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资源的总体储量,同时还要关注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即我们不仅有一个把蛋糕给做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切分蛋糕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针对计划体制造成效率低下、资源分配扭曲、平均主义倾向的严重积弊,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旨在刺激生产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故把效率放在主要位置。但同时我们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在“效率优先”的理念主导下,公平虽然在表面形式上被“兼顾”,而实际生活中却被漠视,从而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一是城乡机会不均等。“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出口企业普遍出现开工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农民工提前返乡,劳务收入减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11]二是地区发展不均衡。根据上海、甘肃两省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690元,为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10元的2.4倍;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00元,为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2680元的4.3倍。三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比如,“2004年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平均收入水平是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平均收入水平是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12]。这种经济资源开发不平衡的结果是人民不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消解了底层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感,影响了经济资源开发利用的质量,也直接导致绩效合法性产出的迟缓和停顿。由此可见,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注重资源总量的增长,也要注重质量的提高,注重经济资源开发的平衡性,惟有如此,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豹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豹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豹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豹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唐龙.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解放[J].江汉论坛,2006,(7).
[9]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庞松.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11]郭晋晖.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破万元[N].第一财经日报,20090116.
[12]王河.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利益均衡机制[J].宁夏社会科学,2009,(7).
[责任编辑:岳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