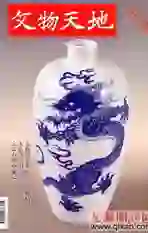上博赴伦敦展出的青铜器
2009-10-26李柏华
李柏华
今年1月底,上海博物馆为配合上海市政府在伦敦举行的“上海周”活动,在大英博物馆成功地举办了《上海博物馆赴伦敦青铜、玉器展》,展期约两个月,共展出60件展品。其中青铜器展品有41件,为本次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一大门类,青铜兵器、礼器和乐器以及青铜器的铭文、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等研究已经使青铜器研究成为一门多课题的综台性学科。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凸显出青铜器作为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应占的崇高地位。通过这一展监,使英国观众充分享受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雅、宁静,感悟到了古代礼仪所表达出的秩序、文化属性和对后世的影响,领略到了青铜器这一中国古代瑰丽艺术的感染力、历史穿透力和文化震撼力。本文选展览中的青铜器精品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爵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管流爵的原型和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一样,都有取型于陶爵的特点。爵作为酒器是注酒和酌酒的酒具,而不是饮酒器。乳钉纹管流爵,1959年从上海冶炼厂即将熔化的废铜中抢救而来,残高20.6厘米,口长16.3厘米,重0.86千克,属夏代晚期。形制为扁圆形,敞口,两侧呈尖瓣状,前端略高,在腹下部设一斜置的管形流,流上有两个方折形饰物。颈上饰弦纹三道,间饰或疏或密的乳钉纹二道,下为一圈较宽且有圆孔的假腹。三足残缺。现有的假足系根据陶爵复原(图一)。
犟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在祭祀礼仪中,翠是盛酒器。此连珠纹辈为20世纪50年代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所得,高27.2厘米,口径17厘米,重1.53千克,属夏代晚期。敝口,长颈,鼓腹,平底连铸空锥足,其形制是为圆体。这种器形器壁较薄,口沿易损,所以早期肇的口沿会加上厚厚的边,在口沿上通常设一对柱,颈腹间有一较大的錾。在聋颈部弦纹中,有不规则小乳钉纹。犟的三个锥足与腹部相通,从口部下视,可见内底有三个三角形的空洞与足相连(图二)。
鼎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青铜礼器,为祭祀时被用来盛放肉食的容器。在中国古代,祭祀是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整个青铜时代,鼎作为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物,一直被使用,直到铁器时代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鼎的使用仍然非常普遍。这件云纹鼎,高18.5厘米,口径16.1厘米,重0.71千克,属夏代晚期。口沿外折,沿边似有二层,上立两个小环耳,器似罐形、为深腹。下连三个空形圆锥足与腹底相通,这是由于当时的合范技巧不够成熟,尚未达到范芯全封闭的铸造技术的缘故。鼎的腹上部饰有一圈用凸起的线条勾勒的云纹来作装饰,显示出其古拙的艺术风格(图三)。
在青铜酒器中,爵、角,霉等器物有錾,卣、壶等有提梁,觚是没有附饰物的。此斜角雷纹杯造型较为特殊,与觚形体相近。因其设錾。所以称之为杯。高13.5厘米,口径12.6厘米,重0.75千克。侈口,束腰,腹连圈足,自口沿至中腹设牛首錾,錾下有垂珥,其下部与腹壁相接,与圈足持平,造型特殊。口沿饰一周斜角雷纹,圈足饰连珠纹两周。杯的形制和纹饰均属于商代晚期(图四)。
青铜卑发展到商代中期,器形已趋成熟。此兽面纹晕,形体较大,高31.1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5千克。敞口,高颈,器壁较薄,器口不是很厚。双柱很高。已经体现出装饰的特点,柱顶似伞盖形。商代中期的霉,通常以圆腹平底者居多,此卑颈腹分段。呈袋腹式,即像鬲一样的袋状腹部,三个袋状腹部下接空心锥足。颈、腹部都装饰了兽面纹,颈部腹间有一较大的弧形錾,属商代中期。从器的造型和纹饰看,此墨在设计上已充分考虑了美化和实用相融合的思想。(图五)
壶是盛酒器,但是小型的壶也可作饮酒器。由考古资料得知壶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但其沿用时间较长,直到汉代壶仍是常见的青铜器之一。壶的形制较多。此壶高33.4厘米,口横15.3厘米,口纵11.7厘米,重5.27千克,属商代晚期。口稍侈,器呈椭圆形,深腹下垂,置低圈足,颈部的两侧设有贯耳,并装饰兽面纹。颈部的兽面纹为倒置的形式,双角自额侧向内卷曲,角侧又衍生出一卷尾的装饰条纹,双目较大,眼角下垂,间饰鼻准线,口阔,两侧配置太目及钩曲身躯的物象。腹部正饰的兽面纹,与颈部的兽面纹相类似,上、下相对,一正一倒,装饰手法别致。因壶内底铸有一个“先”字而得名“先壶”。“先”,应是族氏徽记。(图六) 县为大型的盛酒器,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其形式有方形和圆形二种。亚寞方晷器形为长方形,高53厘米,腹横36.7厘米,腹纵35厘米,重29.68千克,属商晚期。直颈。宽肩、腹鼓、向下逐步斜收,圈足外侈。肩两侧设置一兽首耳,下腹设一兽首耳鼻。器的各部分都饰有繁密精丽的纹饰,头及圈足各饰对称的鸟纹,肩部中央用高浮雕设具羊角的兽,两侧配置曲折角龙纹。腹部的主纹是内卷角兽面纹,上栏的弯角勾喙鸟纹与之相配,腹部的下栏是外卷角兽面纹,圈足上的兽面纹与此相配置。这三种角型不同的物象是商代兽面纹的主要组合纹样,尤其是主纹的角是有一目的兽体,显得更加怪异。整个纹饰表现为多层次的浮雕,并有细密的雷纹作地纹,兽面纹多种角型集于一器,这是殷墟时期青铜器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器的四隅及每一壁面的中间都设棱脊,使器更加雄健瑰丽。纹饰雕刻手法凌厉,有极强的神秘感。口沿内铸铭文两行四字。是为作器者的国名和氏称。方形罄传世较少,此器历见著录。(图七)
此兽面纹鼎高20.2厘米,口径16厘米,重2.26千克,属商代晚期。直口方唇,上立两耳,深腹圜底,短柱足,形态稳重。口沿下装饰有环柱角的龙纹一周,两两相对,头部较大,而体躯短小。腹部饰内卷角兽面纹,体躯向两侧展开,两爪分张不作通常的对拱式,这是商代中期兽面纹特征的孑遗,兽面纹鼻准的隔棱不到下栏底部,这是殷墟早期兽面纹构图的特点之一。纹饰均以细雷纹为地。整体纹饰除双目突起外,其余部分皆为平雕,然而主纹与地纹区分得相当清晰。这类鼎立耳较小且薄,和一般商代晚期鼎耳粗壮并相当发达有明显区别,就这件鼎的形制和纹饰而言,在殷墟出土众多的青铜鼎中也是难得。(图八)
卣因为有提梁可以提拿,所以又被称为提粱卣,卣是盛酒器。此凤纹卣高27.6厘米,口横10.8厘米,重4.89千克,属西周早期。扁圆形,直口,高盖,盖顶为六翼蝉纹组成,盖沿两侧挑出器外,鼓腹下垂,高圈足。提梁纵向。两端设龙首,龙角作多齿状,中有一目纹,非常奇异,提梁饰回首连体龙纹。盖面、盖沿,器头、腹部圈足均设不同形式的凤纹和鸟纹。盖沿及器腹饰对称的大风纹,风载有目纹的三齿形两钩的壮角,短头大翼,长尾下垂处又饰一尖角小鸟。盖面、器头和圈足的纹饰大致相同,均饰弯角长卷尾鸟,空间
饰雷纹,纹饰很精细,一丝不苟。自盖至圈足均匀地安置四条厚实的棱脊。这种卣的形式商末周初皆有,但腹部突出的粗大棱脊,则仅见于周初个别的青铜器。(图九)
觥是盛酒器,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马承源先生认为觥的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风纹牺觥高12.7厘米,长19.5厘米,重0.95千克,20世纪50年代拣选自上海冶炼厂,属商代晚期。器似一头牛犊。前端有短流,口后部扩大与盖吻台,器后部垂短尾,腹下有四个壮实的蹄足,足后部均有突起并列的小趾,趾下设两小孔,腹下设四个成二列的小乳突。流的上部装饰龙纹,两龙相对竖立卷尾,下部设虎耳兽面纹,中间有一条突起的棱脊。器后端为外卷的兽面纹。腹部主体饰长冠凤纹,整个风纹因受地位限制而呈横长形,风有闭合的钩喙,目正圆,头上有一条华丽的长冠,尖端向内卷曲,布于凤的背郝,长尾上卷,爪贴于牺觥的足上,凤的形象很优美,全部纹饰均以雷纹为地。盖是根据湖南衡阳色家召子出土的牺觥所复制。(图十)
与此件凤纹牺觥相同的另一件展品为西周早期的黉引觥,此器高25.4厘米,有斗,斗长21.7厘米。器体呈椭圆形,此觥的盖子似一个变异的兽头,有鼻、眼,并有一对向上翘起圆角,圆角边附有一对伸出的长耳,此种形式在周初相当流行。器尾设錾,用于倾倒时握持。整器仅有几道弦纹作为装饰,与商代晚期繁密华丽的纹饰完全不同,给人以清新静穆的感觉。器附斗,可放置于腹中,用以挹酒。器盖、器体及斗皆铸铭文,其中“赉”引是作器者的人名。传世尚有一觚与此同名。(图十一)
展品中有一件兽首辕饰较为特殊,其造型艺术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辕饰是辕前端的套饰,它的前后有不同的雕刻,正面上为虎首,虎耳竖起,大鼻,阔口咧噬一人首级,人粗眉大眼,鼻正,嘴微启。这种虎食人的图案,在司母戊太方鼎的鼎耳上和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钺上,以及虎食人造型的卣等,都有此种图案的表现。这种辕饰虎食人之像,应与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有关。商周时期贵族出行的坐车,都为木质,为了装饰或牢固,往往会在一些部位配以铜制的装饰,此件兽首辕饰正是其典型的代表。(图十二)
在这次展览中,青铜兵器只有两件,为神兽纹钺和銎钺,时间都为西周早期。钺是具有权杖一类性质的兵器,神兽纹钺长24厘米,为圆弧形片状,中有大穿孔。侧面銎上饰一怪兽,头发后披,兽目睁开,头部二侧各有一耳,鼻似象鼻状,前伸至刀刃口然后向下卷曲。(图十三)
銎钺长13.4厘米,宽刃弧曲,向后作云头状,援部设两圆孔。其管状的銎上设有两个小方孔,为插销固柯用,此为銎内式钺,相当少见。此类形式有学者认为是北方民族之器。从以上二件钺的形制就可以明显看出其风格有显著的不同。(图十四)(32号展品)
盈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盈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流行于西周晚期。此次展出的晋侯辄盈的时间属西周晚期。高约22.2厘米,器形呈椭圆形,有盖,顶设四个扁形的环钮,钮上饰简单的龙纹。器敛口鼓腹,腹的二侧附耳,四足为蹲式的小人。小人二臂上举托住盈的底部,人面向外侧,眼突,阔嘴,整个头部明显有头大人小的感觉。缀的盖顶饰长鼻龙纹,盖缘和器口饰鳞纹一周,其余部分饰沟纹。器盖刻有三行二十四字铭文,记晋侯作此盈。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出土,流散香港,收购回归。(图十五)
虎簋是春秋早期展品,高34.7厘米,腹径23.3厘米,重12.28千克。簋也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在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台与以奇数组台的列鼎配合使用。此器高盖,顶作莲瓣形抓手,器侈口,鼓腹,圈足下连铸方座,两侧设有龙首耳,下有垂耳。盖面腹部及方座都装饰有流转的波曲纹,口沿及圈足饰都饰变形的兽纹。器盖同铭,均为一象形的虎,应是器主的氏族徽记或名号。传此器原出陕西凤翔县。(图十六)
垂鳞纹瓿,高24.8厘米口径15.5厘米,腹径30厘米,重10千克,属西周晚期。此器直口,柬颈,鼓腹,圈足。整体满饰重叠式垂鳞纹,圈足为粗实的绳纹。整个器物、造型简洁、朴实,在视觉上有厚重感。(图十七)
小克鼎的时代为西周中期,其高56.5厘米,口径49厘米,重47.88千克。清光绪年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窖藏,与太克鼎同时出土。传世小克鼎共有七具,除上海博物馆的一件外,其余分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等收藏。而此器为最太,大小成序列,体现了西周的用鼎制度。
小克鼎口部微敛,方唇宽沿,腹部略鼓,底近平,下置蹄足,器壁厚实,形制雄伟。口沿下所饰的变形兽面纹,腹部是宽大的波曲纹。腹内壁铸铭文八行七十二字,记载孝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命膳夫克去执行整顿成周八师的命令。就在当年,膳夫克铸此鼎,以祭祀祖先,乞求康乐,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图十八)
四虎镩为青铜乐器,其时代为西周晚期,高42厘米,舞横17.9厘米,于横26.4厘米,重11.96千克。镩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磬相和使用的乐器。镩为平口,上设钮,器为圆弧形。两侧各饰头向下、尾朝上的二虎。击之能发出短促的单音。镩如大钟,是用以指挥乐队的节奏性乐器。(图十九)
卷龙纹鬲为西周晚期(图录第37号展品),高16.9厘米,口径24.5厘米,重2.49千克。鬲是炊粥器,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陶鬲。其形为太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到了商代晚期的青铜鬲是为盛粥器。至西周中期青铜鬲很盛行。卷龙纹鬲敞口、外侈,口下束颈,并成三个圆状形、组成深腹。腹部圆状处饰对称的龙纹。此器的形制比较少见。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的青铜鬲的下部与此鬲相似。(图二十)
镶嵌鸟兽纹壶属春秋晚期,高55.3厘米,口径16.4厘米,腹径35.6厘米,重6.7千克。直口外侈,长颈宽肩,鼓腹较深,下部收敛,圈足较长。肩两侧饰设兽面衔环为耳,通体施以用红铜镶嵌的长冠凤、独角兽和鹿纹等。整体纹饰分为横七道、竖八道,每个界栏都有一两只鸟或兽纹。整个器体的纹饰以红铜镶嵌,使之产生更好的视觉效果。在青铜器上用镶嵌红铜的方式来装饰纹饰,是春秋晚期的新工艺,它使青铜器更具观赏价值。(图二十一)
镶嵌几何纹方壶为战国晚期的展品,高52.4厘米,口边长12.1厘米,腹边长25.4厘米,重10千克。此种方壶的式样出现于战国,并为战国时期所流行。此器口略侈、圆肩、长颈、鼓腹而斜收,下为方圈足。肩的两侧饰兽面环耳,圈足装饰对称式的钩连云纹。整器以绿松石和银丝镶嵌,且镶嵌物保存完好,极为难得。壶为盛酒之壶,属于酒器,以上二壶,一圆一方,在视觉上形成对比,展出效果极佳。(图二十二)
四虎蟠龙纹豆为春秋晚期,高26.4厘米,口径18.6厘米,重2.38千克。豆是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具,也可用作盛放黍、稷类的饭食。豆也是礼器的一种,常以偶数组合使用。青铜豆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敛口有盖,顶有圆形抓手,下为圆柱形高柄,最下端为盘形圈足。腹外壁四面各有一个衔沿攀壁的猛虎,虎首略超器口,尾部上卷,形象生动。是为很好的装饰。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图二十三) 翼兽益属战国晚期,高26.8厘米,长29.5厘米,重3.77千克。蟊是盛玄酒(即水)以调和酒味浓淡的。它与酒器组合,用水以调和酒。它与盘相结合,则可作为水器。此益为鸟首、兽身、兽爪、鸟尾,器体上饰兽翼纹,上有半圆形提梁,提梁前端上部饰有虎头,提梁两头用四足连器体,中间以环连盖。此器以鸟首为流口,额顶有羽毛片,双目、目眶及颈部是用线条的金银片镶嵌而成。此器倒水时可以自动开合,可见其工艺极为巧妙。1998年自法国巴黎征集。(图二十四)
镶嵌几何纹敦,高25.4厘米,腹径18.8厘米,重4.12千克。敦是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秦代以后消失。此件敦的形制上下对称,器、盖均为半球体,器、盖可分置,各有相同的三足二耳。此敦盖、器口部都镶嵌对称的三角形纹饰,整个器体正反相交,加之用红铜镶嵌几何纹,绿松石镶嵌出卷云纹。使整体效果具对比感。使整件器物更加精美、典雅。(图二十五)(52号展品)
(本文得到陈佩芬先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