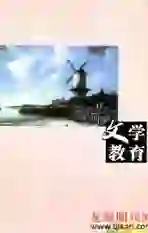读丁燕和沈蕾娟的诗
2009-09-24陈仲义
“原点”:在“物与词”中生长
——读丁燕的“葡萄”
丁燕,70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后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出版诗集《葡萄的帝国》和长篇小说《木兰》等。现居乌鲁木齐自由写作。
春节临近,丁燕从新疆寄来新年礼物《葡萄的帝国》,整整100串葡萄。紫红的、圆润的,在霜后的阳光下,汁液饱满,斑斓中带一点沧桑。
100串葡萄,高密度的、多角度的折射出作者个人的情感史、生活史。它是作者乡愁的居所、信念的载体、也是价值的支点。一块块多棱镜片,闪耀着人格的聚焦。举凡灵魂的狂热、颤抖、疼痛,日常生活的怜悯或悲哀,都有意无意融入葡萄的汁液肉瓤,带上葡萄的“情结”,乃至葡萄的“病根”,从而形成个人史的“原型”意象。
庞德有句名言:“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关于意象主义》)丁燕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秉承这话,葡萄真够她吃一生的了。
葡萄的鲜润多汁,找到她生命在青春期的勃发;性别的觉醒,也在肉质的通透里,发泄情欲的膨胀;从葡萄的血脉,追索家族种族的印记;在袒露的开裂中,不断发表爱的宣言;坏死的皮囊里,也存留着母性的体温;冬去的枝头,继续挺立自恋自强的傲气。火的葡萄、光的葡萄、进行曲的葡萄,充满着梦想、熟透和审度的诉求;金属的葡萄、妃子的葡萄、受伤的葡萄、阴影的葡萄,带着难言的苦衷与挣扎。这一切,构成了丁燕特有的抒情方式——强力自白与判断陈述、柔性物象与坚硬喻指结合的文体,彰显了女性温性中的刚烈和细致中的粗放。
读100首与读1首是有区别的;挑一首来代表100首,可是勉为其难,但篇幅关系,也只能挑一首较短的,以此来略窥“全豹”。
在《葡萄的波浪》中——我试图装成一粒种子,这是全诗的引子,而波浪是该诗的关键词。从前后关系上看,从种子与第二句“立体心脏”的关系上看,波浪明显喻指了葡萄的”“内瓤”。葡萄的内瓤本该是静止的、浑圆的,此时与运动的波浪“挂钩”,虽然波浪的外表打扮为名词,但难掩其强烈的运动气息,加上“心脏”的加入,使得这一动态化的运动结果,生机勃勃。不是吗?波浪的“涌动”、携带“空气和颜色”、波浪“自己的力量”、“一直往前疯跑”、柔软的旋涡、通红发亮。连续6个句子的浓墨重彩,把波浪的“精气神”给调动起来。在波浪的运行中,参杂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积极的、消极的、理智的、非理性的、有活力的、本色的、有陷阱般的、诱惑的,有光明朗照、也有冰凉寒栗的……凡此种种,构成波浪的运动场——即生命的运动场。
此时,“我”与葡萄已相互打开,葡萄的内瓤与波浪相互同化,静态“物”与动态“词”进行对话。内瓤——波浪,波浪——内瓤,在物化观的“化学”作用下,或者说,在主体间性的“关照”下,顺利完成了作者的文本意图:这是一个生死场、一个生存场,充满无法摆脱的人生悖论,无法挽回也无法占有:试图要离开它却根本不能抽身而退;试图要保持距离、警备,却未能如愿以尝;试图要玩转它,却始终难以驾驭。
这样的两难循环,是人生的宿命与悲凉,“一圈圈跑道”(是内瓤——波浪的延伸性辐射)一圈圈地无休止行进,从跑道到跑道,犹如从牢房到牢房,是永远跑不出自由的“操场”!
操场——跑道——牢房,从前半段内瓤、波浪的瘁合想象中,再次“异军突起”,跳跃性的将双方做大跨度的“合谋”,共同深化了该诗的主题。
这是一次成功的人与葡萄的对话。依照传统的“物化”观,是“我”蜕变为“葡萄”,有主动与被动关系。而按目前流行的主体间性理论解释,“我”与“葡萄”已抹掉了主客体界限,同处于主客体对等关系。从这一维度看,庶几与中国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 ——“物我同一”相似。在交往的时代,我们期待人与物、人与词、物与物、词与词的广泛对话,当然,它们必须首先浸淫于充分的诗性氛围里。
附:葡萄的波浪/丁燕
我试图装成一粒种子
试图走进它的立体心脏
试图看看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样
我看见了波浪
涌动的波浪
携带着它的空气和颜色
它自己的力量
一直往前疯跑
那些柔软的旋涡
将冰山都浸泡得通红发亮
我试图要离开
试图用距离挽回自己的忧伤
——我可以消灭它
但我却无法占有它
这是我到达不了的操场
一圈圈跑道
一圈圈属于自己的牢房
是它的
也是我的
古诗,隐性的或显性的开关
——读沈蕾娟“飞”
沈蕾娟,原名沈木槿,1975年生于浙江,现居北京。有诗集《在纬度的温差里》(2004)。
问:忽然来一句古诗开头,“落木千山天远大”,并且单独成行,一定有什么意思?仿佛是一个开关,揿了一下,想把什么东西给点亮?
答:“落木千山天远大”取黄庭坚《登快阁》。黄被称为“点铁成金”的能手。此句气度宏大、卓迈,给人一种宇宙寥廓、天地旷远的感觉。想必是沈小姐读了该诗,或由类似的情景触动了,引发起兴。一副打开天窗说话的豪爽,胸无芥蒂。
问:所以,在此情此景激发下,难免不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阅历、经验,和情感来个“回顾”:“有时我多冷漠,/为一点点小情小爱/忘了这些/就在门外”。大境界和小感触构成某种落差?
答:前面是古典名句,后面对接现代口语,的确有点“硬”,但有醒目撩心之效。诚然,在大千宇宙面前,在渺远的时空里,人的一己小情小爱,鸡毛蒜皮,算得了什么。所以开始自我安慰:就忘了这些吧,把它丢在门外。这是最早的一次小小的“过意不去”,也是一次小小宽解。
问:接下来是:上个世纪,/我像一部默片/只有动静,没有声音。/梦见自下而上我/一截截瘫痪。迅速进入对自己的检讨、谴责,好像有点刻薄?
答:不单刻薄,是对自我、过往历史的“追问”、“拷问”。是否决,干净利落。因为她用到了“瘫痪”一词——是完全不行了。
问:虽说这种自我“非礼”是在梦中进行,怕还是染上女性书写所喜欢的“自虐”。我看有那么一点吧?
答:没错。越发展到后来,女诗人变成“半夜里咬断自己的舌头”。咬断是极端的“自虐”、彻底的自我戕害、“以毒抗毒”的决裂。
问:还好。作者最终并没有完全陷入那个可怕的旋涡。而是让“嘴边开出袅袅的/花。”一个美化的意象,是意味着自我搏斗的中止?清醒?抑或升华?
答:这一荡开的“笑意”,应是精神施洗后,升浮起的满足和慰安,总之,袅袅的花,很美,一扫前面的阴翳和晦暗。
问:是的,当内省恢复平静和理性,主人翁就懂得用过去“磕磕绊绊的眼泪”,来浇灌自家的菜地——“菜地里一棵梨树,/梨树上/一口鸟窝。”
答:用泪水浇灌,这是常用的比拟。不过用磕磕绊绊来形容泪水,使常用修辞丰富了弹性。重要的是,它浇灌到具体的、特指的“菜地”、“梨树”和“鸟窝”,它们已然是作者生命中、阅历中的某种关联物,而且具有寄寓色彩了。
问:好像到这里,作者的心理折磨,开始出现一种超越?因为最后结尾,再一次单独句成一节——“泪尽了你就飞”。有解脱的味道?
答:衔接倒数第二行的“鸟窝”、呼应倒数第五行的“泪水”,的确,一种解脱之情、超脱之意,油然而生。其中包括自我打气、自我发现和自我激励。
问:可是,如果结尾不停留在“泪尽了你就飞”,而是再补上《登快阁》最后原句“此心吾与白鸥盟”,与开头“落木千山天远大”相呼应,会不会形成更好的照亮呢?
答:你这个建议倒可以考虑。实际上白鸥与前面的鸟窝、与飞,有着密切的关联。增加这一句,可能会使女诗人与黄老先生的互文更加鲜明完整。但会不会另留下一点狗尾续貂呢?
附:飞/沈蕾娟
落木千山天远大。
有时我多冷漠,
为一点点小情小爱
忘了这些
就在门外。
上个世纪,我像一部默片
只有动静,没有声音。
梦见自下而上我
一截截瘫痪
到世纪末,
半夜里咬断自己的舌头,
嘴边开出袅袅的
花。
我过去
所有磕磕绊绊的眼泪
只求能浇灌一畦自家的菜地,
菜地里一棵梨树,
梨树上
一口鸟窝。
泪尽了你就飞。
2006.11.24
陈仲义,著名诗评家,现居福建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