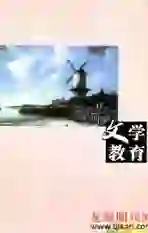浅谈屈骚美学的人格美
2009-09-24高丽君
儒家思想是屈原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屈原发展儒家美学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精神。理解屈骚美学应从人格美、情感美和艺术美这三个方面来阐释,本文先来谈谈人格美。
一.外在美与精神美的统一
在《离骚》中他自我评价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外在美”和“精神美”是屈原所看中人格美的两个方面,并认为二者是互相依存的。他所指的“精神美”是各种美德的结晶,是指道德品质的修养和锤炼。这实际上是屈原评价人格美的基本标准和基本范畴。在《橘颂》和其他诗篇中,屈原还具体的说明了“精神美”的内容。就是“怀乎故都”、“哀民生之多艰”、“独立不迁”、“横而不流”、“中正”、“耿介”、“秉德无私”、“重仁蹈义”等。耿介就是端直不屈,坚定自己的立场,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屈原在作品中提出人除了具备“精神美”外,还应具有的“外修美”。他认为喜好美饰是“外修美”的一种表现。美丽的鲜花,芬芳的香草,装扮着诗人的形象,外显着诗人的心灵,象征着诗人品格的高尚和坚贞。这种“奇美化”的装饰,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它却使诗人的形象升华到了文学史上空前美好的地步。朱熹说:“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洁也。”(《楚辞集注·离骚》)在《离骚》开篇,他谈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体现出屈原对仪表美、服饰美的重视。描写佩玉、佩芳这方面的诗句也很多。佩玉在先秦是一种风尚,如“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离骚》)“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佩芳是一种美好品德的象征。在屈原的作品中数次提到佩芳、采芳、食芳、植芳。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君》)“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离骚》)
这种外在美与精神美的统一反映了屈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屈原吸收了儒家美学中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文质彬彬”、外在形式的美同内在人格的善相统一的思想,进一步高扬了儒家人格美的理想。但是屈原却把这种人格美推向了极致,表现出一种对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热的崇拜,与儒家中庸思想和中原内敛的文化大相径庭。班固在《汉书》中评价屈原是“露才扬己”,他有着张扬、外露的性格特点。屈原崇拜自己的才华,自比于尧舜禹汤。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将会“上能安君,下能养民”;崇拜自己的伟大人格,认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总之,在他看来他具有一种光照日月,如幽兰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与高贵品质。
屈原这种完美主义性格特征,为自己设立了超级道德标准,并且努力趋向他,同时又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他人。所以上官、子兰、子椒、靳尚、南后及其他所谓“众人”,都成为他鄙夷和憎恨的对象。他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的人格高标不允许他宽恕任何人,甚至他自己。
二.执着精神
孟修祥在《楚辞影响史论》中认为自楚族立国,上至君臣、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具有这种坚忍不拔、执着进取的精神,并且世世代代延续下来。《橘颂》有人考证说是屈原举行成年礼时所作,他把自己想象为伯夷那样清高、执着、固执的人物。实际上这是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的抒写。
战国中后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关头。从这时的社会情势看,一是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空前激烈,重新统一的局面即将出现;一是变法运动正在当时各主要国家相继进行。魏文侯支持下的李悝变法;韩昭公用改革家申不害为相,加强政权;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还有著名的商鞅变法。屈原生活在当时的楚国,正处在这一时代激流的潮流之中。当屈原得不到楚怀王的重用时,他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或放弃理想,避世远惑,逍遥自适;或离开楚国乡土,到他国去做客卿,这在当时所谓的“楚材晋用”的风习下,也是行的通的。面对如此艰难的选择,屈原也曾犹豫、彷徨过。“心犹疑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突出了他性格中犹疑的一面,这正是诗人当时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之,舒信修而慕之?”。“曰勉远逝而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通过向灵氛占卜,借灵氛的口吻来说自己的思想斗争。最终执着的精神让他不肯放弃理想和责任,更不肯弃国出走,而是决心与祖国共命运,“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儒家以孔子为始,宣扬的是秩序的调和,在于重构一个以“礼”为规定性的社会结构体。孔子是不满于现实的,他要实现的是恢复周代礼乐的政治理想并为之不断努力,但是孔子的理想并不是对现实的彻底颠覆,而是一种改良、调整,其实施的关键在于“中和”,走的是一条秩序之路。屈原选择的道路是直面,他从不回避社会现实的黑暗,相较儒家而言,甚至更为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政治现实的种种弊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美政”理想,而是自觉主动的去捍卫,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超越了儒家所讲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注入了更多的个性思考与理想坚持,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先天不足。屈骚美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唤醒并启蒙后世一大批文人学者,为自己的理想而执着奋斗。
三.悲剧人格
柏拉图曾经把人分成两类:性格随和的人和脾气执着的人。屈原明显属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却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灯火燃尽,这便成就了一种悲剧的美。在《山海经》中有所谓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阳,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够赶得上太阳,留住那光阴。但是,他失败了,他因为饥渴而最终倒下了。每当看到这个故事,我便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凡的悲剧的美。夸父是在和命运抗争,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英雄悲剧人格。而屈原也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当他一切的努力都成为徒劳,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亡。这是最后的抗争方式,其结果虽然并未能够改变他自己和楚国的命运,但是却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在苟全性命与为理想献身之间,屈原选择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变自己杀父娶母的宿命一样,屈原的抗争是徒劳的,但他的悲剧精神与他的不朽诗篇一样,成为了一种永恒,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
屈原悲剧根源除了政治根源和文化根源外,他耿介、端直的性格也是悲剧发生的另一原因。假如他听从《渔夫》劝告“举世混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餔糟而歠其酾?”悲剧也许会避免。但他的回答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正是他这种视“义”、视“道”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观,让他走上了悲剧的道路,实现了他的君子人格观。
在理想实现的途径上,对于儒家而言,其个体人格的完满与社会秩序的和谐靠的是“仁”与“礼”的规范。“仁”是针对个人的,要求个人遵循社会道德与规定。而“礼”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在于构建一套和谐的等级秩序。“仁”加上“礼”成为儒家学派追求个体理想人格与社会政治的两大关键。屈原从儒家思想中继承了那种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但又与儒家不同,他借助的不是社会关系的纽带,而是凭借个体对于理想的求索与追问,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屈原作为一个孤独求索者的伟大形象。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儒家之士会选择其他道路来弥补这一缺憾。但屈原所接受的楚文化纯真、浪漫赋予他九死不悔的执着,如“橘树”般坚定自己的信念。独特执着的个性决定他也不能像老庄一样隐居山林。
屈原悲剧美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展现了主人公在追求真善美的执着中毁灭,具有崇高的内涵。他把自我的理想追求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个性的毁灭,大大增加了悲剧美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美学史[G].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萧兵,楚辞与美学[G].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3]孟修祥,《楚辞影响史论》[G].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4]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G].北京:中华书局,2007.
高丽君,女,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7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