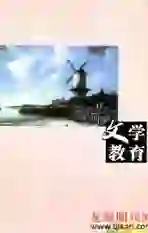“地母”崇拜在文学艺术中的“回归”母题
2009-09-24李红英
一
20世纪神话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的崛起,女神在神话研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人类社会由狩猎时代过渡到农耕时代,这给母神崇拜带来了新的重要内容。女性自然地同生养农作物的土地发展起象征对应关系,这便导致了遍布全球的“地母”崇拜。
华夏民族最早崇拜的地母神是女娲。应劭的《风俗通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中保存了关于女娲造人的神话:“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在此神话中,女娲造人所凭借的仅仅是黄土,而土所表征的也就是大地。大地生长出植物,人类社会中母亲生养子女的现象正与之相似,由于“类比”这一神话思维模式的基本逻辑使然,“以地为阴性名词,图像作女人身”,并由此产生地母崇拜的现象。事实上,女娲在国人的观念中就是作为“地母”偶像的原型。《抱朴子·释滞》中说:“女娲地出。”今之学者亦肯定,“女娲既是地出,就带着庄稼神兼土地神、泥土神的性质。”女娲作为大地母神,不仅靠自身生殖出了人类,而且兼农业生产的保护神。
撇开神话,我们单就汉语中“生”字的原始表象而言,就可以看出原始先民的“地母”信仰,可以看出先民意识中的大地是同母亲的生育特性联系在一起的。
在甲骨文中,生育之“生”字的字形,取形于一棵从大地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小草。中国哲学非常突出地表现着“生”之精神,生育、生命、生态、生机、生气、生生不息,而所有的这些内涵最初都不过是源于一棵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小草。人类的生育的“生”也像大地吐生万物一样,一棵从大地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小草,几乎代表了“生”的所有内涵,包括人类的生殖。人类生育过程,只不过是人类母亲模仿和重复生命在大地子宫中的孕育行为,女性的生产也就是微型的宇宙生产。
所以,对大地母神的崇拜,体现了原始先民的“生”之观念,而这种“生”之观念又与大地紧密相联,他们的生命、生存深深地依恋着大地,就像大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一样。这里的“生”不仅仅包括“生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一种对“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追求。祈望大自然万物繁茂、充满生机,更祈望人类能够生生不息,永恒地生存于这样生机勃勃、万物繁茂的大自然中。
二
晋人扬泉《物理论》云:“炎炎气郁蒸,景风荡物,地之张也;秋风荡生,凉气肃然,地之闭也。”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张”和“闭”,正是由于大地母亲在春夏之季张开大口吐出热气,万物才得以生长;反之,秋冬季节的冷风凉气使万物凋零,正是由于大地之母闭合大口的缘故。一张一闭,一生一死,一善一恶,也就是荣格所说的母亲原型中的“可爱的母亲”与“可怖的母亲”。叶舒宪认为,地母神变成一对女神的情况,在中国表现为空间上的对立母神,也就是所谓的“东母”和“西母”。女娲和西王母就是东母、西母的变形。“在神话思维中,空间方位和时间观念都不是纯然客观的范式,它们同时也是价值范畴,具有相对固定的原型意义。东方由于同春天相认同,在空间意义之外又有了生命、诞生、发生等多种原型价值。”东母便自然地与创造人类及万物的女娲联系在了一起;而西方模式与秋天呼应,代表着生命的衰败和死亡,西王母便与西母对应起来。关于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中有如下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也就是说,西王母最明显的职务便是主刑杀,为死亡之神,是女娲的截然对立面。然而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女神仿佛又是一体的,她们是同一个承载了生命的大地。植物于大地的泥土中萌发生长出来,最终它的根茎枝叶连同种子一起又都同归于萌发了生命的大地泥土中。神话的类比思维认为,动物和人其实也同植物一样,由大地母神创造了生命,最终死亡又回归大地,回到“大地母亲的子宫窝”,(同植物一样,回到生命孕育萌发的所在)。或许,正因为此,中国古人才总是要土葬,死后要入土为安。
大地母神的崇拜,反映了原始初民的生死观念。在远古蛮荒的时代,原始初民逐渐萌发了生命意识,然而伴随着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又不可抗拒地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但是,这种促使他们觉醒的原始理性又使他们对生命的本质有了一种自我界定:生与死的轮回正如昼与夜的交替,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正如黑夜之后,白昼总会来临一样,人的生命也如此轮回,死亡不过是再次回到生命的起点。神话思维的想象,使他们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如此说来,死亡之神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因为死亡意味着回归母体,死亡亦是生命的重新开始。一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原始人的这种生死观念,上古时,有的墓穴,就以女阴的形状为入口,以此来寄寓古人的再生愿望;还有瓮葬,也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瓮的形象象征着一个子宫,死者被置放头部向下,如在母体内待产,寄寓了古人再生的愿望。
对于原始初民来说,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对大地母神都怀有深深的依恋,他们就像植物一样,生,深深地扎根于大地;死,又归于大地。因此,他们不仅崇拜创生之母,同样也敬畏死亡之神。死亡即是回到宇宙大化中,回到生命的起点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大地母神在他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无论是面对生命,还是面对死亡,他们都不会像现代人这样有如此多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困惑。他们就像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生活在母亲的怀抱中,不知道什么是烦恼。而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现代人,在忘记了大地母亲的神圣性的同时,也忘记了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一项需要:扎根。他们生活在高处,心灵也漂浮在空中,没有依托。
三
据《圣经》描述,人类最初生活于“伊甸园”中,无忧无虑。其实,在中国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描述了一个极度丰饶之国,这里有大鸟蛋可以随便捡食,有甘露可以饮用,“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自存”。《山海经·大荒南经》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不绩不经,衣也;不稼不穑,食也。
这完全是神话思维对“原初之美好”的回忆与向往,是典型的伊甸式乐园。仔细想一想,这样一个“乐园”,其实就跟胎儿所甜睡的子宫差不多。从“心理分析和原型模式看,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只有胎儿在母腹里才能实现。”罗海姆曾经论证:原始人对“世界”的构想,来源于胎儿对子宫的感觉。神话和神话思维对于“原初之美好”的回归,实际上就来自于这种胎儿对母亲子宫的感觉,这种感觉存在于人的深层记忆中,在对这个世界进行构想时,它无意识地发挥了作用。
母腹是最大的单纯、洁净、安适、幸福、快乐和温暖,而人的出生就是离开这样的境地。其实,人的出生就是一种被抛出的状态,离开了温暖安适的母腹,也就是离开了人最初的“乐园”。随着人慢慢长大,又渐渐脱离了母亲的呵护,离开了父母筑起的温暖的巢穴,进入到了艰辛、纷扰的人生况境,体会到了孤独、疲惫、无奈、迷茫的人生况味。于是,便渴望回归到那个单纯、洁净、安适、幸福、快乐和温暖之地。“回归”也就成为文学艺术经久不衰的母题,回归的愿望源自于我们对母亲的依恋之情,源自于我们对母亲曾给予生命和安全的追忆。
回归母体是人类永恒不灭的归根渴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渴望是被压抑在潜意识层面的,人类对于母腹的感觉,也处于人的深层记忆中,不易被发掘。被压抑的性本能可以升华为文学艺术,这种回归母体的归根渴望同样也可以升华为文学艺术,回归、生与死便经久不衰地成为了文学艺术表现的母题。当然文学艺术并不直接表现回归母体,但无论回归的内容是什么,在心理上,总是这样一种渴望在起作用。并且,这种渴望似乎拥有更为强劲的力量,经久不衰。
大地的坟墓,亦是大地母亲的子宫窝——人类最初的乐园,没有艰辛的劳绩,没有世事的纷扰,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在原始先民那里,死亡,不像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终结。在他们心目中,生命永恒循环,死亡不过就是回到宇宙大化,进入新的轮回。死亡,也就是重新回归到大地母亲的子宫窝,回归“乐园”。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回归母题才成为人类永恒不灭的归根渴望。
这种永恒不灭的归根渴望在两种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入:一是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它以极端的形式突破意识的外壳,表现出对生命的恐惧和对死亡的迷恋,幻想中,死亡就是回归大地,回归母亲的子宫,回到人类最初的“乐园”,这不正是原始先民的死亡观念在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发挥作用吗?二是在诗人、艺术家那里,它以变相的方式发挥作用,于是便出现了以回归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他们是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代表,把压抑在集体无意中的永恒的归根渴望发掘出来,并把这种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回归原型。几乎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会有这样的代表,因此,回归成为了文学艺术永恒而又普遍的母题。
李红英,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