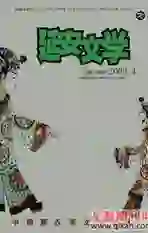陕北民间文化综述
2009-09-08吉胜利
吉胜利
三、陕北艺术作坊的部署(下)
4、布堆画作坊
布堆画与农民画,其实就是剪纸的分支,属“剪纸型”产业。
从艺术脉络上讲,“布堆画”也是同属于意象类作品,以作者“意象”的呈形来创作于实践的。因此它的抽象,它的淳朴,它的原生,不是一言可尽的。古人讲“得意忘言”,其实就指意象间的默契。当观者与作者的意境相映时,想说的一切,都是“欲辩已忘言”。
清代,满人入关之后,采取满式朝服制,里面的“补子”,其实就是典型的“布堆画”。为了区别官级、品衔等差别,在朝服的胸口处做了可以活动的布样图,王爷的为莽,武将的为麟,文臣的为鹤,又按大小品级正副等各有不同。随着升迁或降职,按律更换补子以及胸花。
我们的布堆画与之虽有不同,却也同属画、堆、刺、绣、浮雕等立体,或单层平面堆贴,或双层叠布累折,看之,似浮而摸之;似雕,既有立体感,又有意象境。并且,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宗教祭祀文化,节日礼仪文化,民间习俗文化,写意图腾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下面,我们对它的布阵取势予以概括:
布堆画的艺术的章法布局,讲求在富有实用性,装饰韵味的结构轨迹的时空律动中布阵取势,从而由构成一定韵律感的中心骨线,表现出气势生动,丰满热闹,活力充沛,姿态纷呈的艺术特色。
从它的造型联系的关系性特点上看,类似民间诗歌中的声韵,戏剧中的秧歌剧。它的艺术表现方法,是程式化的,在一定的环境空间中,以时间性的律动衔接来强调生命活动的节奏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某些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来说,这“布”阵中取势的艺术形式更有极其活泼动人的综合装饰效能。
(1)空间取势、力度均衡
陕北布堆画的章法布局(手工),即绘画和一切造型艺术里所谓的“构图”,讲究“以小观大”之法。透视关系的空间处理法则,主要是运用散点透视法,而不同于西洋传统绘画的成角透视。
现代的东方和西方艺术家,都致力于广泛地吸取中国民间画工创作的壁画、版画、工艺品,以及波斯与印度画中的内景、外景的不同空间并列法,结合中国书法、长卷及水墨画、舞台艺术等装饰韵律的表现法则,时常把远景与近景、天空与地面、虚景与实景等等,都有机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艺术中富有国际化构成法则的“蒙太奇”。
我们的布堆画则正是新生派蒙太奇中的佼佼者。具体来说,它以无比简洁的艺术形态来增强赏者对画物的有机律动的旋律与节奏感觉,并还原成艺术的最原始的元素,在一切空间场域的置陈布势里得到新生,由置陈里得出艺术构思的阵势,由布势里从一得出二,直到无限,使“心理时空”的神秘在心灵里醒来,注入到自然生命体态的血脉的流动和颤抖里,在人身、动物、山川里、在空气里……那从立体的“完整”中得出的抽象而纯粹的艺术轨迹,不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屋里冥思苦想就能得出的,它来自狂风骤雨,烈日曝晒,甚或是生命的搏斗中,自原始时期以来,延续为布堆艺术“布阵取势”的心象的流程,并在精神世界里贯通一线,穿引过万物。
而这根精神世界的主线,正是在纷纭复杂的生活事物中,通过时间线索的神态律动的导引,在造型关系中使人们的视线化静观为动观的律动,从而以视觉上的时间流程,从立方体的空间里被提炼、被探寻出来的。堆画艺术也正是善于在这心理时空的探寻中化立体为平面,在这时空的构成中取势传神,在这传神中以运动生姿态,姿态在组合与呼应中出章法。
因此,它使堆画艺术家在创作时处于双重构想之中:一方面是生命活动的时间运动的原理、定律和机制,另一方面则是空间的现实。在这空间的现实里,存在着民间艺术家们日常所见的生动明媚的各个立体物质结构的形态和色彩。由于它们在相互之间的运动中发生有机的联系,各个空间的物质就必须依靠时间的轨迹来沟通,又必须经由布堆画师在种种工艺(如剪纸、农民画、泥塑……)制作条件的制约下,通过平面的构图予以变通和简化。按其形式美的艺术构成的材料组合规律来说,力度均衡是很重要的方面。
(2)格局严紧、动静相成
在布堆画艺术的概念中,人物和布置乍看上去总是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似乎“静态”已经成了它的本质属性。可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来,艺术家们惊奇地发现到历史上任何一件成功的绘画和雕刻作品,都是追求捕捉着静中之动。尤其在发自原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民间艺术中,最能表现出神采流动的动态美。现代派艺术也是从基本格局到万方的仪态中,大力捕捉到这种静态中的动态,并从中寻找到艺术表现方法的极致。
而一个构图单位的形状愈是连贯,就愈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并使我们能够通过各个形态律动轨迹的贯连,还原出整个构图的布阵骨式,其中包括互为因果、对立统一的快与慢、动与静、虚与实、斜与直、纵与横、长与短、上与下、左与右、先与后、远与近、阴与阳等此衬彼托的运动因素。离开这些运动因素,就无法有计划地使构思意匠图象化。
具体来说,各个形体的韵律线在章法组合中扣合相应,构成完整的骨线运动关系,正如将军布阵,运筹帷幄,须使整个军伍行列虚实相间,策划相宜,此出彼入,才能灵巧得势,运行得体。按人物和动物的动作重心及方向连成“动势骨线”,然后比较其力度倾向,则可以明确地得出画面构图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力度平衡。
这种平衡正是在矛盾的力度,互相对比的韵律气势中,以运动的规律产生的动力美学,作用于人的艺术视觉感受,从而在整个画面的章法组合中,作到局整关系的统筹安排,由分散里求集中,由局部里连整体,以达到动势安排中的宾主分明,并造成视觉导向的构图中心。在整个画面上,“静”的因素不是绝对的、孤立的,正是由于“静势”的反衬,才有人与动物“动势”的充分。
以线为韵在章法组合中的导向功能,实质上是对形象的结构运动的轨迹方向(包括动作目的)的运用。它的骨线运行方式,决定形象内或形象间结构部位的关联与呼应。只有充分而有机地组织导向关系,才能进一步在不同的实用条件下,巧妙地发挥适合功能的布局作用。
(3)循序相因、层次分明
布堆画的时空轨迹流程,基于从劳动生活中提炼和升华出结构运动的精华,焕发出活生生的艺术表现力,并由此构成一种简约流畅、质量极高而又为人所共赏的美。它在结构上浑然统一,而非支离破碎;在律动中秩序井然,而非姿态纷杂。
从整体布局上看,虽然许多画面的色彩和线条纵横交错,却能从画面构成的骨线中条理出清晰的运动韵律,引导着情节内容的发展,并从着满构图、满视野的熙熙攘攘的物象与色块相间的变化中,得到一种既清楚明确,又委婉动人的画面布阵气势,而且自上自下,远近相兼,构成前后分明的空间层次。
对于某些故事情节,构图的布阵取势,可在视觉上通过轨迹律动的旋律方向及节奏长短的时间性序列对比,由一个事物的空间,贯引到另一个空间,从而得到对画面情节及主题的宣示目的。进一步说,节奏的本质是紧随着轨迹律动的逻辑发展的,前一序列事件的完成以及后一序列事件的准备。也就是说,节奏是前过程转化来的新的紧张关系的建立,它们根本不需要受固定频率和周期的均匀时间的局限。但是其产生新转折点的位置,却必须是前过程的结尾中,反映于结构关键部位的固有的“节点”。
在各个“节点”的律动贯连下,聚合为形体的轨迹导向的“焦点”,如龙珠吸引着龙头,带动起龙身,而这相寻部位会合处的“焦点”,却往往正是构图主题部位的核心所在。任何构图中心内容的宣示,若缺乏这样一种富有轨迹逻辑吸引力的标向,就得不到浓缩和集中的艺术表现样式。传神焦点,在情感结构中是紧扣人们心扉,并深钻到人们心灵深处的姿态表露,它有内蕴、有活动、有发展、有轨迹,既有集中性,又有无所不在的移动性,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衬托的集群性。
诚然,在这个具有艺术数率的循序变化过程中,不仅艺术创作者头脑的表象,要按自身的数率逻辑(点运动、线运动、平面构成、立体构成的长短比例、面积大小、体积容量……)来组合,而且艺术创作者内心的意志、欲望、情感、思维、直觉、本能,也构成了积极的艺术轨迹的运动组合关系。在许多心理因素衔接过渡、转化的中间地带,有意无意地留下了一块又一块的随机性的“量变空间”,这些空间里存在着许多“可能性”并诱发着多种“可变性”(指的是画内大写意、抽象等概念中的“物身空白”:如山身的空白,天空的空白,各个物自身的空白等等)。
(4)隔物换时、宾主呼应
中国的水墨画有无骨水墨一说,其实布堆画也一样,它也有“不以线为骨”的粘贴法,即用拼图式的方法来贯连,使图容情境完全抽象、大写意。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魏晋南北朝的绘画“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在传统艺术中,对景物进行概括取舍,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活动,经常会改变若干比例关系,不仅存在着人物和衬景关系的“人大于山”,而且存在着人物比例关系间的“主大于从”。
我们的布堆画以至农民画,它们其实也都是从属于“人大于山、主大于从”的范畴,而所谓不写实和不合透视,往往是来自民间的传统装饰绘画,服从艺术和实用两方面要求的手法上的统一。不仅图象造型艺术如此,即如民间传统的戏剧和舞蹈等艺术表现形式,当人物的表演进行了更大的夸张及概括之后,所用的布景和道具,也不过是仅作陪衬,让位于人,显得“人大于山”。这正是一种富有象征和浪漫特点的民间艺术表现手法,它在构图丰满、活泼热闹的民间美术中可以做到极度夸张,特征奇简,装饰的无可再装饰。
从“故事美学”的角度来看,布堆画的美的韵律应该是令人舒适的,虽然说,韵律本身是指音乐、舞蹈中声音和动作在时间上起变化时出现的一种秩序感觉,然而静观形态下的造型艺术品,其本身的线条、形状、色彩中也有一种韵律感。即使是一件静置在那里的绘画作品,人们也一定会顺着构图的韵律从造型的组合关系中移动着自己的视线。以“隔物换时”的布阵取势程序来展示情节律动的“时序结构”,就是依据这一动力学的律动原理产生的。
因此,布堆画之不同于其他美术的重要因素就在于:画家要把所有的构思主题内容的片断,衔接叠缀成类似曲式结构的有机联系因素,才能把统篇的时间性情节过程,透过种种切合实际的观察角度重点描绘出来,并由以“重叠缝补”的艺术构想和想象来构成“衔加空间”,表现为具有时间连续性的生活进程中不同空间场景的“隔物换时”,从而由线—面—体—时,达到空时具备的四元化构成,使隔段的“节”正好处于运动环节的确切部位上,按主次循序组合为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而这统一体中的每个部件,又都凝汇成缺一不可的集群因子,以其艺术生命的肌体,发出整体构图的精神气势。正如许多艺术作品——诗、戏剧、歌曲里,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位置上抽出一句诗、一场戏、一小节音乐,把它放在另一个位置上,而不损害整个作品的意义,就象我们不可能从生物体的某一部位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个部位,而不毁灭该生物的生命一样。这也就是四元化时间流程的动力结构,在视觉形态上所表现的整体演化性的基本涵义。
可以说,以剪纸、农民画和美术的成就而结合起来的布堆贴画技法,具有上承古中西古画传统,又下启民间绘画过渡的新格调。它在民间艺术构图的布艺取势中,推出了种种由起始、变化、高潮和结尾的艺术轨迹。它的骨式多朴多凝,则谐于克一;它的律动循迹序行,则相紊不乱。它配合着时代的步伐,蕴含着情调的轨迹,涌发为艺术的旋律,情思绮合,影响深巨,以民间艺术的种种特有的构合形式,发挥出具有民族精神气势的巨大创造力。
5、鼓作坊(即陕北所有鼓型的制作)
在延安,鼓主要有六种形制:陕北的腰鼓、宜川的胸鼓、洛川的蹩鼓、黄陵的抬鼓、黄龙的猎鼓、志丹的扇鼓,它们的形制与体积各有不同,音声、响亮高低不一,若穿插呼应则交响一曲。或,配以合律的鼓谱,加之阵法的变化,组合未必不能呈势。
这其中以扇鼓最轻而巧;猎鼓、抬鼓最沉且重;蹩鼓大,故音厚贯天;胸鼓小,故微波切地;腰鼓适中而灵活,是以能、狠、蛮、猛、虎、牛、六劲合一。据阵法而论,则六六三十六变,每组六种鼓,六组成阵,阵与六合相应。或,取八卦为象,杂舞蹈为阵,穿引八方,导六十四种变化。
(1)腰鼓的舞
陕北腰鼓从舞动上讲,概括起来有十二种招式:跑、跳、扭、转、蹬、闪、跺、摇、跨、昴、跃、快。
跑:跑时有闪有躲,闪中有踮步,躲中有跳步,通常以马步跑带动。快跑时则跳,慢舞时则蹲,上下彼此起伏有律而不失章法。一个跳上时,一个蹲下来,一动一静,互为照应。
跳:大跑场时有蹦跳、弹跳,小来回时有闪跳、躲转跳,跳、扭一体则自然回摆,头迎脚踮能出一股子虎劲。
扭。正步扭、十字扭、软腰扭,如风似柳。鼓点落,扭在点上,鼓点起,跟在槌上,听音辨位,好不欢快。扭则闪,闪则躲,躲则跃,跃则“鲤鱼跳龙门”。
转:左垫脚转、右垫脚转、周天转、小半身转,因势圆导,滑出一股子漂劲。
蹬:四方蹬、跳蹬、踹蹬,抖动的是身上的土,蹬起的是地上的尘。南拳有“穿堂腿”一说,与之颇为相似。
跺:垫踮跺,左右有序上下点。单脚跺,一脚三踹破地皮。尖不点地,跟不落,单靠脚心捶地皮。
闪:左避,右躲,上拉,下摆,是谓“闪”。不顾前,不顾后,就怕自己没灵劲。
跨:左跨步,右跨步,向前跨三步。步步稳,步步狠,蛮出一股劲。
摇:肩耸、身晃、三摇头。胸挺,腹收,如鲤似猫。
昴:气宇开阔,就在一个“势”字。陕北人骂人“扎势了”,就是这个意思。
跃:有跳而不跃之跃,谓起身;有跃而不跳之跳,谓打挺;跳中有跃,跃中有跳,是之动身。
快:鼓点快,手势、脚势同样快。猛回头,劲转身,连闪带摇,快而不乱,忙而有序,快在“活”上。文也动,武也动,不同在个“劲”字上。
文武二别类:
“文鼓”是以扭为主,重柔性轻刚劲,以打为辅的一种表演方式。因此重文轻武者,表演到一定阶段或时间则不打而扭。鼓手紧握槌绸,扭中带舞,舞中伴劲,劲中含打,打中又扭,相辅相成。与武鼓不同者是,文鼓重在演绎抒情及其形式,通过动作和表情将心境世界托将出来。鼓槌的刚“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彩绸的柔“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舞者“黄中通理,正为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武鼓”是以动态为主要表现形式,打、踢、跨、跺、踹等姿势合一。在旷野土场表演时快收猛放,欢快流畅,又刚又柔,阴阳既济,呈整体的统一性和连续的规范性。但连贯动作难度较大,需要万马奔腾而行云流水的场面。这也就是说,它务必要使群体呈现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忘我的舞动,每人皆是舞场的灵魂,而总灵魂的形成则是“集体忘我”意识。即让鼓者忘却自身的舞与动,完全陶醉于类“酒神式”的狂欢。
鼓场队列:
鼓场开锣一般是以伞头打阵,伞舞者则是先锋勇将。按《周易•乾卦》可划分为六式:
潜龙勿用:不急于拉对列势,将腰鼓和拉花两对并列,由两个伞头同时安角的表演活动。
见龙在田:将两对看似并作一队,但实则交叉互引,如伏龙卧野,辗转身躯。
单龙摆尾:伞头带队拉架势,或集中,或散列,呈尾大于头之势。看似伞头发令,但是尾摆全身,首不由身,身不由己,尾压重心。
龙行于渊:“龙行于渊”一般俗称拜四方。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位对“天、地、君、亲、师”进行参拜。形式有“一队二叉”之说,即,将队形或分作“人”字形、或并作“一”字体。
据古史而论,笔者深感国学之包容性,其不但经史子集谐四为一,而且民俗、风情等类异解,诚然每人可各取所长,集百变之律为绝韵。是以猎鼓之猛,猛在粗犷,人性而不血腥。
(5)抬鼓的蛮
说它蛮,其实是因为它大,敲击时看似蛮劲泗溢。表演时由两人同抬同打,或两抬一打、多抬散打,因此“抬鼓”名副其实。
其队形以平铺为面,呈长方体阵势,有大抬鼓一面(用于指挥),中抬鼓八面,小抬鼓三十二面,大镲六十四副,马锣十六副,龙旗四面,指挥一人。按号令开拔,纵横捭阖之间以势贯阵,假不变以应万变,类一字长蛇而平进。
在军事意义用途上来讲,抬鼓的一字平进式宛如“敢死队”,誓要将千军万马踏于脚下而后快。因此它适宜造势,既可用来挡前,也可用来殿后。在鼓舞中它角色为左龙,与右虎蹩鼓相对应,左右夹击呈并攻之势,誓死环卫中军大营。
(6)蹩鼓的能
说蹩鼓“能”,其实也是夸它威,犹如洪水狂泻音波千里。
它在社火角色中,通常饰三种形式:
大场鼓。由伞头、鼓手、镲头、锣手、文身子组成主队,表演之时由两个上伞头前导,伞头戴瓜皮帽,身着蓝长袍,一手执伞,一手挥蝇甩子,踮脚慢行夺步走,一摇三晃瞌睡虫。期间,小镲鸣,大镲和,按蹩调起势。文身子人数不限,但必须男女各半,统一在鼓奏下扮相。
小场鼓。相较大场而言,它没有文身子,是以队伍小,家当也少。一般由伞头前导,后边依次出场的是两镲手、四鼓手、四镲手、四锣手绕场一周后伞头退出场外,由两镲手指挥,依场子图“蝎子打尾”“白马分鬃”“十字对打”“三角阵冲锋”,使用周流法演绎不待。
过街鼓。从队伍上更加紧编,大小镲等均减半,以鼓手为主导,各自在三—四米空间内表演。表演多为“双脚蹩”,跳跃时双脚同时起落,动作粗犷而有力,誓要将地皮跺穿一般。
据上以言,我们说它“能”,要的其实是一种“悍”;犹如昔日始皇统一六国一般。故说它悍,是军临天下;说它能,是自我陶醉。在一人一世界中,他们自己掌控自己……
附——鼓舞综说
《周礼》讲:“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面,以祈田祖。”《吕氏春秋》言:“岁前一日击鼓驱疫之鬼,谓之除害,亦曰傩。”据此,我们而今所要排演的其实就是一种集秧歌、傩舞、鼓阵为一体的“综合性演出”,它从各方面将要展示出舞动的美、雷动的美、心动的美。
在过去,从娱神到娱人,这是民间艺术所走过的长期历史道路。原始人取材于自己的图腾信仰,成为歌舞艺术发展史的分水岭,它是原始氏族舞蹈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图腾艺术作为舞蹈形式展现宗教形态,其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它曾经渗透到当时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创造,甚至到现代几经变迁,还留有它在人性艺术活动中的鲜明痕迹。
毫泽尔在《艺术社会学》讲:“艺术和社会处于一种连锁反应般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这不仅表示它们总是相互影响着,而且意味着一方的任何变化都与另一方的变化相互关联着,并向自己提出进一步变化的要求。”事实上,我们而今所要做的调整,其实就是属于“自我意识”的艺术,即通过艺术来释放每人心底的枷锁,从而变化并调节自身心理的同时“谐和于外在的社会”。
今之所以创办大型的鼓舞场面,说穿了也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活动,它可以通过展示祖国美好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来表达人民向荣的心声,开启团结、奋进、和谐构造的契机,因此我们去掉以往的某些不健康成分,以宏扬科学、保护传统文化为己任,实施鼓舞整理是有必要而可行的。
A、鼓舞的整理
《周易•系辞传》曾讲“鼓之舞之以尽其神”,这就是“鼓舞”的由来。当然,这样的鼓舞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意义;它代表人类从信神进入到信“理”的境界。
《礼记•乐记》讲:“乐者,通伦理者也。”东汉郑玄注之:“理,分也。”许慎《说文解字序》言:“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乐记》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综而言之,“乐”既音也是礼,它从理而入,借精神以化伦常。
因此,我们的鼓舞,它其实也是一种由“乐”而“礼”由“礼”而“精神”的东西;从理性的角度来划分出心理、意识和艺术的表演层次。是以“鼓之舞之”在我们这里,它穷尽的是人们对谐和理念的契悟,即用鼓乐来鼓舞人心,重寻民俗式的纯朴生态。让我们通过鼓的“舞”来鼓舞精神文明建设“鼓舞”和谐社会的美好未来。
从社会文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它作出以下修整:
1、从服装到道具的更新
人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服装和道具的更新上我们必需与时代潮流相挂钩,以自身特色创本土装饰,用另类而别样的风采展现新的气象。这方面,一是挖掘传统的当地特色,二是根据现有情况加以编整,通过复原昔日民俗原景的基础上适当地改良。
譬如各伞头的服装,我们可以依然保留传统式的长袍,并加以老花镜相配,务使显得更加酸气十足而迂态可居。再譬如,光板皮袄、黑山羊毛擀的毡帽、毡窝子鞋、遍纳袄、裹肚、坎肩、大襟衫、大裆裤、绣花鞋、纱网帽等等,它们均可以用来装扮新的鼓舞阵容。或在阵容添加的同时,剧场当中以小品形式演出地方剧,例如:新媳妇坐花轿,小媳妇骑毛驴回娘家,挑着担子串乡过村摇着拨浪鼓尖声叫卖的货郎,用两头大牲口驮的架窝子,跑长路送客人,巫神跳大神治病,能说会道专门以说媒谋生的巧嘴媒婆子,拉骆驼走四乡为人相面看病的蒙古大夫,背着顺子,穿着破破烂烂,蓬头垢面,打着莲花落说快板唱曲要饭的,赶牲灵走口外的脚夫,开黑店哄钱的寡妇,戴瓜皮帽,鼻梁上架着石头镜,坐在街拐角,专为人写书信、诉状的穷学究秀才,等等。
总之,所谓的更新,是在复古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的“新”主要是在“秧歌剧”的演出方面,用剧情贯穿并搭配鼓舞内容及其形式,以黄土总风情出演民俗华章。也因此,这样的鼓舞是别样的鼓舞,它至少是“露天舞台剧”吧。
2、乐舞的编审
《吕氏春秋•古乐》讲:“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又“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在古代,由致舞百兽而出现了原始的演员和道具,这些道具,往往是些动物的骨骼或毛皮,象葛天氏之乐中的“八阕”舞,它就是以触手之具来演出的。
据考古而言,《尚书•尧典》中所记的“百兽率舞”,舞时有“击石拊石”的伴奏节拍,来自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拟兽舞蹈。原始舞蹈和音乐、诗歌是密不可分的,一直到后代还是如此。所以,古人所谓“乐”,通常就是指舞蹈、乐曲、诗歌三者而言。
原始人舞蹈时通常都是边歌边舞,而且一般都是集体的、群众性的活动,参加者是全氏族的成员。是以当舞蹈还处于这样一种即兴抒发的阶段,艺术加工自然不会很多,所以舞蹈的形式和动作一般都比较简单并接近自然状态,歌曲也处于十分简单的原始阶段,最早的时候,甚或是用来抒发激情、调谐节奏的单音狂呼。
现在,现代与后现代仿佛业已过时,但是回望古人的乐、舞,我们不能不感叹它仍具备当下的实义。即用古乐来唤醒并舞动目前文艺界的枯燥,从而鼓舞未来艺术家对原生艺术的礼赞。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吼”,吼动山河,我们就是要“撼”,撼天动地,用复古而全新来编排“古往今来”的浮世绘。
古人有“五禽戏”,我们有秧歌舞,彼此可以通过借鉴而糅合,用舞+武术+歌乐=新的形式,诚言之,既要有猎鼓的原始狂野,也要有腰鼓的刚美,它们数者与艺术美学的融会,才是映发出夺目光彩的起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讲:“有两种美,即:自由美和附庸美。第一种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说该对象什么。第二种却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并以按照这概念的对象的完满性为前提。第一种唤做此物或彼物的(为自身而存的)美;第二种是作为附属于一个概念的(有条件的美),而归于那些隶属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对象。”因此,我们所要创变的鼓舞之美,她其实即是一种“调谐”的美——即对一切对应和非对应的谐和。说穿了,舞与乐所要表达的形式,就是每人在进入状态后所应有的形式,他们是一体不二的。
所以说,我们的审排其实是强调主体时强调自我的审排,它以舞与乐和、乐与鼓和、鼓与人和、人与舞动的形式描述内容、情节,所以舞动的不仅是整场的气氛,随之而来的是观者与演员的精神上共鸣。是以这样的审排,它是一个学习人文文化的过程,要让每个身临其境的人切身感受到文化对人的熏陶,从心地深处萌发出艺术的种芽。
《史记•乐书》讲:“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几让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又“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这也就是说,乐、舞、礼、诗歌等,它们是育己而及人的,通过人与人间的心境磨擦来感通人生。
在这个包装已呈文化状态下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真正的人文教育来唤醒自我的良知,而能够对此以当头棒喝的,则莫过于宏大的鼓乐。让我们用雷一般的震天响,撼动这久已尘封的吼声。使乐者不以自乐为乐,美者不以自美为美,共乐赏美,才是华章篇幅。
3、通俗化美学鉴赏
美学,它本身是一门高雅的学科,从尖端来讲,并不存在所谓的“通俗化”。笔者之所以要拟此条目,其目的则是为了要让观者通过欣赏也接受教育,即在与舞者产生共鸣之后从往后的临摹之中自教,用“自我”督促自身艺术与人文的修养,使得美与鼓舞,成为心灵上的艺术,普泛于日用伦常的方方面面。
鼓(舞)与美,其实是在于她的舞,舞动是她的灵魂。作为观赏者而言,大众哲学下的普泛美学是他们所能认识并接受的,因为形而上的思维模式毕竟远离日用,从现实的实践当中很难获取,所以简易而实用浅显的是大众最好的审美观。
对于鼓舞的编创而言,我们正是要把握并诠解最普通赏者的心理,从循序渐进的引导角度来把握,使之登堂高雅的同时兼顾通俗,务必不能脱离与群众文艺相辅相成的战线,要以引人入胜的无言胜有言的方式,以“鼓舞”来鼓舞人心。也就是说:一,通过对鼓舞起源的研究,从总体上把握鼓舞与民俗生活的密切关系;二,通过考察民风与俗情、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经济、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文艺等复杂错综关系,来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的鼓舞形态及含义;三,通过研究民间文艺风格的历史演变,证明民俗及文艺、艺术与现下鼓舞创新能力的关系。
民间文艺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把人对于美的概念,凝聚在造型表现手段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在一定社会、心理因素作用下,把审美感受和经验诉诸文艺形式,这样,主客体的相互凝聚和依托,互为表里,为我们勾勒出审美心理的演变视象,这也正是民间美学所关注的观念内容。在这一部分的相关研究中,作为审美对象的文艺作品和具有审美理想和能力的创作者、欣赏者是不可分割的两方面,我们的研究是对当前“文艺审美心灵结构的研究”它要求我们“必须学会从审美经验出发或以之为中心对具体文艺现象作具体的考察,从中建立起关于该种艺术的审美原则”。
因此,我们不但要对文艺现象的自然、社会、心理等主客观因素和有关现象作考察,还要对具体文艺作品从造型、构成和观念、风格境界上作一番品味,追逐它们作为美学分支历程中留下的足音(鼓舞作为新的审美视角)。
B、鼓阵的变化
在传说中,女妖为了对付姜子牙,曾在黄河岸边摆下“九曲黄河阵”,迫使西周大军不得推进。最后,不得已,众仙下界来破之。而事实上,这样的“阵”其实就是演绎民俗而来的,通过九宫配八卦的方式在地上构画出万字回旋式的竿廊。
《周易•系辞传》讲:“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喋之以四以象四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据之以言,我们可知“阵”是源自中国古代的数术一系,以数理拟象显示图阵在方位上的变化,从奇偶相生之间构得错落空间。
因此,我们的鼓阵亦可法九宫、八卦之法而来,即用布墙来代替竹竿搭起的廊。而所谓的布墙,其实就是拉动而环跑着的长旗,旗以长方形为样,跑动式拉开足以象墙,人在阵中,阵在墙内,忽隐忽现,迷离难辩,远望之人山人海,近观之如封似闭,纵横捭阖莫得其端。
(1)鼓阵的结构布局和象征意义
鼓舞之阵主要有两道工序。其一是布踩点。即在鼓场上纵横见方等地布设指挥桩,由三十六人来踩点指挥全局跑场旗的运行。他们手执大幡为桩,身着黑衣为号,与红、黄、蓝、紫、青五旗对应,按左旋右绕方位布局,前后间隔数米,呈天圆地方展示开来。鼓手三百六十五人,象征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内圆以八分位外延,外方以正方体内敛,象征八卦+五行(五色旗)=混元遁式。混元开九宫中心,七七为阵,创四十九人组合。再者,拉彩旗。彩旗由四十九人组合,呈七路开拔,当中两拨旗色为互杂,其它以纯色跑动。杂色运动时为变阵,纯色运动时的定阵,阴阳相间以开谐和辩证。
(2)阵法变化与相应称谓的定向
阵法既从九曲、八卦而来,因此,内九变也随九曲星而设:金、木、水、火、土、日、月、罗猴、计都九个星宿组成。北,一、六为水;南,二、七为火;东,三、八为木;西,四、九为金;中,五、十为土。日从天,月从地,罗猴、计都定坎、离。转五行,五谷丰登;溜八卦,八面玲珑;趟九曲,九久如意。《周易•说卦》讲:“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万物相生相克,相克相生,以相反为相成,以相成为相辅,相辅相成,尔后谐和归一。释氏讲“万法一如”,老子云“道生一”,先秦儒生“太一生水”,综而言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九为变,以八为动,变动而后运,运则行,行则化,化而变之,无阵为阵。
(3)当中的民俗与情趣
对于一般人来说,它可能是图红火看热闹,但作为民俗文艺而言,当中不乏古老的韵律与古义。譬如,八卦的变化象征周而复始;九曲的运行寓意天长地久;五行的背反、谐和象征元圆动力。最后,以不变应万变,寓意“天下大同”。
《周易》以九为阳,代表男性;以六为阴,代表女性;阴阳合和,则“抓髻娃娃”。因此,全景式演出它旨在烘托出“注重生命,崇尚科学”的思维理念,即用民俗中淳朴的心地净土,来育化并育教出符合谐和心理。而民俗文艺和谐气氛中的谐和辩证,说穿了,其实就是民俗情趣当中的“大团圆”习俗。
C、整体性搭配
对于任何一门文艺或艺术而言,都绝对是离不开整体性搭配的,也就是说,连环式的整体运作是大联欢造势的氛围,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整场活跃,而不至于陷入局限的空泛。
因此,我们的鼓舞需要一种“一以贯之”的搭配,即用文化理念来锁定全局,从而在精神深处酝酿并制作出高质量的场面。让鼓者的舞,唱者的歌,演者的走场,在穿插有序配合有度中进行,从一场—二场—三场—四场中层层贯连,即可单独成剧,也能整场成戏,分合之中见真章。
第一场:雷鼓开天。由猎鼓、抬鼓、蹩鼓组成重型鼓队,用分合间隔式拉开、靠近,利用音波间的共鸣与广场回音来雷动八方。三组先各自为队,最后变为内三角和外三角阵势,用对翻的形式来变化。临近结尾时,三鼓跑场,类若三句半,用各自鼓点谐律而奏。
第二场:花鼓闹春。腰鼓打头阵,胸鼓压场,扇鼓领舞,逐一以周流形式对练,各自互为首尾,以自身百出花样取巧。其间,幡旗互动,用拉跑形式布阵,使之呈外形上似堡似营,杀气腾腾而刚风泗溢。再者,场内燃放烟花,从烟雾中透出粗犷、豪迈。用“腰鼓百面春雷发”,擂动“清歌一曲梁尘起”。
第三场:百戏争艳。由社火、杂耍、民歌等组合成场子戏,可以分为“小踢场”、“大跑样”、“二人场子”、“八人场子”、“独角戏”等。其它小节目,在伞头的率领和唢呐、打击乐伴奏下,通过载歌载舞形式,既突出了扭、摆、走、跳的欢快活跃,又暗合了朴质的潇洒,使奔放的韵律节奏宛若天籁。再后面,尾随着蛮婆、蛮汉等一些丑角人物,进行花样卖丑,侧面添加了喜剧色彩和生活情趣。
第四场:普天同庆。各舞各阵不再轮番上场,由集体性推出齐上台,在自身所处区域内尽情表演,也可在互换跑动的同时相互套戏,彼此反串剧情和曲艺,用“大方无隅、大象无形”来内外互动,让赏者观者尽可参与进来“一起情景表演”。最后,由旗队和幡队仗仪,重鼓开道,大锣击响,整场配合巡游,绕场周一围而欢……。
D、秧歌剧情的融解
对于“秧歌”的起源,诸多学者争论已久,本文此处也无意引证,只是从抒情极其形式上予以概括。《诗经•大序》中说过一段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也就是说,一切之歌舞形式,其实皆缘自人的心情而发,感之于心,动之以情,尔后形于舞蹈、歌以五音、表之朗诵焉。
由是,艺术的节律,即同艺术生命的心律在搏动,是自然形态运动节律的凝练和集中,它以诗的言语节律贯通艺海,涵怀于乐思和画意之中。诚然,音乐是旋律心声的诗,绘画是线条色彩的诗,泥塑是凝于固体的诗,秧歌是活动雕塑的诗,“歌舞汇演”则是这一切形象的画面与乐音的交响诗……似静欲动,动归于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宇宙万物处于一定规律的运动之中。意识形态的运动中存在着永恒的诗律。
1、民歌剧情
民诗民歌、生自方言,诗韵广录、遂成采风。
首先从歌曲的产生来说,民歌本来就是人民群众真挚感情的产物,即所谓的“情动于中”,没有真挚的感情就不会产生民歌。民歌艺术在情和声的关系上能够很自然地作到相称、统一,就是因为它掌握着以情带声、声以载歌的创作原则。对它来说,声不足以载情就说明音乐艺术的表情能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尚未能把人的“情动于中”的感情强度准确地反映出来;声过于情,则又使人感到浮夸,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不真挚。只有声、情相称才是真挚的。
其次,《礼记•乐记》曾讲:“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就是说,情之动,是由于外界客观事物的刺激。于是“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竟旄,谓之乐”。“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其意也就是说,当人们内心的情感波动需要表达的时候,那是非表达不可的,然而只有通过特定的形式,经由声音、文采、节奏等特定手段的修饰并表现出来,才能构成艺术创作。
自上古以来,民间歌曲的曲调就通过对语调的强调而将种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鲜明地呈现出来,作到了以情带声,声以载情,情声相称。这也正是舞蹈和戏曲音乐从母体—民歌—民俗中遗传下来的一些美的素质。通过任意来表现真挚的情感,这本来只靠语言就能够作到,由于语音、语调的变化,语言在达意的同时也起着表情作用。可是它加上曲调、渲染、补充和深化,就能取得更为突出的艺术效果。诚然,我们所谓的“道情”就缘自于此。
根据其旋律及唱法,可将之分为三大系:其一是高腔民歌,它的特点是高亢、嘹亮、自由、奔放,音域宽、跳动大、拖腔长,震声多用刚嗓;其二是平腔民歌,它的特点是悠长、平稳、柔和、深情,节奏多变化,拖腔不很长;其三是矮腔民歌,它的特点是优美、回旋、紧凑,音域不宽,大跳较少,节奏规整,平拖腔,多用鼻腔压韵。从总体看来,都结构整齐严紧、分段道情、朗朗上口,而且可以自由地变幻情绪,因而传习普遍。就当中的劳动号子而言,它产生于体力劳动,起着指挥劳动,统一动作,鼓舞情绪,减轻疲劳的作用。而不同的劳动,都有它各自不同的号子,如《木夯号子》、《鄜县号子》、《吆号子》等,总的特点是拙实有力,节奏感强,直出直落,抒情性少。
从“小曲”、“小调”而论,内容则主要是在“乡情恋歌”方面,如《走西口》、《兰花花》、《五哥放羊》等等都是。它们内容以爱情为多,随编随唱随流传,以七字句为主,装饰音、滑调、拖腔特多,具有天黄土厚的味道。信天游曾唱道:“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就无法解忧愁。”人们正是在这苦也苦出乐子中,乐天而知命,挥歌而解忧,是以信天游也称“顺天游”。“满天的云彩风吹散,咱俩的婚姻人搅乱;风吹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她们在歌唱中倾诉思恋之情,反抗旧礼教的束缚,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情感……。
2、场子剧情
所谓“场子剧情”,顾名思义,它就是指小型对角戏的演出——即类似于今天的小品。在过去,它也被称为“演故事”或“耍场子”,表示快而简略又富有趣味。从风格的表演来说,虽属民间戏曲形式,但其唱腔来自民歌,所以仍属民歌系分支(当然,其中也有不动声色的过场戏)。
分开来讲,它有以下形式:
(1)、扳旱船。旱船,不是真船,以木框为骨架,彩色纸裱糊,用组合花灯、花束等装饰而成。船底边沿蒙以浅蓝色彩绸,船篷形似轿顶,装饰精致,轻盈而欢快。彩船的前甲板上放有交叉的新笤帚,用绿布裹好,笤帚上穿好两只小花鞋,似坐船的双腿叠坐势。前后舱舨上安装两只点燃的蜡烛莲花彩灯,船身前后交叉系两根彩绸套在舞者肩上,如坐船状,船的两边各有一名舞伴,俗称帮船女。船的前后有两名老艄公,手持木桨,作划船姿势,用两条腿赶来赶去,做出各种动作,似船稳行波面之上,一面跑一面还唱着扳船调。坐船女通常身着彩服,头束宫发,别金簪,垂银链,呈小家碧玉状。一手扶着船沿,一手拿着丝绢回舞,双脚踩着小碎步,侧身平划如同漂在水上一样,仿佛伴随波动而颤。一般通唱:“雪里梅花雪里开,东风绕上云头来,有朝一日雪消开,呼啦啦闪上个旱船来(开场)……老叔父,小兄弟,快把路儿往开腾,我扳着船儿要起身,操心把咱的路挡定(过场)。”从总体上讲,整个编排均取法于真实的行船场面为依据,表演过程有顺水行船、逆水行船、遇漩转涡等,从头到尾以动态情节贯串。有甚者艄公船女自编对白,以各种诙谐姿态、滑稽表情、幽默的语言来逗趣观众。
(2)、踩高跷。高跷,俗名“拐子”;寓意踩者站不稳好象拐子一般。它通常取材于《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因此,经常由男孩子来主打,将双腿绑扎在一副木踏腿上,颠来复去,犹如风摆木偶一样。传统演技中有跳桌子、跌叉子、扑蝴蝶、过天桥、踩扁担等。后来虽有女演员加入,但通常使用低跷,即只有尺许,男孩的则足有三四尺,这也是生理及安全的需要。期间,因为要站在高跷上,所以往往长袍马褂,有的还糊个大花脸,是以趣态百出,好不热闹。
(3)、舞龙灯。龙灯由竹条、荆条、麦杆、莲草等扎成,有时在口内安装烟花燃放,点着时花火泗溅,来回翻舞,真是犹如活龙一般。说它有灯,有时指的是眼灯或引球灯,眼灯后来是安装着的灯泡,引球也一样,这样比以往容易使用也安全。梁元帝曾在《对烛赋》中易“烛龙”为“龙烛”:“本知龙烛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而这或许就是龙灯的由来。龙,《山海经•大荒东经》讲:“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龙经》注之:“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土,不饮渴泉,所谓饮於清,游於清者。”这其实也就是说,龙是一种综合性图腾意象,它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鱼的尾,鹿的角,虎的爪,鱼鳞和鬚……于是便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从人的精神境界上讲,它其实就是每人心底的“变通心理”,《说文》讲:“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凳天,秋分而入渊”,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舞龙舞动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它代表了“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
(4)、耍狮子。“狮”字古写为“师”,是外来语,由波斯文“师尔”一词的发音转变而来。汉代时,它随着佛教文化的东渡而传入,因此大多与佛教故事题材相关,如文殊菩萨的坐骑等等。至于它何时转化成一种舞技,则是众说纷纭,唐代时白居易在《西凉伎》一诗中,对狮子舞技的写状是:“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阴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这已经和我们目前所舞的狮子造型特征,从大体上说接近了。
3、抒情形式(即总体剧情)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眼界”里,视与听的领域本来就是融于一体,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它们相生相克:古人在提出与“五质”相对应的“五色”——赤、黄、青、黑、白的变化时,常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的变化相提并论。《吕氏春秋•识音》讲:“耳之情欲声。心弗(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心,和心在于行识。”可见,“五声”与“五色”受“五情”的支配,在形象的表现中综合,又在综合的表现中深化。
据上以言,所谓剧情形式,它们亦都是抒情的不同表现——即整场互动之间,蕴发着的“内心视象”。我国古人讲求“六根互用”,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意识相互作用,这也就是说,各个感官并不孤立的,它们是一个感官的分枝,多多少少能相互代替。因此,从整场性全局来看,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表现,而众多的表演又汇成了一种形式——总体谐和。即群体以一种自然释放的形态来展现民间艺术的风采。
在古时候,人们几乎全都相信,他们有意制造的噪音,能够吓走邪恶的妖魔,因此往往用重音来撼动全局,譬如鼓、铜鼓等等的使用。也就是说,“鼓噪”是形、声、色三位一体的,它以“舞”噪动所有之形式,或整场抒情以外的意象。是以从秧歌剧情来讲,人们对声乐或乐器发生的“谐”或“噪”的艺术感觉中,既存在着对音质、声色感受力的生理反应,又存在着发自艺术气氛感受内质的心理感应,而且,同汉民族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我们之所以往往要在广场上闹秧歌,其实就是一种以“噪”化“谐”的同欢辩证,在山间、田野和广场里……打扮得五光十色的花鼓队、高跷、社火、大鼓、重镲演奏时,不但不闻其“噪”,而且会因这“噪”而内心愉悦……谐噪合一,这似乎已经成了身心健全人们的共同心理。在由主旋律线划出的艺术轨迹的统觉联系中,除蕴含着谐噪对比因素的质感关系外,还以五声和五色的内质关系为介因,而由集群的轨迹运动方式,表现为动静和疏密的对比关系,并进而组成“异能同构”的统觉结构。
“异能”,指各个艺术门类的特殊表现性能;“同构”,指多门艺术轨迹的共同律动结构。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抒情及其形式的“总剧情”。它经由细腻心理和宏场表演的变化出来,其基本奥妙有三:一是夸张了动作的幅度,二是增强了“蒙太奇”的感染,三是明确了“主旋律”的目的。因此,演员每表现一种发自内心的思维与情感,就会带动起全身体态活动的韵律与表情,于是在深化情态语言和艺术符号作用下,相应产生出系统,明确身法和步伐,使统场宛若一如。
这样的艺术创造,在效果上将永远是最纯粹、最有力的。而当它一旦与时代的科技美相融合,就会充分地发挥出艺术感应的高强度,并具有一种进行时空转变的独一无二的吸引力。这一吸引力能够驱使旁观者加入到富有创造性的新秧歌的宏大领域中去,并在这宏大领域的舞圈中无限地延续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