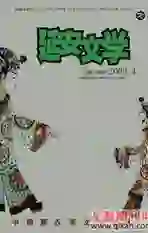与智慧为邻
2009-09-08梁捷
梁 捷
苏格拉底对我们很重要
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很少有比苏格拉底更重要的思想家了。虽然我们不可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任何知识,因为他知道的只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一无所知的人却能教会我们创造性思考和明智地生活的能力,这似乎又是别处都学不到的。
七在西方文化里可是一个神秘的数字。《旧约》里面就有“七宗罪”,中世纪的时候,很多人更是直接用魔鬼撒旦的七种形象来代表这七种罪恶。在这本书的主题倒也是“充分运用你智慧的七把钥匙”。作者说,这七把钥匙都是苏格拉底通过一生的对话和一生的行动展示给我们看的,那是另一支和圣经一样古老而神秘的古希腊传统。
简单点说,这七把钥匙分别是“认识你自己”;“提出重要的问题”;“独立思考”;“挑战传统”;“与朋友一起成长”;“说出真相”和“加强你的精神”。看似简单,却着实不易掌握。这也就是两千多年来,无数人反复阅读《柏拉图对话录》的原因。它需要被一代代人重复阅读,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它都闪耀出独特的光芒,智慧的光芒。
我们来不及细细追索每一把钥匙包含的深刻含义,事实上,这也许要花费你一生的时间,苏格拉底不就用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些内容吗?甚至连他的死都是那么平静,那么自然,那么耐人寻味。不到生死关头,一般人很难理解这种直面死亡的智慧。所以,就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把钥匙:认识你自己。
这句简洁的格言绝非只对苏格拉底而言。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对此感到困惑,甚至毕生都无法参透这个问题。是啊,我是谁,我为什么是我?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我们也许真的永远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但现在问题摆在了面前,应该如何解答?导师苏格拉底已经去世,我们只有再去寻找明师,再去访问高人。日复一日,我们坚持苏格拉底的追问精神,坚持审视自己的生活,坚持同自己内心对话,渐渐地,我们仿佛能听到内心深处的苏格拉底的声音。就这样,我们终于寻回了自我,也就找到真正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
作者暗示,这七条法则既是处理人生问题,化解日常矛盾的法则,还是我们深入阅读传递苏格拉底思想的《柏拉图对话录》等经典著作的钥匙。阅读苏格拉底有无数条路径,而我们阅读苏格拉底的根本目的也还是返观自身,寻求生活的答案,所以这七把钥匙也许是最最适合的捷径。
作者把七把金钥匙交给了我们,又出人意料地补了一章,“女性的苏格拉底之道”。为什么作者特别要叮咛女性?绝非作者或者苏格拉底看不起女性,苏格拉底就曾说,“按照性别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好比按照头发的多少判断一个人的智慧。”苏格拉底一生最尊敬女性,他的智慧也都是从女人那里得来:母亲,妻子,女教师。所以,女人才是真正的智慧守护神!
晨开的莲花
瑜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七种体育运动之一,麦当娜每天就要花上2小时做瑜伽。但又据说在练习瑜伽的人当中,每四个就有一个受伤的,可见瑜伽可不是那么好练的,它不光只是一种“休闲运动”,更是心思与情命的结合,是对光明与力量的追求,是印度教千百年来研习的一套宇宙观。瑜伽大师阿罗频多曾告诫我们,瑜伽不是一条易行的路。
印度有三圣,圣雄甘地,圣哲阿罗频多和圣诗泰戈尔。都说圣雄圣在精神,圣诗圣在文采,而圣哲阿罗频多则主要是在哲思深度上非同一般。在实在是个大大的误解。印度哪有什么哲学,“印度哲学”又怎么能光凭思考来认识,印度三圣并非印度三哲,“圣”与才智,职位,财富,武力一切外在之物都无关,它只与心灵相通。印度三圣都是在心灵的修行上达到了旁人望尘莫及的境界,这只是修持的结果。用阿罗频多的话说,他是在追求一种“超心思底精神造诣”。
精神也有造诣?精神如何来练习?统而言之——瑜伽。瑜伽是讲究行,智,信这三条原则的,缺一不可。最常见的罗遮瑜伽(Rajayoga)就是“将我们内中的元素,结合,功能,力量,皆能加以分解或消融,能从新结合,而发动新奇底前所未能底工事。”通过身体练习,我们可能摆脱关节,肌肉的束缚,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柔软动作来。这有什么稀奇。有谁能够摆脱空气呼吸的束缚,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更重要的是,有谁能摆脱熙熙攘攘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尘世的束缚,让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
阿多频多的瑜伽术不同于以往诸家,他是自创的,“…我称之为整体底瑜伽,那是说它采集了旧底各派瑜伽之菁华和许多方法,——其新,是在其目标,立场,及方法之全备上。”
众所周知,佛教不同于瑜伽,一是外道,一是正统;一个无我,一个有我;一是讲究“诸法无我”,一个讲究“梵我合一”。所以,修习瑜伽,必须首先懂得瑜伽的目标。习瑜伽者,不追求永生不死,亦不追求涅槃西方。习瑜伽者不畏惧死,那只是“有死之我”随着肉体消散,性灵仍旧退回性灵世界,安寓其中,等待新生而已。但瑜伽追求的是生命的上升,向神圣权能的靠拢,听从“神圣母亲”的召唤,最终自我圆成。
瑜伽的立场,则是梵我合一。印度素来没有历史观念,时间飞驶,历史轮回,修习瑜伽者不知换了几代,唯有宇宙,唯有大梵亘然不动。所以,修习瑜伽不应追求什么个人成就,那些都不过是易逝的幻觉,瑜伽应该追求永恒的“神圣势力”,感知她,进入她,呼唤她,在心里静思。最终,瑜伽的立场仍然是宇宙的而非超宇宙的,
再来看方法。阿罗频多和他的译者徐梵澄一样,都经历了从西方返回本土的过程。从阿罗频多的教育背景来看,他是深谙西方科学的。他7岁就去英国求学,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从他与学生的一些通信来看,他也熟练地引用柏拉图,雪莱到柏格森,弗洛伊德等古今大师的言论,与他推崇的各种“吠陀”,“奥义书”,尤其是他最心仪的“薄迦梵歌”相互参照。但是,他真正开始研习瑜伽却是回到印度之后,在印度的监狱中。四面铁窗,暗无天日,却正好帮助他摈弃了俗世的干扰,这真是阴差阳错,使得他能“超心思底进化”,真正的进行精神实践。他与“神圣者”相接触,窥见内中的自我-不死之我,这是最最纯洁的,非外在所能影响。阿罗频多身体失去了自由,却从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真正的自由。
可见,瑜伽终究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我们不能忘记阿罗频多早年参与的印度民族运动,不惜使用一切暴力手段;我们也不能忘记徐梵澄早年翻译尼采,原本是左翼青年中最最激进的一个。后来,他们都由社会实践转入精神实践,但向上的追求却始终不息。阿罗频多喜欢谈论上升和下降,但徐梵澄看来,无论升降,必须有一基础平台,在此之上才可以谈什么升降。这个基础就是瑜伽的实践。阿罗频多自称花费了三十年的光阴进行这样一种探险,终成一代大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梵语里,阿罗频多的意思是“晨开的莲花”。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修习瑜伽者也必须荡涤灵魂,这样才能心思安定,才能自我知觉,才能感受到“神圣权能”的召唤。更重要的是,莲花具有永远向上的品质。所以,阿罗频多网站的首页印着他的一句名言,所有修习瑜伽者都应该铭记,那就是“向上,超越你自己”。
学习死亡
雅斯贝斯甚至蒙田早就提过,从事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学习死亡。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有一年,我开始学习死亡学(Thanatology)。
蒙田说,“既然我看到了我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有限的,我就想从分量上拓展它。我想借我所控制的速度,借我所利用的活力补偿它的流动的急速来遏止它的飞行速度。在短促生命的范围内,我必须使它更加深刻、更加充实。”我一直和蒙田一般地设想,但又觉得这种想法过于托大,敢于遏止死亡的飞行速度;又觉得这种想法过于懦弱,在死亡面前患得患失。
哲学应该研究真、善、美的问题。死亡却是虚假的,恶劣的,丑陋的,与那三个字不沾边。但死亡有极强魅力,虽不一定毁灭,但是一个终结,如同置于命运终点处的一块磁石,不断吸引我们的注意。
西方思想界早有大量论述死亡的著作。武大段德智教授专门编过一本《西方死亡哲学》,综述这方面的思想。年轻时我曾对存在主义着迷,虽然没有哲学基础,但也总把“向死而生”之类的警句挂在嘴边。岁数渐长,见识到一些真实而残酷的死亡,思想才慢慢从存在主义退回到伦理学,死和生这两方面,都是直到生命终结都未必完全理解的。我从傅伟勋教授的著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中了解到“死亡学”。对于死亡,人们总有一些常识,多少“了解”死亡为何物。经过一段研究过程之后,才会真正感到,它是最为深刻、最难了解的一门“生命的学问”。
即使是名家、大师,面临生死考验,往往也会烦躁不安。用我最近读到布罗特(DorisBrothers)的新书《面向不确定的心理学》(TowardaPsychologyofUncertainty)的阐释,那就是对即将到来死亡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烦恼。一种内心深处的虚无逐渐将我们的生命吞噬,这是我们出生以来就有的内心秘密,长期压抑的死亡直觉,终有一天不得不直接面对。
读一些吴宓资料时,发现很多人提到吴宓晚年一直在试图预知死期,计算可以精确到日期。我们无从知晓吴宓的推算方法,也许根据自己身体衰弱的速度,也许根据传统的数术,总之他并没有算准,但是对他心理安慰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早在1969年出版的名著《死亡和死亡的过程》中,把罹患绝症、时日无多的病人的心理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拒绝,愤怒,妥协,沮丧和接受。这套范式在死亡学里得到大量案例的验证,也成为临终关怀的基本准则。
但是近来有很多学者开始不同意这套范式。他们认为,垂死的病人经历的这几个阶段,其实是医生逐渐披露信息导致的应激反应。就内心而言,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向衰弱。
人的生命时而柔韧,时而脆弱。这次的汶川地震猛地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我学习过那么多种逐渐走向死亡、面对死亡的方法,却不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数万人在几分钟内失去生命。无论他们此前是哭是笑,健康或者病痛,是否做好准备,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
我们愕然之下,很快产生一种羞愧。他们死了,我们活着,谁更好,天知道。布朗肖说,我们幸存者的“我还活着”的意识,是对一种无法分析的情感无助中脱身和释怀。我们从毁灭威胁中被解放出来,我们终于过上了失去他们后的生活。可我们都是没有活着的活者,没有死去的死者,我们总处于活和死之间;我们不相信我们听说和体会到的远方的死的经验,我们也不相信能理解其本质。
我们捐钱,捐血,或者赶赴灾区,恨不得以自残方式来缓解内心的愧疚;我们想用娱乐来躲避心理负担,却又深知娱乐会造成更深的抑郁;我们想写点什么,另一只手又把我们张开的嘴堵上。就在一天又一天的电视新闻里,我们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着。
我们并不一定惧怕死亡,往往只是惧怕最后支撑我们意识离去的那一刹。许多种宗教都教育我们超克生死对立之困惑,站在那濒死的一前后展望,所谓死而不灭,生死两通。那只是面对自己死亡的心灵控制,大规模陌生人的非自然死亡,触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却也帮助我们越过那一刹。很多人已经不能清楚记得5月12日那一刹的感觉,只是从那以后,他们死了,我们活着。
现在有个新词,Megadeath,意义与地震造成的大规模死亡有些接近。它源于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意指瞬间夺去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这个词直接导致对我们政治环境的反思。在Megadeath中,你的死与我的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人在事前指挥,也没有人能在事后超越它而冷眼旁观。
人之为人,在于人会死亡。动物不死,动物只有毁灭。按照维柯的说法,拉丁语里humanitas这个词就来源于humando,意为埋葬。埋葬同胞,举行仪式,这才有了历史,开端总是这样地被记录下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他们不再参与未来的历史,身影则会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