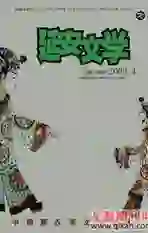梨园散记
2009-09-08罗培林
罗培林
1
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当教师的姐夫告诉我,县文工团招收学员,每月发十八元生活费,三年学习期满后,录为正式演职人员,也就意味着吃公家饭了。姐夫问我愿不愿意去。怎不愿意?我一千个同意。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学校专门给县文工团腾了一间教室,把课桌都挪在后面,讲台上放了一架风琴,还有二胡,笛子等乐器。讲台下面坐了三个主考官。我走进考场,考官问道:“小同学,你唱什么歌?”我战战兢兢回答:“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笑道“哈哈,又是这首歌”。老师用风琴给我拉了过门,我便放开嗓门吼了那首我最拿手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主考老师一致认为我是棵好苗子。当即就通知我半个月后到县城参加复试。
临近复试前,母亲将她藏在箱子里准备给哥哥结婚用的一块蓝色老布取了出来,手工给我缝了一条前开口西式裤子,又把一块旧被单洗净漂白后给我缝了一件衬衫。姐姐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黑色毛背心,又将自己的一双白色女式凉鞋“贡献”了出来,强行让我穿上,我坚决不同意。姐怒道:
“不识好歹,一家人全力以赴为你忙活,还不是为你好,快穿上!”
“不!我就不穿女式鞋!”
“小娃娃家,什么女式男式的,考演员不穿漂亮点行吗?你想不想考上?”
“想——做梦也想。”
“那就听我的,穿上!”就这样,在姐姐的精心“炮制”和威逼下,我上着白色衬衫,黑色毛背心(毛背心有点长,只好扎在裤子里),下穿蓝色裤子,脚蹬一双白色女式凉鞋。虽然不太合体,但也穿戴一新。回想起那身行头,在全乡八个参加复试的考生当中,我还是最牛气的一个。
我们一行八人坐了一辆链轨拖拉机,52公里的路程颠簸了一整天,晚上才进了县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集中到人民大礼堂门口。大礼堂又高又大,又宽敞。我是第一次进县城,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好狗日的!那房子大概能坐1000多人,听说是开会和放电影、唱戏的地方。我感到特别新奇,一会儿瞅瞅那长长的街道,街道尽头站着又高又大的毛主席塑像;一会儿绕着大礼堂跑了一圈又一圈,蹦蹦跳跳,美美高兴了一阵子。主考老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1000多名考生一下子涌进大礼堂,嘈杂声嗡嗡响成一片,把整个礼堂都快抬起来了,一会儿,从后台走出一个人来。吹着哨子喊到:“大家静一静,考试就要开始了,请乐队就坐。”这时,舞台一侧的凳子上就坐了十几位乐手。那位拿着哨子的人就开始叫考生的名字。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此时,我的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在那双女式白凉鞋上,生怕别的考生看到我的鞋。为此,我就头仰的高高的等候主考老师叫我的名字,两只脚始终勾在座椅的后面藏着。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心慌意乱,稀里胡涂地跑上台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毕,就像小偷一样溜下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偷觑其它小考生,观察有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的女式鞋。经过我细心观察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的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待心情平静了一会儿,我感到一阵后悔,自己只顾怕别人笑话那双女式凉鞋,竟然连唱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想:逑僵了,这下八成考不上了!当演员吃公家饭的梦想多半成泡影了。
在懵懵懂懂中我闯进最后的复试。参加复试的有60人,最终录取的名额是48人。我想:一定要使尽浑身解数,竭尽全力向最后一关冲刺。最后的复试场设在礼堂后面的化妆间里,主考老师和考生面对面的进行测试。见此情景,我平静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糟了,主考老师坐的这么近,我的鞋不是一下子就钻到他们的眼窝里了吗?我得与别人换着穿一下鞋?不行!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的黑底吗?再说时间也来不及,就要轮到我了,我心急如焚地东瞅瞅,西望望,眼前突然一亮,我发现身后的角落里放着一些戏箱,便偷偷退到戏箱前,脱下了那双扎眼的女式鞋往箱子缝里一塞。一下好像放下了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浑身一阵轻松。我光着脚片子走进考场,一个立正姿势站好,双手向后一背,挺起胸,昂起头放开嗓门吼了一段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紧接着又唱了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末了,我深深给老师们鞠了一躬。就在这时,有一位好心的女老师说话了:“小后生,你的鞋呢?咋光着脚丫子上场呢?”顷刻间,全场人的眼睛全盯住了我的一双光脚片子,紧接着就是哄堂大笑。
2
考入县文工团那会儿,我刚满十三岁。招收的学徒中多半是演员,少半是乐队,我在演员队。那时,文艺界很是吃香,我们这些戏娃子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每月18块生活费,38斤粮(杂粮多),练功服、洗漱用具等都是团里发,基本属于供给制。灶上管包吃,隔三岔五还能吃一顿肉,总算落个饱肚子。
最难挨的就是艰苦而近乎残忍的基本功训练。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集体跑操,跑到东河湾喊嗓子,七点再跑回团里练功,顺唱。尤其练武功:先是压腿、搬腿,压腿还好,是自己压,疼得厉害压轻点,而搬腿就不同了,搬腿是教练搬。当时,文艺刚刚复苏,老演员陆续回团,他们热情都特别高,所有的老演员都是教练,恨不得一下子就将我们培养成戏梁,推上舞台。男女教练齐动手,搬腿的搬腿,下腰的下腰,那时,他们又不太懂科学的练功方法,大多用的土办法,有时甚至动用大刑。记得,教练常常给我们坐“老虎凳”,就是将腿平放在一条长板凳上,用一条带子将腿紧紧绑在板凳上,然后教练将我们的脚后跟往高抬,抬一下往脚下垫一块砖头,一连要垫三四块,垫不进的时候,教练就用把刀抽我们的屁股,抽一下,我们就疼得惨叫一声向前爬一下,乘此机会儿,教练就在你屁股下再加一块砖头。那腿弯的筋骨痛得钻心,痛得直喊娘,那汗水搅和着泪水就在我们的脸上洪水似地流淌。
进团三个月的冬训,简直就像血与火的战场,我们那帮戏娃子个个好似负了伤的但没有倒下的战士。我当时想:再苦再痛,也比在农村挨饿受冻好得多。在走出农村吃公家饭的信念的支配下,在“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的思想指引下,我们48名小学员没一个退缩过。记得十冬腊月,拿大顶,一拿就半个小时,汗水滴到地上就结成了冰。我的大腿根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梅花斑,痛得我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上厕所竟然蹲下站不起来。为了让腰身变细变软,教练给我们亲手扎练功带,那练功带用硬凡布做成,紧紧扎在腰间的光身子上,痛得要命,气也不好出。教练不让松开,晚上睡觉也不准松开,几个月过后,那练功带就把我的皮肉都给扎烂了,带子和血肉粘在一起,后来,只好用温开水将带子浸湿慢慢扒下来。整个冬训,不让请假,不让家人来访。
临近年关,在公社工作的爸爸和当教师的姐姐来看我,姐姐见我瘦成了一个小马猴,走起路来拐着腿,就抱住我痛哭起来,爸爸也在一边暗暗流泪,姐姐哭着要看我的腿。我心里流着泪,却强忍着不哭出来,按住裤腿,不让姐姐看我身上的伤痕,假装没事,笑着说:“没事,我这里很好,你们不要担心。”爸爸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靖娃,太受罪,就不要学戏了,跟我回去继续上学。”姐姐也帮腔,让我回去。小小年纪的我被一种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坚定地回答:“不!我决不回去,我一定要学成名演员。”
第二年春天,情况开始好转,我们的筋骨慢慢变柔软,渐渐适应了环境。加之,团里开始排戏,第一本戏就是“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主要演员都是我们的老师扮演,我们这些戏娃子有扮演八路军战士的,也有扮演日本鬼子的,还有扮演喝粥等群众角色的。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我们十几个年龄相当,个头相等的男女小学员扮演八路军战士,成天起来练习那段挥动战刀的舞蹈“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后来,团里又给我们排练《大生产》、《小八路见到毛主席》等现代舞蹈,前者我和一个小师妹扮演抬西红柿的小孩,后者,我又和两个小师弟,两个小师妹扮演小八路。我们一块吃饭,一块练功排戏、一块演出、一块嬉戏玩耍,亲如兄弟姐妹,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再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叫人难堪而无聊的事,不知哪个顽皮的师兄弟就在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间开始配对对,将我们男女学员全部配成了对儿,不久,就在全团传扬开来。给我配的对儿就是跟我一块抬西红柿,一块演小八路的那个瘦弱身材黄毛小丫头片子的小师妹,本来我们之间有说有笑,亲如兄妹,这下可好,我们见面谁也不敢跟谁说话了,连个招呼也不敢打,表面看就像仇人似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十八岁,期间五年,我竟然没跟我那小师妹说一句话。不过也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虽然表面不说话,可我俩的眼睛却会说话了,我有时无意中看她,她正好在看我,我的心就一阵狂跳,脸红得发烫。有人夸她,我就在心里高兴,有人说她的不是,我就在心里骂人家。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
正当我们一天天长大,功夫也一天天长进,就要上台扮演角色之时,一场意外发生了。
那天早上,我因感冒,身体就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没有请假,继续参加练功。快要收功时,教练已离开功场,我的一个高桌后空翻,怎么也做不好,于是,我在两个师兄弟的帮助下,从一张高桌上往下翻后空翻,不料,翻到空中,我的身子被一个师弟掀偏,完全失控,一头栽到那师弟的头顶上,然后又重重甩在地上……
我的鼻梁被师弟的头撞扁了,变成了塌鼻子,右胳膊小桡骨骨折。教练闻讯赶来,命令师兄弟们将我抬到县医院。那时,医疗条件较差,骨科医生没用什么医疗器械,凭经验给我接上了胳膊,用两块木板夹住,绑上绷带。然后,就开始医治我的鼻子,医生焦急地说:“没有麻药,你怕疼吗?”我迷迷糊糊答应:“不怕!”我那时十八岁,导演已给我排了《智取威虎山》片段,我扮演杨子荣,一个革命英雄,没鼻子那怎行?再说,我那黄毛丫头片子的小师妹已脱掉了黄毛,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看到我没鼻子会有多么伤心啊!为了事业,为了爱,鼻子再疼,我决不喊疼。咬着牙,含着生眼泪花儿。医生问我:“疼吗?”我说:“不疼。”于是,医生就用铁镊子将药棉一块一块添进我的鼻腔,硬是将我那塌陷的鼻梁给添了起来。与此同时,保住了我的事业,也保住了我那段神神秘秘没有表达过的爱……
3
在“样板戏”风靡全国时,我们团排练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本“样板戏”。本来,革命现代戏的确凝聚了不少艺术家的心血,她是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艺术造诣方面达到一个新的巅峰,但是,她却被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并授予她“特殊”的使命。
那时,我对“样板戏”总有一种恐惧感,因为“样板戏”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念,全用刻板刻出一样,都有了固定模式,决不允许变样,多走一步,少说一句,都被提高到阶级立场问题。演员稍有不慎,就有挨“批斗”的可能,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记得,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团要汇报演出,县“革命委员会”全体领导都要来,尤其是,从军分区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也要来观看演出。不料,演出前两小时,我团扮演日本鬼子“伍长”的一个年轻演员因男女作风问题,被军管书记给停了职。书记和导演临时决定要我顶替。我那时只演过一些群众角色,从来没扮演过有台词的角儿,这个“伍长”还有几句台词,出场也不少,算得上是个角儿了。因为,他是一个反面角色,我学得都是杨子荣,郭箭光等正面角色,所以,让我扮演“伍长”就非常害怕,而且,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学会那些台词和动作,就更加困难了。我本来就很害怕,再加上这么大负担,我简直就要紧张死了。可这是任务,这是工作,不容退却,不容置疑的革命工作。“上!舞台就是战场!死也要上!”军管书记瞪着牛眼大声朝我呐喊。我强压住因恐惧而狂跳的心,硬撑着背台词,练动作。
戏开了,前奏一响,灯光一亮,台下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我浑身颤抖,额头冒着冷汗,两腿不听使唤,此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上厕所……“轮你上场了!”导演焦急地低声催我,我却紧张的迈不出脚步,导演急了,一把将我推了出去,我趔趄着冲出台口,稀里糊涂喊了声:“报告队长!”
“讲!”扮演日本军官鸠山的是我一个大胖子老师。
“李玉和招了!”因为过度紧张,我一下子说错了台词,台下“嗡嗡”一阵骚乱!
“不,不不不!”扮演鸠山的胖老师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他先是一愣,然后就急中生智将戏连接下去:“凭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李玉和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不会招供的!”
“是是是,是不会招供的”我战战兢兢胡乱应着声。
“滚!下去再审!”胖鸠山在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我连滚带爬下了台。
闯祸了,闯大祸了。当晚,戏一完,我就被软禁了起来,把我跟那个犯了男女作风问题的师哥关在一个房间,外面还有人照着。那师哥在外出演出时,假冒解放军蒙哄一个女知青,说自己是某部队某排的排长,然后,就和人家好上了,一块吃饭,一起看电影。可后来,老是不回部队,那女知青就开始怀疑,便暗暗跟他说的部队联系,那部队根本就没有他这么个军官,那女知青火了,就在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将他抓了去,审查了一番,他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派出所看他没构成什么实事,然后就叫去团领导将其交给单位处理。
演革命“样板戏”竟然说错了台词,而且还说反了,尽敢说钢铁汉子,共产党的大英雄:李玉和招供了!李玉和一招供就没戏了,这分明就是破坏“样板戏”,破坏“样板戏”也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一师哥谈恋爱,跟谁不能谈,偏偏谈了个知情,还假冒军官,那年月,军婚犯两年半,知青犯三年半,虽然指的是强奸军婚和知青的犯罪。但是,假冒军官蒙哄女知青不犯罪也是犯错的呀!犯大错的呀!为此,书记就组织全团演职人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文件、读报纸、然后就结合实际,批斗我们师兄弟俩。批斗的结果是:师哥受到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我呢?记过一次。
每次开批斗会,总有一个小女孩老是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偷偷流泪,暗暗伤心……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就是和我贫富厮守、相濡以沫大半辈子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