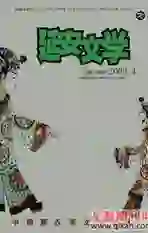泽雉:生命的形象
2009-09-08夏可君
夏可君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这一个语段出自庄子的《养生主》。这段语句,似乎是一个谜!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篇章的呢,它的前面一段大致是那个著名的庖丁解牛的卮言,后面接着的则是老聃之死其友吊之的重言。这个语段,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位置?与养生有关?启发养生之道?有着关涉养生的微言大义?也许,如此的追问,如此的解释欲望,已经陷入了语义和解释本身的樊笼了!
也许,这个语句所出现的位置,根本就没有道理!它就在那里,简简单单的句子,或许就是庄子随手写下的几个句子?后来忘记了删掉它?忘记了把它置于更大的故事的背景中,忘记去解释和说理?庄子把它放错了地方?后来的庄子门徒把它误入其间了?(如同德里达在那本《马刺,尼采的风格》的小书中写道尼采的一个奇特的语句:“我忘了我的伞”。)
好一个错置!应该把这一段涂掉抹去?!
历史上也似乎很少有解经家去注意和解释这个语段。只是在一个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毕来德(Billeter)教授那里,这个句子恢复了它本有的意蕴!并且激发了我们这里的思考。对于我们的解释传统,它似乎就是后来的错简或插入。它似乎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必要的。是后人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而插入的。是的,那就意味着可以删掉的!
庄子的文本其实很多这样的句子,没有来由,一个残篇,或者一个碎片,孤零零地被放在那里。这些句子让我们手足无措,但是,又让我们轻忽它们。或者它们有时如一道过不去的槛,停在那里,考验我们的耐心。
这一次,我们就不得不停顿在这道槛上!也许,庄子的每一个句子都是这样的“一道道”槛。一个难关!让我们迈不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庄子思想时候那样的步伐!没有他书写时的手法?思想不过是一种步伐(pas),思想每一次都是面对自己无法迈出的步伐,面对思想本身的界限!思想之为思想,在道家就是上路,走上一条道路,不仅仅是路,而是上路——走上道的步伐——是对步伐本身的反省:是对不可能走上“道”的步伐的反省。
两千年了,我们似乎就一直没有看到庄子文本中的那个动物,那些动物们,那些植物,怪物啊什么的,啊,我们总是看到了人:太多的人,孔子啊,老子啊,惠施啊,等等。我们没有看到庄子文本中的这些动物,“好个动物们!”我们当然也没有看到动物们行走的步伐!我们没有它们的步伐?因为我们是人?尤其是那些小动物,庄子文本中有很多的小动物,很卑微很卑贱的动物,鼹鼠啊,夏虫啊什么的。所谓“蝍蛆甘带,鸱鸦嗜鼠”,所谓“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我们看不到这些动物,因为我们的眼神太高了,这些小动物们在很底很低的身位上生活,在靠近大地的位置上生存,有着奇特的步子,或者,有时它们又太高了,比如那《逍遥游》的鲲鹏,那速度似乎太快了,那是飞跃的步伐。这些低低小小的动物大概是不能逍遥游的了,它们的步伐似乎庄子本人也有时不太在意。
这一次有些不同,庄子似乎是一个好的丹青高手,他在野外写生,跟随着小动物的步伐,写生——那是绘写活生生的生物和风景。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只野雉。庄子看到的方式必定和我们不一样,他描绘的方式必定和我们不一样。
让我们如此标点,表明其步伐节奏: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这一次的动物是一只泽雉,是旷野水泽地中的野鸡了,你看它,走十步——啄到食物,走百步——找到水饮;它不期待被囚禁在樊笼中,在樊笼中,即便神情如同一个王,还是不好!(传统的注释:蕲同期。犹言不期而遇。下同。李云:“樊,藩也,所以笼鸟。”神虽王,不善也。释文:“王,于况反。”不善,谓不自得。鸟在泽则适,在樊则拘;人束缚于荣华,必失所养。三喻。)——其实本来不必翻译,因为句子很简单,上面括号中是传统的解释。
一只雉,在野外,现在我们看到它,看到它的样子,在我们眼里,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步伐,它寻找食物,它饮水的步伐,十步或者百步,大致的虚数,这是说,它寻找食物的艰难?还是说它的闲庭信步?因为,野外水泽之地是敞开的。野雉可以在野外之地,不被我们注视地生活,那是它的世界。
“不蕲”:不祈求,不期待。“祈求”总是意味着意愿,它没有要被关在樊笼中被畜养的意愿。它是一直野鸡,不属于被“畜养”的人的世界。是的,“畜”——那是人对动物的看管方式。动物进入人的世界,就是“畜”,“畜”——也是界限的划分和圈定!动物,在人的畜养中,成为人类世界中的一员?什么样的一员?成为被看管者统与被照料者,被给予食物,然后动物自身注定成物被人所食的食物?这也是一种养生的方式?如同庖丁解牛,说的也是动物,庄子要通过动物来启发人与自身生命的关系?因为动物是纯然的生命或者赤裸的生命(barelife,如同Agamben所言)?或者,人在照看和畜养动物中,人成为了人!人与动物区分开来!
“畜”——是人和动物区分的开始。“畜”——是人类生活空间的开始。“畜”——是动物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开始。“畜”——似乎一定就是在樊笼中的,“樊”这个字本身即是对动物的“围圈”,把动物围圈起来,“圈养”起来——养育人类!动物就成为人类的一员,等待“被吃”的一员。
而在野外,在旷野之地,动物们的生命世界,没有明确的界限,当然,据说,生物世界是有着生命圈的,但是动物可以飞跃,可以离开这个生物圈。它们可以超越人类圈定的范围。动物,这里的野雉,不愿意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它的步伐独特!因为:“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庄子•秋水》)
人类的生活世界都是由区分和界分构成的,由围圈而形成的,一般的真理都是与划分(Ur-teilen)、与围墙一道产生。人与动物的区分是最初的区分。真理是最为精致的樊笼?直到有一天成为无形的精神,成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神经!当我们圈定动物,我们也圈定了我们的生命?也囚禁了我们自己的步伐。我们圈定动物,我们就失去了那广大的野外之地,那无尽的空旷之地?或者,我们在圈定动物时,我们其实也在圈定我们自己?限制我们?
那只野雉似乎没有看到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看着它,它有它自己的步伐,十步或者百步,寻找食物是艰难的。而如果被圈养起来,也许就有更多的食物可吃了!它没有看到庄子,庄子似乎也没有看着它,庄子看到了什么?看着何处?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视像(visionnaire)?如同毕来德教授的追问,这里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谜?庄子在成为一个艺术家?
庄子看到的是一个王(wáng,平声)?这个王的神(神情?神态?精神?)很畅旺(wàng,去声)。“旺”和“王”,声音和语调有着共鸣。似乎有着双关,看起来很神气,就应该趾高气扬!脚步迈得高高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它在樊笼之中而已!庄子看得很奇怪,他产生了错视?在交叠的错视中,他在一只樊笼中的野雉身上看到的是更加神气的另一种身位样式:一个现实的王者。庄子的跳跃很快。他的笔在急述地涂抹:那只野雉,现在被涂改或涂画为一个王!神气活现的王者!
也许这个王就戴着野雉做的王冠!这个形象,是谁呢?好一个政治神学的漫画?或现代风俗画?当然,我们在字面上绘画、绘图,王——在我们笔下,不,在庄子笔下成为了一个人——一个王!或者,有着至为尊贵的王者一般的神态!而且,如同神明一般——我们在绘文,在描绘,在涂重彩,我们要把那个本来的野雉的形象涂掉,它不好看!
其实这个句子的前面一段文本就是关于相貌的(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应该指出来的,这是关于相貌或形貌如何看待或描绘的问题):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焉。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相貌,如果是“天”给予的,是天自身在绘文,那就不能由我们人来判定其丑美了,他有着他自身存在的唯一性和合理性,是自身给予的,那是天之生命自身的书写或绘图了!我们似乎一只看不到这样的相貌或形象!因为我们的眼神已经是在人类世界的樊笼之中了?已经受到人类眼睛分类的限制了。
我们要把这个不好看的野雉涂成好看的最为神气的王?没错,野雉也可以是王!如果它生活在这个旷野的空间,并没有人为的限制分类,它就是一个纯然的生命存在,旷野就是一个可以在其间随意散步的空间,它可以由自己的步伐,而不是被囚禁在人类的樊笼之中,失去自己的步伐。
如同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一只笼子寻找一只鸟!”人类已经被自身的思维或者存在本身所限制,以至于已经离不开鸟了,需要一次次吞食鸟——张开的囚笼如同一张口。或者说,颠倒过来,连笼子本身也在渴望成为一只可以飞走的鸟!
我们现在的解释似乎也在胡乱涂写呢?我们的解释似乎也在涂鸦,不,涂鸡!庄子在野外写生,他在画一幅中国文化早已失传了的花鸟画中的动物画,可惜,这里,没有花。不,庄子不是在画大写意的花鸟画,而不是没有生命的工笔画,他是在胡乱涂抹,只是大写意:那个神气活现的王,呼之欲出!如同晚明徐渭的那些作品!那般如此的神奇,在阳光之下,那是颜色和光线本身在闪耀,试图聚集起来。
但是,突然,庄子的手停顿下来:他感受到了什么:什么不妥?什么“不善”也?也许那还是只野雉,在幻觉中,这个在涂画的形象在自身变化,时而是野雉,时而如同一个“王”,在摇晃不定。如果定格清晰下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只在樊笼中的野雉,或者华美的大鸟,比如在现代的动物园中的那些珍奇:孔雀,我们等待她的展翅或开屏,当她们开屏,那是最为神气的时刻!那个时候,她们是视野中的唯一风景,是视觉的主宰者,是光线之王!
神态的转换,一个丑陋的野雉在水泽肮脏之地低头艰辛寻找着食物,而一只孔雀或大鸟则时态畅旺,趾高气扬!但是,前者在无人之野外的空旷之地,后者在樊笼之中!这是两种神态或生命姿态的差异!卑贱和丑陋的,华丽和高贵,它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空间!在它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门槛!但是,后者是不善的,不好的!是野雉所不意愿的!庄子在涂抹后者,他要把形象还原为野雉本来的样子!
或者,他撕碎了画布,因为这个图像本身也是一个框框,一个形象的樊笼,一道槛。进入那个动物的生命空间,是进入我们原初的生命空间,在那里,我们没有樊笼。但是,我们只能停留在这个门槛上!这个句子本身上!突然,我们看到庄子向着野雉走过去,他似乎要走上前与那只野雉对话?他听到了野雉——不蕲的生命的声音?只是这个对话,我们现在才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