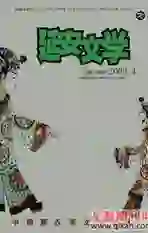现代派文学辞典
2009-09-08贾勤
贾 勤
M
美学
美学旨在反抗。美在美学之前,它被提出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分化,而且,美的概念是一个异化的征兆,此标准之建立即显示出分化之轨迹与心灵之磨难。最后,它所要反抗的对象促成了它在理论上的可能。在反抗中它渴望理解与沟通,它渴望人间的真情,但是它本质中的超越性使它曲高和寡,所谓曲高之意并非赞美,乃是它的抽象特征,而这一点恰好是人情的反动。括而言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学走向了美的反面,使美成为了一个概念。此概念遂只能表现为反抗与强调,也许美学一词应该更确切的表述为“对美的怀疑”。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所谓“诗歌美学”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们为反对人们误解自己的语言而斗争,这才是真的。
梦
梦中与古人对话。讨论二个问题。①生活问题。②艺术问题。古人说:虽然艺术问题并非最重要的,但我愿意先来讨论它。(这样的说法,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至于那个生活问题,古人并未议及。(这说明,生活难以讨论,我以前说过,很难在生活中讨论生活。)就在问题的讨论才开了个头时,古人忽然隐退了,仿佛是一种整体环境的退更,然后那古人的概念就一一变成了那些我熟悉的朋友、亲人等等。那个古人没来得及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成了真正的惟一的能够被一直保存的问题。生活一词,又占据了广大的梦境,不单单是刻在石头上。——雨果说,命运一词被刻在石头上,以拉丁文的形式。在中国,则是以篆书的形式。梦,日复一日的奇迹与折磨。
梦遗
梦遗之后,为什么后悔?你假戏真作,你付出没有回报,你动了真情而对方却是一个替身,你找不到她更谈不上追她,你不能讲理这只是生理,你不能认真这只是一场梦。可是,从此,你就爱上了一个没有名姓的女子,她不知在何处,她经常变幻身份与面孔,有时你认识她、有时不认识,有时她是名人、有时是普通人,有时她主动、有时被动,等等情形,她都很美,你都很傻很认真。总之,现在要说的是,你为什么后悔?你真的后悔吗?后悔是针对什么而言?是爱的程度,或者是爱的实现层面(情感、生理),或者是作爱的过程被打断,或者是过于压抑(因为梦中双方都没有多少语言,沟通依赖于感应)——语言仿佛是爱的证据,但其实语言并不能承担此种重负。那你到底后悔什么?一开始你并不后悔,你只是喜悦,只是狂喜,只是暗自高兴,仿佛真有所获。后来却有所不同,你要在现实当中对应落实此种梦境,也就是说,美(美人)要寻找她的形式(身体)。这意味着,梦醒之后,冲动没有停息,秘密的性欲从梦中来到人间,此种跨越将性行为从虚无中拯救出来,但是你却终于后悔了。为什么?你为何感到空虚?与其说是后悔不如说是空虚。你失去了梦中绝对的自由,被迫恋爱身边某人,尤其难以容忍的是你还要假装她正是梦中人(仍然是替身),美的形式无法满足其自身的内容,美人其实只有身体。你要不要?你无法再回到梦中,床上多了一个人。
谜-密
美学的事业乃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最终表现为“谜”与“密”,谜是人生,而密是历史。两者皆不可强解,内密外谜正是我们熟悉的“事业”(易传云: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也是写作推进的形式。诗人的情感永远是一个秘密。在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中,只有他们还拥有暴风雨式的感情,而一般人却只会作梦,然后在醒来之后否定它。诗人却致力于梦境的恢复,着迷于那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场景,以及暂时摆脱死亡的狂喜,迫不及待的放弃一切,只为保存某一次纯属偶然的幻像,祈求它能重现。而那些永恒的事物真得就默默矗立在那里,在等候。象征之物最终被赋予象征的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
命运
个人开始觉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命运之时,想像中的命运之神就产生了。一开始,仿佛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之神,随后人们发现了规律,就比如每个人都有属相或星座,但很快人们发现星座与属相的数量是有限的。人们发现命运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尽管人们仍然在乎命运的差异,但已经无力主动的选择它了。在古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仿佛是三姐妹,是“必然”的女儿:阿特洛波斯、克罗托和拉刻西斯。所谓有限恐怕是指命运的三个阶段:开始、经过、结束。——她们如此分配任务:克罗托纺线那生命之线,拉刻西斯挑起波澜使生命之线遭受考验,而阿特洛波斯的字义却是“不可避免的”,她要剪断那线,于是生命终结。
在我们汉代的《白虎通义》中,命运也被分为三种:寿命、遭命、随命。——寿命是正命,是善始善终者,是一个人所得于天的全部(不论长短),是不考虑意外情况的发生计算出的一个单位。遭命是非命,行善得恶,祈福不应,于是,在正义的立场中我们无法解释君子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随命是应命,因人之不同作为而赋予人相应之命,善恶随报。总之,天之所付与我们的生命就是命运展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因其主观的认识而得到的东西就是命运的内涵。无论何种人都将得到命运的考验,他必须经过此种历险或者才能完成他的任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使命”,即是说,人类仿佛是命运最好的使者。
N
尼采(Nietzsche)
海德格尔(Heidegger)论尼采形而上学的五重性:①本质:强力意志。存在者本身之存在。②实存: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③真理的本质:公正。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④真理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强力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⑤人类:超人。为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要求的那个人类。
纽带
114查询小姐。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丰满的文本,就是我说的那个要素,存在物之间的纽带,罗兰•巴特说的“文之悦”。她有声音,有情绪(在控制当中),有回应(单独回应于人物之间)。她的意义在于充满。她既是空白又是内容,文的最高级形式,并且此种形式仍然认同语言(非装饰性的语言,语言在释放声音,得到你的确认)。她是最令人满意的意外,完全永远的独立于现象界的照应之外。你不能去找她,尽管她肯定在某处,但并无地理学上的意义。就算找到,她已变化。此种变化包含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冲动,而这也是文本的严密性所在。这样,读者与人物双方才始终是安全的、秘密的。一种始终对立,却并不矛盾的关系令阅读成为可能。那么,再次阅读势必成为检查文本的新标准。不同读者的阅读亦是重复阅读的延续(变相)。一面镜子照出了不同的人,此人势必不能在镜子当中寻找自己,他将陷入与人相逢的人生中去。所以,文本之外的寻找是毫无意义的,人物早已各就各位,而寻找者却始终觉得他们处于变化之中。人生与阅读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能否重复是个关键。于是,再次阅读得到了人生的保障,而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特殊爱好。从寻找到阅读的蜕变是个关键。既然能够观察(即阅历、阅世、阅读),又何必寻找?与其寻找,不如直接成为作者。巴特以为,阅读本身甚至就是成为作者的一种途径,你直接成为当下文本的作者。我说过,不必寻找,一切早就安排好了。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你创造了你寻找的东西,通过阅读与写作都能够成为作者。
O
○
如果将O这字母看作是数学中的○的话,应该比较有意思。德国数学家弗雷格说到数学中的零时,是用哲学家的口吻来描述的:“零(○)是一个与自身不相等的概念。”在此描述中,零有点像中国太极的外圆(一个○),而太极是什么同样没人知道,它是否与自身相等?或者它只是无?太极的概念当中于是又增添了无极。弗雷格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在与自身不相等这个概念之下没有任何东西,因此零就是这个数。”
在哲学中,零是指存在的原初状态。但它不是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零,作为一个数,既不比其它数大,也不比其它数小。它仿佛是数字的边界,仅此而已。维特根斯坦这样说过:“我是世界的界限,你是我的界限。”充满了无奈的探求,但是没有挫折感与失败的沮丧,相反,话语中指明世界有其本质性的边界。此种边界是司马迁说过的“天人之际”的际字。際(繁体际),事物相会之处留下的缝隙。这个际字,完全是从启示中获得的。说文中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下面的小字其实是三竖,所谓三垂日月星也,上面的二是代表天。观象于天得到了启示,明示人以吉凶。从此,伟大的历史学家都致力于探求那个存在的界限(际),这正是西方史家所谓的历史观念或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那个“绝对”。
P
排比
排比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要欲擒故纵的加速此种修辞的反动与暴露,然后毁灭它喋喋不休的罗列。排比句注定要失败。对现象世界的罗列注定要失败。妄图通过一种连绵不绝的语气来模仿永恒的节奏注定要失败。一切隐喻注定要失败。就在文章展开之时,如同身体展开之时、如同黑夜展开之时、如同柔情与创造展开之时一样,排比句注定要出现。如同你出现在另一张床上、如同光明出现在黑暗中、如同狂乱的想像遭遇呼吸的停顿,排比句所营造的高潮注定要失败。身体的要求与快乐注定要失败。要么抚摸你,要么嫉妒你,性别的差异既可以使人欣赏,也可以导致迷惑。为什么我不是你,如果是你,第一人称就将失败。出现了两个你,而没有了我,他人之中将没有我的位格,都是你。同一的立场,同一种元素,爱你注定要失败。水火相憎,男女妄图僣越自己的归属,一索再索,渎则不告。水火在既济之后的空虚使得人生看上去有了思索的余地。排比句之后,文章仿佛要从头写起。而你我之间的纠缠只在人称形态上略具意味。线索所引出的主题并不能令人惊奇,影响世界的全部没有办法充分曝光,那需要一个更加广阔的宇宙,更加强大的光明。在你的眼里,我只是一个线索,它引发了你的问题,但我并非此问题的要素,你在我身上创造了你要求的意义,可惜我的对象始终隐藏,我的排比句似的表达注定要失败。我还有什么?我不想再使用“你”这个字,这并不会影响你的存有,更不会伤害你。在没有你的文章中,势必会出现广大的空白,如同人生中出现了空白一样,通常我们都会用想像去满足它,而在那空白之处(也就是真正的现场),隐隐约约,我们找到了约会的地方。众所周知,人称是开放的。
批评
作品本身就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它阐明了作者在写作当中如何对传统作全面的理解与运用以及批判。
Q
气候
许倬云先生曾经考察过气候的变化与民族移动的关系。他说:“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长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国的纪录。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他引用了竺可桢先生的气候学研究,发现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颇多契合,这不能完全解释为巧合。大抵气温在相当一个时期低于平均温度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受到威胁,才与中原发生战争。气候是多么直接的“天道”,植物的生长周期一旦被缩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破裂了,至此,由寒冷导致的迁徙遂改变了历史的命运。战争几乎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果之外,更大的循环使人投入,这种循环就是生活的力量。“生活,生活,不惜一切代价地生活。”——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如是说。
墙
与黄河不同,没有人试图去寻找长城的源头。它从开始的时候开始,随时随地开始,区别于河流。没有人用河流比喻长城。长城是墙(wall)。诗人成路写过“边墙连接的灶火”(在此我却不打算谈论边墙与火热生活的关系),边墙的边应该理解为界限,某种划定,二者之间,而非一极。边,指文化的警惕性而言,不同文化的界限就是边。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文化边缘耸立着墙。墙,就地涌起。从空间中涌起,所以我才说,人不会去寻找它的源头,它不像河流一样在空间中推开。长城,你可以走上去,沿着它的脊梁走,果然不像河流。是的,它不可渡。不是说,你可以轻易臻于彼岸,两岸之间不同于墙里墙外。你走在这条界限之上颇不同于顺流飘荡或逆流而上,长城没有那种绵延的流动与阻力。在界限这个意义上,它的内部略无阻碍,它指向两边的辽阔。
强喻
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了“强喻”的概念。语言就是强喻(语言=强喻)。更早的时候,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层层推进,仍说不清,此即强喻。道本身是什么虽然说不清楚,但可以强说道“大”,大的观念较易建立,然并非大小之大,而是观念中的大,不Big,而是Great。由此推论:①不同语言描述同一观念必然不同。②同一种语言描述某些概念也不尽相同。③前者为名词之类,后者则是观念性的,也就是说,生活的语言是可能的,而哲学的语言却受到语言本身的限制。讨论哲学须另创符号,另起炉灶,除语言之外,哲学(观念)亦早就存在于人脑之中,所以不得不讨论。故人类生活中几套系统遂并行不悖。强喻的事实遂亦并不显得那么夸张了。任何对于本质的发现与重新描述事实上都在本质的表现当中充分展露过了。思想家的所得未必对大众有多大意义,尤其不能夸大此种意义。④要知道,强喻的背后仍然是事实本身。⑤语言既是最高级的,同时也就是最后的(最后即强喻,没办法的办法,硬上、强行)。比如登山,最高处乃是一种纯粹的象征,人类所征服者乃是欲望本身。又,语言(叙述,说)与文字(符号,写)是世界的基础。
情感
情感对语言的依赖。情感是否总是需要表达?我们理解自己,只是拙于表达,但是真的需要表达吗?表达的太多太久,情感终于平淡了。也就是说,它摆脱了对语言的依赖。此即无言之境。“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一种情感的理解,所以从一开始道就排斥语言。与生活平行的语言想要说明生活何其艰难。误解由此而来,越说越急,直至无言以对,此种沉默乃是出于被迫与无奈,不是懂得沉默以后的沉默,当然亦有可能借此契机理解沉默之必然。于是我想到人类最初的沉默,以及初次打破此种沉默的欣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