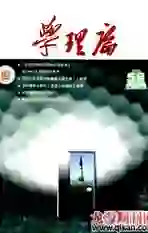交往:回到德育的原点
2009-06-15余芳
余 芳
摘要:交往德育是师生共处主体间意义关系情境,通过对话和理解,得以不断觉解与境界提升的道德教育活动,它是一种和灌输德育截然不同的德育理念,是对灌输德育的扬弃与超越。彭未名教授在《交往德育论》一书以交往理论为规范基础,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大学德育及德育研究中的种种人文缺失的弊端和误区做深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评述,并由此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交往德育”。
关键词:交往德育;灌输德育;书评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39—02
德育回到原点——交往,这意味着解放德育,也意味着人的快乐、自由与解放,因为快乐、自由与解放,真诚与美好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个交往——互动、互融的自我实现过程。因此,研究德育不能不研究交往。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彭未名教授撰写的著作——《交往德育论》一书正是做了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变”中寻“宗”,以应对万变——让德育回到交往这一基本问题,让人性复归。
一
在灌输性的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及受教育者均困陷于特设观念的藩篱、淹没于固定知识的洪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探索,以及对交往和觉解的期望、对美好而真诚生活的企求,便构成了交往德育论基于“宗”的反思性探究与建构的“一以贯之”的主线。作者以坚定的信念认为:反思,即人自己思自己,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交往德育作为解放了的、回到原点的德育理念,可以为灌输德育——一种对人的强迫、控制的德育理念——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思路、一个方向。在这里,德育——一个主体间交往的对话、理解、生成和共享的过程,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和中介,其间人作为不完善的存在,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并试图在主体间性交往中使自己不断觉解,变得完善,同时也使生活变的真诚而美好。它是师生共处主体间意义关系情境,通过对话、理解和生成,得以不断觉解与境界提升的道德教育活动。它是一种与灌输德育截然不同的德育理念,是对灌输德育的扬弃与超越。
二
《交往德育论》从文化和自我、交往与觉解切入,最终回到人的自我觉解,其中交往作为快乐、自由的实践和真诚、美好的生活的精髓,使得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生成意义”,共享快乐、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灌输关系与交往关系体现相互对立的文化范式,前者是强制,后者是解放;前者是目的理性的——主客二分的征服、分治和文化侵犯,后者是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的互动、协同和文化融合。德育本来便是一个文化现象,交往德育作为一种区别于以儒家自我及以他人为中心的文化力德育、观念自我及以观念为中心的政治力德育、物化自我及以个人为中心的科技力德育的以交往为中心的文化力德育,则更是一种文化存在。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交往德育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文化存在,是一种人的存在生存,其真谛乃是冀盼作用于师生真诚而非扭曲的交往,指向一种“美好而真诚”的生活。在此,交往不仅仅是一种德育方式,它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理念。作者通过对灌输与交往、对德育和人性的阐释,对交往的德育意义和德育的交往意义的剖析,提出并建构交往德育理论,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每一位意识到在德育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教师和学生,都应该读读这本书。我相信,《交往德育论》的付梓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景观。
三
《交往德育论》将大学德育置于作为现在的过去和作为未来的现在背景下展开反思,并将这种反思贯穿于建构交往德育理论的全过程。它体现着一种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结合。《交往德育论》审视了大学德育在中国大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及在当代的价值走向,并对此做“价值介入”式诠释。中国大学德育发端于古代儒家文化推动德育的时代,随着文化、自我与交往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发展,大学德育显现出泛政治化倾向——强调政治功利目的,从政治关系出发,通过政治力来推行,造就的是观念自我;当前的大学德育则主要从经济关系出发,以经济力(表现为科技力)推行,具市场性要素和科技性特质,导致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此三种德育均属灌输德育,其“自我”是扭曲的、非健全的。真正可使自我本性回归和价值呈现的德育理念,当是交往德育。交往德育置德育于文化领域,从生活世界的交往出发,通过“文化化人”生成道德规范和觉解了的人。《交往德育论》之德育研究对大学德育则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且不是为了别的东西,而是为了德育本身。道德价值不都是外在的,还有所谓“内在的价值”这种东西,那就是德育本身的使命与旨归——人的真诚而美好的生活。
四
在《交往德育论》中,作者对占主导地位的灌输德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交往德育的主张。但是,他对灌输的诠释性批判,不纯粹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愤懑和牢骚式的表情脑力活动,它表现出一定的智慧和勇气,这种智慧和勇气,来源于一种非常真实和有形的体验,诚可谓是“修辞立其诚。”(《周易·文言》)从作者的经历中,我们可见一斑:作为在大学里学习和研究的学生,他直接与五所大学的教师有生师之份;作为在大学里教书的先生,他至少与三所大学有缘,——迄今历时二十余载。这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体验,没有特定的起始日期。尽管他根本没有达到我认识的一些人所体验到的依附与压抑程度,但也不是那些浅尝辄止的人所体验到的滋味。相反,我们的被动和占有是那种不宣而至、不请自来,甚至是自然而然的、无拘无束的拘束,摆脱它更是要付出大的努力。这种精神的“强迫”如不像我们曾遭受的物质的“强制”那样得到缓减,它便会占据我们整个的身心,使人变得萎琐麻木,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这种学习生活,而今天的灌输德育仍在影响着成百上千万的学生。他们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灌输下郁闷、烦躁、麻木——他们不是被鼓励或训练来认识和应对具体的现实,而是被“湮没”在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出现批判性反思意识和自我觉解反应的“沉默”或“休眠”状态之中。可见,交往德育的信念植根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用以说明德育并没有终结的社会憧憬是以广阔的生活世界的经验背景为支柱的。
五
在这里,交往不是一种机械化了的口号式观念、社会活动和教育实践,而是一种生活信念和德育理念,指向生活的真诚美好和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交往德育理念与那种仅仅反映交往方法的空洞的陈词滥调有着天壤之别。为此,我们有必要领悟作者超越教室空间并对社会将带来益处的交往德育主张的精髓,以及理解交往的认识论关系及意义。
过去的有些德育学著述要么过多地把经验挂在嘴边,构成对本体简化论的看法;要么错误地将交往概念转变成一种方法,从而看不到方法背后的理念问题及事实。交往德育论力避把本体与经验从权力、行为和历史构成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群中分离出去的危险,也力避把交往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当然,作者更不想将之变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因为这会在一方面造成把交往德育转变成一种引起对话交谈的方法,为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牢骚的或无聊的群体治疗;另一方面,会误以为是在为教师提供一个处理课堂过失的安全可靠的教育空间。这其实还是灌输德育。交往须要对知识客体和世界客体及人的生活有一种持久的热情。因此,交往德育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更好地理解知识和世界客体的理念。否则,交往德育便成了对话交谈,只注重谈论个人的生活阅历。——它超越了建立在矛盾的两极分化以及不加鉴别地求助于经验话题的基础之上的不同观念。
六
灌输德育往往使用相同的语言,视其为普遍接受和应该接受的一部分。这种普遍接受只有“标准”话语才谈得上,要么就是霸权话语——是不应受置疑的。随着这一切的发生,语言便产生了新的力量。语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人在交往和生活过程中借以发现自己并发掘潜力的手段。进入交往,每个人又重新赢得了说出自己的话的权利。当一个学生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此种教育体验,他就会逐渐获得一种新的语言和新的自我意识,发现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是生活的创造者,而且他们的整个学习可以是充满创造性的。随着那些被排挤在德育边缘的人得到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再也不会愿意只充当客体,只会被动地应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教育及周围的变化。他们更有可能决定投身于变革教育结构和生活结构的活动,借助交往,德育可以摆脱传统的结构并得以实现现代化。
我们不难看出,把彭未名教授的交往德育主张机械化,这不仅会导致交往德育论的非价值介入的误解,而且还会认为交往德育是一种“德育”方法,而不是一种德育理念。交往德育论是以充分发展了的哲学人类学(即人类本质的理论)、交往理论和觉解哲学为依据的,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世俗的德育学,它拥有自身的特质,不可以复归到任何其他的德育身上。对《交往德育论》中所提出的德育主张的可能的误解,不仅在于把其德育目标——把师生从“占有生存”转变成“存在生存”、指向“美好而真诚”的生活——非价值化,而且在于使交往德育的思想脱离了它对包括哈贝马斯、马克思、黑格尔、萨特和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传统的大量借鉴。
七
在当今中国社会及大学面临转轨和关键性转折,以及具有标志意义的新时期开启的时代,作者将目光投向大学德育面向未来的有效理念及优效模式的预制,其意义也许在于对德育人文缺失之困境和边缘化情形的反思,及对交往德育的期许和希望。
当然,处在这样一个思想、道德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任何道德教育理论都会受到不同观念的挑战。交往德育论是以当代中国大学的道德教育为理论背景和依托的,因而主要是以当代中国青年学子的视角来看待道德教育的。这样,在交往德育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就相对忽略了中小学品德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忽略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中的道德交往。另外,交往德育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初步的,更多深刻的思想观念还有待于今后的探索,这就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如对传统德育的界定、对德育形态的划分标准、对交往的理解和交往在德育中的意义等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德育及德育研究要回到原点。大学德育要不断凸现师生作为人的本性、作为主体的自主性和作为自我的个性。《交往德育论》正散发着人性、自主性和个性,这将成为一种使我们始终把人当作人、当作主体来理解的永在的力量。
让我们以交往解读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