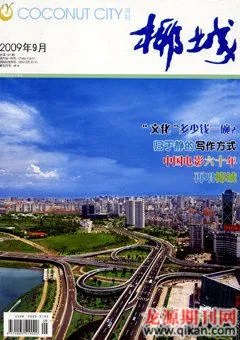小说二题
2009-06-04严敬
严 敬
保安室
好多地方都在闹禽流感,鸽场也跟着封场了。我们在给鸽舍消毒的时候捡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某女工的老公写给她的。我们很奇怪,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有什么事一拨手机就明白了,居然还有人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传情达意。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老婆,亲爱的老婆:你好!
我非常想你,我一直都在想你。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你知道吗?整整半年了。你那个鸡巴工有什么干头,说封场就封场,跟蹲大牢似的,人都要憋出病来了。你上回问我受得了不,我可真受不了。受不了怎么办?也得受啊。镇上我可没有去过,即使去镇上,我也是办正经事,从来不干那事。听他们说,镇上有很多小姐,都年轻水灵得很,都是从外地来的,花几十元就可以和她们中的一个来一回。中秋节那天,阿发邀我到镇上去,你知道,我和阿发是好朋友,我就请他喝了酒。我们都喝得有点醉了。我们暂时都不想回家。你知道,利利我让他到爹那里过节去了,你又不在家,家里空荡荡的,我真的不想回去。阿发的老婆也不在家。我们就想在镇上耍耍。我俩又跑去喝起茶来。后来我经不住撺掇,就和阿发去了那种地方,但是,我什么也没干,我向你保证,你可以回来检查,听说小姐们大多数都有脏病,和她们干了,很容易传染上。我干没干,等你回来就知道了。有一位小姐,相貌也过得去,她叫我“大哥”,要我到她包间里去坐,我想,她肯定是要和我干那事,我吓坏了,我没应她,趁她没留神,我不声不响地溜了。阿发还在屋子里,他要有什么意外怎么办?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自顾自逃回了家。这是真的。这事千万不要对阿发的老婆讲,你要发誓,不然阿发就要恨死我了。我本来也不应该对你说,但你是我的老婆呀,我不该有事瞒着你不是。你们快开场了吧,我的那玩意都要生锈了,也该擦擦了,还有一个月行不?但是我一定等着你。
你忠实的老公
保安室被辟作了会客室。这点子不知是谁想的。刚开始大家还只当它是保安室,在大家的眼里,它就是平常的保安室。过了一个月后,也许是两个月吧,许多人倒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地方。它的位置处在场大门口,正好是咽喉部位,无论是外面的人,还是被封在场里的人,都要止步于此。最后有人提议,何不将保安室改作会客室。这个提议起初是当作玩笑说出来的,说的人肯定也准备一笑了之。并且有人注意到,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是被关在鸽舍里的人,而是一个处在封锁线以外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简直有点幸灾乐祸。
有的小孩被带到保安室和他的妈妈相见,小孩或许是五岁,或许两岁,甚至是正在吃奶的。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们就是一些男人。有的男人装着给老婆送东西到这里来,磨磨蹭蹭和老婆见一面。也有男人不愿到这里来见老婆,这些男人不乐意叫人看出他们在想老婆,他们认为让人看出自己想老婆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但也有男人非常高兴,他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频频举杯庆祝自己终于成了脱缰的野马。
保安室以前只有一张光秃秃的弹簧床和一把长椅。小孩们来的时候可以在上面尽情玩耍。弹簧床立即变成绷床,他们轻轻跃起,然后落下,弹簧就会把他们的躯体向上弹去。他们玩得专心致志,他们的父母足以安心地说上好一会儿的话。后来有人为孩子着想,在弹簧床上铺了一张凉席。承他(她)想得周到,如果不这样,弹簧就会在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吃进他们的肉里去,那种精致的花纹印得很深,久久不能消去。对于孩子们细嫩的肌肤是如此,对孩子们的父母,弹簧床就更不肯客气,它们往往扎得还要深。不过,大人们对此是丝毫不会去计较的。
因为保安室的窗户是三面透明的,毫无遮挡,一眼望得透穿,有人建议给它装上窗帘,理由简单得要命,现在它变成了会客室,是家人团聚的地方,那么,它就要保护住一些家庭的秘密。没有人反对。大家心里都很别扭,虽然都发誓在此不可能制造出自己家庭的氛围,但是,谁都保证不了,以后自己就一定不在那里会见自己的家人。即使是支持给保安室挂窗帘的人,也不好意思说得出口。如果说出来了,无疑表明自己将要把保安室看作是自己临时的家。幸好有人行大于言,默默无声地干了。其实并没有要场里开支一分钱,只不过是用旧报纸将窗户糊住而已,从外面再也瞧不见里面的动静了。与开始所说的窗帘,大相径庭,然而作用却是一样的。开始一说是窗帘,浪漫的人马上想到那种温馨的富有情调的豪华宾馆式的款式,这样的窗帘,厚厚的,从房顶上垂挂下来,像一堵严实的墙,密不透风,但要说服领导同意购置,是不可想象的,除非领导也来此享受一回。出乎意料的是,现在有人不声不响替大家办成了这桩事。
吃完晚饭后,许多人都沿着场区的小路绕开了圈子。从高处看,缓缓移动的人群像一个转动的磨盘,从磨盘里传出吱吱喳喳的响声。大家有用不完的气力这样一直转动下去,接下来的夜晚就容易打发了。
夕阳睁着巨眼厌倦地瞧着这些被围困的男女。它早已洞悉了他们的心事,它无法给予他们一点点同情,假如它对他们还存有哪怕一丝的怜悯的话,它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落下山去。
又一个姗姗来迟的夜晚,和又一个漫漫的长夜。晚风是撩人的,开始它藏在椰树的叶梢上,轻轻地滑溜,划到我们的脸上,再往后,它变得残忍起来,从暗蓝的夜空下,从整棵树的身上,朝我们吹洒过来,蹂躏我们的心灵。
刚吃完晚饭,就有人扭开了音响,放出那段喜气洋洋、如同奔驰的车子一样的“芭比女孩”。我们跟着这两个身材苗条、姿色艳丽的女孩跳起舞来,我们学着她们朝上举起双臂,往旁边踢自己的双腿,还左右扭动长满赘肉、僵硬的腰。所有的女人都沉醉在“芭比女孩”之中,她们肆无忌惮地让自己饱满的乳房和庞大的屁股朝四方扩张。在另一面雪白的墙壁上,是她们舞动的影子,影子相叠,尖削的手指夸张地增长了好几倍,使她们看上去变成了一群张狂的魔鬼。每一个完美的音符都变成一磅重锤,敲打在这个叫做“心”的铁砧上。
天早就黑透了,菁菁从舞场退下来,她到大门口,朝外张望起来。她又来到保安室。保安室里另一个女工已坐在里面的长椅上。她明白,她晚了一步。那个女工抬头朝她望了一眼,眼里闪动着隐约的歉意。菁菁走进去,挨着那女工坐下。
菁菁说:“今天,没跳舞?”
“今天,不跳了。”
“老公要来?”
“嗯。那死鬼,说来总不来。还害羞,还说看老婆,怕人家笑话。”
“今天,肯定来呀。”
女工抬起头,菁菁和她相视一笑,转身走出保安室。
菁菁走进场门口一棵树的阴影里。她面对着通往外面的那条大路。路上铺的石灰被灯光照得发红,杂乱的脚印,此刻显得更加沉寂。在路拐弯处,怱然出现了一盏灯,灯光越来越强,是一辆摩托车。来人到场门口,隔着大门,他没有看见阴影里的菁菁,他犹豫了一下,伸手掏出手机,刚要拨,保安室的女工就走出来,冲他招手。男人被领进了保安室。
真有趣,头顶上的夜空被分成了三块,先说西边的吧,那底下是城市,繁华的灯光映红了半空,使那里像燃烧着的彻夜不灭的晚霞。城里人在做什么呢?购物?喝茶?忙着和情人幽会?总之,城里人夜晚比白天还要忙。
转弯的地方又有一盏灯。菁菁的眼睛对准了它。她渴望它朝她驶来。但是,这条道只走一半,它就拐上了另一条道。唉。再看东边的天吧。月亮升起来了,红红的,仿佛一张羞怯的脸蛋,它的嘴唇抹了口红,鼻子上也有,甚至眉毛也是红的。木麻黄的针叶轻拂着它,宛如披拂在它额头上的一绺秀发。这张脸庞被一双看不见的大手捧着,奉献在东边幽暗的天空上。从家里到这里,起码有五十公里,不过,骑摩托车也很快的呀。菁菁倚身的这棵树,开始她以为它有影子,其实没有,现在慢慢有了,越来越浓了。突然,离她不远的一块矩形的月光熄灭了,她蓦地一惊,随即那处月光又亮了,明亮的月光好像为了检讨自己的过失,亮得比先前更厉害了,似乎表明自己再也没有消失的企图。菁菁望着保安室想笑,但是,一股酸楚的泪水却堵住了她的胸口。她扶着身边的树,把一把鼻涕擤在树的身上。
头顶上的夜空是水绿色的,既深厚又轻盈,那儿滑翔着一股巨大的无声的凉风。几颗星星不停地洗濯,眼神明亮而又感伤。菁菁想,他大概不来了。他也害怕别人笑话。
保安室里悄无声息,灯光亮得小心翼翼。
月亮渐渐走到头顶,菁菁和树变成一个雨伞般大小的阴影。皎洁的夜空,有时飘过一片浅色的云。“芭比女孩”仍在狂舞,强劲的舞曲如同火花朝夜色迸射。月光下一个人朝场大门口走来。菁菁知道那是场里的一个保安人员。等那人走近,菁菁差点惊叫起来,那人居然是她老公。菁菁仍缩在阴影里,好像故意留点时间好打量自己的男人。男人焦急地张望起来。他的脸显得光洁,没有往日的汗渍,甚至那些醒目的疙疙瘩瘩也不见了。他的双眼灼灼发亮。这张脸使菁菁觉得陌生,她从这张脸上看出了蕴积在他身上的一股野蛮的令人激动的力量。菁菁从阴影里蹿出来。
他们只能隔着大门说话。“你能出来吗?”男人说。
“不能。”
“就一会儿。”男人说,一边扭过头朝他身后的橡胶林看一眼,“没人看得见。一会儿。”
“不能呀。”
“我进去。”
“更不能。”
“那,怎么办?我不能白来。”
“就这样说说话呗。说说话也好啊。”
“当然。”男人说。“但我一点也不甘心,我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
“别说傻话,我也想。”
“出来,从这大门上跳出来,一会儿就成。”
“不行。我会被开除的。”
“开除就开除,管它那么多,总之,我不能白来。”
“你。”菁菁说,“这样还不行吗?”
男人不吱声。过了片刻,男人轻声哼了一声。菁菁说:“我们再聊一会儿,我们可以到保安室。”
男人往保安室去,菁菁说:“等一等,那里面还有人,再等一会,就可以轮到我们了。”
菁菁隔着铁栅栏门被男人紧紧搂着,菁菁想推开男人,却又更急切地将自己送上去,承接着自己的男人。他们的一部分从栅栏的空隙处到达了对方,另一部分则被阻挡得若即若离。菁菁说:“别,别这样,要被人看见的。”
男人凶狠地说:“我不怕,你是我老婆。”
菁菁送走男人的时候,月亮早就偏西了,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蹑手蹑脚回到鸽舍。她正要上床,忽然睡在另一个铺位的姐妹问:“老公来了?”菁菁没应。“老公心疼你啊,跑这么远犒劳你来了。”菁菁骂起来:“死样的,还不睡觉。”姐妹说:“别忘了,我也心疼你,我煲了一只鸽子,在电饭锅,快吃了吧。鸽子补得很,一鸽九鸡嘛。”
去海南
霞是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当她知道我回到家乡,非常高兴。我们见面时,她竟毫不隐瞒她的喜悦之情。看来,我们有可能坐下来叙叙旧了。她经营着一家百货批发部,常常有人上门做生意,所以我们的话题屡屡被打断。于是,我提议,我们另找一个时间和地方再聊。她同意了。但是,她疑虑起来:“我们在哪儿聊呢?”我装着思考的样子,然后坚定地说:“到我家里。”她看了我一下,说:“就这样。”
她应该考虑到了我们见面后可能出现的结果。虽然我也想把结局导向我策划的地方去,但是,事情最终没有出现这种结果。整个过程一直都是很顺利的,最后,到了关键的地方却卡住了。
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家了,打开家门,到处布满了灰尘,为了晚上的约会,我着手打扫起来。我只保留了房间里一盏灯线路的畅通。霞款款而来的时候,立即注意到了我家照明的现状。在踏上楼梯时,她现出片刻的犹豫,又一次说道:“灯呢?”“线都断了,小心。”说着,我轻轻揽住她的腰肢。星光穿过窗棂,映在霞丰润、绷得很紧的脸庞上。坐下了很久,霞怱然拂拭了一下她搁手的沙发布面。我马上意识到,沙发上仍粘有我没有擦净的灰尘。这差不多等于告诉我,一切到此为止。之后,霞嫣然一笑,说:“过几天,我妹妹也要到海南去,假若她愿意和你结伴而行的话,那么路上请多关照。”这是那个晚上霞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像她就只专门为表达这个意思来的。接着,我引她下楼,我们一起穿过底楼的黑暗。
结果刘云从广东的一个城市返回到家乡。其实,她这样做与她的目的地完全背道而驰。我推迟了我的行期。刘云似乎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如果她直接从广东到海南的话,这些事情都将被省略。在这几天里,她看望了她六岁的儿子,与过去的朋友相聚,甚至还会见了她的前夫。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已启程,都纷纷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又动了要再见霞的念头。屋外的风越来越暖和了,一只小黄雀在枝头上脆声鸣唤。这只鸟越看越眼熟,是不是就是几年前的那只?
我们的行期定在第四天的下午。我打电话告诉刘云,这天有一趟长途汽车开往海南,让她作好启程的准备。她说:“不能再推迟一两天吗?”我说:“不能,我得赶回去上班。”她说:“就这样吧。”旁边有一个男声问:“谁?”只听见刘云“啪”的一声合上了手机。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怎样来叙述我的这次旅行,因为它像我的其他许多次经历一样平淡无奇,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我却老是爱回头朝自己的过去张望。这一张望,就显示出那么多的毛病来。
首先,我们动身的时候,家乡还处在残冬的戏弄之下,我们带着一身的倦怠下车,海南却以初夏的丰姿迎接了我们。花团锦簇、绿影婆娑的海口让刘云大惊小怪起来。她满脸兴奋,流露出一股清纯的、如同初恋的女孩的那般神情。她挨着我的臂膀,对我说:“我们像跨过了一个季节似的。”“但是,”我说,“我们这一年里没有了春天。”她转过头,定睛看着我:“是这样吗?”我说:“是的。”不管刘云有多么激动,我心里却是冷冰冰的,我觉得大多数女人都喜欢做作,总想以做作的表情来感染你的情绪,当她感叹眼前情境的美好时,差不多就是要你认同她的美好。仔细想来,那时我差点就要那么想了。
此外,一路上我成了她断断续续的话语的倾听者,我承认,我不是没有一点好奇之心的。
看得出来,刘云的脸也是被各种化妆品浸渍过的,她纹过眉,双唇上涂着唇膏。从南方回来的或者在那儿呆过的女人,基本就是这样。我猜不准她的年龄,这是很费脑子的事。当然,我是不用去费这番心事的,就像你不想买西瓜,何必老揣测着它的生熟呢?我告诉她长途车起程的时间,让她到时径直登车。直到汽车快要开的前一刻,她才姗姗而来。她只背了一个小小的坤包,不像出远门的样子。的确,许多女人出门不喜欢拎着大包小包,不过,只有自信的女人才敢真的这样做。刘云稍弯了一下腰,手轻轻将坤包往身后推去,看见了我,就说:“哎”,同时一笑,朝这边走来。我们的铺位在底层,我问她是喜欢里面还是外边,刚开始她说随便,随后又说,如果我不在意的话,她想在里面。汽车要开了,她打开车窗,探出头,朝车外的一个方向挥手。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是霞来给她送行。不远的地方伫立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他也向这边挥了一下手。
在南边,女士们新流行着一种发式,说得离奇,叫什么离子烫,特点就是烫过的发反而像没有烫过的,发梢参差不齐,发根直如悬丝,仔细瞧去,一帘青丝中却隐藏着无垠的波纹。这种发式富于变幻,使女士们看上去皆有朦胧迷离之色。你知道,我想说的,刘云也为自己准备了这种发式。窗外的风撩起她的一绺头发,掩住了她的眼睛。她好像在想什么,好长时间她都顽固地保持着沉默。这一开始就有点让我心灰意懒,我曾经想,漫长的旅途有一个熟人作伴可能会变得轻松的,不料会适得其反。
汽车走了一阵,从窗外晃过的或是越冬的农作物,或是黄褐色的土地。一轮黯淡的红日低低地悬在空中,空气阴冷而清新。我在回味和霞的交往,有许多次我拿手挽住她的长发,但她后来嫁给了别人。我给她打电话,在电话里,我们还聊天。
“啊”,突然刘云长吁了一口气,她用手拂了拂头发,又揉起眼睛:“我睡着了。”她侧转头,望着我不好意思地一笑。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南边呆过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但刘云继续说:“一大清早的,就这么犯困。”我模棱两可地附和道:“我也经常是这样。”刘云倏忽惊醒了:“什么这样?”接着,她可能觉得不必这样认真,便故作轻松地一笑。这样,刚才站在路边给刘云送行的那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她是她的前夫?要不然是另外的什么男人?
汽车笔直向南开去。我们的行程将要纵贯江西、广东两个省,全长约两千公里。沿途要穿过平原、丘陵和山地,还有点缀在这些地貌上的一系列城市和乡村。躺在汽车里,有时我们能看得很远,即使山不太大,我们也能看到。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高空俯视,在纵横交错的大道上奔驰的汽车看上去势必如同蠕蠕爬行的蚁虫。
车子一点点朝南行驶,气候也渐渐温暖宜人,高速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盛开着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即使在车子里,我们也能闻到那浓郁扑鼻的熏香。车子在这种阵势中奔跑了一段时间,接着就进入了一座城市。似乎春天就这样在眼前一晃而过。
刘云忽然健谈起来。她说她本来打算从广州坐飞机直接飞海南,结果却飞回了故乡。
“我想去海南之前先回家看看我的儿子,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没见过我的儿子了。我很想他,梦里都在想他。你儿子呢?是留在家里,还是带在身边?”
“带在身边。”我说。
“这是对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儿子,其他都是假的。我离婚的时候,首先要的就是儿子,他拼命来和我抢,我死都不给。哼,他说我养不活儿子,我偏要养给他看。”
“你是为赌气才出来的?”
“为我儿子。儿子要长大,要读书,以后要花那么多的钱,反正为儿子我得豁出去呀。”
“是的呀。”我赞同道。“我们也老是在想着儿子。广东,你在广东那边干什么?”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的黑亮的眼眸投向了窗外的蓝天。只一会儿,她就收回了她的目光。“打工呀,”她说。“什么制衣厂、食品厂、电子厂,我都呆过。”
汽车停住了,司机招呼大家下车吃饭。刘云有一副亭亭玉立的身材,举手投足透着一股妩媚之气。看上去,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女人。餐馆里只有那种低廉劣质的快餐,我望着她说:“很抱歉,只能请你吃这样的饭了。”我还要了两听啤酒,我和她一人一听地喝了起来。上车的时候,刘云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手机,对着手机慢声细语地说起来。等她上车来,她告诉我是家里打来的。坐定后,她忽而问我,我们到了哪里,我说我们刚过了吉安。她再次打开手机,耳语道:“千万不要多想了,听我的话,好吗?告诉你,我们到了吉安。”
赣南山地,气候温暖湿润,山间暮霭缭绕,路旁树木散发出一股浓烈撩人的气息,在薄暮中朦胧欲睡。车内渐无人声,只有马达的异常单调的嘶鸣。一个星期前,从夜暮降临开始,我就在等待着霞的到来。应该说,我是怀着某种幻想的,我甚至设计好了一些可能出现的细节。我觉得霞应该有所改变。不管怎么说,那一晚将要算作是我和霞的某种状态的结束或另一种状态的开始。但那一夜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结束,什么也没有开始。霞笑吟吟地说:“许多人都涌往海南,那儿好吗?我妹妹也想去看一下,我妹妹……”
有一会儿,马达的声音突然小了,接着,我就体会到一种奔腾宣泄的舒快的感觉。原来,汽车一溜风般地滑下了一个长长的陡坡。
“你睡了吗?”刘云压抑着声音问。我转过头,刘云侧着身子,背对着我。她在打手机,我险些以为她是在和我说话。“没睡?在等我的电话,嘻,嘻,有那么重要吗?不至于吧,你对别的女人也会这么说的吧,……会的。……不要看得那么重,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真的,嘻,嘻,我也这样想,只是不好说出来。……当然,我一点也不会怪你,是我不好,我不能做像你希望的那样好。……嘻,嘻,你知道,回去的这几天,差不多全给了你,是啊,我也不会忘记,以后都不会忘,再也不会有了。……什么?……我不想再见到他,他令我伤心,他到我妈家来看孩子,我知道他又有女人了,这和我没关系,我也有我的自由。……嘻,嘻,言重了吧,你要我的保证,嘻,嘻,我保证不了。”最后,是那边一个劲地在说,刘云握着手机认真地听,还不停地嘻嘻地笑。
天亮的时候,汽车爬出了山地。我们在一家简陋的餐馆停车就餐。刘云洗嗽完毕之后,又登上车给自己丰润的嘴唇涂上唇膏。这趟长途车上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但与刘云相比,她们就只显得漂亮而己。吃完早餐,汽车又匆匆地往前开。我们进入了广东的地界。
“中午就可以到达广州。你到过广州吗?”刘云说。
“没有。”
“我就住在广州。”
“哦。”
她说的真准,汽车正午时果真到了广州。车子没有进城,擦着城边而过。我以陌生人的崇敬,对这座堆满财富的城市投去了深深的一瞥。刘云热情地为我介绍着,看来她对它很熟。
眼看一座城池又要被我们的汽车抛在后面了,这时,刘云的手机响了,“喂”了一声后,刘云换了柔和的普通话和对方说起来:“喂,我是云,我现在还在家乡,”她抬起眼朝我看了一眼,“哦,听不清是嘛,我正在车上,去探望一个熟人,可能还要半个月左右吧,等到了广州,我就给你打电话。就这样。”
刘云又看了我一眼,她想和我说什么,但还是把头别回去了。
此后,汽车差不多是沿着海岸线朝徐闻那个方向蠕动的。凌晨四点,汽车抵达海安,上了汽渡。再有一、两个小时,渡过琼州海峡,就可以跨上海南岛,我们的旅途就结束了。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有一个问题在上岛前需要解决。
“那个人你认识吗?”
“哪个?”她似乎没有料到我终于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哦,那个嘛,”她心照不宣地一笑,坦然地说:“不,不认识。是熟人牵的线,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几次,我的感觉还可以。他在海口,他让我过来看一看。”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她常住在广州,用霞的话说,她妹妹就这样在外漂泊,在霞的想象中,她妹妹居无定所,过着流浪一般的生活。她建议和希望她结束这种不稳定的生活。霞不知怎么打听到那个叫吴天的男人也在海口,更重要的是吴天现在是个独身的男人。于是,这个男人的电话号码便传递给了刘云。几个回合后,吴天可能就盛情邀请她到海南来。
“听我姐姐说,你跟他还是同学?”
“我的同学中是有个叫吴天的。”
“他人怎么样?”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的声音浑厚有力,听上去就是一个沉稳成熟的人。”
“你计划在海南呆多少天?”
“说不好,看看再说吧。”
“假若他让你满意,弄好了,你就嫁给他?”
“为什么不呢?”她笑起来,自我解嘲似的。
“你姐让你和我同路,大概就是想叫你从我这里多了解一点吴天的情况吧,你瞧,我使你失望了。”
“没有,你是一个好人,我姐也这么说。”
这是我们上岛前的谈话。
刘云一直没办法和吴天联系上,电话的回答是对方不在服务区。刘云说,他们约好了,她一到海口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来接她。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我本来以为,到了海口把她交给吴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情况有了变化,我不得不留下来陪她。她倒没有显出焦急,直到她再次掏出手机拨起来,对方仍无消息,她照样不慌不忙。也许,她料想后果总不至于太严重吧。吴天今天没有消息,明天大概就会从天而降吧。
我带她到一家酒馆吃饭,吃完饭就给她登记住宿。这些事本来应该不是我干的。她应该让另一个叫吴天的男人直接领走。最后,刘云索性不打电话了。夜晚,我们在一家火锅店喝酒。
“告诉我,我姐姐为什么同别人结了婚,她当初本来是打算嫁给你的。”
“你得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婚?”
“嘻,嘻,嘻。”刘云一阵笑。
“哈,哈,哈。”这是我的声音。
有一天,我在上班,门卫喊我说有人找我,我到值班室一看,原来刘云坐在那儿,旁边还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我只是礼貌地和那个男人点点头,便与刘云问候起来。刘云表情怪怪的,最后她让那男人到门外的商店去买点什么。那男人刚出去,刘云就说:“不认识你的老同学呀?”
“怎么,哪个是我的老同学?”
“他呀,他就是吴天。”
“他是吴天?我可不认识。”
刘云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起来。但她很快镇静自若。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马上说:“他的变化真大啊。”
“是嘛,就是嘛。”刘云娇嗲地说。趁那男人没回来,我急忙搂抱了一下刘云,我说:“想在海南呆下去吗?”
“你同意吗?”
那个陌生的男人回来了,他朝我露出温文尔雅的一笑。这笑很谦逊,很有节制,好像一切都了然于胸。
过后,我似乎也明白了,那个男人或许真的就叫吴天,只是他不是我的那个叫做吴天的同学。但是对于刘云,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甚至又想到了霞,她不是差点就做了我的妻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她会想除我以外的男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