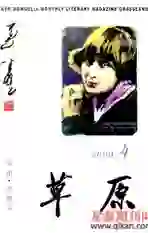书房有无中
2009-05-22杨挺
杨 挺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名不副实的。就拿我来说,从名义上来说是个和书有关的人,无论是教书写书还是编书,总还是和书在打交道。可是在我们这个行当之中我又是个名实不符的人,因为当我的同行们每每谈起自己的书和书房时。我就觉得我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干了几十年文字的差事,却没有一间自己的书房,说起来总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合时宜。
确实,我在我的文字生涯中至今还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在我的经历之中。前二十几年是自己过生活,东飘西零。衣食无定,何谈书与书房。那时候书是偷偷摸摸地搞。读是夜半三更地读。常常是在上夜班的车间,或是休息的山野林间,总之没有固定居所,何来书房书斋。待及拎几箱书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欲成家立业,却是谈何容易,在我们当年的物价和收入的差率下,有一间住房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何谈有间书房。在我们那一年毕业的同学之中我们俩还算是幸运的,没几年就住上了楼房。虽然不大,但是总是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这也是全靠了长辈的福荫。才有了如此的蜗居。
人这一生。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总是不断地虚实相补,总是在有无之间变幻目标。刚搬进小楼时,兴致和心劲都很高,于是,把那一大一小的两间房中的大间布置成书房,剩余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卧室。从视觉上看,整体感觉是好看了,开阔的空间,整齐的书架。还有朋友赠的字画。有点书香门第的样子了。可是世间事有许多是要用务实的眼光去看,只有亲尝冰火才能冷暖自知。我的书房也就是独自完整地存在了一小段时间,就很快被必然事件打破了它的完整和独立,这个入侵者就是我的女儿。因为那间卧室实在是太小了,大人和孩子挤在一起很是难受,于是我们便决定在我的书房里为女儿加一张小床。再往后,又给她加学习的桌椅,于是家庭的重心向女儿倾斜,我们也就把原先我们的卧室彻底腾了出来。将书和女儿安置进去。我们住进大屋,女儿独居小屋,一统天下变为南北分治。我的书房也就化为了乌有。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职业的关系,女儿越来越大,书也越来越多,那间小屋是越来越拥挤。书架上的书由一层摆放变为多层码放。再往后是我们每个人的书都各自为阵,我的书放在高处,女儿的书放在桌上。妻子的书放在床边,大屋小屋到处是书,后来报刊没有地方放,就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厕所里放置一个角架,上面也都堆满了报刊杂志。每每到冲澡的时候还得准备一块塑料布来遮盖。于是我家的人都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厕上阅读,而且是乐此不疲。到后来我们搬到一处大一点的住处,书报有了放处,但我们还是保留了这个“陋习”。只是随着条件的逐渐好转。我们的毛病却越来越多。就以我为例,当年我风光一时之时,正是我各方面条件困难之时。自己在大学里教书。课程多且杂。自己又是心高气盛,总想一鸣惊人。于是自己把自己搞得很苦也很累,常常是有整块时间就是写东西,零散时间用来读书。倒是一忙就忘记了蜗居的大小,只要有一块空间就可以了,连一灯一凳一桌都不敢奢求。结果是女儿独居一间小屋,有书有桌有椅有台灯有音乐,她还在门上贴一张小纸条,上曰“进屋请敲门。不得容许请勿入内”。一半天地叫她这么一纸禁令就给划走了一半。剩下一间稍大一些,我们的衣食住行全在其间,大床、电视、衣柜、饭桌、沙发、茶几统统都在这里,关键是妻子要看电视,人家在学校累了一天,有些放松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我的空间就只能是或者和老婆一起看电视。或者另找地方干自己要干的事情。弹丸之地,无处容身,常常慨叹中国之大竟没有我放书桌的地方。但这也是自嘲的笑话,现在住房条件改善了。面积是当年的一倍还多。女儿也自豪地考入了清华大学,可是我却在这空空落落的家中觉察到一些寂寥,时不时忆起当年的情境。那一家人紧紧凑凑地团聚在一起,俯仰之间鼻息可闻的日子。岂不快哉!人这种生物就是喜欢扎堆,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不新不旧,不老不少,二十年前还算前卫,而今却连手机的绝大部分功能都不知晓。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一种可以浸透历史屏障和灵魂肉体的汁液,使得我们虽身处都市,却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传统心理,在生命的漂泊中,一旦看不见自己家的烟囱,就鼻子酸酸的,心里空空的,脸上凄凄的,眼睛呆呆的。
古诗云“山色有无中”,说的是一种中庸的心态。我现在回忆当年之情景,犹如隔水看山,云雾飘渺。确实,我的书房就在我的寻找和变通有无之间。那些年,白天女儿上学去。我就可以潜入进去,去写去读去备课去完成约稿。一到她快回家我就会主动地让出这片天地。在随时随地之间去找寻我的一己之地。如果是遇到了急稿。而且老婆也有事情,我便躲到厨房里去,将菜板横在膝间,一只小马扎,一杯旧茶水,一枝老钢笔,一盒廉价烟,倒也悠然自得。我的许多稿子就是在这样的书房里写出来的。其实写作这种劳作是一种吃软不吃硬的活计,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们只能在想要表达但又难以表达之时,才会充满情致和欲望。在我的理论中有一条是“冰箱理论”,其大意是:人的表达是需要冷却的,越是严密冷却和多有压力的,就越能充满能量,就越能有所突破。这书房也是如此,小有小的作用,至少它不会让你东张西望,它逼迫你一心一意去进入你营造的文学和想像的世界。它让你突破它的围裹和限制,它让你只能在字纸上突围,它让你真正忘记你的处境和卑微。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一切都充满了辩证法。但凡功成名就之后,条件就会好将起来。但是,这个时候人的心劲儿和气力都已经是强弩之末,需要靠名气来吃饭了。此时就像是一句老话一样“有牙时没肉,有肉时没牙”。套用在书房这个话题上也是如此。有能力写的时候,没有书房没有条件。等到有了书房有了名头之后,却没有了激情和心力。我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年至不惑或是知天命,都在文字这一行当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华发早生,多情笑我,时至今日,方才有间像样的居所,于是个个都给自己预备下个书房,几番拾掇都挺像个样子。于是,起斋名,求字画,添新书,买赝品,然后是大功告成,每每是天天摩挲,日日自赏,一生不如意之闷气,一泻而光,至于其它志气则是难以再起。于是乎,吴钩常看却只是烈士暮年,虽偶有千里之心,却觉得还是伏枥舒坦。安逸于书房之气派,陶醉于阔大之书斋。然后是没几年功夫便一个个没了踪影。再也不去弄什么文字了。
当然。这样的收场也无可厚非,忙活了大半辈子,有个好的生活条件也是应该的。古人讲“老吾老及人之老”,谁人不老呢?老到临头,有个好日子好住所好书房,也是老有所得。让那些年轻人去蹭蹬攀登去吧。咱们已经修成正果了。可是,我到今日还是四下在寻找自己的书房。尽管前些年乔迁新居,但仍然是没有自己的书房,徒增了许多面积,却在间数上依然不足,女儿的房间依
然如常,只是需要日日清扫;客厅无中生有,面积还挺大,擦一遍脑门要出汗,还比往日多加了几张沙发:我们的卧室也添加了不少新鲜玩意。但都是让人舒坦得只想躺着看书而不想坐着写字的物件。生存条件是大有改善,可是让人长脸的书房依然无踪,所以在搬家时我非常头疼我们的那些书籍的所在。因为这么些年的只进不出,就是女儿的那些课本和读物也是不少,何况我们两个人都是和字纸打交道的。其数其量可想而知是一番什么景象。那年的整个搬家其实就是对付书籍,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带什么物件到新居去,甚至连碗筷都没搬动,其他大件更是全部“转业”到旧货市场。翻来倒去,折腾出一大堆自己认为无用之书,让贩旧书的用板车拉走了。新居里还是把书架放在客厅里,倒也显得与众不同。可是我的书房还是在有无之中,我的写作经常是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好在我现在老是在班上干活,书房对我不是那么十分重要,再加上我现在练习用电脑写作,也占不了多大地方,搁哪都行,有没有书房都问题不大。只是有时候觉得有些遗憾,怎么这么多年自己还没有弄上一间书房:也常常看见报刊杂志上登出某某书房的照片,心里也是觉得有些发虚。
可是我这个人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不太计较那些形式的存在。吃穿如此。名利如此,什么书房更是如此。在我的眼里,书房不书房都不重要,关键是看对你有用与否。有书房好,没书房也不是不好,不能因此而判定高下优劣。学问家的书房。汗牛充栋是一种风景。作家的书房,佳作连绵也是一种景观;至于我和我的同类者,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边缘状态;世间有许多事情,区别就在所处的位置,有则过于实,无则过于虚。处于有和无之间,正是游刃有余的空间,它既可以让人工作,又可以催人进取。山色有无之中,充满神奇的魅力;书房的有无,原本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居者之心。心中的有无那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在世,惟有心累。处在若即若离之间最好。陶渊明有诗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虽不是在说什么形而下的具体事物,可是那道理是说万事顺其自然,不必拘泥形式的,关键在于理解和施行。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有一间书房,可我现在也不沮丧没有书房。若有若元的现在就挺好,而且会更好,我相信这一点!
责任编辑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