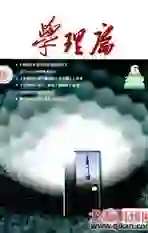略论《唐李问对》对“奇正”思想的发展
2009-05-21赵良
赵 良
摘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后人辑录唐太宗李世民和唐初名将李靖讨论兵法的语录,书中对军事谋略中的“奇正”思想有独到见解,丰富发展了奇正的主要内容,提出“奇正相变”的军事思想,论速了“奇正”与“虚实”、“分合”“阴阳”等诸多军事范畴的内在联系,总结了诸多关于“奇正”军事训练教育的思想。
关键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奇正
中图分类号:K2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6-0124-03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唐李问对》或《李卫公问对》,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该书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辑成,分上、中、下三卷,共98个问答,1万余字。书中所论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旁征博引,对前人的军事思想大胆评说,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书中有许多关于“奇正”思想的论述,这些观点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拓展了“奇正”思想的内涵
“奇正”是中国军事思想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术语。老子有著名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之说,孙子将其移植、应用到军事领域中,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由此可以衍生出无数的战法。“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孙子认为奇正是相生相长、循环往复的,因此战争中要善于运用奇正,并注重把握奇正的变化,这样才会“善出奇正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之后,孙膑又对奇正思想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也”,他认为,奇就是特殊,与一般使用的方法相对应,“发而为正,其未发者为奇”,形于敌者往往为正,隐于后,深藏不露,隐而未发者往往就是奇。之后,历代兵家论及“奇正”思想的不胜枚举,但多为抽象的概述或仅仅停留在奇正思想重要性的阐述上,部分论述虽然涉及奇正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但也仅仅限于纯军事领域,甚至只是停留在战术层面上,缺乏对奇正思想向大战略乃至军事哲学思想领域的延伸。《唐李问对》中有大量关于“奇正”思想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却没有拘泥于前人的思想藩篱,其中既有理论上的概括,也有形象化的举例,使得“奇正”思想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和理论化,从而实现了对“奇正”思想内涵的拓展升华。
首先,《问对》将“奇正”思想拓展到大战略的范畴,提出政治攻心为正,军事打击为奇的观点。书中开篇即云:“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李靖在此提到的“正兵”其实就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政治战。其后《问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黄帝以来,先正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这样《问对》就将“奇正”的范畴扩大到大战略上来,主张政治为先、为正,军事为后、为奇,强调两者的综合运用。李靖在对话中多次强调“正兵”,也就是政治战的作用,“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由此可以看出,《问对》对于“正兵”策略的使用是十分推崇的,认为这是战争胜利的基础,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从军事实践层面上讲,《问对》要求在实际作战中也要注重政治战与军事战的结合,在歼灭东突厥的战争中,李靖建议唐太宗首先在政治上“以蛮夷攻蛮夷”,采取分化对方的手段,挑拨存在矛盾的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并适时拉拢实力较弱的突利,使颧利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并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此术可谓为正。尔后,李靖又建议唐太宗在实力对比还没有达到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奇”用兵,出其不意的出兵远征,以3000轻骑击溃东突厥主力,并最终一举擒获颉利,平定东突厥,基本杜绝了北方边患。
其次,《问对》还将奇正思想具体化,并列举了了大量战例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奇正的解释往往过于抽象、笼统,使人们难以正确理解和运用,《问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分析霍邑之战时,太宗与李靖两人详细探讨了当时的细节问题,认为“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这些论述结合实际的战例,可谓绘声绘色,使人如身临其境,从而对一般意义上的奇正有了感性认识。同时,《问对》还对奇正概念的转换进行了研究,作者在解释霍邑之战胜利的原因时谈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变为正,则安能胜哉”,也就是说,霍邑之战中因建成坠马造成原本主攻的右军少却,结果在客观上使得正变为奇,从而为赢得胜利埋下了伏笔;而在评析曹操所说的“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的结论时,李靖则认为“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也就是说奇正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具体何为正,何为奇,应根据情况的变化来确定。
二、提出了“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理论
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问对》提出“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理论,认为奇正理论的灵魂是奇正相变。“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也就是说,奇正是辩证统一的矛盾体,其本质上没有分别,都是为实现夺取主动权的目的而实施的手段。“奇正相变”理论的精髓就是要使军队在运用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此时为奇彼为正,此地为正彼为奇,也就是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李靖提出“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其关键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其核心则是“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通过示形等各种手段多方以误之,“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从而达到“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境界,形成“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战场态势。
除理论阐述外,《问对》还对奇正变化的具体运用予以探讨。《问对》还对作战时奇正的兵力配置做了分析,认为一般应以“正兵”为主战部队,“奇兵”则作为机动部队,“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怛在实际过程中,奇兵与正兵的配置并非绝对的,“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删,这表明《问对》所说的奇兵与正兵的兵力配置和使用,是根据战场形势的不同而加以区分的。
在兵力使用上,一般要坚持在战略上以正为主,《问对》在总结黄帝征蚩尤、诸葛亮平南以及霍邑之战、大唐西征突厥等诸多战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
的战略指导方针,要求在“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惑”的情况下,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能盲目出击。而在具体的战役战术运用上,则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奇制胜。当然,《问对》主要强调无论在兵力配置还是兵力使用上,奇正都并非绝对,而是要达到两者之间的灵活转换、变化,惟此,方能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三、论述了“奇正”与“虚实”、“分合”、“阴阳”诸范畴的关系
《问对》的又一大贡献就是论述了“奇正”同“虚实”、“分合”、“阴阳”等军事范畴的关系。中国传统兵法善用辩证思维思考军事问题,并总结出诸多具有辩证思想的哲学范畴,如攻与守、众与寡、主与客、虚与实、奇与正、全与破、分与合、迂与直、阴与阳、进与退等等。前人在提及这些军事范畴时较少将它们结合起来,而李靖在论述战略指导规律时,抓住了这些对偶性的军事范畴之间的联系,并集中论述了“奇正”与“虚实”、“分合”以及“阴阳”之间的关系。
在战略指导上,《问对》认为,“奇正”与“虚实”总是相互联系、互为关联、相互影响的。“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这表明,奇正的运用是为了达到我势常实,敌势常虚的目的,通过对兵力部署,军队的调动,使敌人出现错误判断,落入我之圈套,这时则“敌虚则我必为奇”,当敌人出现虚弱之处时,我则采取变化的特殊战法予以打击。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对奇正的灵活运用,“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才能使敌莫测我之“虚实”。对敌虚实的正确判断和把握则是奇正运用的前提条件,“奇正在我,虚实在敌”,通过奇正的变换,我们可以了解对方的虚实,进而为我准确确定奇正的运用方式提供保证。《问对》卷中写到“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由此可以看出只知奇正,不知虚实,则奇不为奇,正难为正,易为敌所乘。只有知奇正,明虚实,善应对,方为上乘。
“奇正”与“分合”也是两对联系紧密的军事范畴。李靖认为“奇正”的灵活运用离不开部队分合为变,军队灵活多变的分合也是一种奇正,因此,在平时训练中要“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日: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熟悉“分合”之变,战时才能达到“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嗍的境地。此外,《问对》认为还可以通过对兵力配置的分合达到对部队和战法奇正的调配,“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分与合的确定需要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来确定,这就要求为将者能够做到临时制变,始终遵循“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的原则。
《问对》还将奇正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结合起来。我国古代早有“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的阴阳转换的思想观念,而《问对》将之延伸到军事范畴,提出“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这其实是将奇正思想从单纯的军事领域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天时、气节等事物因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那么同样在军事领域对付敌人也要随着形势变化而制定策略。奇正在本质上就是“兵家阴阳之妙也”,所谓的奇正之变,其实就是“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这与阴阳转换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问对》认为“奇正”与“分合”、“虚实”、“阴阳”的关系其实可以表述为以分合之变为奇正之兵,以奇正之兵达敌虚我实之形势,妙择阴阳变换之时机,最后形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
四、总结了“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的军事训练思想导
《问对》虽然强调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认为“临时制变者不可作胜穷也”,但在实践操作层面,《问对》也提出“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并进而总结形成了“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的军事训练思想。
首先,《问对》认为将领对奇正思想的认识把握是取胜的关键,因此十分重视培养将领们运用奇正的能力。“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在这里,对“奇正”的把握不单单是一个将领军事指挥能力的体现,更是影响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因素。书中唐太宗指出“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对此李靖提出:“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在此,李靖认为将领们要想做到避实击虚,首先就要学会奇正相变之术,尔后才能较好的把握虚实,否则“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更为可贵的是,李靖也认识到单纯在训练场上对将领们进行奇正与虚实的训练是不够的,“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平时的训练是基础,而只有兵临阵前,灵活运用才能真正领会到奇正思想的真谛。
其次,《问对》还对普通士兵提出了要求,强调在平时就进行奇兵、正兵的教育训练。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李靖并没有脱离实际,而是提出“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二术”就是指将部队分为奇兵和正兵两部分,分别加以训练。“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来提高部队对奇正的认识和运用,使为将者深谙分合之变,为兵者熟悉教战之术,先达以奇为奇,以正为正之境界,然后才能更进一步把握住“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理论的真谛,从而最终达至“形人而我无形”的“奇正之极致”的境界。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