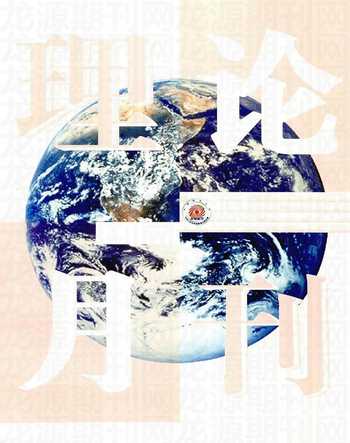小说文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考辩
2009-04-29周和军
周和军
摘要:新时期小说采用意识流文体进行创作,一方面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复苏和觉醒,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身的艺术创新和发展趋势的一种体现,“向内转”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创作倾向。本文认为,经历了“文革”精神创伤的新时期作家采用意识流文体应该是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描绘人的意识流动、情绪感受、知觉印象这种艺术形式间接表达作者对于社会现实、人生经历、意识形态的反省和思考。
关键词:意识流文体;意识形态;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136-03
王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甚至回避“意识流”的字样。王蒙非常推崇鲁迅的散本诗《好的故事》,他喜欢鲁迅描绘的那种流动的、连绵的、叠加的意象,他说:“《好的故事》对我是一种启示,一种吸引,一种创作心理学意味上的暗示。直到今天,当我努力去追踪、去记录、去模拟那稍纵即逝的形象的推移,情绪的流转,意念的更迭,去表现那‘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播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的生活的五光十色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尝试,我的心情和我的追求,都可以从《好的故事》里得到鼓励和参照。”事实上,《好的故事》是一篇意识流式的作品,描写的是一条梦幻意识中的山光云影下的奇妙“河流”。后来,王蒙在为张承志意职流式小说《绿夜》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再次讲到了创作心理中的“河流”,他的赞美溢于言表:
中国的和希腊的哲人,都曾经用水流来比喻生活,比喻时光,比喻历史的伸延、连续和变化无休。
水流的几个特性是迷人的。第一,映照着世界的影象。第二,它改变着世界的影象。第三,它时时保持着又改变着自身。第四,它有文(纹)采,有浪花(浪花里可以看到从白光中折出的赤橙黄绿青篮紫,看到彩虹),或曲、或直、或急、或缓、或奔泻而下、或委迤回环,有它天然形成的节奏、振荡、结构。
王蒙称赞《绿夜》是“真正的无始无终的思考与情绪的水流,抽刀也断不开的难分难解的水流”,《绿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的乐章”。
经历过几番政治沉浮的王蒙在新时期采用意识流这种艺术形式来掩盖他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反省思考与思想质疑,“他率先把历史叙事和个人的内省意识结合起来,‘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王蒙的小说迅速跃进到一个较高的艺术层次。”所以,王蒙采用意识流手法,“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形式变革的需要,而是出于表现他意识到的复杂内容,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难以直接表达的那些意义。他采取人物心理活动的方式,把那种复杂性呈现出来”,“在王蒙刻画的那些‘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身上,那种恍恍惚惚的心理,表明他们本身对现实的犹疑”,“一个所谓完全与过去决裂的时代,不断地在人们意识中,在想象和回忆中,在质疑和辨析中,被过去所侵入,或者说,过去还是那样深刻地卷入现在。”我们以王蒙作品为例进行考察,如《夜的眼》中: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
这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主人公陈杲是一位作家,到北京参加作品研讨会,受当地领导之托求一位“朋友”批条买汽车配件,小说表现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拷问:“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我们,我们有什么呢?”,作者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不良现象:“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再一条,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揭露出“文革”之后干部队伍中形成的特权阶层和利益关系网,体现了作者对丑陋社会现实的反感和批判。作品中也有对于当时敏感问题一民主的思考: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杲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的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陈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
这一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城市中的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也凸显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大城市已提出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要求,边远小镇还在为满足温饱的“羊腿”奔波忙碌。“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王蒙把民主看作是获得羊腿的必要前提和手段,也表达出王蒙认为民主应该关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这些都是借助了意识流文体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难以直接言说的内容和意义。
《蝴蝶》也是通过意识流文体诉说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反思的作品,叙述了主人公张思远在时代政治洪流中的生活遭际,他对于自身经历和个人生活的回忆就是对中国政治运动的深刻反省,个人完全被政治所控制和支配,作品中充满了对于“右倾”和“文革”政治运动的思考和批判。如对于刚刚解放时的张思远:
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在对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
这一段反映出当时人民大众对于领导干部的盲目崇拜:“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个体在当时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缺乏理性的反思和独立的思考。“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则反映出个人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的巨大力量和无比威力,他也借机俘获了一个少女的爱情,这是他的权力身份和个人收益的戏剧性地结合。
当张思远官复原职并升任副部长时,他回到乡村。请求和曾经救过他的医生秋文结为连理时,秋文不愿做他的部长夫人,不愿放弃她现在的工作、生活和乡亲,并且义正严词地批判了他的官僚作风和自私行为,实际上,王蒙是借秋文之口说出了当权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他“希望权势者能考虑人民的利益,‘文革结束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问题就解决了,掌权者就站到人民的一边,王蒙对此是深以为虑的。这就是王蒙与同时代作家的不同之处。他没有通过重述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去论证现实的合法性,
而是保持怀疑。”王蒙的另一部小说《布礼》,一定程度上,也是“借助‘意识流这一非常规的艺术手段来解除‘典型论的封锁,通过反抗、磨合而与它达成一种‘新型的文学妥协关系。它更试图松弛正统与异端、必然与偶然、中心与边缘、整体与碎片的制约功能和对立模式,以《布礼》等作品为‘样本来探求和尝试一个与时代环境大致相匹配的叙述新模式。‘我在寻找什么这种典型的王蒙的‘自述,反映了一代作家在两个‘历史之间自相矛盾的‘寻找心态与历史性的挣扎。”
这种文体技巧和政治内容结合的现象受到了国外一些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把王蒙的意识流文体看成一种“技巧的政治”。如李欧梵把美国批评家马克·肖勒(Mark Sehorer)的文章《作为发现的技巧》(又译为《技巧的探讨》)作为其理论前提,探讨了新时期小说中的艺术技巧与表现内容的关系问题。他指出,“1976年以后有一批作家开始重新注意技巧,以此作为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拨正,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他认为新时期小说技巧和政治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在一个政治弥漫于一切生活领域的社会里,这一种‘艺术的姿态不可避免地也有其政治内涵,而这一挑战的‘社会效果现在还只是刚开始被感觉到。”王蒙在当时是“1976年以来出现和重新出现的”“决然进行文学语言的试验而著称的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王蒙所进行的意识流试验“只不过想把这一现实从意识形态的掌握中解放出来罢了。”他把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比喻成展览,“在这展览中,将中国生活的经验转化为‘实现的内容的过程就会变成一种调和,形式、技巧方面的激进的试验,最后所服务的人道主义观点也将只能用于巩固中国的固有的雍容面子。他认为,王蒙采用意识流文体是一种政治技巧。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拨正、突破和粉饰。
也有国外学者把这种技巧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称之为“尾巴”,称王蒙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光明尾巴”。美国学者非尔·威廉斯(Phil Williams)在评论王蒙《蝴蝶》时撰写了论文《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中指出:“中国的现代小说正在抛弃‘伟大的归来的手法,然而,这种手法的残余仍然继续在如同结尾这种明显的部分出现,一只有多种颜色的翅膀和鲜艳的身躯的蝴蝶,终究会有一条光明的尾巴!”西里尔·伯奇也认为:王蒙新时期创作的小说“非常注意继续进行官方的道德说教”,“从官员的角度完全维护这种说教,继续为保持和恢复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时期之后的大变革中个别知识分子的革命信仰而斗争。他对艺术创新的探索将他的作品推向了中国现实小说的前沿。”其作品“在争论中经受住了被否定的考验,在于他巧妙地给作品设计了一个向上的结尾,尽管有时看起来只不过是很勉强地加上的‘光明尾巴”。
我认为,国外学者的评价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王蒙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民间意识形态”代表,这可从他与胡乔木的交往得到佐证,胡乔木一方面劝戒王蒙在创作上不要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又真诚地关注他的创作。前者说明他的意识流文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质和疏离,后者又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希望和期冀。王蒙的人生经历与他采用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政治的风云变幻、起落沉浮的人生经历让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刚刚被摘掉“右派”的帽子的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激情自诉:“我们是被党的乳汁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搞极左的人极力割断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说我们是‘反党的,是党的敌人,把我们驱逐出党……但是,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向着党。而当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和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念和忠诚。”王蒙遭受了长期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奴役之后仍无怨无悔忠诚于党,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操守和坚定信念。“对于我来说,革命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真、善、美是文学的追求,也是革命的目标。既然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政治,我们的生活无处不具有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影响,那么脱离政治,只能是脱离了生活,或者是脱离了生活的激流,远离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亦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王蒙坚决反对用政治说教来代替文学,也就暗示出应该选择合适的文学样式来表达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
新时期的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重新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身份,他感慨地说:“拨乱反正就是起死回生。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这叫作复活于文坛。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和王蒙境遇相似的张贤亮也说过,在三中全会以后,“我就面临着我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必须要严肃地思考自己的命运了。所谓严肃,当然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于是,我极其自然地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党的三中全会制订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用‘四人帮时风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的生命线!”很多同志委屈了几十年,“只要党一旦相信了他们,承认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士。就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毫不计较个人恩怨,马上忘我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他们在这样那样的考验面前,却都作出正确的抉择,始终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作家在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认同时,自主自觉地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要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当读者对《春之声》中出现的意象进行不同的理解时,王蒙表现出敏感和担忧:“小说中的火车头即指党中央时,我的天,可叫人吓了一跳,如果那样写,那还叫小说吗?那还叫生活吗?那还叫艺术吗?如果崭新的火车头代表中央,那么破旧的车厢又代表什么呢?难道代表人民和祖国么?我的天,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说明王蒙对于“文革”式的思维方式和政治阴霾仍心有余悸。
事实上,“‘新时期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两股并行的创作冲动,其一是面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叙事,其二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形式创新叙事。前者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偏向于现代主义思潮。”王蒙的创作一方面要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呼声。揭露现实中丑陋和阴暗的一面,就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王蒙的自身遭际只能让他更加谨慎和小心;另一方面,王蒙又是一个敏锐的、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家,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涌入让王蒙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外壳,可以将这两股创作冲动合二为一。王蒙在进行历史反思时,“也许还试图去揭示更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些以王蒙当时的思考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但王蒙显然不会直接去碰撞历史难题。意识流一类的叙述可以把那种复杂性的思考改装成艺术形式和表现技艺。”就这一时期的写作来看,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还是属于现实主义类型。所以,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和凸显人物的非理性、潜意识、无意识或性意识的西方意识流小说截然不同,“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为‘意识流小说获取意识形态许可的合法性:只有剔除‘意识流描写人们潜意识内容的特质——这些内容在70年代末往往被视为腐朽和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为意识形态所不容,强调意识流作为超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才能为意识流手法的借鉴获得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因此,在70年代末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还很强大的时候,中国作家选择‘意识流小说,实际上是逃避意识形态规约的本能举动。”所以,新时期作家选择“意识流”文体是规避意识形态束缚的一种叙事策略,也是作家艺术革新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