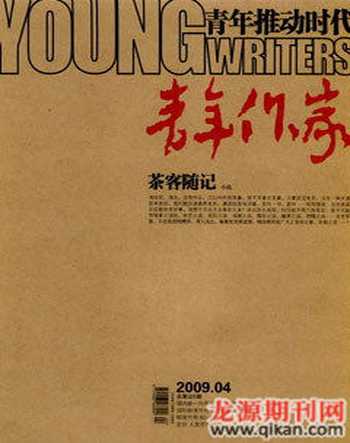伊沙的诗
2009-04-29伊沙
伊 沙
扇子
休想在我面前摇扇子
我看见那玩意就想撕
哪怕是诸葛孔明的
鹅毛扇
地球村的真相
奥运开幕啦
地球和谐啦
世界大同啦
80来个国家的头头脑脑
云集于北京
像80来只怪鸟
栖息于钢架的鸟巢
感受着中国的热浪滔天
不由自主地摇起了
一把把折扇
电视机前
妻子刚说:
“你瞧普京
热得都有点不耐烦了”
话音未落
电视下沿
迅速蹿出一行跑马字
报告着一条爆炸性的突发新闻:
“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
2008年8月8日
想想曾有一个同胞
举着一面那时的国旗
孤独入场的历史
想想当年的
西方报纸上
漫画中的中国人
扎着一条大辫子
顶着一颗大鸭蛋
也就理解了这个民族
今天晚上的喜欲狂
但是我
却过得不甚开心
原因并不复杂
感冒了
热伤风
涕泗交流好难受
旗手的选择
中国的旗手
还是选择了那个
最高的巨人
地球人都知道
他的大名
美国的旗手
则是选择了一个
最晚获取美国国籍
和代表资格的选手
他原本是苏丹
达尔富尔的难民
在历史的现场中
一想到从今往后
以至于很多年里
我定然会这么跟人讲起
或在诗文中写道:
“就是北京开奥运的那年……”
我便愈加珍视眼前的生活——
尽管那不过是
把沙发坐穿把电视看爆罢了
我已经有一周没有下过楼了
聆听国歌
奥运会颁奖礼上的升旗奏歌仪式
等于是各国国歌的大汇演
它们无愧是国歌
首首都那么好听
只是调子悲伤忧郁的风格
令我更为注意获奖选手的表情
更想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切
一路听下来
我的耳朵告诉我
最悲(并且最短)的国歌出自于日本国
名字叫《君之代》
我忽然感到十分扫兴
我有隐私道不得
一幅幅黑白的
奥运历史画卷
令我呆呆地想道
这便是世界
不带咱玩的岁月
现在才意识到
好生可怜啊
不过那时候
那个孤独的可怜人
充实着呢
迷狂得狠
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
以为全世界的人民
(运动员当然包括其中)
都吃不饱穿不暖
垂死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需要靠他这个疯子
将他们解救出来
并将这些旧世界般的
黑白画面
涂抹成彩色的
我们的过去
一位朝鲜运动员
获得了金牌
我对儿子说:
“她心里一准儿想着金将军”
第二天报上的采访中
果然就是这么写的
儿子一脸崇拜地说:
“爸爸,你真了不起!”
我接过他还回来的报纸说:
“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是我们的过去
过去了没多久的过去”
柏林1936
我瞎想
自己是站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希特勒的位置上
反而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在奥运会所设的所有项目中
各个人种各显其能
绝无优劣高下之分
怎么能够得出
日尔曼是优等人种的结论
问题在于他是政客
在一个丧心病狂的政客眼中
体育又算得了什么
这个政客如此忘我
忘记了自己是全场
最为瘦小枯干的一个鬼
还天生一副小丑的模样
日全食
从初亏到全食
是一个过程
需要等一小时
真是怪异的天象
月牙般的太阳
高高地挂在天上
其实看起来
比天象更加怪异的
是大地上的人们
那些浑然不觉的人们
那些茫然无知的人们
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们
那些日牙边的脚手架上
正在干活的民工
被倒挂在日牙上
日头终于被天狗吃了
狗肚子里泻露的黑暗
又吞没了大地上的一切
举头仰望黑太阳
你看见的是命运之神
诡秘一笑的脸
状态
午夜听雨
思忖着
我所听见的雨声
和春秋时有何不同
我的两扇耳朵
和古人有何一样
对不起
我不是复古派
也不是为了
搞搞雅意
这是一个正在写作
历史小说的作家
再正常不过的意识
无此他的状态
反倒是可疑的
奥运与地震
遗忘的理由多么充足
遗忘的力量多么强大
只需要三个月
一场可怕的灾难
已经远在天边
那位独揽三金的川籍选手
绝口不提家乡的灾民
谁还好意思提
那位双手指天的乒乓教练
显然也不是在指
天堂里的数万亡魂
老实说:我也忘了
脑忘
心忘
惟有身体不曾忘
一看跳水头就晕
颠颠儿地去瞧医生
血压不高也不低
医生诊断为:地震后遗症
再遭拒签记
未签的护照
连同一封英文的拒签信
比我脚步更快地
到达了我的家
四年以后再遭拒签
从美国换成了英国
与上次一致的结论是
本人有移民倾向
(真是怨煞我也)
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
英国的签证官比那美国的
做得有理有据
对我的嫌疑描述具体——
奥尔德堡诗歌节的邀请信上
写得一清二楚
为其提供了确凿的罪证
他们要为我的朗诵付费200英镑
签证官认定:这构成了一种雇佣关系
也就违反了大不列颠的相关法律
而我即将在英出版的英译本诗集
不菲的版税构成了又一罪证
呜呼!我人未出国
已在异国犯法
当然,这人皆有份的200英镑
绝不会让其他国家受邀的诗人
遭致像我一样的下场
让这个已经举办至20届的
国际诗歌节办不成
那些来自美国、澳大利亚
爱尔兰、南非等国的诗人们
是绝不会被英国的签证官判定
有移民倾向而加以拒签
(没准儿还欢迎移民呢)
如此说来我便是为国承担了
(金牌第一顶个屁用)
为那些赖在人家那儿死活不走
洗黑碗打黑工的不争气的同胞承担
那就承担吧
谁叫我是中国的大诗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