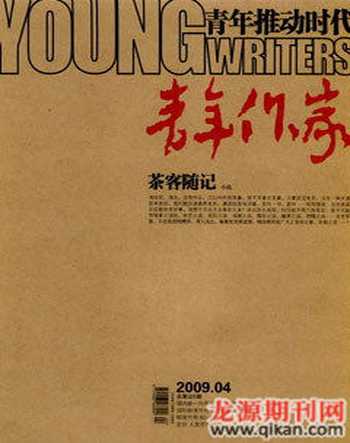非非与我的价值发生学
2009-04-29蒋蓝
蒋 蓝
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一条可以上溯的河流。水被石头割破,又被永无休止的冲力所揉搓。没有怒涛翻卷的汹涌,也缺乏信步幽径的娴熟,我就像忘记流淌的水,突然找不到干涸的河床,它在某种迷失的缓慢里,终于发现了那些蛰伏在土壤里的痕迹。因此,回忆的过程,往往与发现具有相同的冒险意味。
我回忆起了清秀的诗人尚仲敏。回忆起了单色印刷封面的16开本的《非非年鉴》。回忆起了《非非评论》,以及那时我对周伦佑、周伦佐、蓝马等人的形象推测。这些回忆被无敷的琐事隔离着,又被为数不多的信件所连缀。在我的河床上,那一片片开满云朵和阳光的水洼,立水为冰,竖冰为刀,时间的断片卡在我的肌体里,似乎预示了某种疼痛与荆棘丛生的玄机,将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展开它们的芒刺。
1
我的老家自流井,距离成都不过200多公里,但此形成的经济、文化距离却至少要以十年计算。体现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用一个例子就已经足够。1986年,当第三代诗人开始旁逸而出、朦胧诗的余绪呈现出回光返照的辉煌时,家乡的文人仍然在热烈讨论后者“懂”与“不懂”的口水争论。制式文学规范出来的创作圭臬,牢牢控制着本地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因此,当我首次从一个去成都开会的评论家手里接过一张《非非评论》时,一种浓重的陌生化感觉自始至终笼罩着我的阅读和思考。为什么是陌生化?那就是因为陌生,陌生其文体,陌生其观点,陌生其指向,也陌生其愤怒。从头至尾的陌生,使我拥有了“经验化的陌生”——这足以让人沮丧。记得首版上是周伦佑的长文《论第二诗界》,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定义了,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却明确给了我一种异端的、要从蓝蚂蚁制服一样的诗歌队伍里突围而去的勇气和底气。
一切似乎均遵照一种无形的安排而在推进。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就是尚仲敏。
尚仲敏毕业于重庆大学,被分配到成都水电学校教书。因为他的恋人是我的邻居,他经常出没在我的居所附近。来无影,去无踪。我注视着这个昂首挺胸、气质十足的诗人,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他发表在《诗歌报》上的《我对诗歌的看法》等文章,成为了我们开始交谈的话题。他很少从座位上起身,但满脸的笑意打消了我的疑虑。口语。语感。还原。举手为声。骑在牛背上找牛。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啊,祖国……他在口语里复活着他壮丽的诗歌风景。比如,那从《月儿弯弯照高楼》的冷峻笔法里,突然弥漫开的感动。偶尔,他用特立独行的沙哑声带朗诵起一些诗句,尤其是毛的《沁园春·雪》,抑扬顿挫,额头放光,引得周围的听众大受感染。
记得他经常说出周氏兄弟的名字,并描述周伦佑在成都和西昌的一些事情,引起了我不少兴趣和想象。在我的推测里,周伦佑应该是一个一直有着成熟模样的人,是一种可以放弃物质生活的诸多需求而专注于形而上领域收成的人。生活里有些人,提前长成了局长的模样,皮里阳秋,肚皮挺起,双手叉腰,可惜一直没有当成局长。但周应该是另一种人:即他的外形在他激烈的内心煎熬下,获得了被理想主义液汁全力浸渍后的非凡造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怪想法?现在回忆起来,估计是我透过他铺衍的理论的天罗地网,以及早期诗歌里闪现的理性的凌厉冰块,所复活出来的印象。2005年8月,我首次看到了周伦佑拍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照片,这种印象进一步获得了佐证。
1986年的秋季,在一阵冲动之下,我提笔给周伦佑写了一封信,诉说了我对“非非”的粗略印象以及一些近于混乱的认识。二周后收到了周的回信。他对我的错误认识予以了纠正,简明地提出了创办“非非”的目的及其意义。应该说,这封信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透过这页32克的白打信笺纸,我似乎看到了一幅正在展开的无法预测的画卷。
我陆续寄了一些诗作给周伦佑,他每信必复,认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作品,经我修改后又回到了那个叫“西昌市急救输血站”的终极地。记得我有《死亡》等3首诗,被他留用了。我必须承认,在我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语体之前,尚、周二人起到的引领作用,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现在看来,这种引领的意义十分奇妙,就像划过暗夜的一股热流,我不能十分确定,但却明确感到了热流的流向,甚至它流淌时发出的声音。这不但在自己的写作里,就是在自己日益困难的工作环境里,这股热流经常从我疲乏之极的身体里呼啸而过,从曾经阅读过的那些歌德派的夸饰语句中冲过,裹挟着金属的残片和大鹰的羽毛,为我开启了一个心驰神往的域界。我别无选择,我已经中谶。
在这期间,我去过成都几次,但每一次都没有见到周伦佑。但他留在成都诗友耳朵里的一些声音,都被别人转述出来。他几乎成了神龙见尾不见首的人物。
记得是在1989年,久不见面的尚仲敏突然落座在我家的椅子上,他拿出了2册杂志,送给了我。这就是我保存至今的《非非年鉴》1988卷和1989卷。如今,翻翻这泛黄的纸页,看见我在上面画出的狂乱的着重线,一种从没有说出的感觉终于圆成:对于感觉、思想都说不上早熟的我来讲,当时没有进入“非非”,的确是上帝意志一种富有深意的表达。我只能静静地观察,努力修炼自己的炼金术。当一把刀,切开空气不再风声大作、银光泼地时,而是毫无声息地等候,等到铁锈长满全身,等到浑身漆黑,但即使到了那种地步,也未必就预示着势如破竹。
从80年代末的夏季开始,诗人们走上了街头,肩负起了传道者的宿命。从那时开始,整个“非非”似乎突然消失于人头攒动的诗坛,他们被广播站式的语流彻底淹没了。接下来是消沉,委顿。啤酒。卤鸭子。女人。接下来全民都在做生意。从深夜娱乐场所退出来的诗人,沉浸在廉价化妆品所激发出来的汗水与快感中,他们把注意力从形而上的领域放回到皮带之下的敏锐里。
更奇怪的是,从90年代开始,诗人们变得不会写信了。
2
1992年开始,我到成都在一家挂靠在省社科联旗下的文化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所谓文化经济,就是以文化的名义搞钱。从本质上说,比商人直接问鼎利润,多一层遮羞布。我开始学习经营获利,学会如何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不至于被房东扫地出门。这个阶段,尚仲敏、蓝马合伙开设的位于黉门街的集团公司开业了。
尚仲敏的额头,比前几年多出了几道不显眼的皱纹。记得在一家叫“耕读园”的台湾人开设的茶坊里,从天花板投射下来的光,在他额头柔和地散开,他像一个镀金时代的宠儿,沙哑的嗓子不再朗诵诗歌,不再谈论密斯周。他说,冒险。赚钱。要凭思维赚大钱。然后真诚地笑。我承认,我的思维总是比时代慢一步,的确没有从他的教诲里学到妙手空空赚大钱的法子。而这个秘诀似乎蓝马也没有学到。这个时候,周伦佑在哪里呢?我问他们,他们说不知道。
直到1995年冬季的一天,由于东北诗人杨春光的缘故,周伦佑和在蓉的李亚伟、翟永明等近十位诗人应邀来到我所在的位于东门街95号6楼的文化经济研究所。周
穿一件短哔叽大衣,双手深深插进衣袋捣鼓着什么,戴着眼镜,显得有些矜持。哦,他戴了一顶鸭舌帽,很少说话,在一大帮诗人中显得卓尔不群。他与我握手时,我觉得他的手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粗糙。为什么会有那种想象?如今想起来也觉得毫无理由,但那时的确就是这么想的。在众人陆续散去后,我和周伦佑、黎正光、杨春光等几个人去吃火锅。
几杯啤酒下肚,酒力足以击退寒风,周脱了短大衣,谈了一些近年他经历的事件。涉嫌非法出版。打锣坪。想象大鸟。反暴力修辞。他说,要使暴力失去耐心。他竖起一根手指,手指如蜡烛,然后劈开空气,给了我强烈的印象。这个手势把我往年阅读他作品的印象全部激活了,这个独自点燃蜡烛的诗人,不但让我看到了微弱的火,也看到了那流淌下来的泪——这,难道就是曾经引领我的那股热流吗?
而且,这次与周的见面,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观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无法割裂的血肉关系。周的经历深深感动了我。精神只是物质历险的结果。没有纯粹的“坐而论道”或者来自“书斋的痛苦”,如果有的话,这些纸片上的思想一定是不堪一击的。从这个意见出发,我把那些“书斋里的革命”并“从事灵魂的冒险”之举,看作是灵感或烧酒的等价作用。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与周伦佑的联系多了些,也差不多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词锋断片》的写作。
由于受帕斯卡尔《沉思录》和尼采文本的诱惑,我迷上了断片的写作。而有“蓝花诗人”之称的诺瓦利斯,就有一本文集叫《Fragmente》,意谓断片、片段、残稿,至于钱钟书将其译为《碑金集》,固然美,但似乎失去了本意。因为断片本就是自古希腊以始的一种表达思想的最为理想的文体。我断断续续写作了3年,不时为各种生存的干扰所打乱。那时,我骑着一辆125型的摩托车不停穿梭在体制的走廊和巷道里,就像一个兜售走私货的贩子。偶尔走神,也突入到感情的危险地带。在经历了一次重大祸事之后,我躺在家里足足休息了30天。
1997年秋季,周伦佑应我邀请,到自贡一聚。相关情况,我在《有关<女邻居>的私人档案》(见《非非》总第8卷)当中已有详细描述。后来周伦佑为我的思想随笔《黑暗之书》所撰写的评论《后非非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开启》(见《非非》总第10卷及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散文·2004·秋之卷》)当中,也记录了他当时阅读我的《词锋断片》的感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000年5月,我参加了四川省作家协会举办的省第三届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我估计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文艺盛会了,我还给雨田、席永君、杨然、杨远宏等诗人打招呼、喝酒。会后我就留在了成都,参与了古图书工作室的相关工作。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与周伦佑的交往很自然地密切起来。
2000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带着一个穿大红衬衣和白色涤纶长裤的人,叩开了我租赁的小房子。来人是陈亚平。他嘴里流水线一般生产着夸饰词和大词,随着挥舞的手势在空气里不断铺排着自己的诗歌乌托邦。多年以后,诗歌圈子才发现,“大红衬衣和白色涤纶长裤”是陈的标志性建筑。周饶有兴味,话锋一转,谈及《非非》将很快复刊的重大决定。这就意味着,在经过8年的停顿后,“非非”重出江湖,这固然充满机遇,更充满挑战——如何超越自己的挑战;如何将诗歌的“非非”,进一步扩展为文学的“非非”、文化的“非非”、思想的“非非”?“非非”自身的内爆力与扩张力,还能够保证自己拥有一往无前的脚力吗?
这个时期,陈亚平身上那种类似“宣传队播种机。”的热力因子感染着“非非”里的很多人,使《非非》第8卷(即复刊号)的编辑工作十分顺利。他每次出现,红衬衣的火焰中,头发总是湿腻腻的。
在此,应该谈及思想随笔之于我的“发生学关系”。因为这是我写作过程中的重大变化,就仿佛被一个不明物体击中,它一直嵌在我的体内,炭火一样促使我不能停息。
与很多诗人不同的是,我一直有一种大量读书的固执习惯。这种扰乱“灵台”的举动,诗人们都说危险啊,我不过一笑置之。这一积累过程周伦佑在阅读我的《词锋断片》时就感觉到了。他没有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反而支持我,并对我在思想的成型过程中,应该重视的价值向度予以了反复强调——理清脉络,确定一个文本必须达到的四个目标,这是值得我终身铭记并受用匪浅的。
契机出现在一次寒风基的聚会。
2001年年底,伦佑的夫人周亚琴来成都,请“非非”同仁吃饭。在一家叫球迷火锅的大排挡里,突然,我感到了寒风中的暖意,将僵硬的肢体逐一打通的感动。一种充盈而自然的气流让我的骨骼卡卡发响。我说,我要写几篇文章。相信在场的陈亚平、陈小蘩等人均没有当回事。当晚,我写出了《堕落的最底部》。
然后,我完成了《思想的飞地》;完成了《蛊的阴谋和阳谋》;完成了《异端的宿命史》……
我的工作室搬到位于成都西郊的中央花园以后,周伦佑经常来我处,处理有关“非非”的稿件、对外联络、“非非”网站的设计、内容编排,一干就是一整天。间或对我正在推进的思想随笔提出他的不少意见,这对我十分有益。他成为了我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就像我在荒原里跋涉,终于找到了一个确定方位的觇标。因此,自己的思想,伴随着文字的反复推演。逐步得到了清晰和明确,并呈现出锋利的刃口。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睡眠极少,头脑清醒。如同经过冰镇,完成了20余万字的思想随笔,然后大病一场。
因此,刊发在《非非》总第10卷上的《黑暗之书》,不过是我完成总数的十分之一。我要说的很简单,没有自天而降的奇迹,一切都有迹可寻。
周伦佑、祝勇、敬文东、朱大可、周晓枫、张闳、高维生、马叙、王川、张清华、麦家、章治萍等作家和评论家则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他们对我的思想随笔的期许。我们处在一个典型的后极权时代,这是任何一个写作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侈谈民主与自由的知识人,应该好好读一读1884年3月24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它再明白不过的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对这一黑暗予以全面剖析,剔除其沐猴而冠、道貌岸然的诸多粉饰,让它在柳叶刀下露出本来面目,是我笔力荡涤的首个阶段。而我要同时准进的工作,则实在太多。
诺瓦利斯在《断片》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哲学家只是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诗人则解开一切束缚。”说实话,我很难消受这来自天国的福音。我只是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的身体经历和思想经历,就决定了他的枝条上盛开什么花朵。或者拒绝开放,或者用叶片击退风暴,就像周伦佑,就像宣告自己无罪的白色花。
断片的书写生活以及呈现经验的断片,诗与文之间完全独立,但因缺乏深刻的联系,单件作品可能完美于一个命题,但呈现出诗与文的封闭性与孤立性——这就
是我目睹自己以及大量诗人的文字生涯。因为诗人的文本不过是一堆对自由抒发的蹈空碎语,甚至是渴望被御用的“曲线救名”的机会主义策略,如果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与印证的话,则一定可以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复活体。
相反,诗与诗之间存在某种内在或隐蔽的联系,并在文体的迁徙过程里,文章与诗有时可能不够完美,但所有的诗与文将复活为我的全部,并将我的领土,清晰地铺展在一具绞肉机的锋刃之前。在既往的“团结紧张”的和谐模式下,人们心知肚明,“严肃活泼”给谁看?光荣花戴在谁的胸脯上?用拉康的话来讲,是一个利维坦式的“大他者”。拉康在著作《论文集十一》关键章节中,勾勒出了异化后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异化的对照面,即脱离:在“大他者”的森森利齿下异化,紧跟着是跳出“大他者”的队列。当人们的意识到“大他者”本身是那么前后矛盾的,绝对虚伪的时候,那么脱离“大他者”的行动就开始了……
3
2005年8月的一个雨天,在中央花园侧的茶坊里,我问周伦佑,迄今为止,在思想史上有三种最主要的思潮: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从思想谱系着眼,你认为“非非”属于哪一种思潮?周的回答是: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思潮”是一种流行的思想和观点,它固然不可能“纯而又纯”,它体现出来的主要价值倾向则是可以判定的。因此,我认为,纵观“非非”20年以来的推进与它经历的三次转型(20年以来,非非主义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判(反文化、反价值),90年代的道德批判(红色写作、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进入到当前的意识形态—一历史的批判阶段),“非非”无疑是急进主义的典型阐释者与实践者。在中国,急进主义大多率领风骚三五天。但是,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非非”这样拥有强盛生命力的急进群体了。
埃里希·弗洛姆晚年在《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一文里阐明了欲带领人类走出异化社会的“埃及”的先知存在的意义。他写道:“先知……他是一位揭示那已被预先决定了未来的预言者吗?他是一个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或愉快消息的传播者吗?他是卡桑德拉(cass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女预言者)的一个儿子吗?或者是他的一个神谕,他像阿波罗神谕那样,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尽管实际上他的指示可能是模棱两可的?”
这话,移之于“非非”也许是具有现实和超现实的双重意义。“非非”难道是当代汉语写作的卡桑德拉吗?非也。但历史的事实却证明:“非非”无疑是率先敲响体制写作丧钟的第一人。只要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非非”用一系列明确而大幅度的语言、美学实践,不但宣布了“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它还进一步宣布了“制式文化”与“制式写作”对自由思想的空前危害。
“非非”不但是摩顶接踵的实践者,同时也是富有深刻启示性的预言者。
“非非”的价值谱系中,其认识的发生学逻辑体现在对权力语境的辨认上:1集权是指权力集中使用;2极权主义是指高度集权和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统治;3权威主义,也有时候被称为“威权主义”,是指相对集权的政治上实施强控制而经济上放任自由的国家所实施的政治统治。这就意味着,集权与分权是一组概念,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权威主义是一组概念,它们分别描述三种状态的政治组织和生活方式。深入当下的汉语处境,坚持从艺术的立场而非政治博弈角度介入写作与思想,承担责任,正是“非非”不同于往常急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地方。
4
有一天,一个作者发来email问我,他看了很多个版本的解释,到底什么才是“非非主义”?我一时为之语塞。是啊,经历了两代人的“非非”,尽管有众多不同的解释版本,我该选择哪一个呢?
“非”字,《说文解字》释为:“韦也,从飞下羽皮,取其相背也。”非字之象,本意是指一只在空中展开翅膀的飞鸟形象,也近似于光源的发射。从造字立场来看,“非”字应该是会意字,两个背对着的东西。从语法上来看它是表示否定的一个词汇。而从结构上着眼,它是一个独体字。这个“非”字,汉语言里是指不对,常常和另外一个符号“是”放在一起,这个“是”和“非”相反。是“永远正确”的。
是是非非。谁是谁非,是非不分,是非分明等等,“是”与“非”永远是对立的动词。所以,“非非”不是“永远正确”的。它是连续的飞翔;是永不停止的动词;是不断的解构与结构;是对立的紧张;是悖论构成的聚力与张力所组合出来的力的流程图;是如鲁迅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是一道续接生命断片的黄钟大吕,为汉语写作和思想,送来了声震五内的金属之声。它们构成纠结的“非非系”,将是“非非”既留给世界、也是留给自己的客观存在。
但是,“是”与“非”从来有别。所谓是非不分,就是说分辨不出正确和错误。《荀子·修身》中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非谓之愚。”就是说能辩是非的是智者。我自知为愚者,也就只能以是非辩是非,询问是非了。在这个意义上,“非非”没有采取早年“非非式”的模棱两可,而是在时代的铁幕上,刻划出了自己的价值痕迹。
“非非”指向自由的天空,但“非非”从来没有忘记脚下的土地。这就仿佛“韭”字。非字在上形似一丛韭菜,一字在下代表土地,合起来“韭”字像一丛生长的植物。《说文解字》指出:“一种而九,故谓之韭。”
就这么非非,20年了,弹指一瞬间。诗人诺瓦利斯说:“生是死的开始。生是为了死。死是结束,同时也是开始,是分离,同时也是更紧密的自我连结。通过死而完成了还原。”但愿人们记住这样的话。在对立、对创生成中成长的“非非”,所形成的“非非系”,其实就跟古希腊哲人对哲学的解释一样。“非非”,就是关于生与死的学问。
祝愿“非非”!祝愿它二十年的飞翔与挫折,扛着石头的大鸟们。祝愿振翮飞翔的大鸟——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