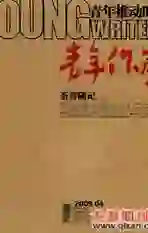乡土
2009-04-29文林
文 林
很多年以后,敖哥在回忆他父亲时,还念念不忘那封只在白纸的中央写了一行字的信。据敖哥说,那是他父亲一生中写得最短的一封信。也是他父亲一生中写的唯一一行诗。
敖哥是在去年秋天东山上开满了野菊花的某一天,向我透露他父亲那封只有一行字信的内容的,他说他父亲当年用蝇头小楷在纸的正中央写到:“白纸是你弄脏的,要负责任。”我听后有些不明白,直到后来敖哥给我讲起他在川湘故道上的那段往事,我才懂得了他父亲写这封信的真正含义。
那时的秀山是封闭的,许多娱乐活动都要往东越过白河到湖南的花垣和吉首才能看到。敖哥是名吉他手,他只能在闪烁的霓虹光芒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据官庄的人回忆,那些日子敖哥留着长发,肩上挎着一把红棉牌特大号吉他,常常穿行于四川和湖南之间。敖哥再次见到林晓晓是在辞去教师职务的第二年春天,那时的敖哥在川东地区已经是有名头的人物了。凡是喜欢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几乎都知道敖哥和那些由敖哥主持的歌舞演唱会。林晓晓是敖哥教书时学校里的学生,按她的话说,自己的音乐才能没有被敖哥发现纯属是个误会。因为敖歌教书的那一年,林晓晓正在害喉炎病,她的嗓子成天都在承受着针刺般的疼痛。林晓晓喜欢敖哥的歌,她说那些歌都长着翅膀。能够带她飞出官庄。她曾在敖哥辞职的那个下午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准备自杀,但却被一只鸟救了下来。她说那只鸟的叫声很像敖哥,整座山都被那鸟的叫声唤醒了,那一刻她沉浸在一片空灵之中,甚至看见穿越官庄的319国道像一条绸带飘了起来。那天,林晓晓坐在长满芭茅草的山顶上狠狠地哭了一场,后来便退学去了吉首。
敖哥再次见到林晓晓时,湘西的旅游业正在蓬勃兴起,无论是张家界的自然景观,还是凤凰古城和德夯苗寨,都在以喝风的速廖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据敖哥说,他是在舞会散场后吃夜宵时与林晓晓相遇的。在当时吉首最大的夜啤酒餐厅里,敖哥看见了正在端盘子的材晓晓:
“你啷个在这里呢?”
“啊,都来了好久咯!”林晓晓有些不自然。
“不读书了?”
“不读了。你坐噻?”林晓晓赶紧收拾敖哥身前的桌子。
那天晚上,敖哥一直喝到林晓晓下班,当林晓晓扶着有些瘫软的敖哥走在大街上时,东方的天空已在翻鱼肚白了。
敖哥和林晓晓同居了。那天上午,林晓晓在敖哥的身子下用惶恐的眼光看着一脸兴奋的敖哥,她说她是第一次,她要敖哥对天发誓,今生今世不再碰其她女人。那时,敖哥已经急不可待了,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红着一双眼睛就给林晓晓刺了进去……
敖哥并没有像林晓晓想象的那样,带她到歌舞厅里唱歌,他觉得林晓晓既然已经做了自己的女朋友、事实上的老婆,就应该守妇道,烧饭料理家务,使自己过上有人服侍的生活。而林晓晓却不愿意,她认为凭她的条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名气的歌手,挣更多的钱。这样,两人的关系在做爱后的第二天就变得紧张起来。
敖哥依然昼伏夜出,挎着他的吉他去歌舞厅串场。如今,他的歌已经唱红了整个湘西,名声像酉水、沅江上的木筏一样,就要下常德了。而林晓晓却变得闲了下来,她既不用到餐厅端盘子,也无需为生存犯愁。她除了有时去歌舞厅看看敖哥的演出,其他时间不是睡觉,就是逛商店。据敖哥后来回忆,林晓晓那时一天比一天无聊,有时,她会站在一个卖油粑粑的摊前长时间的发愣,或者又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早睡到晚,再后来,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购物。敖哥说,那段时间林晓晓每天的花销几乎能赶上一个十级国家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但林晓晓却认为那根本不算什么,自己成天没有事做,只有买东西才能让时间过得快一些,况且比起敖哥当时的收入,她花去的充其量也就是九牛一毛。
林晓晓的确在与敖哥同居的那个春天,开始了她一生中最疯狂的购物行动,那些日子,凡是商店里新到的时装、首饰、鞋帽、箱包和化妆品,林晓晓都会毫不犹豫地买回家,一样一样地摆弄、尝试、过瘾,以至于有一天当敖哥发现连自己睡觉的屋子都已经变成了堆放鞋子的仓库时,才不得不向林晓晓提出警告。
那天早上,两人大吵了一架,林晓晓的哭声惊动了院子里的邻居。据楼上的张婆婆后来给敖哥说,她刚听到林晓晓歇斯底里的尖叫时,还以为是隔壁小学校里的高音喇叭失了真。
林晓晓把一个多月来买的东西全部扔到了窗外的院子里,她蹲在地上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号啕着“受不了了!”那副绝望的样子,还真把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敖哥吓了一跳。
林晓晓赢了,她在与敖哥的那场对抗中表现出的烈性,让敖哥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畏惧。敖哥说,那种畏惧来源于男人的威严突然间丧失。林晓晓终于成为了八十年代中期吉首最豪华歌舞厅里的一名歌手,她演唱的歌曲大都出自敖哥之手,她的伴奏乐队也是由敖哥担纲组建的最豪华阵容,林晓晓几乎在一夜间就和敖哥齐名了。
现在,林晓晓比敖哥忙多了,她甚至忙得连换一双鞋子的时间都没有。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乐队和经纪人,出门也不用站在路边等车了,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就连狗闻了都会迷失方向。她和敖哥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那时,林晓晓已经住进了宾馆,她与敖哥分居的理由是敖哥永无止境的鼾声弄得她难以入睡。
她仍然唱着敖哥的歌,只是神态已变得懒洋洋的,腔调也越来越洋气,当敖哥有一天向她指出,这样唱完全失去了歌词所表达的意义时,林晓晓却满不在乎地对敖哥说,她不是在唱给乡巴佬听。
林晓晓完全像一只飞出了山沟的金凤凰,过上了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她在和敖哥分手的那个下午,将一个装有一万元钱的大信封放到敖哥的枕头上说:
“这是还你的,今后我们俩就清了。”
敖哥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就像个傻B,什么话也说不出,眼睁睁看着林晓晓走向院子外停着的一辆黑色皇冠轿车。
敖哥是在林晓晓离开自己的那年秋天回到已阔别四载的故乡官庄的。林晓晓的离去无疑使敖哥厌烦了都市的生活,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酉阳县龙潭中学教书。据敖哥说,那个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给他留下的记忆就像是一则童话。很多年后敖哥告诉我,那一夜是他过得最惬意的,他又听到了窗外溪流边悠扬的蛙鸣,看到了深蓝色的山峦在稍淡一点的天空下绵延伸展,犹如一头看不到首尾的巨兽,他还第一次喝出了不加蜂蜜的苦荞酒其实也带甜味。
官庄又能听到敖哥的吉他声了,他常常和幼年时代的伙伴们围坐在青烟缭绕的火铺上,一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边扯着嗓子高唱色意朦胧的土家民歌。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敖哥在官庄的马路边开起了专营酸菜鱼的餐馆。那时,由重庆去湖南、贵州东南方向的货车都要经319国道过官庄,敖哥给餐馆取名叫“急刹车”,还高薪聘请了两个土家族妹子做迎宾小姐。官庄一时间热闹了起来,许多当地的头面人物都把“急刹车”餐馆当作了请客的一个标准,而敖哥也再次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人物。
敖哥在远离都市的官庄过起了自娱自乐的悠闲生活,他用父亲留在家里的毛笔为餐馆写了一幅对联,上
联:“天不管地不管酒管”,下联:“醒也罢醉也罢喝罢”,横批是“管他三七二十一”。那些日子,餐馆里常常是夜夜笙歌,粗话里夹着年轻女子的笑声一直要持续到天明。
敖哥呼吸着由自己创造的官庄有史以来最热闹的气息,他的吉他声无疑就是热闹的中心。那段时间他将大量的土家民歌元素融到自己的歌唱风格中,形成了后来具有影响的现代川东摇滚。
“急刹车”餐馆真的要急刹车了。由于319国道实施改建,餐馆必须让路,敖哥在那个秀山历史上雨水最多的季节再次离开了官庄。他后来告诉我,这次是无奈的。因为搞“急刹车”餐馆,敖哥不仅把歌舞厅里赚到的钱全部投了进去,而且还借了一些外债,餐馆开业不到半年,这些投入只能是打水漂漂了。
敖哥这次没有去大城市,他选择了三省交界的边城茶洞。那时白河的水还没有被污染,沈从文笔下的翠翠码头还依稀可见,来自湖南花垣、贵州松桃和四川秀山的商贩,每五天就会在茶洞相聚热闹一次,把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茶洞镇弄得就像一座大戏台,尽多少人世间的悲喜剧在这里上演。
敖哥在靠近原国立茶洞师范学校,今花垣县第三中学的校门口租了一间面积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他要在这里招收吉他学员,让他的吉他声随白河奔流不息。那个雨季,他在镇上四处张贴招生广告,使所有看到他的人都充满了好奇。
吉他学习班开学的那一天正好逢场,敖哥领着十几个十五六岁手持吉他的孩子,分坐在镇西头街道两边的屋檐下。他一边大声嚷着,一边纠正孩子们握琴的姿势。霎时间,许多赶场的人围了过来,有两个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老汉还不停地招呼周围的人安静,说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敖哥的吉他学习班取得了初步成绩,那些有着歌星梦想的孩子们,已经可以坐在白河边用吉他伴奏着唱《故乡的亲人》了。那个秋天,茶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抒情,镇子上几个感觉好的大爷大娘也和孩子们一样,不时哼唱起一两句旋律优美的美国乡村歌曲。敖哥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茶洞人的生活,他的许多习惯成了茶洞年轻^效仿的榜样,比如留长发,睡懒觉,喝夜酒。凡是敖哥喜欢的,如今都会很快地流行起来。这也是林晓晓所没有想到的。据林晓晓后来给敖哥说,她真正懂得敖哥的了不起,就是在茶洞的那些日子。
林晓晓来到茶洞纯属偶然,那已经是敖哥办吉他学习班的第二个年头了。那天,敖哥在翠翠码头送走两个来自贵州松桃的朋友后,突然发现了站在码头边的林晓晓。据敖哥说,他第一眼看见林晓晓时,还以为是在做梦。林晓晓已经没有了几年前在吉首的那种风光,她穿着一件过时了的粉红色风衣,比起从前瘦了许多。她看见敖哥朝自己走来的时候并没有显露太多的诧异,只是用有些呆滞的目光狠狠地看了敖哥一眼。
“你啷个在这里呢?”
“啊,路过。”林晓晓的声音很沙哑。
“不唱歌了?”
“不唱了。”林晓晓低下了头。
敖哥说,那天他和林晓晓在白河边站了很久,他的脑子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过去许多和林晓晓在一起的情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地重现在他的眼前。后来,河面上升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雾,敖哥牵上林晓晓的手向他的小屋走去。
敖哥和林晓晓又同居了,这也是那个早春里茶洞镇最大的新闻。大人们议论着眼前这个来历不明却带着一脸忧郁的女子,而孩子们则似乎看到了又一个崇拜者,他们像害怕惊扰了林晓晓似的,都站在远远的用一种猜测和艳羡的眼光看着她,偶尔有一两个胆大的,也只是对着林晓晓木然的脸飞快地笑一笑。
林晓晓确实已不是过去的林晓晓了,她在湘西红了整整两年之后,突然又被再次发作的喉炎病带回到了从前。这次,她再也不能歌唱了,她被北京上海大医院里的名医诊断为晚期喉癌。据敖哥后来给我说,林晓晓那天在白河边本来是打算自杀的,却意外地碰到了自己。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林晓晓因再次遇到敖哥而获得了生命的归朴。
敖哥是在和林晓晓做完爱后才知道她已患晚期喉癌的。那天晚上,敖哥很后悔,他之所以将林晓晓带回来,只是想找回在吉首时丢掉的面子。但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林晓晓以为敖哥的心里一直都还装着自己,如今她躺在敖哥的身边,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愧疚。她不止一次地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敖哥,今生今世再也不离开敖哥了。
敖哥终于没有将心中的那份后悔告诉林晓晓,他只是给远在酉阳龙潭中学教书的父亲写了一封诉说自己内心苦闷的信。但茶洞人还是感觉到敖哥变得沉默了,他的琴声越来越沉重,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出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说敖哥的魂被那个突然到来的神秘女子勾走了,茶洞要不了多久,就听不到敖哥的吉他声了。然而细心的人又发现,那个名叫林晓晓的神秘女子,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带走敖哥,相反,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个神秘女子变得越来越开心,偶尔还向身边的人露出甜甜的一笑。
其实,林晓晓已不能支付她作化疗所需的高额费用了,她每天都必须注射大量的杜仑丁,以缓解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病痛。现在,她的痛有时折磨得让她恨不能将喉咙切割开,但她仍然坚强地支撑着,她没有让镇上的人看到她病痛的样子,甚至就连敖哥也很难听到她哼一声。她只是尽量把自己放在白河沿岸的青山绿水中,让痛随着河水流走,让生命化作无边的宁静。那些日子,林晓晓特别喜欢敖哥带着她到河边唱歌。据敖哥说,每逢此况,他们身后不远处都会站着许多人,这些人中男女老少参差不齐,站在那里就像一面回音墙,常常使歌声突然间变得响亮起来。
敖哥是在林晓晓病重的时候收到父亲回信的,他打开薄薄的信纸,上面只有父亲用蝇头小楷在纸的正中央写的一句话:“白纸是你弄脏的,要负责任。”那天中午,敖哥站在白河边,手里拿着父亲的信,久久没有离去。
林晓晓已经不能进食了,她躺在床上像一截枯萎的木头。她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暗淡,长时间地盯着布满灰尘的竹席屋棚。她现在只能用手势向敖哥传达自己的意思,她要敖哥坐在她的身边,过上一阵子就弹唱两首熟悉的歌。那些天,镇上的人常常听到许多凄美的歌声从敖哥的小屋里飘出。
敖哥承受着一个生命即将完结时散发出的痛苦,他没有让镇子里的好心人插手帮忙,也没有违背林晓晓的意愿,通知她家里的亲人。他只是默默地为林晓晓做着这样或那样的事情,闲下来时就盯着林晓晓看。敖哥后来对我说,那时他能从林晓晓的某个局部看到很远,就像以前在官庄教书时,他能从黑板的缝隙里看到自己的将来。
林晓晓终于在桃花谢落的时候死了,她的遗体被装在敖哥给她置办的柏木棺材里。那天,正好又逢茶洞场,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几个敖哥的学生还自发地穿上了孝服,他们弹着吉他唱着歌,走在灵柩的前面,犹如几只哀鸣的小天鹅。
林晓晓的灵柩由一辆牛车拉着,缓缓驶过白河往五十里外的官庄而去。那天天气晴朗,一抹春天的阳光洒落在白河两岸。清风中的翠竹摇曳着,如同无数的凤尾。敖哥说,那时他仿佛又听到了林晓晓的歌声,她温润、缠绵,就像眼前的四月天。敖哥还说,那天白河的河面上突然冒出来一对鸳鸯,他们依偎着,顺着一波波的清流向远方缓缓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