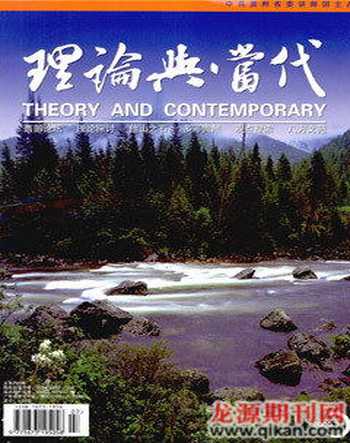黔北酒文化的历史视角
2009-04-29范松
范 松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经常被一些大人用来考孩子,其实他们自己也未必明白。因为这本是一个人类无法解答的悬疑。
近期看到一则报道称:加拿大某古生物学者通过对7千万年前恐龙蛋化石的研究后,发现是恐龙首先建造了类似鸟窝的巢穴,产下类似鸟蛋的蛋,然后恐龙再进化成鸟类,因为鸡也属于鸟类的一种,是由这些产下了类似鸡蛋的肉食恐龙进化而成。于是,一些人宣布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就是:先有蛋,后有鸡。
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解释,是否能终结这个延续了若干世纪的争论,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岂料一个类似的问题又摆在生活越来越富裕,喜欢品酒饮茶的人们面前。
早些年便已有人提出如下的疑问:我们日常喝的酒无疑是由人酿造出来的,但按照生物进化的轨迹,还在人类诞生以前,生物界的一些动植物在它们的生命结束以后,在温度、湿度和环境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发酵,会生成一种类似于酒的东西——尽管那时的动物们未必会去喝它。但那年那月,类似于酒的这种让人类钟爱了数千年的东西,是不是早已先于人类便存在了呢?
虽然这种猜想并不一定能证明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酒这种醉倒众生的东西已经存在于世间,但却可拓宽我们关于酒源的一些思考。后世许多站在人类至上立场的朋友,对酒先于人而出现的结论总是嗤之以鼻,在他们的眼中,没有人便酿不出美酒,酒是因人而生,因人而美,更因人才得以传承。于是,在那些善于编撰故事的文人笔下,便诞生出许多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人其事的“酒祖宗”。让酒这种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通过生活积累创造出来的饮品,变成了类似于后世专利时代个别人的发明,而历朝历代的史家们竟然转抄不误,用一本书的记载去印证另一本书。这实在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各种各样的“酒源说”虽然让人目不暇接,归纳起来,无非也就3种。即:仪狄造酒、杜康造酒和黄帝造酒。
在几种酒源说中,仪狄造酒恐怕是流传最早,受到质疑也最多的一种。《战国策·魏策》说:“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秦汉时期的文献有不少类似的记载,_直延续到宋代还有人承认这一说法,只是补充说明仪狄作的是“酒醪”,即我们今天的“甜酒酿”一类的东西。
其实,《战国策》的这段记录本身就有许多疑点。仪狄既然是禹时的一名女妪,造出了酒,献给了禹品尝,但经书里居然没有记她的名字。可见,有没有仪狄这样一个人本身就成问题。其次,禹既然“饮而甘之”,觉得味道好极了,却反而下令禁止制造,并疏远仪狄,似乎也有些不合情理。再者,仪狄所造的“旨酒”既然属于甜酒酿一类食品,禹品尝了这种淡淡的甜酒,居然便会联想到后世必定有人因为喝甜酒导致亡国,这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
或许因为仪狄造酒之说漏洞太多,后世又有人提出了“杜康造酒说”。这个杜康据说是夏后相的遗腹子,做过有仍氏的牧正和有虞氏的庖正。《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说,杜康即是少康,系夏朝国王,“有田十里,奴隶五百”,那个恢复夏朝统治,被称为“少康中兴”的人指的就是他。文献中虽有“杜康作秫酒”的记载,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或称“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实际上,究竟有没有杜康这个人,历史上同样有人持怀疑态度。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将杜康当作酒的代名词,因为传说他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封为“酒仙”。所以曹操的诗中才会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的句子。
还有一种酒源说,直接将酒的发明。归结到中国传说时代最著名的人物黄帝身上。其主要依据是,这位传说中的黄帝,曾经与岐伯讨论过“汤液醪醴”的问题。《黄帝内经·素问》载:“黄帝问日: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答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炊以稻薪者,取丙辛化火之义,以化生五藏之津。”岐伯的意思是:“五谷皆可汤液醪醴,而养五藏”。这哪里是在讨论怎么造酒,已经是在从医学的角度探讨酒的功用。所以,酒绝不可能是黄帝的发明创造,反而证明在黄帝之前,酒已经盛行于世。据说历史上备受推崇的三代帝王中,尧和舜的酒量都很大,可至“千钟”,后世的孔夫子,同样是好酒之徒,放开了喝,竟然“百觚”不醉。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酒源的文献记载,你抄过来,我抄过去,几乎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历史上的酒究竟出现在哪一个历史阶段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具权威性和科学可信度的,应该是那些通过考古发掘对出土文物研究的成果。
一些关于酒文化的书籍提出,对于人类来说,酒的出现应该以一定的农业生产水平为基础。只有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当人们已经用石锄、石镰一类农具将社会生产水平推进到一定的高度,麴蘖酿酒的事才会发生。这显然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分析,考古学家们通过对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物的分析,对这种观点做了印证。那里发现的袋形窖穴及窖穴中的栗粒和穗,说明那一时期的人们,除了养活自己,开始具备了用剩余粮食酿酒的条件。
无论从地形、地貌、区位、气候哪方面进行考察,贵州高原都是世界上最适合物种生存繁衍的地区。不客气地说,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了。还在山顶洞人出现之前,贵州的水城硝灰洞人就已生活在距今六盘水市一带,并运用他们的智慧,率先创造出打制石片的锐棱砸击法。这种由贵州古人类开创和发明的工具制造法,不仅是贵州旧石器时期文化的主旋律,某种意义上,甚至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
贵州的史前文化遗址十分丰富。以往曾有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贵州有较多发现,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贵州境内的文化遗存并不突出。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否定了这一结论。事实是,无论距今几十万年至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或是距今一万余年至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贵州都有着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
坐落在黔西县沙井乡的观音洞,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与旧石器共生的文化遗址,也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代表。它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一起,分别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曾指出,它“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但在贵州,尤其在沿赤水河一线,类似观音洞时期的文化遗存并不少见。毕节境内的二道河是赤水河的一条支流,就在二道河上游的海子街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名为扁扁洞的旧石器文化遗址,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石制品的研究,专家们发现了它与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内在文化联系。这足以证明,数十万年前,沿赤水河流域已经是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子孙的乐园。史前人类在那里创造着古老的文化,发展那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丰富多彩的生活奠定基础。
扁扁洞遗址以西的毕节青场,有一处名为老鸦洞的文
化遗址。1983年,贵州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那里发现了1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动物化石。那之后,包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内的几家单位,又多次组织有计划的联合发掘研究。发掘的九层堆积土中,共有七层含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其中的一层竟是灰烬层,含有烧骨和碳屑。它不仅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该遗址的断代依据,证明生活在老鸦洞的史前人类处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交替期,更依稀向我们揭示出当时人类的生活景况。
如果说扁扁洞、老鸦洞两处遗址都处于赤水河上游地区的话,沿赤水河往东至仁怀、习水,再经遵义进入桐梓,这一线的史前文化遗存同样十分丰富。
桐梓河是赤水河下游的一级支流,其中的一段也是仁怀、桐梓两县间的界河,下游在习水县境内称牛渡河。该河总长9l公里,在桐梓县境内的积雨面积达1162平方公里,是桐梓县南部的主要河流。沿桐梓河往东不远即是远近闻名的九坝镇。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那里一处叫岩灰洞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意外获得lO多件石制品和2枚人牙化石。1983年发掘时又获得人牙化石4枚。这些人牙化石前臼齿的齿冠尺寸与北京猿人类似,门齿又与早期智人接近。这种继云南元谋猿人之后发现的古人类,学术上被命名为桐梓人。他的发现,揭开了贵州高原史前社会生活的面纱。
赤水河流入习水县的地点是该县郎庙乡的两岔河,流经回龙、隆兴、醒民、土城,于小坝一带的居仕岩出境。土城是习水县的西部重镇,有着悠远的历史。1983年出版的《贵州文物》杂志介绍说,上世纪40年代,当地人就在赤水河谷两侧的阶地拾得过打磨精细,两面有刃的石斧。曾将之称为“雷楔”,视作无价之宝。那以后又陆续在附近的十多处地点,发现和搜集到新石器若干件。专家们研究发现,这批史前石器的石质均为砾石,系就地取材加工制作而成。足见土城附近气候炎热的赤水河阶地、坝子与两侧河谷地带,是十分适于古人类生产与生活地区。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与有计划的必掘,将会有更多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发现。
历史上,贵州这片土地是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这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例如区位上距离中央王朝统治中心遥远,山重水复、地形复杂、交通梗阻等妨碍了对外交流。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只将目光投向土地肥沃富饶、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以便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养活数量庞大为他们护卫保驾的官僚机器和军队。因此源自古代的各种文献,涉及到物产时,言必称中原,言必称黄河流域。似乎中华文化是一种单元的,从黄河流域扩散开来的文化。虽然这种文化研究上的狭视,早已被后来大量的史前文化研究成果所否定。但在酒源研究上,今天的许多著作,仍不免保留着一些这方面的痕迹。
人们在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中华酒文化的时候,提得最多的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和磁山文化等遗址,而这些遗址几乎全都在黄河中下游。理由不外是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粮食堆积遗存和类似于后世酒具的陶制品。事实上,长江流域发现的文化遗存并不比上述地区逊色。撇开河姆渡、三星堆遗址不说,就在昔日鲜为人知的贵州,就在赤水河流经的广袤地区,同类的史前文化遗存不仅内容丰富,更可令人眼花缭乱。
早些年,极少有人了解贵州史前文化的辉煌,所以,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先生才会发出“贵州有如此多的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实出我们预料”这样的感叹。近年来,贵州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不仅为人们了解中华酒文化的源流,提供了大量考古佐证,也揭示出茅台其所以能成为国酒享誉世界的历史根源。
2006年5月9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在京揭晓,威宁中水遗址人选“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水位于乌蒙山中段,东南距威宁县城约100公里,西北距云南昭通市20公里。这个贵州西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才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中水遗址所包含的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三个类型的遗存不仅在时间上早晚可相互衔接,而且还具有密切的演变关系,足可建立贵州西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序列。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贵州省考古所与四川大学联合在威宁中水进行的发掘中,发现大量农作物,其中主要是稻谷。吴家大坪遗址的3个坑内出土大量稻米,鸡公山遗址发掘的300多个坑中,80%以上的坑都有稻米颗粒出土。中科院考古所的专家研究后认为,稻米颗粒短粗,水稻特别矮小,比现在水田种植的粳稻还短小,不像是水田种植的。经技术检测,出土的稻米距今3115年左右,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早稻农业实物遗存。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说明,早在距今数千年前,有着辉煌史前文化的贵州高原,已经充分具备了生产酒的基础条件。
研究酒源的学者,还喜欢用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说事。举出某些遗址出土的红陶或灰褐陶的碗、大小口壶,或彩陶碗、罐、杯,或深腹碗、罐、双系小口壶等为证,并特意说明这些东西虽不是专用酒具,却可以完全用于盛酒和饮酒。
然而,类似这样的陶制品在赤水河流域并不少见。威宁中水出土的文物中,不仅有大量陶罐、陶瓶、陶片及部分青铜器,还发现了祭祀台遗址和大量用于祭祀的水稻。毕节瓦窑遗址的发现,显示夜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青铜时代,那里的出土物除铜器外,还发现了专门烧制陶器的圆形单孔小陶窑,出土的文物包括壶、罐、碗、豆、钵、圈足和纺轮。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显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并不大。
沿赤水河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酒文化的发源地并不一定就在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黄河流域。许多事实证明,赤水河同样是中华酒文化的孕育者。仁怀、习水、赤水等县市,甚至包括与之相邻的四川古蔺县,历来是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有关考古成果显示,距今数十万年前,赤水河一带就有了古人类的足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里的土著人已会用磨光的石斧开荒种地,用双孔刀收割粮食,用石杵和石磨来加工谷物。五千年前,他们已经以农业为主,过上了定居生活,还学会了烧陶、纺织,更重要的是有了与酿酒直接相关的“粮食剩余”。
贵州这片地区并没有从娘胎里带来的落后。灿烂辉煌的史前文化自不用说,即使夏商之世的鬼方,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这一带依然拥有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都可对此做出充分的证明。夜郎不仅有10万精兵,有着颇为发达的青铜冶炼业,还享受着宁静农业定居生活。人们在夜郎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的陶制品,壶、罐、碗、豆、杯、瓶一应俱全,一些陶器的显眼部位还有以横、竖、斜为主的刻画符号,大有汉字“象形”、“指事”一类的特点。面对如此众多的陶制品,我们已经没有再去探讨它们中哪些属于酒具,哪些可以用来盛酒的必要了。
我们今天所饮的酒,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劳动者在长期生产过程中,积累、发明和创造出来的。辽阔的中华大地既是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一体多元的文化氛围下,酒的起源绝不可能局限于一处或少数几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其他区域性河流流域都有可能发明和创造出自己喜爱的酒,发展本地区一定历史时期里的酒文化。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的作用下,那些不具备酿酒优裕环境与条件,缺少独特工艺的酒,逐渐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虽不得已又不可避免地退出了社会舞台。而到今天,国酒茅台的一枝独秀,赤水河流域酒业的兴旺,最终证明以茅台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正是那条源于云南、主体流经贵州的赤水河,孕育和铸造了中华酒文化的辉煌。
责任编辑:田茂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