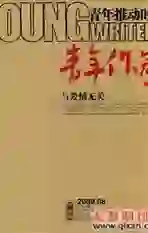滴血的红高粱(外一篇)
2009-04-29长笑
长 笑
拴在西厢房的驴拉长声音叫了起来,然后又用蹄子刨地,一下连一下刨得很重,那声音把刘先生本来就安静不下来的心搅得更乱。牲口怕是渴了,刘先生缓慢地把放大镜从一本发了黄的《本草纲目》上移开,出溜下地,穿上鞋来到院子里。两只大白鹅见到刘先生,一扭一扭地朝他走来,嘴里“嘎嘎”的叫着。刘先生没理它们,径直走到西厢房给驴添了点儿水,看着驴喝了几口,拍一下驴的脖子,就走到院子里对着日头伸了伸懒腰。
刚才,小郑子家二小子来请他,叫他给小郑子去扎扎针,说是小郑子快不行了。当时刘先生的儿子刘敏正在堂屋收拾药箱子要出去,听见后走进屋就对小郑子家老二说我爹的腿疼,出不去,把小郑子家老二打发走了。
好像好几年没有见到小郑子了,尽管住在同一个村,尽管原来还在一起搭档过,因为那些不堪回首的老事,刘先生永远也不想见他,所以,当儿子拒绝他给小郑子去扎针后,他只是不自然地摸了摸腿,看着小郑子家老二走了。
他问儿子,说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刘敏说他当年害得咱还不够吗?再说,快死的人,你就能给扎好?我都怀疑是想在咱身上赖个棺材钱。刘敏说着撇了撇嘴,五官严重变了形,那样子像是遇到了十分不相信的事。既然儿子这样说,刘先生没有再说什么,等儿子背起药箱去出诊,他就接着看他的本草纲目。
艳艳的日头晒在身上很暖,整个身子像是浸泡在一盆温水中,那种热热的感觉顺着毛孔往心里钻。两只白鹅见刘先生不理它们,扑棱几下翅膀朝着东厢房的门口走去,几只老母鸡在南墙下的背阴处刨食,小院显得温馨而宁静。刘先生习惯地摸一摸胡子,脸上带出了一丝幸福。他的胡子保养得很好,雪白,飘逸,有半尺多长,配上满头白发和仍旧红润丰满的脸,的确有一种仙风道骨的风韵。先生两个字是村里人对他的尊称,他也以这两个字为自豪。
现在的日子叫刘先生满足,儿子接过了他的诊所,已经在这一带闯出了一点儿名声,孙子上了大学,他自己每天除去吃喝就是看看书,只偶尔有人来请他给扎扎针,安逸,闲在。什么叫幸福?刘先生感觉这就是幸福,而这晚年的幸福对比起年轻时的坎坷就更显得珍贵。想想小郑子,当年那么风光,到了晚年怎么样?听说已经在炕上躺了两年,儿女们伺候得已经不耐烦了。
不知道现在的小郑子什么样子,一个在炕上躺了两年的人还能有人形?想想当年,就好像是昨天,日子可真快。
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不时地摸一下胡须或者头发,刘先生在院子里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地走。他喜欢这阳光,喜欢这样走,喜欢院子在阳光下的宁静,总觉得阳光晒在泥土上发出一种味道,尽管很淡,却叫人舒服。
六十年代初他回到了村里,那时候小郑子精干,是村里诊所唯一的赤脚医生,而诊所就开在他家的堂屋。由于小郑子的家斜对着公社大院,公社的人和拿药的人在他家里每天都络绎不绝,对于一个村里人来说,这已经足够显赫,所以村子里的人就管小郑子家叫郑家门楼。尽管他家的门楼不高,也不是很大,但在人们心目中还是觉得够气派。刘先生那时候年轻,回到村里和小郑子搭档,也成了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印象中小郑子非常神气,仿佛在他那五短的身材上随时都放射着一种光芒。小郑子爱笑,但笑完后一扭头立刻就一脸严肃,故而刘先生一直也不知道他那笑是真的还是假的。
回村以前的那一段经历,是刘先生一直不肯提起的,村里人知道的不当着他说,儿女们也不敢问,那绝对是刘先生心头的一块隐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少,知道那些事的人不多了。那时的刘先生应该是个才子,他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高中生,在北京读书,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那时他每天想得除去功课外就是诗词歌赋。曾经抱着红楼梦流泪,也曾站在北戴河的海边吟咏“翩翩海鸥我惊起,片片白云是渔帆”,几乎是雄心万丈,不知道将来毕业后去干一番什么大事业。却没想到,家里的媳妇由于和他母亲打架,上吊死了,他的命运也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被举得高高的人一下子摔在了地上,完全都成了碎片。按说,媳妇的死和刘先生没有大的瓜葛,可丈人家揪住不放,加上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法律可讲,况且他家里的成份又高,就把刘先生关进了大狱,一关就是五年。还好,监狱里管事的人见他是高中生,也没有什么大罪,安排他学狱医,给犯人看病,甚至在他刑满释放的时候还想将他留在监狱工作。刘先生不干,对监狱的领导说知道的说我工作了,不知道的还会以为我仍旧被关着。就这样,他回到了村里,和小郑子成了搭档。当然,当时的刘先生知道自己几两重,一是比小郑子年轻,二是自己是刑满释放份子,所以他就成了小郑子的跟班。
本来,刘先生的生活会这样安定下来,要不是以后发生的两件事,他的命运可能要好一些。但是,像所有事情一样,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谁也不敢保证不出现偶然。
两只大白鹅中的一只,伸长了脖子叫了一声,那样子好像是在和刘先生打招呼。刘先生看一眼,朝鹅走过去,他突然想摸摸鹅身上那雪白的羽毛,甚至把鹅搂在怀中呆一会儿。但是,两只鹅看刘先生快要走到它们跟前,竟一扭一扭地走开了。刘先生摇摇头,微微笑一下,那样子像是在无奈中还有些慈爱。
小郑子今年应该是七十六,正好他大五岁。按说还不老,可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年。人哪,什么好也不如身子骨儿好,啥时享福也不如老来享福。
刚回到村里的时候,小郑子简直是刘先生的偶像,人家早就是诊所的医生,属于前辈,加上他家和公社的领导们打得火热,况且他自己是一个刚从监狱放出来的人,心理上总觉得比任何人都矮三分。所以,那时候的刘先生不仅怕公社的干部,就连村里的乡亲他也怵头,那种卑贱的感觉时刻像一座见不到太阳的大山在他附近,分分秒秒影响着他。所以,他只有给小郑子背药箱的份儿,见到谁也是怯生生的一副面孔。而小郑子,则是意气风发,站在村里的任何地方都是一号人物。
现在呢,听说自从小郑子躺到炕上以后,孩子们已经失去了伺候的耐心,冷一顿热一顿,一两个月也不定给擦一回身子,他躺的房间臭得进不去人。也难怪,人都说百日床前无孝子,怪不得儿女,都是该享的福在年轻时享完了。刘先生摸一下胡须,一股说不上是怜悯还是无奈的心情涌上来,叹一口气,扭头往屋里走。
到炕上坐下后,扭回身在窗台上拿他的放大镜,想继续看《本草纲目》。隔着玻璃照在窗台上的光线很足,在放大镜底下照出了一个白亮亮的光点儿,不知道从哪来的一只蚂蚁在放大镜旁边爬着,似乎是想爬上放大镜上去,但努了几次力都爬不上去,终于还是放弃了,蚂蚁绕开放大镜像是要朝炕上爬。刘先生想把它捏起来,但又担心那细小的身躯经不住自己手指的力量,犹豫了一下,就把手放到蚂蚁旁边,看着蚂蚁笨拙的爬上自己的手指,再沿着手指往手背上爬。这是一只还很小的蚂蚁,呈棕红色,像是刚来到世界上不久的一个小生命,它的腰身很细,拖着一个相对大点儿的肚子,那些脚显得那么细小,以至于爬在自己的皮肤上竟没有多大的感觉。刘先生知道,这就是老了,人一老手上的皮肤就粗糙了,感觉也没有年轻时候那样灵敏。于是,刘先生感叹一声,知道自己虽然一直保养得很好,但毕竟是快要落山的日头了。
他平举着手,害怕那只蚂蚁掉下来,出溜下炕走到院子里,看着蚂蚁爬到墙上,心里有了一丝暖意,再看这小东西一眼,才走回屋里。
放大镜下的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必须要调整好距离,怎么也不如自己的眼睛好使。但是,眼花了,不借助花镜或者放大镜再也看不了书。
“鸟产于林,故羽似叶;兽产于山,故毛似草。”这是为了适应,为了生存的适应。年轻时的刘先生什么也不敢说,看见的当作没看见,听见的死死压在心底。这是他当时的做人准则,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几乎是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但是,千小心万小心,他还是在这上头吃了亏。那一次是给南头的张耀看病,照例是他背药箱,也照例是看着小郑子给张耀测体温,小郑子说需要输液,他就只好回诊所去拿输液的东西和药。诊所是小郑子家的堂屋,但他没找到生理盐水,想着有可能被小郑子放到了他家的东屋,就来到小郑子住的东屋去找,推了一下门发现是关着的,只发出“咣当”的一声响动。他有些奇怪,觉得小郑子的媳妇应该在家,就下意识地从门帘的缝隙里朝里看了看,没想到就看见小郑子媳妇和公社的刘书记两个人正在里边急急忙忙提裤子,一黑一白两个肥大的屁股像两颗炸弹在他的心里炸响了,顿时,他觉得脑袋“嗡”的一下,浑身的汗毛都仿佛在一瞬间立了起来,他赶紧逃离了现场。
从此他知道了小郑子家为什么那么有权势,为什么连村里的干部都看小郑子家的眼色,也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从此,他的话更少,做事情也更加倍地小心。
公社的刘书记没事人一样,小郑子媳妇也和没事人一样。书记还是照常到小郑子家串门,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倒是刘先生总觉得别扭,再不敢正眼看刘书记,也不敢正眼看小郑子媳妇。他自己发誓,这件事就当没有看见,誓死和谁也不说,而且提醒自己,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再不到小郑子家任何一个角落乱串。但是,他的心里却怎么也挥不掉这个阴影,总觉得自己的身旁放着一包炸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
突然有一天,是他自己在诊所,不知道小郑子媳妇是故意还是无心,她来到堂屋和他搭讪,他能听出来,小郑子媳妇没有要紧的事可说,倒是那双眼睛里发出来的光像是两把钩子,不仅锋利,还带着寒光,叫他从心里往外冷。小郑子媳妇说看你的话很少啊,整天像个老和尚。他不言声,听小郑子媳妇接着说。小郑子媳妇说不爱说话的人好,省得言多语失。他懂这话里包含的意思,只是他没有办法告诉小郑子媳妇自己的决定。他发现,其实小郑子媳妇并不漂亮,很普通的一个人,只是从后边看那一扭一扭的屁股倒很丰满。
刘先生知道,后来他的遭遇肯定和这次发生的事情有关,不是小郑子的媳妇倒霉,是他倒霉,他预感到自己当赤脚医生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那一段日子,他一直处在紧张和焦虑当中,害怕自己要出什么事,可好长时间又没出,就好像一个听到死刑宣判的人,却又迟迟没人搭理他,所受的折磨真是难以忍受。这事现在说起来奇怪,当初受折磨的本应该是公社书记和小郑子媳妇,而事情就是那样荒唐,正好颠倒了过来。
惶惶不安中,他过了好长时间,事情在他的心里慢慢地有点儿淡了,他以为只要永远不说,可能就没事了。所以,他的头一直低着,从来不敢到书记和小郑子媳妇面前去晃悠。
拿着放大镜的手晃了一下,书上印的荠菜的锯齿形叶子被放大成了一座座山峰,然后模糊了。他移开放大镜,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用左手再摸一下胡须,端起已经有些凉了的茶水咽下去一小口,就听见院子里的鹅有些发狠的叫。
是小郑子的大儿子,眼泡有些浮肿,一副落魄的样子,和早年在县城工作时的模样相比简直变成了两个人。那时候他回到家里后总昂着头走路,见谁也爱搭不理,只是后来他在的厂子倒闭又回到家里,才变成这个样。小郑子的大儿子管刘先生叫叔,是乡亲辈儿,他说还是请刘叔到我们家去一趟,说我爹眼看是不行了,可我姐姐还没赶到,想请你老人家给他扎扎,能多留一天最好。看见刘先生皱眉就又接着说,我知道当年我爹娘对不住您老人家,但现在是看着我去,求您老了。刘先生说为什么非等你姐姐?小郑子的大儿子说我姐姐的理数太多,想叫我爹穿她准备的装老衣服。刘先生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说我扎扎就能多留一天?小郑子的大儿子说我相信您老,所以特地来请您,您就去一趟吧,给他看看也是好的,即便是扎不了,也能告诉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刘先生一辈子就怕别人求他,况且他觉得也应该去看看小郑子,那个和自己一辈子恩恩怨怨的人,现在是什么样。于是,他带上自己的针,跟着小郑子的大儿子走出来。
小郑子不是个厚道人,刘先生的体会最深。按说凭他以后的遭遇,说什么也不应该去给他扎针,但人不是老了吗,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吗?小郑子这几年的日子也报应了他,刘先生不想再和他计较。
那一年,难忘的秋天,像是有一把刻刀深深地在心上刻下了一道疤痕,任何时候触碰到那里它都会疼痛。
正是刘先生提心吊胆熬日子的时候,是个傍晚,日头红得像血一样,仿佛把大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映红了,诊所窗户上的玻璃向屋里反射着红光,他有些烦躁,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几次忍不住跑到外边看日头。日头很大,一点儿也不刺眼,好像是在西边的天上淌着的一汪血,炫目,灿烂。
生子骑个车子风风火火来到了诊所,说刘更把腿砍坏了,叫他们快去,于是他跟着小郑子带上药箱也骑着车子来到了高粱地。
那年的高粱格外的红,没放倒的高粱遮天蔽日,放倒了的高粱秸尸体一样七躺八歪。血红的日头照在血一样的高梁上,看得叫人心里震颤。刘更的腿被镰刀开了一道口子,本家的侄子正用一只手给他使劲儿按着,浓浓的血依旧顺着侄子的手指缝往外流,沿着刘更的腿淌到地上,泥土变成了暗红。小郑子不紧不慢,一边开着药箱一边问旁边的人怎么砍的,他在旁边猜想肯定是伤着了血管儿,必须紧急处理。小郑子叫当家侄子松开手,顿时,那血浆带着压力喷了出来,直接就喷到地上的高粱上,在泛着白霜的高粱叶子的沟槽里形成了一道小河,然后再从叶子上滴落下来。小郑子先是用药棉擦,想敷上消炎药再给刘更包扎,但无论如何也敷不住,因为在血流的冲击下药粉连一会儿也呆不住。没办法的情况下,小郑子就用绷带硬是给刘更捆上,但没有多一会儿,血顺着绷带依旧朝外流。
记得那时候一切都是红色的,红的惊心动魄,只有刘更的脸越来越白,什么时候想起那个场面他的眼前就都是红色。
刘更是他的本家,论辈分还应该管刘更叫叔叔。平日里刘更壮得像头牛一样,尽管有些二百五,但他生就了一副媚骨,整天给小郑子家干这干那,无论是自留地的庄稼还是小郑子家的茅房,凡是又累又脏的活儿刘更全包了,几乎就是小郑子家的长工。谁都看得出来,刘更就是凭了这个,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按说小郑子应该抓紧给刘更抢救才行,赶紧用止血钳止血,不能叫刘更失血过多。可看他那个样子,不仅不着急,还分明是不懂,就任由刘更的血往外流。
到处都是红色,惨红惨红的红色。他知道自己应该下手,赶紧把刘更的血止住。但是,这在众人面前小郑子肯定下不来台,加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那件事,他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时候,刘先生瞧不起刘更,但怎么说刘更也是当家的叔叔,如果他再不下手,刘更肯定有危险。
刘更身下的高粱几乎全浸上了血,旁边高粱叶子的沟槽都像小河一样流,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出声,只有秋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的心也在滴血,因为他感到了一阵阵的疼痛。看看刘更,脸色越来越白,而小郑子还在自言自语: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终于,他下定了决心,推开小郑子,很快把刘更的血止住,然后进行了包扎,但刘更却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看一眼小郑子,发现小郑子对他说你早点儿干什么着,这话似乎是埋怨他不早下手,但他分明在小郑子的眼里读出了一种恶毒,一种带有仇恨的恶毒。
他知道,把小郑子伤了,在众人面前伤了,肯定是下不来台。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
果然,当年的冬天,借着一个小小的运动,刘先生被关进了“学习班”,检查,批斗,游街,逐步升级。他就成了坏分子,刑满释放分子,再也不能当赤脚医生,只能跟着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儿,而且每天早晨还要扫大街。
三天一批斗,五天一游街,这些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孩子老婆也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他负责清扫的街道就是小郑子家门口那段儿,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灰尘飘扬中他甚至能听到小郑子家的嬉笑,看到小郑子两口子趾高气扬的在他面前走过,看到刘更对公社书记还有小郑子一家奴颜婢膝。每当这个时候,他的眼前就会出现那红红的高粱,出现高粱叶子上小河一样的鲜血。他经常想,他是坏人吗?从小回忆到大,他没做过坏事,可他却成了坏分子,那些嘴里喊万岁,偷着通奸的人倒趾高气扬是好人,这是命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是命,为什么偏偏对他这样不公?他的头发就是在那个时候全白了的,连带着胡子也过早的白了。
那时候没有想到过翻身,他甚至想一把火将小郑子家全烧死,把公社的大院烧成平地,然后他就自杀。是儿子和老婆叫他下不了那个决心,就那样忍受了那么多年,直到取消成分,摘掉帽子,他好长时间都还都是不敢直起腰,也不愿在郑家门楼前走过。仇恨,那个时候他浑身的血液里流淌着的都是仇恨。
路上,小郑子的大儿子说看您老的身体多好,这才是福。他说是的,有个好身子骨比什么都强。他问小郑子的大儿子,说小郑子多长时间不进食了,还能不能说话。两个人一路说着话,就来到了大街上。
日头很足,尽管他们走得不快,但身上还是感觉有些热,谁家的狗趴在门前张着大嘴喘气,看见他们过来一双眼睛就随着他们移动,没有恶意,也没有友善。这一段往前就是当年他扫街负责的地段,好像那时候他扫街总有一条狗跟着他,不远也不近,那时他觉得自己也像一条狗,而且是丧家的狗。最难忘的是一次他正在扫街,小郑子媳妇扭着屁股迎面走了过来,竟然停下来看他扫街,那样子,那神态仿佛是许多无形的芒刺,隔着衣服朝他身上扎,叫他没有一个地方不刺痒。他停住不是,扫也不是,索性弄起冲天的尘土,这才把小郑子媳妇赶走。她临走的时候骂了一句缺德,但他听着不像是恨,倒有几许嬉笑的意味,但不知怎么,那嬉笑却比恨还让他更难受。恨还说明是在乎你,要是连恨都不恨了,说明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像一块砖头,也像一棵树,没人想起你,也没人恨你,你所能告诉人家的只是你还存在着。他觉得厌恶,恨不得追上去拍她几扫帚。
郑家门楼还是老样子,门也还是那两扇门,只是都显得有些破败,给人一种阴森灰暗的感觉,刘先生奇怪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小郑子的儿子们怎么也不翻盖翻盖。
小郑子还躺在那间过去就是他们卧室的炕上,从前这里是诊所的时候,刘先生总觉得这个房间又宽敞又明亮,可今天却觉得很昏暗,而且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屋里气味儿非常难闻,要不是刘先生这样干了大半辈子大夫的人肯定没人受得了这样的味道。小郑子仰面躺在炕上,已经瘦得不成人形,脸色发紫,而且带着一种黑灰色,和死人的脸没有多大区别。他的眼睛闭着,嘴张成了一个圆,一口一口的倒着气。他的旁边放着一个空碗,再远一点儿有个暖瓶,靠近那张老桌子的上方挂着小郑子老婆的遗像。
这就是小郑子,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家伙?刘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要不是他那两只稍有一些三角形的眼还真不好看出来。
小郑子的大儿子大声对小郑子说爸,我刘叔看你来了,小郑子没有反映,甚至紧闭着的眼睛一点动静都没有。刘先生挨着小郑子的头坐了下去,拿过他那只枯柴一样的胳膊,把手指放在小郑子的脉搏上,自己眯上了眼。
其实,在监狱当狱医的时候,刘先生学得是西医,还是他被打成坏分子以后,为了打发难熬的日子每天晚上看中医书,十来年的时间,使他从简单知道一些西医的知识变成了一个有些经验的中医,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找他扎针。
屋里很静,只有小郑子一口一口倒气的声音,却也很微弱。过了一阵,刘先生挪个地方,又拿起小郑子另一只手。这次他没有眯上眼,而是在小郑子的脸上打量,还用另一只手翻翻小郑子的眼皮。一边翻看着,一边冲小郑子的大儿子摇了摇头。
他站起来,打个手势,把小郑子的大儿子叫到一边,对他说扎针也没用,准备后事吧,拖不了多长时间了。小郑子的大儿子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然后,两个人又回到小郑子身边,却看到小郑子睁开了眼,忽闪忽闪的似乎在找人。他的儿女们围了上去,大儿子大声说爸,我刘叔来看你了,刘先生只好走到前边,凑近了对小郑子说,还认得我吗?
小郑子已经有些暗淡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刘先生,像是在自己的脑袋里搜寻模模糊糊的记忆,也像是有些茫然。他脸上的皱纹已经开了,那层死灰色又加重了几分。“我是北头的老刘,咱还在一起搭档过呢。”刘先生尽量放大了声音喊。突然,小郑子无神的眼神聚到了一起,嘴一张一合地动,像是在说什么,而且他的手微微动了几下,那意思是要去抓刘先生,可又已经没有了那份力量。刘先生说你别动,好好躺着,就主动抓起了他的一只手,顿时,一股冰凉的感觉从自己的掌心传过来。“别动,你会好的。”他知道这是在欺骗小郑子,但不欺骗又能说什么?再看看小郑子的脸,却发现他那往下深凹着的眼窝里有了泪水。小郑子肯定想说什么,特别费力地想,眼睛里放射出最后那一点儿光芒,分明很激动。“别动,你不要动,安静点儿好吗?”刘先生说着,用力抓了抓小郑子的手。并扭过头去冲小郑子的儿女们说,快,给你爹穿装老的衣裳。没想到,小郑子的儿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动,他只好又扭回头去看小郑子怎么样了。小郑子喘气越来越急促,突然,他的脑袋一歪,嘴里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小郑子就这样在刘先生的面前走了,那最后一口鲜血,叫刘先生又想起了那天的红高粱,红得耀眼,红得瘆人。他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小郑子的家,听着背后传来的震天动地的哭声,一股热热的东西朝胸腔涌上来,他感觉到有些堵得慌,便又回过头去,看了看郑家门楼。
日头还是那样足,温暖又均匀地向大地喷洒着光辉,但郑家门楼却还是显得有些阴森。
光棍高二
从正房出来,高二抹抹嘴,连着打了两个饱嗝儿。抬头看看天,灰啦吧唧的没几颗星星,就一路哼哼回到自己的偏房。开着灯,掏出烟点了,吸一口,看看早已经发了黑的茶缸子还有半缸子水,便端起来“咕咚咕咚”灌下肚子。擦擦嘴,把灯关了,顺手带上门。看一眼正房,灯影下嫂子的影子晃动着,就喊一声“我玩儿去了”,抬脚朝外就走。照例,远远地又传来嫂子的喊声:“早点儿回来——”。
一句“早点儿回来”,高二不知道听了多少年。他差不多天天吃了饭出去,光棍家,被是凉被,炕是冷炕,不出去干什么?出去走走,哪热闹上哪,大姑娘小媳妇是人家的,看在眼里是自个儿的,哪儿也能消磨几个时辰的光景。等夜深了,困倦了,回到这个家,一躺就睡着,老长的黑夜就过去了。所以,这么多年高二养成的习惯是吃完晚饭就出去,哪次出去嫂子也要喊一声“早点儿回来”。尽管高二天天听,听惯了,背也能背下来,但每听一次心里还是暖暖的。
再听一次吧,赶明儿起怕是再也听不见了,高二的心竟有点酸酸的。于是,提了脚加快步子朝外走。
高二不高,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比他高,加上他说话口吃,所以一辈子也没混上个女人,从小的时候他就跟着哥嫂过。哥嫂住正房,他住偏房,哥嫂一家三口睡一条炕,他光棍一人打着滚儿睡。后来侄子大了,过来和他作伴儿,就两个人一条炕。再后来侄子住校,又考上了大学,就又剩了他一个人睡。一个人就一个人吧,倒也清静,吃饭有嫂子做,衣服嫂子洗,日子过得省心。不想五年前哥哥一场病老早的死了,高二就和嫂子一起扛起供侄子上大学的担子。但嫂子还是住正房,高二也没走出那间低矮的偏房。尽管村里有人说叫他和嫂子合了过,但想想侄子,又看看嫂子,没看出什么意思来,高二就没敢往心里去。前些日子侄子来了电话,说是侄媳妇快要生了,让嫂子搬到城里去住。想想也是,侄子那小两口都是有工作的人,哪有工夫带孩子?嫂子是非去不可了。但今后的日子,怕是真正就光棍了。
说也奇怪,高二就不明白,怎么自己想事的时候就不口吃,怕就怕一张嘴。张嘴说话就费劲,而且越着急越费劲。其实原来高二的口吃不是很严重,加上他尽量少说话,说话时也随时注意,村里人知道高二口吃的人还真不多。但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年起,高二的口吃就严重了,一到人堆里就不行,连句完整话也说不清。所以他就尽量少说话,就当个听着的,听到人家说到好笑的时候笑,不到不说不行的时候就不开口。
想想今天要去的地方,无非还是张大乱那儿。张大乱家开着个赌局,人多,想呆到什么时候呆到什么时候。抬头再看看天,没有月亮,仅有的几颗星星忽闪忽闪的亮着,忘了看天气预报,估摸着明天是个好天。跑县城的汽车赶早儿走,嫂子带得东西多,要借大龙家的驴车送到车站。回头把那垛花生秧子给他喂驴,反正自己放着也没用,不亏了他。想着,高二先去了一趟大龙家,磕巴着和大龙说了,就又走到了街上。
其实自打哥哥死了以后,高二不是没想过和嫂子合了过,虽说嫂子今年都过五十了,但看起来还是那么好看,那身上哪都是软乎乎的,不知道让嫂子搂搂是什么滋味。高二这辈子白来,快要五十的人连女人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冤死了。没了哥哥高二勤快了许多,除去种地还磨豆腐,回到家里不是干这就是干那,一刻也不闲着,帮助嫂子把侄子供了出来,还在城里成了家。这个家有他高二一半功劳。嫂子知道,侄子也知道,嫂子对他高二像对自己的弟弟一样,侄子哪次回来都给他买好多东西。高二也知道村里有人和嫂子提起过那件事,但他偷偷看过嫂子,竟在嫂子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自己不能显露,要是嫂子没那意思以后怎么见面?所以他也装不知道,直到侄子来了电话要接嫂子走,高二的心才又动了,所以今天就多看了嫂子几眼。
不知道白天嫂子那眼神是什么意思,反正和从前看他不一样,难道嫂子有什么想法?
白天的时候,高二帮嫂子拾掇东西。嫂子拱着腰从立橱往外翻腾衣服,高二在后边发现嫂子胖了,一个肥肥大大的屁股把裤子撑得紧紧的。高二就觉得心里跳得厉害,忙着扭了头。等回过头来想再看看时,嫂子已经回过了身,好像发现了他那眼神,把个高二臊得赶紧扭了头。有好几次,高二发现,嫂子好像要说什么,可又没说,眼睛里分明有话。
想说什么?高二猜不透。
一路瞎琢磨着,高二走得很慢,看看张大乱家已经到了,远远就听见了里边的人声。灯火通明的窗子上映出了屋子里杂乱的身影。高二拍一下脑袋,咳嗽一声走了进去。尽管张大乱的屋子很大,但里边还是烟雾腾腾,尤其是在这晚上,灯一照就更显出了烟。靠炕头的地方五个人或蹲或坐正在“顶牛”,但围着“打看灯”的人还有四五个。高二不言声走了进去,想找个旮旯坐下,不想还是让人看见了,打看灯的刘五一只脚踩着炕帮站着,见到高二就伸手在高二的脑袋上捋了一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才说“老高来了?”引得炕上正抓着牛牌的几个人抬了头看他。
“嚯,老高今儿个来晚了啊。”
“看样儿今儿个老高吃好的了。”
“是他妈吃好的了,你们看他那腮帮子上还油光马亮的哪。”
“别,别——,别老拿我——,我,开心。”高二说着先是挤到跟前看一眼牌,就要躲到炕的另一端团着。
“高二,给倒点儿水,全村数遍了也就是我和你叫声高二。”是正端着牌的小六子,一边递给高二水杯,一边把张牌“啪”的一声拍在炕上:“两头五!结了,叫你们炸刺。”
小六子说的对,村里人都和高二叫“老高”,那话里含着两层意思,是明显的。表面上是尊重他,加了个“老”字,其实是正话反说,笑话他矮。
高二正端着已经没有多少水的壶往外倒,忽听的小六子炸呼,扭了头对小六子说:“我——,我,我一来你就运气,这把帐,帐,帐,赢,赢,赢多了,你给我,我——,抽个喜——,喜,喜头。”
高二好容易说完了这句话,引得满屋子笑声。小六子先是笑着往自己的裆下搂过了钱,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看看高二,又看看自己裆下的那堆钱,发现不是五十的就是一百的,便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十块的递给高二。说声“拿着吧,给你嫂子买好吃的去。”于是,满屋子又是笑声。高二接过钱揣进怀里,说了声“谢谢”便朝外走,把在堂屋的土锅炉捅旺了,再座上一壶水,回到里屋团进炕角上。
“他妈的,老高就是勤快,他要不来都没水喝。”
“对了,老高,赶明儿不是你嫂子要走吗?”
“啊——,是,是。”
“那还不快回去陪陪,今个摸不着可就没日子了。”
“去,去——,去你的。”
“老高,你到底摸着过没有。”
“傻海,你——,你,你别胡,胡说。”
“说真的高二”,那个叫小六子的说着话并没有看高二,眼睛盯着摆在炕上的牌,捏起手里的一张又放下再捏起一张,喊了声“三儿六,说,我给你截死,爱算帐你们就算,谁怕谁呀。”然后才又接着对高二说:“村里的人知道你老高是好人,这些年帮助嫂子拉扯侄子也不容易,可赶明儿你嫂子一走,谁管你?”
“我——,我,我一个人吃饱——饱了——,一家子不,不,不饿。”
“顺张大天”。小六子上了一张牌又说高二:“回家吧,守着嫂子多呆会儿,明儿起你天天来这呆着。”
“就是,保不定你嫂子热了被窝儿等着呢。”
“我,我,我,我不理你们。”
于是,在一屋子人的哄笑声中高二走了出来,看看天已经不早,街上的饭铺怕是也没了人,就朝家走去。
嫂子,唉——。高二叹口气,想想这么多年衣服都是嫂子洗,饭也都是嫂子做,就连内衣也是扔给嫂子,明儿嫂子一走,真不知道以后什么样子,这心里就翻了过子。看看走到自家的门口,把门开了,进去再锁上,咳嗽一声回到自己的偏房,衣服没脱,灯也没点,就躺在了炕上。
不知怎么,想到嫂子要走这心里就酸。不仅想着今后这个家就剩了自己一个人,再也没人喊一声“早点儿回来”,再也没人给做饭洗衣。甚至还想到了后院那个女人。“唉——”,高二叹了口气。
高二这辈子就见过一回女人的身子。那年天气发闷,他拿了凉席到屋顶上去睡。不知道怎么,后半夜的风一吹,他就醒了。天上一轮黄亮亮的月亮,把星星比的暗了许多。他不知道月亮上那些影子都是什么,只觉得那里好远好远,有很多神秘的事情在那里。他对着月亮发呆,心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感觉,想起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只有满脑袋希望。希望着长大,以为长大了什么都是美好的。想不到的是,人越大烦恼越多。倒是这月亮,远远的,亮亮的,好像还能勾起点儿人的希望。
后院的门一响,那个女人光着身子走了出来。大概她不知道前院屋顶上有人,走起路来不紧不慢,一身白花花的肉被月亮一照,叫高二看了个清清楚楚。女人很胖,两个奶子很大,走路的时候挺得老高。就这样,高二把女人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看得一清二楚,害得高二再也没睡着觉,抓了一夜的凉席。
不困,怎么也不困。白天嫂子的眼神什么意思?那眼神里有事,肯定有事,想想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嫂子那样的眼神,高二的心就动了。这是最后的机会,明儿嫂子一走再没机会了。不行,应该去看看,要是嫂子真有想法怕是给留着门呢。想着,高二一下子坐起来,出溜下炕,用轻得不能再轻的脚步先走到嫂子房前听听,见一点动静没有,就又悄悄来到门前,他知道门是双扇的,平时在里边能插上,就慢慢地推了推,那门竟裂开了一条缝,他的心“咚”的一下跳快了,但再推却推不动。怪了,这门不应该是这样子,要是在里边插上应该一点儿也推不动,怎么能推开条缝呢?高二非常奇怪,就从门的缝隙里伸进手去,发现这门竟是用一根细绳条在里边栓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高二楞了。他的心不知道跳得有多快,但却一点声音也不敢弄出来。他开始想像嫂子的模样,想嫂子为什么栓这么一条能解开的绳子,想着想着,竟想起了他的哥哥,想起他的侄子,在门外呆了很长时间。终于,他悄悄地一步一步后退,退回了自己的偏房。
这一夜,高二一直没睡着,很早就起来去借车,帮助嫂子装上要带的东西。起初不敢看嫂子,后来嫂子对他说以后自己出去要早点儿回来,心里就是一热,眼里模糊了,只好把头低了。看等着嫂子上了车,一路上再没有什么话,直到汽车来了,嫂子上了车,才隔着车窗对他挥了挥手。
送嫂子回来,高二往炕上一躺,“呜呜”的哭起来,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有好几天,高二没有出门,但不知道谁最先发现,高二的口吃却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