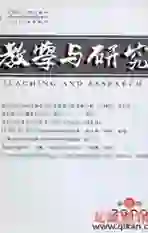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及研究理路
2009-04-29阎静
阎 静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规范性;社会学;人类行为学
[摘 要] 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法兰克福批判社会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关系“批判转向”的主要理论家都深受其影响。如今该学派虽不再代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正统观点的最主要挑战,但仍然是后实证主义理论中极具影响的流派之一。迄今为止,该流派研究议题十分宽泛。本文从规范的、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三大维度对该流派的发展进行梳理。保持普世主义特征,围绕排斥、对话、差异、苦难和伤害等主题尝试重建现代性方案和探究政治共同体新形式是该流派的总体研究理路。
[中图分类号] D8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9-0070-09
20世纪80年代初,居于国际关系理论正统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在世界现实问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国际思潮暗流涌动,并最终在此时汇合成一股批判的洪流,向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理论发起猛烈冲击,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批判转向”,而首当其冲者就是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in IR)。二十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十分不同,各种非主流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已经有了巨大影响。实证主义主导且带有浓重“科学”味道的美国学术领域已经将各种批判理论元素深深吸纳其中,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十分有影响的“结构主义转向”(constructivist turn)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批判转向的诸多方面。在欧洲和英国,各种批判理论与焕然一新的英国学派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方面。如今的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虽然不再在对正统观点的挑战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至今仍极具影响。本文尝试对该流派的思想来源和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理路进行探讨梳理。
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与国际关系“批判转向”
国际关系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由团结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所组成的一个影响较大的社会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姆、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因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并构建了自成体系的批判社会理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所谓的“彻底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世界已经坠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异,它不为自由而为奴役服务,科学和技术也发挥着“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为求得人在精神方面的真正解放,现代社会中包括理性、科学和技术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在批判之列。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社会理论家,虽然改变了早期激进的批判立场,调和了批判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的紧张关系,汲取了实证科学的一些方面,但理性批判这面大旗始终未曾丢弃过。[1](preface)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解放主旨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贬低、对实证主义的反驳、对知识批判功能的推崇、对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讨伐,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性的深刻反省,它不仅引发了20世纪中期关于认识论的哲学大辩论,也对包括国际政治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1981年,罗伯特•考克斯(Cox)、理查德•阿希利(Ashley)两篇文章——《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现实主义和人类旨趣》发表,次年安德鲁•林克莱特(Linklater)教授的专著《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和公民》出版,三位学者对当时主流理论的批判作品不仅揭开了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批判转向”,而且还使得法兰克福学派这一著名的社会科学思潮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三员批判大将的理论各有差异,但在那时,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的影响,并将之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分别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新和意义深远的国际政治理论见解。考克斯在霍克海姆“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著名分类,并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的命题,以及“知识从来服务于特定的目标”的论点为后人所广泛推崇。[2](P126-155)
而阿什利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解放、公正的主旨,使哈贝马斯的“三种旨趣”——技术工具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的分类不胫而走。所谓技术工具旨趣旨在理解如何扩展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实践旨趣目标是理解如何创造和维持共同体的稳定;解放旨趣则为了识别和消除不必要的社会束缚和规则。阿什利指出,这三种旨趣组成了知识的内涵,构造出主体的分析模式,揭示了知识“价值中立”的难处所在,摧毁了旧式的主体/客体的区分。强调如果缺少解放者的目标,有关社会的知识也是不完整的。而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实证主义代替了原有的历史、价值、反思和实践关怀,使无政府状态上升到一种物化的国际结构,国家只能在它的统治下行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其主导和解释下的国际政治理论由此而堕落成一种技术统治工具、一种问题解决理论。[3](P204-246)为了正本清源,解放国际政治理论中被压抑的实践旨趣,有必要抵制新现实主义的实证主义技术统治。
林克莱特也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获得了启迪,他把哈贝马斯的理性分类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的分析之中,提出了技术—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战略理性的分类。技术—工具理性是指学习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实践理性是指学习如何建构秩序和社会公意,战略理性则是指在实际或潜在的冲突情势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人。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技术—工具理性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密切联系;道德实践理性与受批判社会理论影响的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之间有内在一致性;战略理性则与新现实主义密不可分。[4](P32)新现实主义最应当检讨的是它对人类解放机制的忽视,它实际上限制了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类解放的期望。因此,与人类自由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证。[5](P198)为此,需要开启一种“有着解放意图”的历史社会学,以解释国家是如何被人类历史所建构,特别是要解释那些促使主权国家形成并将国家与外部世界疏离的社会纽带,又是如何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之后,林克莱特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政治共同体的转型,是以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为基础,强调发展一种不受任何歪曲的沟通概念和公开对话的社会学习,重视国际间沟通理性或道德实践理性的作用,致力于通过自由对话决定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通过与所有其他人的公开对话促进与不公正排斥相决裂的后主权时代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6](CH4)近年来,林氏新进阐发的“伤害观”也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尤其是早期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理论养料。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在林氏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因此,在国际理论中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被称为“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也有称“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也有些学者直接称该流派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in IR)或“批判理论”。此外,在学术界的广义和狭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区分中,广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是指对主流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说,也被称为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后实证主义或反思主义理论。而狭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专指“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和“新葛兰西”批判理论(“neo-Gramscian” critical theory)①。批判风暴之后的阿什利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而考克斯则更多地关注国际制度和经济组织研究,在促进“新葛兰西”批判理论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只有林克莱特,始终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在其批判理论研究的不同时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追求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还有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D•劳埃德•琼斯(Deiniol L. Jones)和肯尼斯•贝尼斯(Kenneth Baynes)等,[7](P5)而林克莱特则被誉为“国际关系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8](P7)
二、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研究理路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执牛耳者,林克莱特一直尝试构筑一座宏大的批判理论大厦。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提出,“以人类解放为宗旨,将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包容和排斥问题(inclusion and exclusion)确立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从规范的、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normative, sociological and praxeological domain)三大维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他相信,“通过展示不同方法的力量,批判理论能够勾勒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方式”。[9](P78)不同的学者对法兰克福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总结研究视角可能各不相同,在此,笔者借鉴林氏三大维度的研究方法,尝试对法兰克福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以下主要简用“批判理论”)二十多年来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
(一)规范维度
这里的“规范”与规范理论中所指的规范有所不同。批判理论的规范领域主要侧重批评现存社会惯例,探讨从特殊的社会安排中排斥一些人而包容另一些人的哲学缘由,并构想更完美生活方式的理性原则。在批判转向后的十余年,批判理论主要集中抨击实证主义,对主体/客体关系进行了再认识。正如考克斯认识到的,知识并不产生于主体对客观现实的某种中立的观察,而是反映了此前已经存在的社会目标和利益。[2](P126-155)也正像前面阿什利所指出的,三种旨趣组成了知识的内涵,构造出主体的分析模式,强调正是人的需要和目标,决定着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知识。知识总是具有一定政治目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获得了主导地位。
有关“免疫力”命题(指国际体系有其不受人的主观意愿或其他冲击干扰的自我稳定的能力)批判理论与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最尖锐的对立。后实证主义的几乎所有分支都热衷于强调这一重要的主题,它也是连接不同批判立场的一条纽带。批判理论家指出,“免疫力”命题放弃了在观察权力问题时的历史角度。限定在问题解决范围的知识,只能提高意识形态的作用,即力图使现状成为永恒。“免疫力”的语言不止使人造环境变成半自然的力量,它还可能使各种政治行为主体心安理得地看待既成的政治事实。新现实主义的辩护词掩盖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国际体系的改革,应当始于国家观念的转变,不应当再把国家看成是某种道德的共同体,而应当代之以新的权利与义务统一的联合体。[5](P25)批判理论探讨了新型共同体的前景,在那里,个人和集团可以获得更高层次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它的信念来自于马克思的一个设定:现有的一切表面上稳固的事物最终都将消亡,人类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可以更好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批判理论拒绝了世上有一种替现有社会秩序辩护的不可改变的伦理。
霍夫曼在1987年提出,“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将是国际关系理论下一阶段发展的主导”[10](P231-249)的观点受到该学派内外广泛的质疑和否定。20世纪90年代后,批判理论将走向何方,成为一个广泛争论的问题。对此如何做出理性的回答,批判理论内部也产生了分化,尤其是对一些道德普世主义概念和解放全人类的主题是否具有排斥性的争论。早期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就对“全人类被联合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的普遍社会中”这一马克思的洞见进行了反思,指责它没有对农民阶级给予高度重视。许多19世纪的学者就认为,马克思普遍解放方案的核心具有极端排斥性。包括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内的许多最新的激进观点也再次抨击了解放全人类这一主题,并指出,各种抽象的普世主义概念是造成对非西方民族的征服与压迫,以及妇女在公共领域被长期排斥的始作俑者。与对普世主义的批判紧密相连的是,批判理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排斥现象塑造了所有当代社会的不公正。批判理论尽管没有尝试重构道德普世主义,但是它却反思了包括国内、跨国和国际的所有排斥模式。而在这些讨论的最前沿,就是创造更开放的对话的社会安排这一规范性承诺。
超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这一波的发展中最为明显。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批判理论就批评了马克思过于强调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的意义,而对种族、民族、性别、国家建构和战争的分析却不重视。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已经扩大了研究范围,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不公正的排斥形式。批判理论的核心特征就是攻击所有使附属群体的成员丧失权利的社会排斥模式自然化的企图。根本的道德目标就是取消“范围限制”,在这种范围限制中,基于阶级、性别、种族、族裔等道德上不相关的差异而拒绝一些群体获得特权阶级已享有的权利。[11](P193)无论是依靠系谱方法(genealogical techniques)还是批判方法,不同形式的批判理论旨在剥夺这些体制所拥有的合法的传统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12](P6)
不同的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基于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相关差异的决定不能由那些从中受益最大化的群体来决定。依此逻辑,各种排斥模式必须通过对话来考查,而这种对话对于圈内和圈外群体都是公开的。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方式成为有口皆碑的典范。哈贝马斯认为,要对理想的话语共同体的普遍程序做出理性的规范性承诺。当代批判理论的不同分支对于对话共同体的优点和它们成功存在的前提条件拥有相似的看法。[13](P162)对对话的承诺要求各共同体比过去更加普世性、更加尊重人类差异,社会的发展把人类所遭受的共同灾难和苦痛看得比人类差异更为重要。[14](CH9)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共同体在寻求一致和理解时不抹杀人类的差异。[15](P120)
时至今日,摒弃进入话语共同体的各种限制形式的普世主义承诺依然是批判理论研究的核心。为了回应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批判,当代批判理论的规范性聚焦更加突出对差异的尊重,尽管后来它才意识到这就是改良的普世主义的一个关键所在。马克思关于权力和财富的非对称性批判仍然是批判理论所保留的方面。综合二十多年来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国际批判理论的规范性目标大致可以归纳:通过对话和同意而非强权和武力来进一步扩展社会互动的范围;尊重差异进而扩大进入话语共同体的成员的数量;创造社会经济前提条件,以便有效而非名义上地包含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16](P31)而且,近几年来,基于“不伤害”和“人类共同脆弱性”而阐发的“伤害观”逐渐成为批判理论全球道德规范研究的核心关注。[17]
(二)社会学维度
针对批判理论过于晦涩抽象,批判理论的学者们没有产生有用的社会学分析这一批评,林克莱特回应到,后实证主义对最新的社会学研究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此时此刻对此进行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是,批判理论无需重走前辈之路。他认为,无论是对差异问题的大量研究,还是对种族、伦理、性别、文明差异所引起的道德相关性研究,批判理论都在社会学分析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此相连的研究,例如,西方各民族同非西方民族经历了一系列消极互动后才铸造了各自的文明认同,同时也通过排斥性实践获得了民族认同和共同目标方面的论著也大量涌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学者,尤其是新葛兰西学派,他们借助严密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和解决世界秩序和全球霸权的相关课题;[18]组成批判转向的许多发展趋势在新安全研究等课题中也展现无遗。此外,许多学者还详细枚举了这些经验性研究议程的诸多要点①。可以说,批判理论已经将这些社会学分析的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林克莱特直言不讳地表示,“在过去十余年里,就我们对经验性研究议程的演进所做的简要分析,完全表明当代批判理论家们没有必要因为未能做出深入具体的经验研究而向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大师们道歉。”[16](P32)
后实证主义经验性研究议程都带着明确的规范性和批判性的目标。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学源自于上面所阐述的规范性理想?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内容要求消除由以下三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享受权利平等、尊重世界观的巨大差异和减少财富不平等的努力。这些措施的关键是要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以便人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对话,进而促使如弗雷泽(Fraser)所提倡的所有成员都“平等参与”之局面的形成。吉登斯(Giddens)认为,主流社会学致力于一种演进的社会变化概念的研究,几乎没有关注外部力量和内部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19]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学逐渐开拓这一被忽略的项目研究。从曼恩(Mann)和纳尔逊(Nelson)等人的社会学研究可见,减少物质财富不平等的道德规范就是为了开创与普遍对话共同体这一理想相适应的社会局面。而且纳尔逊社会学中有关文明的架构和文明间关系的分析也呈现了同样的主题,他认为,取消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不公正差异是世界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①。
分析过去各种社会间体系和当代国家间社会诸原则的历史发展,以及融合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相连的规范目标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是批判理论的社会学领域的主要聚焦。而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经验性分析是批判理论超越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可以尝试做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社会同过去任何社会间体系相比,更加赞同排除对享有平等权的限制,尊重差异,以及向被系统性排斥的群体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特点。从表面上来看,现代性独有的特质显而易见,在围绕现代公民身份权的斗争中,它致力于扩大权利、尊重差异、增进平等。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在最近的发展中也是非常明显地体现着现代性的这些特质。尊重文化差异和减少民族国家内部财富不平等虽然没有带动减少国际上的不公正,但是就此得出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毫无进展的结论是荒谬的。防止国家间社会转化为一个帝国并使其和平转型的承诺,对现代国家间社会而言是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而且,根据这些规范性承诺,在国际社会结构方面更激进的变革依然也是可能的。
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十分强调贯穿现代社会和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排斥形式,它们对在现代世界体系内抵制主导排斥模式的各种反霸权力量进行了分析。如此,它们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转向了反对黑暗和压迫力量的现代性的进一步潜力。一些“新经院哲学”(new scholasticism)的评论家对当代批判理论缺失了具体的社会学分析的指责并没有击中要害。[20](P301-32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展示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形式中可供选择的政治和社会安排是多么的明显,批判理论在阐述现代性的社会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确切地讲,这一事业的核心就是对对话、差异、排斥和伤害进行辩证的社会学分析。
对现代性特性的分析需要被置于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并允许对不同的社会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对文化差异和经济不平等的敏感的普遍对话概念进行评估。历史已经显示了世界政治组织的不同形式并展示了其不同的特性。[6](CH4)同过去相比,更加世界主义的、更尊重文化差异和对财富分配不公正更为敏感的政治共同体新形式的美好前景,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理念的体现,它表达了现代性的进步面。这种前景也已经出现在强调种族差异具有重要性的文明之中。一直以来,同过去的社会体系相比较,更具同化性的社会似乎是财富和权力空前不平等发展的温床,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而且,现代性并没有削减这种黑暗面。是否能产生代表现代性进步方面的政治安排是批判理论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所在。
新世纪以来,以林克莱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家将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是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在西欧对暴力和残忍这种公共和私人行为正在变化的情感反应的分析)引入国际关系领域②,进而发展为将不同国家体系中对苦难、伤害和脆弱,以及对残忍和同情的主导倾向的普遍态度视为国际关系批判社会学研究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这些主题也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议程和方向。
(三)人类行为学维度
雷蒙•阿隆在反思治国方略时,使用了人类行为学这个词,[21](P577)批判理论引入了这个词。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人类行为学领域主要探究现代性已经积累起来的能用于产生政治共同体新形式的道德资本。[9](P79)在批判风暴之后的20多年,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国际批判理论在内的后实证主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最主要的批评是,后实证主义研究与公众政策和治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相脱离。[20](P310)但是,对后实证主义的这种批评没有提及、甚至忽略了考克斯的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分。事实上,各种批判理论对处在前沿的政策事务、政治结构和有关人类治理的可供选择的模式的研究,都是高度警觉的。
法兰克福学派国际批判理论始终关注诸如当前的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可选择的模式等重大问题,而非关注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的修正主义的解决办法相连的渐进主义的政策主张。从批判风暴一直到近年来,批判理论的人类行为学领域对关于政治共同体未来可选择模式这样的长期性问题的大量研究,几乎无人能视而不见。同时,它还始终致力于人类治理新模式的可能性的探索,并反思有助于实现这一理想的重大发展。虽然最新的批判研究总体上还没有尝试将国际关系研究从对当前政策和实践事务的研究,朝着更高的独立的哲学研究方向转变。但是它的宏伟目标之一就是重新捕捉在这一领域形成之初业已存在的道德伦理精神中的一些实质方面,而非重蹈早期理想主义的覆辙。目前批判理论人类行为学最明确的关注在于,当下政策措施必须同更长期的规范性目标相结合,而这种规范性目标将批判理论同古典政治哲学和它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反思相结合。相反,有关人类行为学的现实主义描述却强调这些规范承诺和权力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批判理论的方法关注将之构筑进现代社会结构的更大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批判理论相关学术讨论逐渐转向了围绕关于现代性和启蒙项目的争论。批判社会理论中的语言范畴——普遍性、理性、进步、启蒙运动和解放等被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进一步借鉴引入。在批判理论中,有关现代性不同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能够通过公正的国际规范的逐渐积累而被解决成为其中心关注之一。因为,国际规范的积累服务于阻止有害的排斥性体系和权力政治的恢复,以及使规范进一步发展的双重目的。而批判理论认识到,公民身份思想就扮演着这样的双重角色。由此,在对不公正的排斥体系抵制过程中产生的现代公民身份成为国际关系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人类行为学的首要聚焦。公民身份的思想将道德资源提供给现代社会,并用它在国内以及国家关系上去产生新的和更有包容性的安排。而设计对普遍性和差异更敏感的政治共同体新形式的前景,在对公民身份有严肃承诺的现存生活形式中是内在的。世界主义民主的支持者捍卫这一观点。[22](P121-162)反思现代性进步的一面如何能被镶嵌在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中,并继续与各种形式的非正义的排斥作斗争仍然是现代社会公民身份思想的重中之重。
世纪之交体现这一精神的研究设想一些能够突破主权、领土、国籍和公民身份之间关系的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非常有意义的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在不抹去人类差异的前提下,对体现更高世界主义抱负的社会的哲学捍卫,不断被反映在人类治理新模式和揭示现代性潜力的有关共同体和公民身份的新形式的分析中,这也是近十余年来批判理论人类行为学研究的核心追求。而这些追求在德里达、林克莱特、哈贝马斯和华莱士(Wallace)等人对欧洲后主权社会的可能的治理模式、跨国公民身份和后主权时代的欧洲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得以清晰体现。
批判理论期望通过对对话、公开和同意的承诺,渐趋弱化国际关系中权力和武力的主导地位。遵从这种规范性要求的更重要的主张认为,政治主体应该竭尽全力让他们的行动符合所设想的普遍话语共同体赞同的主张,并支持促使这一共同体诞生的各种措施。[23](P133)国际关系中目前的沟通框架应给予拥有这一理想的人们更加具体的指导。在现代国际史中的外交对话很长时间被局限在国家范围之内,而且只关注政治强权国家如何维持政治秩序。虽然开放了与如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对话这些重要的动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对话扩展至全球治理的事务中,它主要包括个体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国际社会的正义、对自然环境和非人类物种的更大的关注等方面。此外,批判理论在近年来有关伦理和外交政策的讨论中,更加强调共同体必须关注避免对共同体之外其他人造成伤害,避免在对外部人的伤害中成为受益者,以及对“遥远的陌生人”的苦难更加敏感等世界主义原则。[24](P19-36)即便如此,世界政治一些主导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并未减弱。批判理论对外交对话当前状况进行的反思,可以把握国际社会在普遍对话共同体这一理想上取得了多大进步,或者是还与之相距多远的一条最佳途径。一种普遍话语共同体不会因为政治弱势和缺乏尊敬而排除各种声音,禁止完全迥异的各种观点。而且这种反思还将可能产生最为期望的发展轨道和变革模式。批判的人类行为学在强调国际社会的道德缺陷及其发展的内在可能性和理想方向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根据上述的规范性要求和社会学考察目标,批判理论的人类行为学研究将开始逐渐进入探究外交政策决策和分析这一尚未完全触及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学科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虽然从80年代后期以来它不再代表本领域内对正统观点构成的主要挑战,但它仍然是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中极其重要的流派之一。如果说它最初主要致力于驳斥新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话,那么它今日的研究议程已是相当宽泛。依然保持普世主义特性,围绕排斥、对话、差异、苦难和伤害等主题尝试重建现代性方案以及探究政治共同体新形式,它的研究轮廓日渐清晰。
参考文献:
[1]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From Horkheimer to Haberma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 R. Cox.Social Force,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J]. Millennium, 1981,(10).
[3] R. Ashley.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s [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1,(25).
[4] A. Linklater.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St.Martin Press, 1989.
[5] A. Linklater.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London: Macmillan, 1982.
[6] A. Linklater.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7] Richard Wyn Jones. Introduction: Locating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in Richard Wyn Jones(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C].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8] Nicholas Rengger, Ben Thirkell-White. Still Critical After All These Year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33).
[9] A. Linklater.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J]. Millennium, 1992, (22).
[10] M. Hoffm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J]. Millennium,Vol.16, No.2,1987.
[11] J.M.Bernstein.Recovering Ethical Life: Habermas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M]. London: Methuen, 1995.
[12] David Couzens Hoy, Thomas McCarth.Critical Theory [M]. Oxford: Blackwell, 1994.
[13] Kenneth Baynes. Deliberative Politics, the Public Sphere, and Global Democracy [A].in Richard Wyn Jones(ed.).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C].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14] Richard Rorty.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5] Habermas.The Past as Fu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16] A Linklater.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in R. Wyn Jones (ed.).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M]. Loneon:Lynne Reinner, 2001.
[17] Andrew Linklater.The Harm Principle and Globlal Ethics [J].Global Society, Vol.20,No.3, July 2006; Andrew Linklater.Towards a Sociology of Global Morals with an “Emancipatory Intent”[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33).
[18] R. Cox,Timothy Sinclair.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 M.Cochran.International Ethics as Pragmatic Critique: Confronting the Epistemological Impasse of the Cosmopolitan/ Communitatian Debate[Z].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London,1996;Anthony Giddens.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
[20] W.Wallace.Truth and Power, Monks and Technocrats: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6,22(3).
[21] 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6.
[22] D.Archibugi.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in D. Archibugi,D. Held(eds.).Cosmopolitan Democracy [C].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5.
[23] D.Bohler.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and Critial Morality: On the Possibility and Moral Significance of a Self-Enlightenment of Reason [A].in Seyla Benbib, Fred Dallmayr(eds.). The Communicative Ethics Controversy[C].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24] A. Linklater.Distant Suffering and Cosmopolitan Obligations[J].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44).
The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in IR: Origins and Academic Route
YAN 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0013, China)
[Key words] the Frankfurt school餾 critical theory; the Frankfurt school餾 critical theory in IR; normative; sociology; praxeology
[Abstract] The direct origi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餾 IR critical theory is the Frankfurt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ajor IR theorists in the early 1980s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is thought. Although this school of thought no longer stands for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to the mainstream IR theories, it is still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of positivist theories. Up till now, the research themes of that school is of a large scop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ffer a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IR from the normative, sociological and praxeological domains.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route of that school is to maintain the features of universalism and explore new forms of political community by analyzing such themes as exclusion, discourse, difference, suffer and harm.
[责任编辑 刘蔚然]
注:
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介绍和它与国际政治理论的关系国外有大量的作品论述,其中全方位概述的是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对其起源有很好论述的是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73;对其中心原则最清晰阐释的当属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From Horkheimer to Haberma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国内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版)第十八章中有较全面论述。在钮菊生等的论文中也有不错的总结,参见《试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
①此引自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国际政治重点学科理论研讨会——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观点摘要。参见林贤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非主流”学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6月。
①有关新安全研究主要参看K. Krause and M. Williams(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概述批判理论经验性研究诸多要点的主要参看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R,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Richard Devetak, “Postmoder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Scott Burchill, A. Linklater, et al.(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Macmillan, 1996, pp.179-209, pp.145-178.
①Benjamin Nelson, Civilisational Complexes and Inter-Civilisation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73,74(1).曼恩的论述主要参见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79—105.
②这种方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林克莱特,此外学者Haferkamp和Mennell等也是这种方法的极力推崇者。参见H.Haferkamp, From the Intra-State to the Inter-State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1987,(4),pp.545-557; S.Mennell, Comment on Haferkamp,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1987,(4),pp.559-561; Andrew Linklater,Norbert Elias, The“Civilizing Process”and th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4,(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