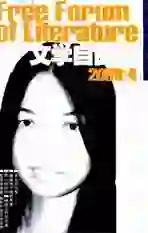谁能许旧体诗一个未来?
2009-04-19尽心
尽 心
拙文《“新诗时代”即将结束》有幸在2007年第3期的《文学自由谈》刊出,那时候笔者认为所谓的“旧体”和“新体”迟早会平分秋色,“一边倒”的时代即将结束。之后拙文《新体诗的形式》(2008年第1期)再蒙刊出,那是为“新诗90年”写的一篇小文章,笔者认为“新诗”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诗歌作品,主要针对“新体”而言,并没有明确提出旧格律体属于“新诗”的范畴。现在写这篇小文章,则认为“新诗”不仅包括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六种(改革后的旧体格律诗词、自度曲、比较“方正”的打油诗、强调建筑美和音乐美的新体诗、借鉴外国诗样式的诗、体式完全自由的诗),而且认为今人创作的旧格律体也应该属于广义的“新诗”范畴。
诗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部分。笔者再次强调,新诗、旧诗,其实是时间的界定,并不是体式的界定。唐代的近体诗(今体诗)现在被称为旧体诗,现在的新诗在许多年之后也是旧诗。老杜说“新诗改罢自长吟”,总不会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体自由诗吧?
“新诗”必须正名,如果单单把那种“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自由体的诗称为“新诗”,那么这个“时代”必将结束于不久的将来,当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新诗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无论自由体还是格律体,自由体有趋于本土化的,有的受外国诗影响更为明显。格律体应该既包括传统的不可随意乱改的旧格律体,也包括改良之后的新格律体。声韵的改革不是不可以,“自度曲”也不是不可以,而是改了以后应该称为“新格律体”。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样子看上去方方正正,平仄格律随心所欲,是否称为“半格律体”或可商榷,但至少应该算是新诗大家庭中的一员。
就诗人主体而言,不少诗人都是“两栖”,“不薄新诗爱旧诗”,无论他们写作什么体裁的诗歌,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都是“诗人”、新时代的诗人。最多说明一下以创作什么体式为主,总不能以“新诗人”、“旧诗人”划分吧。
今年5月下旬,笔者去西安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第23届诗词研讨会。几乎是与此同时,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也在西安召开。前者是以旧体诗为主的研讨会,每年召开一两次,这次会据说是历年来接待水平最好的一次。后者是以新体诗为主,诗歌节期间有大型演出、论坛等等,形式多样,场面宏大。据说两个活动参会的人员都是一百多人(诗歌节那边应该多一些),而投入的资金后者是前者的三十多倍,后者的整体规模和宣传力度自然都为前者所望尘莫及。
这次西安的诗歌节给了旧体诗界十个宝贵的名额,据说第一届诗歌节给的名额是四个,虽然不足受邀代表的十分之一,虽然再仔细看来,这十个旧体诗代表大部分与主办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毕竞“新诗”接纳了曾经试图打倒砸烂的“旧体诗”,尽管某些人称之为“收容”。
以往旧体诗词界的会议和活动的受邀者往往以老同志居多,往往以创作者居多。这次研讨会最为明显的是出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他们是各高校的博士、博士后,乃至副教授、教授。当然,资深的学者、教授更多,他们大多是理论与创作的结合者,有多年来的不懈参与者,也有首次应邀而来的发烧友。
研讨会的内容,除了对于当代诗词家的作品评赏,如于右任、启功、叶嘉莹等,也有不少人照例提到旧体诗词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改革”的呼声依然此起彼伏。笔者以为,旧瓶确实要装新酒。重要的是如何酿造新鲜而美味的好酒,而不是跟那个瓶子过不去。改革与创新,涉及的形式问题较多,而对于内容方面的创新则往往浅尝辄止。旧体诗词从形式上讲是一个早已经定格的事物,遗产可以继承,而继承的本身就是发扬,不是所谓的“改革创新”。发展,不是砸烂原来的规矩,如果试图让它脱胎换骨,结果必然面目全非。另外,如果太强调推出这个“新事物”,反而会加速旧事物的灭亡。
至于改革,是一个母体孕育新生儿的过程,笔者固然守“旧”,但不是主张把这个“新生儿”扼杀于襁褓之中,只是认为他的名字叫“新体诗”,而不是“旧体诗”而已。
这次诗词研讨会总共安排了22位发言者,前一天开幕式之后发言了六位,第二天上午安排了16位。已经到了午饭时间,第12位发言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大概是由于会议前后操劳过度,而慷慨陈词时又情绪激动,他在发言时突发脑溢血。笔者当时在台下,感觉他说话时渐渐吐字不清很吃力,起初以为是扩音器的问题,后来旁边有诗友提醒老先生嘴歪了,恐怕是中风。于是会议中断,老先生被当即送医院抢救。老先生一片丹心献诗词,他在发言中称旧体诗当下的地位恰如“小妾”,要“不择手段”争取地位。特别强调要“抱粗腿”,意思是争取财大气粗者的支持,最好能够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可以给诗词办会、出书、造势等等,意在弘扬诗词。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当前诗词的形势过冷,所以总要摇旗呐喊,试图用催化剂使之“烈火烹油”般地燃烧起来。笔者却以为恰恰相反,诗诃目前似乎是有些过热,是“蒸蒸日上”,花团锦簇,艳丽招摇,“繁荣”得很。
旧体诗领域的活动确实非常频繁,大赛、笔会、培训、研讨会,年来持续不断,都非常热闹,还动不动就授予个“诗词之乡”、“诗教先进单位”什么的,很是敲锣打鼓一番。这些活动当然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级各界的重视等等。被重视了,就可以召开更多的会议,就可以拥有更多的热闹。
虽然一般报刊发表旧体诗的园地非常有限,但是全国范围内的诗词报刊至少有六百多种。《中华诗词》杂志创刊15年,从季刊到双月刊到月刊,每个月的发行量已达2.5万份。据说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诗歌类刊物。而写诗词的肯定比读诗词的人要多,因为不少人虽然写,但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读别人的,因此旧体诗的创作确实异常兴旺,创作队伍异常庞大,而且抛头露面的参与意识也特别强烈。某次诗词大赛,短短三个半月时间,组委会收到海内外包括两岸三地寄来的十一万余首诗词作品,比《全唐诗》的两倍还要多。而各级各类刊物每年发表的诗词作品至少有二十万首。据说全国的“诗词人口”保守估计有“百万大军”,全国的诗词组织至少有两千个以上。如丁国成先生所说:“头雁高飞群雁随,头羊领路群羊追。中华诗词学会就像领头的雁、带路的羊……”中华诗词学成立22年来在组织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热闹归热闹,也总有些人坐在冷板凳上认真探讨着旧体诗歌的本质,探讨生命的宣泄与感悟,探讨文化的积淀与释放,在混沌中摸索前行。乍看这次全国诗词研讨会的论文,不仅涉及的方方面面多了,而且深度似乎也有所增加。诗词界的会议远离了自娱自乐与相拥取暖,诗词界之外也响起了更多关注的声音,比如旧体诗词入文学史的问题等等。
旧体诗词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赶出历史舞台,不可能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也不可能没有立足之地。但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旧体诗词的所谓“复兴”只是一些人的美好愿望而已。旧格律体的诗词创作其实从来没有消歇,在最冷寂的时候仍然不乏好诗,薪火相传从未间断。不是说活动多了,参与的人多了就是“复兴”。真正的好诗一般不是开会写出来的,创作毕竞是一种比较主观的个体行为。对于个体而言,陶冶性情,诗意了自己栖居的环境。社会的效益目前还不是很明显,不知道千年之后能否会成为琥珀。
同时,新诗界也在反思。新诗是人们头脑中诗歌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人的观念至今根深蒂固。但观念归观念。衰弱的态势,尴尬的处境,背离传统却无法获得纯粹的自由,无奈中迎风招展的似乎只有一面旗帜而已。表面看来,新诗显然达不到旧体诗领域的这些数字,以写作新体诗为主的诗人们也似乎总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存在,偶尔标新立异,枝繁叶茂,却脚下空空。
新诗一直试图找寻传统化和民族化的途径,但是它们所认可的传统诗词是古人的创作,不是今人的创作。新、旧二者虽然目前还不至于水火不相容,毕竟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巨川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新诗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所形成的新汉语思维和话语结构依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这个潜藏的思想编码的影响,不管走得多远,也不管你是否愿意,新诗必然要回归传统诗学的视野之中,我们在寻求外来文化优点的同时,真正需要解决的还是中国问题。因此,我们在关注新诗的同时,更要关注当下的传统诗词(包括现代旧体诗),真正做到‘还历史以真实面貌。”
就狭义而言,新体诗任重道远,但谁又能许旧体诗一个未来呢?就广义而言,几千年的中国诗,近百年的旁支分流,百川归海,终究是天空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