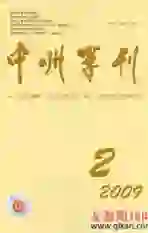从身体美学看文学经典的影像存在
2009-04-14洪艳
洪 艳
摘要: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面临着种种困境。在电子媒介主导的今天。文学经典已经进入“后经典时代”,其存在方式已发生显著变化,影像存在成为经典传承的最重要方武。经典改编的核心是文字向影像的转变,文学经典的影像存在过程也是文学经典的世俗化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影像作品与原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复杂的变化,与这一转变密切相关的是身体在美学中的地位。因而,从身体问题入手既能理解影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也能理解媒介和艺术的变迁。
关键词:文学经典;电影改编;影像存在;身体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231-04
媒介时代影像存在几乎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电子传媒重塑了人的感觉器官,影像存在成为信息最重要的存在方式。甚至可以说,影像媒介将整个人的生存环境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美学场。在这一美学场中,文学经典的命运又如何呢?有人说文学经典已经死亡。笔者在带领学生所做的一次暑期调查中发现,人们对经典名著的兴趣并没有消失。在对450名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众进行采访时,98%的人都表示对经典名著有所了解,而且仍然有接近30%的受访者表示读过原著,并且大部分都认为名著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甚至比较大的影响。可见,只要有人的存在,对思想和诗性的需求就不可能完全停止,经典死亡是个伪命题。调查结果同时表明,文学经典在存在和接受方式上又的确与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采访中,近60%的受访者是通过电视、电影和网络了解文学经典的,一半以上记忆最深刻的场景都是电影电视中的镜头。
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从“实在”转向“存在”,由对事物的存在本质的研究转向存在方式的研究,关注的重心由对事物是什么的追究转向研究其怎样存在。对文学经典而言,则不再追究什么是经典,而是追问经典是怎样存在的。我们也可以将文学经典是否死亡的问题搁置。而应该研究其存在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其中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是典型的文字信息向影像信息的转变,是以影像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存在。在电子传媒主导人类生活的今天,从影像存在来研究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
一、经典的影像存在
库切在《何谓经典》一文中认为,经典是“经历过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这首先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经典,经过时间的淘洗和人为破坏后得以留存的作品都是生命力最强大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在流变的历史中把握到了更多的不变的东西,历久不衰,比如荷马史诗、先秦诸子的著作。所以作家蒂姆·洛特(Tim Lott)认为,经典必须“讲出一些永恒的东西,不局限于这个时代”。鲁思‘伦德尔(Ruth Rendell)认为,经典必须是完全自出机杼的作品,是以前没有过的东西。他们的观点切中了人们对经典的传统共识:普世性、崇高性和独创性。当经典被改编成电影时,最容易被破坏的也正是这些特征。
本文所指的“影像”是指以“画面”为中心的包括声音在内的一个拟真的动态声画系统。这里排除了照片、绘画、投影等静态影像,同时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重点也不放在电视和网络视频等其他媒体,而以电影的经典改编为主。海德格尔提出,存在者是某种“实”的东西,而存在本身不是任何物。他认为,我们只有通过此在(Dasein)的生存去领会存在,或者说,存在只有通过此在的生存领会才可能绽现出来。由此意义上来看,文学经典的存在问题,既是存在的问题又是存在者的问题。如果说存在者是固定的,而存在是敞开的,那么对文学经典而言也是如此:经典文本是固定的。而对文学经典的认识和理解是敞开的,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途径和理解方式。文学经典是在活动过程当中获得本体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而物态化、形式化了的集情理形质诸因素为一体的“审美感性直观”。这一感性直观在当下又体现为由抽象的文学形象转变而来的电子媒介构成的感性的电子影像。
文学形象是文本中呈现出的、具体的、感性的、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能唤起人的美感的人生图画。在文学经典中,这种人生图画虽然不可见却能够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丰满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敞开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影像世界则将这一想象中的世界变为拟真世界,将原来可以无数的能指指向了一个固定的所指。由以记录精神世界为主的文字转向以再现物质现实世界为主的影像艺术,原来的经典也许已经不再是经典,原来的二流甚至三流作品却有可能成为新的经典。因为文学的本质是语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是分离的;而影像的本质是“照相本性”,图像的能指与所指实现了合一。文字是抽象的,直接诉诸人的理性,天生具有启发性,文字的抽象性和对文化的需求使其更具有精英性。影像是具体的,直接诉诸人的感性,因而天生具有娱乐性,其接受的开放性也使其天然地具有了平民性。文字是静止的,是更倾向于时间的媒介;影像是运动的,更倾向于空间性。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就成为文学经典影像存在的最显见也最基本的冲突。即便改编后的电影作品是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它与原作品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为经典的传承发挥着作用。
经典文学的文本本身是存在者,但是文学经典是一种存在。是在历史波段中的一个在世界、主体和作品之间的动态过程,其电影改编可以看成是这一存在方式的变形和衍生,其中心就是作品的想象化世界和电影的影像化世界之间的转换,影像应该是核心。文学经典直接面对的是世界,这个世界在早期是经验的世界,在大众媒介诞生后则成为经验世界和媒介化世界在观念世界中的综合,文学作品的存在是在经由作者与世界和读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电影改编后的影像存在方式则需面对实有的经验世界、媒介化世界以及经典作品所构造的文字的世界,其存在需要经由导演与作者、世界、读者、观众的交往和导演直接与世界、观众的交往这样两部分共同完成。
二、影像与身体美学
影像媒介最大程度地突破了人的感官局限,使我们被无穷尽的声光色影所包围。媒介不再是认识世界的助手(求真),也不是企图改善这个世界的工具(求善),转而被纯粹的娱乐和游戏所主宰(求美)。这种转变是乐观者认为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还是悲观者所说的人的整个精神生活的后退?抑或是媒介对审美的侵犯?这些都与感觉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感性在美学中地位的沉浮与媒介的变革刚好相呼应。所以,从身体问题人手既能理解影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也能理解媒介和艺术的变迁,也就可以理解整个影视改编的历史,并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来探讨经典该如何改编。
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人的存在是神秘的,它那么显而易见又无法把握;
人们转而从身体去把握存在,因为身体是实在的,但身体也是神秘的。“不解之谜就在于此,即我的身体同时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是感觉者也是被感觉者,是看者又是被看者,从艺术归根结底诞生于以身体为中心的交换体系来看,回归身体之谜应该是破解艺术之谜的一条可行路径。尤其是身体美学中将感性与理性看做一体的努力。
“身体美学”这一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提出的。他认为,身体美学是“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他说自己是受到维特根斯坦提到的人有一种“对其身体的美学的感受”的启发而有兴趣去发展一种他称之为“身体美学”的哲学概念,他将其构想为一门致力于提高对作为感性审美欣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基地的身体的理解、利用和经验的学问。
身体的美学意义是在现代思想中被发现的,但只有置身于历史语境中才能够给它一个恰当的理解。身体问题首要关涉的就是作为感性学或者感觉学的美学,因而这一转向首先可以看做是对感性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回归。审美一词的古希腊含义就是“完善的感性”。“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对美学对象进行了最早的界定:“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单就它本身来看),这就是美。”到了康德提出审美不涉及利害计较和欲念满足,美和审美就远离了认识而归到意志和情感领域,是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协调,康德将审美看做是纯粹理性到实践理性的中介。经由歌德和席勒的推动,到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彻底恢复了感性的重要地位。但作为感觉器官的身体在美学中一直是缺失的、被排斥的,感性美一直被人的精神美与理智美所压制。
19世纪末西方美学开启了“人类本体论转向”,其中尼采哲学为人的感性生命复仇和正名的功劳最大,他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它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在他看来,美首先是身体的美,就是拥有高度强力感的身体。20世纪初期,以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为代表的一些美学家以“美即美感”这一主题悬搁、转换、否定了古典美学以美的本质为基础的思考方式,开启了现代美学的新局面,源于古希腊的从现象后面追求本体精神的一元论失去了位置。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思潮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席卷了整个人文领域。其中梅洛‘庞帝创立了“身体——主体”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克服笛卡儿以来的身心二元论的关键,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身体教学。梅洛‘庞帝主张把抽象的身体还原到直接经验的身体,在他看来,在身体知觉中显现的事物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事物本身,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因而身体美学首要地指以身体为主体的美学,以身体感觉为中心的、由身体出发的美学。如梅洛·庞帝所言,身体在这里具有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身体是世界和我们自身交互建构地投射出来的焦点。以实用主义为基点创立“身体美学”概念的舒斯特曼也认为,“身体美学本质上并不关注身体,而是关注身体的意识和中介,关注具体化的精神”⑦。
身体是基点并不等于艺术只是感觉问题,艺术从根本上是一种精神生活,过度突出身体问题就会导致硬币的另一面被遮蔽。尤其是身体美学的观念与媒介社会、消费社会的现实相互吸纳,消费社会产品过剩,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趋于饱和(没饱和甚至匮乏的那部分已被这样的社会挤出视线之外),庞大的生产机器还在加速运转中。于是,工业和媒介联手,即刻满足人的欲望又不断引发新的欲望,将人的欲望的作用推向了极致。身体探索不再是对存在问题的追究,不再是追求自我解放和确证主体存在的途径,更不再是革命大叙事中的劳动和牺牲。“身体越来越成为政治物,它的自然属性被自己的消费行为改写甚至被消灭,它越来越和自己的本性相脱离,甚至成为自我本性的反对者。”身体美学中由身体而出发的精神性一面逐步消失,纯粹的感官形式完全占了上风,与大众文化不谋而和地走到了一起。“当代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围绕身体建构的文化,其主题是欲望,其价值是身体性愉快。”而最能直接刺激起身体性愉快的当然是图像和声音,“影像和声音透过移植互相强化”,制造出给人最直接刺激的比现实更像现实的声光色的拟态世界。由此,影像媒介彻底取得了对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领地的进犯,电影改编文学经典也由原来的借文学经典发展电影而变为了文学经典的存在途径之一。在改编的电影中,原著的影响呈逐渐削弱的趋势。
三、文学经典电影改编的实践与观念
从感性到理性再回到感性(也可以说从身体到精神再回到身体,当然此感性已非彼感性,此身体也非彼身体),是艺7R发展的一个规律,也是经典的命运——经典改编也就在这样的二者的冲突与妥协中产生。“感官”既是改编可行性的切入点,又是使改编后的电影与经典分离的力量。
文学经典电影改编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可称为“照搬式改编”。在电影理论上,巴赞和克拉考尔提出的“非纯电影”和“非电影化改编”的电影改编理论起着主导作用。最早的名著改编电影是法国人乔治·梅里爱在1902年摄制成的《月球旅行记》。之后,美国人格里菲斯把杰克·伦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爱伦·坡、欧·亨利、莫泊桑、史蒂文森、勃朗宁等人的作品都搬上了银幕。格里菲斯曾说过:“狄更斯的写作方法就是我现在所使用的方法,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的故事是用形象来叙述罢了。”受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电影改编有着强烈的简单化倾向,“影片影像无非是字幕内容的能动的华丽的图解”。比如1910年由意大利人娄沙维欧·吉罗拉默导演的《李尔王》,整个影片只持续了17分钟,由于影片的文字说明频繁出现,看这部默片就像在银幕上读《李尔王》的连环画。著名编剧兼制片人迈克·比克特改编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也是如此,其场景的安排、语言的节拍、诗句的速度,几乎都保持原样。这一时期经典名著的电影改编是枯燥的,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再现出小说的电影对等物。虽然也有一些改编已经开始注重电影化的手法,但情节基本上忠于原著,要求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比较准确、完整地再现原作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以及风格、情调等。在文学经典中。作家处于一种几乎是全知的指导者地位,改编者基本也都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态对待原著,影片中的摄影机(或者说摄影机后的导演)也大都采取一种全知的视角、居高临下的态度展现故事。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也是名著改编的第一个高潮。仅仅在1926到1927年两年期间,就有20多部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素材改编的电影问世。这些改编大多停留在对原作的图解和视觉“翻译”上,技法简单,生硬拖沓,难以把握到原著的精髓。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影工作者基本上仍然坚持:“改编经典著作,无论如何要保持原作的思想、风格,不得随意改动情节。”这首先
缘于当时整个的人文环境:理性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崇尚人的价值和尊严,赞美忠诚、友爱、奋斗等人类的永恒意义,相信崇高,相信有普遍真理的存在,直觉的感官刺激的美尚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婢女地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最粗浅的艺术。其次是影像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还是新生事物,从表现手法到理念都未成熟,文字媒介的思维和感知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处于主导地位。艺术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阐释,导演则是对阐释的阐释,这样,对文学经典进行电影改编既存在对原作理解的深度的问题,也存在导演自身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完全照搬经典既不符合艺术规律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种类型可称为“创新式改编”,即依据原作所提供的叙事框架和涵义、形象、灵魂,依据原作所提供的历史的、具体的环境以及特定社会的和心理的制约条件,对原作进行增删、重组,创造出一部与原作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完整的影视作品。这是一种既历时又共时的改编形态,它既在经典改编的历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阶段,同时又几乎贯穿在整个经典改编的每个阶段之中。具体操作层面上有两种倾向:一是摆脱,即电影力求摆脱小说的束缚和控制,实现完全的独立;二是创新,即电影创作者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性。努力将原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保留,又要适应电影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商品性要求,是这一时期改编的普遍追求。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改编形态,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则很难达到完美。这是改,编经典最辉煌的时期,大量经典被搬上银幕并取得成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如《教父》、《沉默的羔羊》、《辛德勒的名单》、《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伊凡的童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等。
这一时期,整个文化的重心开始从抽象的精神走向可见的人体,媒介手段也从文字开始向影像偏离,电影理论走向成熟,电影开始取得独立的艺术地位,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开始追求其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现代性成为艺术哲学的主要思潮,对改编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典的地位已经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众文化开始崛起,感官快乐逐步取得了自己的地位,人们认识到“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品,而且要跟时代能够结合”。身体在艺术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但是并没有形成对精神的反叛,而是相对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点来互相支撑。文字和影像的影响相得益彰。人们因为喜爱原著而去看影视作品,也因为影视作品的影响而去读原著。
第三种类型可称为“颠覆式改编”。这一时期的电影观念出现多元化趋势,创作风格更加多样。受布鲁斯东理论影响,原著成为故事梗概或者一堆素材,视觉形象被认为是最重要元素。比如1992年日本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改编,唐僧居然由女明星反串,让原本木讷、见了女人就脸红的唐僧摇身一变而成了“泡妞”专家。香港版的《大话西游》则凭借导演刘镇伟天才的拼贴演绎和周星驰炉火纯青的表演,将消费文化中后现代元素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当代中国“大话”式的电影艺术时空模式,比较成功地戏仿了历史和神话。《大话西游》在20世纪末期成了“新经典”,被当成后现代文化的代表作。之后,网络上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大话”社区,新的影像和声音以FLASH、MP3等新形式流传,更有很多“大话”迷在网络游戏中以虚拟的身份参与其中。最有趣的现象恐怕是,由影像的繁荣又推动了网络形式的新的“大话”版本的写作,比如《悟空传》。值得关注的还有国际上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国内的“红色经典”改编等。这些改编都体现了“身体”被解放了的狂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却已将经典的核心特征损失殆尽。
此时娱乐作为消费文化的核心成为文化的主流,“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推倒了权威和偶像,意义或者说终极价值被放逐,美学领域完成了身体美学的转向。各类的戏仿和调侃经典的文字和影像在流传,“超级女声”等诸多全民造星运动打破现代主义形成的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简单二元对立结构,确立以大众文化传播为主导的新文化商业传播模式,这一切也意味着“后经典时代”的到来。
在“后经典时代”,人们对“经典”本身的态度和认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经典文学魅力减退,人们读原著的热情骤减,文学经典的简化本和影像改编成为大多数人接触经典的主要途径。其次,人们对经典的解读更加多元化,经典文学所蕴涵的终极理想和固定意义不再被普遍尊重,经典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因素被更多挖掘出来,对文学名著的“麻辣解读”、“水煮解读”泛滥。再次,经典相对于大众文化失去了优越性。最后,经典创作活动也已式微,“后经典时代”的传播模式是:创作者——艺术中介机构——接受者,从事艺术流通和买卖的专门机构成为传播中的重要环节,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艺术创作的这种外在取向,限制了艺术家对人的心灵本质的思考和对生活的细微探究,因而新的经典很难诞生。
在这一背景下,对经典的改编更加危险,但也更具实际意义。危险在于,对经典的肆意利用可能加快经典的死亡,但同时,在影像已占据整个文化领地的时候,更需要用影像这种方式来传承经典。重要的是如何在尊重“感官”快乐的基础上,借用身体美学试图将感性和理性看做一体的努力,寻找途径通过影像存在的作品推动人们去更多的读原著,利用影像的魅力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吸纳经典的精髓。
责任编辑: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