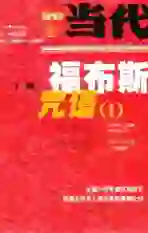非典型正当防卫
2009-03-21孙春平
孙春平
1
我对我的大外甥媳妇谢秉玉的印象不好,非常之不好。虽然我和她并没产生过任何正面的冲突。
我的老姐姐生有二子一女,大儿子尚森,二儿子尚磊,女儿尚淼。这三个子女的婚姻有点像打扑克的抓娘娘,出牌虽也有顺序,但又不完全按顺序。上家出了牌,二家管得起就管,管不起就跳过去,第三家管,或者第四家管,谁手气好抓了好牌,就控制了牌局,抢先出光了自己牌的是赢家,手里最后还抓着牌的便是输者,娘娘。老姐姐家的这张牌桌上,第一赢家是老二尚磊,抢在哥哥前面结了婚,次者是女儿尚淼,也嫁了出去自己挑门过日子。等弟弟妹妹都抱上了孩子,老大尚森手里还抓着老厚的一把牌,急得抓耳挠腮,愣是出不去,老大难了。
尚森的牌卡在他当兵入伍上。尚森当的是工程兵,掏山洞时排哑炮,轰的一响,他变成了血葫芦,身上留些伤疤倒在其次,聋了一只耳也在其次,关键是脑子被那一震一摔受了伤害,原本机机灵灵的一个小伙子,出院后就变得木憨憨的了,说傻还没傻,可不傻也比正常人脑袋里缺根筋。转业后,地方上按照伤残军人待遇安排他进了红星机械厂,厂里因才用卒,这种材料也只配当楔固卯,就安排他当了门卫守大门。这样的一种情况,再想出净手里的牌,是不是就很难了?时光倒退十几年,户口的事还很讲究,乡下的姑娘不想娶,怕日后生下孩子连进学堂都不好解决,可有城市户口的大姑娘小寡妇一个个地见过,摇头的都是人家。为这事,我的姐姐、姐夫心里窝的火,就从来没熄灭过。
尚森三十多岁那年,我姐姐的大儿媳终于闪亮登场了。谢秉玉是乡间一所小学的老师,因是中专毕业,却有着一份城镇户口,当年二十六周岁,在乡下,基本已可纳入大龄未婚女青年范畴了。老姐姐专程去找我,说两人已见过一面,人家答应再见面,但要求家里能说话算数的人一定到场。娘亲舅大,姐夫又是个提前退休的老工人,一辈子木讷,老姐姐便让我全权代表。出面前,我问老姐姐,模样……就别挑了吧?老姐姐说,人家不是有条件嘛,这回,你就说了算。
以我设想,女方只要脑子没病,身体没有严重残疾,高矮胖瘦嘴大眼小的,就别再挑剔了。及至尚森带着谢秉玉走进我的办公室,我的心陡地就提到了嗓子眼。我看了坐等在沙发上的姐姐和姐夫一眼,发现老两口也是满面惊讶,他们心里的想法也肯定与我一般无二,似冰又似炭:这能是尚森的媳妇吗?
站在我们面前的谢秉玉,如果用标致二字形容,肯定夸张了,有点儿过,但说标准,应该是没谁会反对。她,一米六几的个头儿,丰满结实的身材,略显有些黑红的肤色,椭圆形的脸庞上鼻直唇红,只是眼睛稍小了些,但黝黑、明亮,目光里透着聪慧与倔强。
谢秉玉沉静而从容地坐在了我们面前,沉吟片刻,直奔主题:“大舅,叔,婶,尚森把他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在把关系确定下来之前,我要谈谈我的条件。这条件我想过很久,这涉及到我和我全家人的生存,所以,还请各位长辈不要见怪。一、我是师范小中专毕业,在乡里的小学教了几年书,但到现在还没转正,一直是个民办教师。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希望能在结婚前调到市里来,并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我看了老姐姐一眼,老姐姐急把目光躲闪开。我明白了,在我出场之前,一家人其实已知道了谢秉玉的这个条件,他们把球盘送到了我的脚下,就是看我这临门一脚的魄力与能力,一脚踢进,大功告成;临降怯战,万事皆休。当时,我的工作职务是市教委副主任,似可权充这个家庭的一道压桌主菜。
我犹豫了一下,问:“这事,原则上说,我们一起争取吧……但是不是可以等等机会,别急?”
谢秉玉说:“当然。你们不急,我自己急也没用。”
这句话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你们不把这事办下来,也别急着结婚。
我心生不悦,说:“你还有什么条件,请都说出来。”话一出口,我都感觉到了口气的生硬,这不是相亲,而是商务会议桌前的谈判。
谢秉玉以谈判对谈判,她说:“我的家境不好。我父亲有病,已不能下地劳作,家里的日子全靠我母亲撑持。我弟弟考上大学了,刚读大二。在我离开那个家门之前,我必须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因此,我的第二个希望,就是结婚前,能得到六万元的经济支持。”
六万元,就像一块六万钧的巨石凭空而落,砸得几人心里都狠狠地颤了颤。时光倒退到十余年前,六万元可不是笔小数目,当时,就连我这副处级的公务员,月收入也不过千余,姐夫在厂里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元吧。况且姐姐家接连刚刚处理完尚磊和,尚淼的婚事,本就有限的家底不仅彻底告罄,据我所知,还背上了不菲的债务,起码,欠了我的,就有上万吧。
我说:“为父治病,助弟上学,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作为姐姐,都无可非议。这样好不好,咱们分期支付,婚前三万,婚后三年,每年一万,你弟弟也正好可以毕业了。”
谢秉玉坚决地摇头:“不。我不想把麻烦带到以后去,还是一次性利索的好。”
我说:“秉玉同志,咱们双方,都是普普通通的小门小户人家,收入有限,他们家又刚处理完两个子女的婚姻大事,还是多理解、多宽容些的好。来日方长,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承诺。”
谢秉玉说:“我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难处。”
我又说:“拖欠支出的部分,可以按银行利率,支付利息。”
谢秉玉硬撅撅地说:“我不要利息。”
我心里愈发不悦。这是赤裸裸明白无误的买卖婚姻,新中国都成立快半个世纪了,而且是坐在一个城市教委的办公室里讨价还价,还这般正儿八经,说来难堪,也很滑稽。
姐夫望定我,说:“他舅,那就定下吧,大不了,我砸锅卖铁。”
我明白那目光中的内容,也理解砸锅卖铁的确切含义,只好长嘘了一口气,说:“好,那你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2
我对谢秉玉的成见,绝对不是仅仅因为这一次的不愉快谈判。我在教育口工作了多年,听过见过的贫困学生和教师多了,还亲自经手处理过一些事件。有人说,私字是万恶之源。可这贫穷,就是这私欲的温床。当人们的生存面临挑战的时候,往往那极端的手段就被催生出来了。人穷志短,虽不是全部,但也是大部。多少让人唏嘘感叹的社会故事,不是因为贫穷而起呢。
两块巨石移开。婚车迅即启动。秉玉嫁给尚森之后,便同老姐姐和姐夫住在了一起。单位分房已是历史,家中再无购房之力,对此,秉玉倒也没再说出什么,也许,她也看出来了,家里的这根骨头,确是再榨不出什么油水了。
秉玉和尚森办理结婚登记的头一天,我将手里的全部积蓄,外加以我的名义借来的一部分,一共六万,放到了秉玉的身边。那一刻,秉玉深深垂头,没敢看我。我从正在装修的新房退出来,进了老姐姐的房间。姐夫将一个老式陈旧的塑料皮笔记本放到我手上,说,这个,放在你手上,东西在里面呢。我忙推回去,说,姐夫,这是跟谁,你骂我呀?
姐姐家的房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盖的楼房,两间,六十多平米,原来是厂里分的,后来参加了房改,就算姐姐和姐夫的私产了。姐姐将南
面较大的那间腾出来,给大儿子做了新房,老两口住到了北间去。
一年后,秉玉生了,好家伙,竟是一对龙凤胎。一家人大喜,转而便是淡淡的忧愁。家里还背了饥荒呢,一下子添了两张嘴。尚森所在的机械厂又是死不了活不起的样子,姐夫提前退休,若不是考虑尚森是伤残军人,只怕也早让他下岗了。但日子还得将就着过。粗茶淡饭的,荏苒数年,倒也自得其乐。
可是,姐夫突然心梗,倒在了小区里的棋盘前。在住院治疗的半月里,正好赶上学校放暑假,护理的任务便全部由秉玉承担起来了。尚磊和尚淼夫妇闻讯,都急赶到了医院。那一幕,我是在病房里亲眼所见的,尚磊和尚淼分别将一叠厚厚的钞票放在了父亲的枕旁,但秉玉都坚决地送回了尚磊和尚淼的手上,说爸爸的病,我和尚森会尽力的,这个钱,用不着,真的用不着。
我和姐姐对望了一眼,心里的滋味不知是沉重还是欣慰。这个推拒的潜台词我们都懂,按照民间不成文的规定,父母养老送终的任务由哪位子女撑持,老人的遗产便由谁继承。这种民约俗成,在乡下人的心目中,分量就更重。可眼下,姐夫不过是初病,姐姐也刚六十硬硬朗朗,这么早就存此打算,是不是也太处心积虑、操之过急了吧?
但这些话,没法说出口,对谁都不好说。
姐夫出院后一月,突然旧病复发,再次在卫生间里歪倒。从此再没醒来。
姐姐家的糟乱事,其实是从这一天才真正开始的。
3
隔年初春的一天,是星期日,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去她家一趟,马上就去,一分钟也不要耽误。
三对夫妇已都聚在了姐姐的家里,迎接我的是小屋子里的满满登登、乌烟瘴气和一张张沉郁冷峻的面孔,姐姐坐在床心默默地擦沮。那神情,我想当年遭遇“9·11”袭击时,美国佬也不过如此。
我问:“姐,怎么了?”
姐姐说:“你姐夫留下的那个塑料皮笔记本不见了。”
我的心拧了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姐姐说:“我前天夜里还看来着,今早起再去看,就不见了。”
我说:“会不会是两个毛孩子翻出去玩了?
问问。”
秉玉说:“不用问,他们俩才多大,登得了那么高?”
姐姐说:“不会是孩子。那东西我是放在立柜顶上的纤维板夹层里,那夹层还是你姐夫活着时特意加上去的呢,连我上去摸,都得踩上椅子。”
我说:“不会是看过后忘了往回放吧?”
姐姐说:“哪能。不放回去,我还敢闭眼睡觉啊?”
我把目光盯向了大外甥:“尚森,你没看过吧?”
尚森倔哼哼地说:“舅,你别这么看我。我都不知道我爸还留下什么笔记本。舅,一个破笔记本,还找什么呀?”
我没正面回答尚森的问话,也没敢再把目光盯向秉玉,投鼠忌器,我怕她炸。此事若是大人所为,问肯定是问不出来的。
尚磊说:“舅,您既来了,就带我们找找吧。”
秉玉立刻接话说:“找就找。也别光从这边一处找,你们那两个家也都找找看。”
尚淼用胳膊肘碰了二哥尚磊一下,响应说:“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谁也别离窝儿,先从这边找,然后去我家,最后是二哥家。找谁家时谁在外边躲躲,别沾边,避避嫌,都好。”
我问姐姐:“姐,你说呢?”
姐姐说:“都这么说,就找拽吧。你们几个,心里不愿意,就都骂我。自从你们老爸过世后,我心里一直乱,脑子也大不如以前了。一个老糊涂的妈,你们都担待吧。”
那天,我的身份便是监察御史,率领尚家的三个儿女及他们的配偶全面搜检。每到一家,那家的夫妇便由母亲陪着,守在门外的楼道里,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可远去。北方初春,乍暖还寒,可我知道,那寒的是在人的心里。一个家庭,因为一个笔记本,闹到这种程度,彼此间都变成了大明王朝的东厂侦探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虽还没算彻底撕开面皮,也够叫人心里打战儿的了。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不介绍介绍我姐夫留下来的那个塑料皮笔记本了。那个笔记本没留下几个有价值的字迹,却夹着一些邮票。姐夫生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也没刻意收集攒存过邮票,他的集邮仅限于收到了亲戚朋友的来信,他看邮票花花绿绿的好看,便用剪刀从信封上剪下来,夹进笔记本了事,也不管成套不成套、缺张不缺张的,更没有拿到集邮市场上去做过验证和交流。尚淼处朋友时,有一次带男友邹惠民来家玩,尚淼知邹惠民爱集邮,便把爸爸的那个笔记本拿给他看。没想邹惠民漫不经心地翻着翻着,一双眼陡地惊直了,他拿起一张邮票,说没想你爸还藏着这么一张宝贝呀!尚淼本来也对集邮不感兴趣,便追问这张怎么了。邹惠民说,你真不懂呀?这张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台湾没红,怎么叫全国?再加西沙和南沙也没印上去,所以发行后很快就停止出售和使用了,物以稀为贵,眼下这张,拿到集邮市场上去,足可卖上七八万。但你爸这张品相差点,下剪子时把边儿上的邮齿伤了一些,可能在价格上就要打些折扣。尚淼又惊又喜,急喊爸爸妈妈快来看。从那往后,姐夫的这个笔记本就轻易不示人了。
为这张邮票的事,姐姐、姐夫找过我,还拉上尚淼和邹惠民,一起去了集邮市场。那天,一听说真龙露相,我们立刻被人们团团围住了,有人开价,一手钱,一手货,七万。姐夫犹豫,心有所动,当时家里正张罗尚淼的婚事呢。邹惠民拦阻说,大叔:还是别卖吧。这种东西,可比文物,价格随风涨,涨幅比银行利息高多了,而且只涨不落,明年就可能值十万,留留吧。等我有了钱,您也稀罕够了,您说话,不管贵贱,这东西也不能落到外人手里去!姐姐也说,咱俩的岁数也都不小了,就留着它做救命钱吧,不到万不得已,咱先不出手。姐姐还特意叮嘱尚淼小两口,说这个事,你们可给我记牢实了,除了你舅,家里人再不许让外人知道!那次,为了支付谢秉玉的六万元财礼,姐夫要将这张邮票放到我手上,就有了以此抵押之意。
那天,我和姐姐带着众子女在三个家庭搜检,可谓是天翻地覆见缝寻针,但一无所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悄声问姐姐:“你看谁最可能?”
姐姐反问:“那你说呢?”
我心里自有怀疑的重点,却不好说出口。尚淼和邹惠民夫妇是最知那张小纸片片的分量和底细,但邹惠民若存此心,第一次见那张邮票就故作懵懂好不好?当时若是悄然将那张邮票从笔记本中抽出归己,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粗心大意的姐夫都不会有所察觉。尚淼是姐姐的贴心小棉袄,想来也不会去偷夺母亲的救命之物吧?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尚森夫妇了。大外甥憨钝如稚,想来不会有这种心智。那么谢秉玉呢?她知道家里存着那个笔记本吗?她知道笔记本中夹着的那张邮票的价值吗?不好说啦!
夜已很深,空中飘淋着雨夹雪,天气愈发凛冽。秉玉有算计,上午从家里出来时,就带了一把伞,撑在自己和姐姐的头上。尚森和我也打了一把伞,是出门时尚磊塞过来的。几个人走在雨夜里,一路沙沙,是雨声的沙沙,也是脚步的沙沙,谁都不说话,都在想着心事。先到了姐姐家楼下,
子交出来,我跟她有个死活!
尚淼在市交通台当主播,经多见广,水火不惧,嘴头子上也如戟如剑,锋利了得。我怕她出马一条枪,烧起家里的烽火,忙着晓以利害,多侧面多角度地反复向她说明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刚直性子的尚淼总算抹了一把愤慨的泪水,悻悻作罢。
而对尚磊,我则提醒他莫动声色,早筑堤坝,辟出退路,疏财免灾。那一阵,或“六一”,或“九九”,或春节,或中秋,尚磊忙着跑银行,隐姓埋名地将一笔笔资金划寄到慈善机构或希望工程账号上去。尚磊把那些银行的底单拿给我看过,我叮嘱说,好好保存着吧,积雪真若埋不住死孩子。这总还算最后一道护身符。
6
去冬腊月里的一天,入夜时分,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又叫我马上去一趟,说她家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家庭会议,人已经都聚齐了。我心里紧了一下,不知他们又要演出怎样的闹剧,便推脱说,既是你们家里的事,就你们家里人自己研究决定吧,我这边有客人,不去了。尚淼抢过电话去,说,大舅,我知道你不愿掺和我们家的乱糟事,但这次您务必得来,家里有客人我们就等您,您不到,,我们的会不开,虚席以待。我说,舅这几天的身体不好,你舅妈还给我熬着药呢。尚淼说,那我们就举家移师,去大舅家开会。这次家庭会,大舅就是躺在床上,也得帮我们掌掌这个舵。我只好说,能不能告诉我,又是什么事?尚淼迟疑了一下说,这出戏,我妈是编剧、导演兼女一号,缺了大舅临场监制,十有八九就要演砸。话筒里,我听姐姐在旁边嘟哝说,你们才要往砸了演呢,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少掺和!
自己的事?在那个家里,姐姐除了洗衣做饭带孩子,哪还有什么自己的事?我只好披衣蹬鞋,急急赴会。尚家果然是虚席以待,那个三人长沙发上,姐姐和尚淼各坐了一边,留出中间的位置,那显然就是我的了。其他人则围成半圈,各坐在茶几周围。姐姐见我进屋,率先起身相迎,六十开外的面孔竟小姑娘般地变成了火烧云,含了明显的羞涩,嘀咕说,我说是自己的事,他们还非要把你折腾来。
原来是姐姐要再续老伴,而且已有了明确的目标,甚至双方已在商量婚嫁之事了。姐姐每天白天在家里忙碌,傍晚时,吃过晚饭,才算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她的自由时间是去住宅附近的公园里跳中老年迪斯科,跳来跳去的,便跟一位老先生熟悉了,并生出了感情。那位老先生年近七旬,原来是红星厂的工程师,很斯文也很传统的一个人,老伴病逝后,也是跟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姐夫去世已近四载,孤雁清苦,走此一步,倒也正常。既论了婚嫁,姐姐就先把这事说给了女儿。尚淼不保守,听了嘻嘻笑。说我老妈行啊,焕发革命第二春,会赶时髦啦!只是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结什么婚?愿好两人就好呗,我不反对。可姐姐说,我才不干那鬼鬼祟祟不正经的事,想两人好,就去办下结婚证,大大方方地在一起过日子。尚淼说,那你就去他家过,我做老妈坚强的后盾。姐姐说,他那个家。不是还有儿子儿媳妇嘛,听说都反对老爹娶后妈。
这个事,如果放在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家庭,本也不是什么太难办的事,一对期盼夕阳灿烂的皓首恋人,出去再租一户房子单过也就是了。可偏偏那位老先生也是红星厂的老人儿,厂子效益不好,加之退休时已是十余年前,每月的退休金不过几百;我姐姐年轻时不过在街办厂当过几年工人,连大集体都算不上,只是个小集体,勉强争取到手的退休金更是少得可怜。如果两位老人再去租房,仅此一项,就要支出两人共同收入的一半。更令两边其他子女愤而难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位老人本来都是有住房的,凭什么仅因某一子鸠占鹊巢,就要逼着老人再去租房?
情况好比秃子头顶上的蟑螂,再清楚不过了。尚淼代母主持会议,问尚磊:“二哥,先说说你的意见。”
尚磊对谢秉玉一笑,先递我一根烟,又递了尚森一根,说:“父亲不在,兄长为尊。还是让大哥先说吧。”
尚磊不惧他哥,却惧他嫂,因为他的七寸短处正在嫂子的掌控之下。他不率先开口,却把临门一脚的这个球传送到大哥尚森脚下,这些年的官场生涯;混得不是一无所获呀。
憨钝的尚森说:“我们家的事,都是我媳妇拿主意,还是让秉玉说吧。”
秉玉望望婆母,又望望我:“妈,大舅。那我就代表尚森,先说说我们的意见?”
尚淼却抢先横出了一枪:“嫂子,可别。这是我们尚家的事情,还是内外有别的好,让我们尚家的子女先说吧。”
秉玉淡然一笑,果然就不言了。
尚磊说:“尚淼,大哥和嫂子不说,那就你先说。”
尚淼说:“我说就我说。其实我的意见早就跟我妈说过了,我妈年龄还不算大,本着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我坚决支持老妈找一个亲亲密密老爱人。但是,咱们与时俱进,只重内容淡化形式,结婚的事,还是先放下好不好?”
姐姐应声反对:“不好。我可不想让人指指戳戳。老不正经。”
尚淼说:“妈,外人的嘴,你且让他们说去,不信还能说塌了天!家里人,哼,我看谁敢?”
秉玉又是淡然一笑:“妈的脸皮,可能这辈子也难修炼得这么刀枪不入了。”
“你什么意思?”尚淼横在手里的枪,陡然直逼了秉玉的门面。
秉玉说:“价值多元,荣辱自知,各人自有各人的活法,还是别逼着别人非跟自己一样的好。”
尚淼跳了起来:“就是跟了我一样,又怎么啦?”
秉玉不再接招儿,却将不知什么时候备在手心里的一个小纸条递到了尚淼的面前。这个动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出的,急性子的尚淼立刻展开了纸条。我坐在尚淼的身边,目光掠过,清晰地看到纸条上是一组阿拉伯数字。那组数字我难记得真切。但那张纸条却好似变成了如来佛手里的照妖镜,尚淼的神情立即大变,她先是怔了怔。再畏怯地睨视了秉玉一眼,然后就萎坐在沙发一角,嘟哝说:“妈,这个事,还是您自己拿主意吧。”再往后,我就看尚淼搓着那纸条,一直搓得碎如齑粉,丢弃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去了。
那天,依着尚淼“内外有别”的原则,尚磊媳妇、尚淼女婿以及秉玉,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不再多言。围绕着母亲再婚一事,尚家的三个子女的态度分别是:尚森“支持”;尚淼“反对”;尚磊是“都行”,两边倒,等于弃权。这样的一种结局,留给我这个裁判长或日监票人的难题,便只好用官场上最习以为常的办法去处理了:“这个议题,别急着决定,大家都冷静冷静,好好想一想,找时间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好不好?”
7
那天,走出姐姐家的门,夜已很深。我抬头望天,只见天河旁的三星已经横移,以我在当年下乡时学来的看星星判时辰的浅薄经验,估计已近午夜了。尚淼拉我们几人去喝粥,说有家粥店不错,就在电台附近,她有时夜里做节目,肚子饿了,常去那里垫补。尚磊也说,说了半宿的话,我的肚子早就叫了。我知这兄妹俩必是另有话要再跟我说,便跟他们一起打车奔了粥店。
时下的粥店。可非当年的李玉和粥棚脱险时的那种处所,各种名日粥的食品和佐粥小菜
花样翻新,价格也让人瞠目。在邹惠民和尚磊媳妇忙着去做安排的时候,尚淼问我:
“大舅,今天我家这事,我知让您为难了。难得您和我们兄妹俩单独一坐,你说说看,这事怎么往下发展才好?”
我说:“以我原来的笨理儿估计,这个事,应该是由你或你二哥站出来支持你妈,怎么还掉过来了?”
尚淼说:“大舅真没看出这里面的磨磨儿?”
我说:“这似乎有些不符合常理。”
尚淼说:“不合常理的才是某人的歪理。我大哥那人,完全没主意,他的主意都是由谢秉玉来拿。让我妈抓紧结婚,等于让我妈抓了把扫帚。先把自己扫地出门,那我爸留下的那户房子就等于提前落在他们的名下了。”
我似有大悟,心沉了沉,原来还是财产继承问题,世事繁杂,却万变难离其宗。话已说到这里,留给我这长辈的任务也就只能多做开导了。我作沉吟状,有意拖延片刻,才说:“你们兄妹三人,你和你二哥的条件都好些,只有你大哥,命运不济,就只好依附在你爸你妈的老房子里。既是一奶同胞,彼此多些宽容,就别再斤斤计较了吧。”
尚淼说:“哪是我们计较?是某人心术不正,早揣吞象的贪心!若是好说好商量,同根而生,谁愿相煎?又谁愿把家里的笑话闹到外面去?可有些事,您也是知道的,我爸生病,我们连掏医疗费的孝心都被她拒绝了,又黑着心把我二哥的小记事本藏匿在手,你说她想干什么?虽说这些年我爸我妈一直跟他们吃住在一起,可房子是我爸我妈的,老两口每月又有退休金,虽说不多,也足够那种粗茶淡饭。逢年过节,大事小情,我和我二哥对父母家尽的孝心作的贡献,哪次不远远超过他们?凭什么父母遗产就都要归到他们名下?况且,我妈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呢,这么早就狮子大开口,想来也太让人寒心了吧?”
坐在一旁的尚磊冷笑自嘲:“不是我怕井绳,而是井绳已套在我的脖子上,不怕不行了。”
我往尚淼身边凑了凑,低声问:“今天,你大嫂递了你一张纸条,那上边写的是什么?”
尚淼的脸腾地红了,红成了紫猪肝。好一阵。她才说:“大舅,你别问了。这女人心太恶。也想像治我二哥似的,掐我的七寸呢。大舅也小心些吧,可别让她再抓住你的什么小辫子,了不得!”
那天的夜宵,吃得无滋无味。我想,尚家的事情,我真的必须远远避离了。那不光是泥潭,而且是陷阱,井沿上布满溜冰,井底下荆棘铁藜,一不小心,滑滚进去,摔个鼻青脸肿,还算是小事一桩。绝对险境啊!
8
春节后的一天,姐姐突然跑到我家,脸上竟满是喜色。她告诉我,秉玉在外面租了一户一室楼房,正带人做着简单整理和粉刷,说收拾完就和尚森带两个孩子出去单过了。我大惊,也大惑,问秉玉和尚森不想要你们的房子啦?姐姐摇头,说我这可没敢问,怕炸锅。
我和老姐姐一起去了秉玉租下的新住所。秉玉正带着几个装修工人在忙,一身白点,两手铁锈,满脸的汗水。小屋子也就四十多平米的样子,七层,顶楼。在我们这个城市,可算是最贫寒的住所了。
迎着我疑惑的目光,秉玉说:“我妈能找到一份晚年的幸福,我高兴,是真心实意的高兴。做儿女的,我和尚森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我小心地措辞说:“不知你们……对日后的日子,还有什么打算?”
秉玉说:“大舅不问,搬过家我也要去找您呢。我和尚森都没能耐,估计这辈子。想买一处自己的住房,做梦吧。两个孩子现在都小,好将就,但再过几年,就难了。所以我还是想请大舅帮我们把这事早些定下来,真到了我妈不再住她那户房子的时候,还是让我和尚森能搬回去。”
“这个想法,不会是你和尚森的灵机一动吧?”我问。
“其实,自从我妈说了和那位老先生的事,我和尚森就这样商量过了,别看尚森憨,他的心却善良,他不愿看到老妈受委屈。”
“那天开家庭会,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打算说出来?”
“尚淼不是不让外来的人张嘴嘛。尚森嘴拙,也说不出子午卯酉。我也想,不说也好,与其说,不如做吧。”
我长叹了一口气,说:“可有些话不说透,就是一家人,也难免互相猜疑啦。”
秉玉神情冷下来,说:“大舅。我明白您话里的意思。可没能耐的人,最怕的是受欺负。您可能不知道,平时尚淼和她二嫂走得有多近?两人早建了统一战线,还放出话来,说不能让家里的便宜都让傻大哥和奸大嫂一家都占了去。有些话,更不好听,我们不能不防啦。可我也有做人的准则,人不犯我,我是绝不会犯人的。”
那天,我和姐姐回家,一路感慨。我说,以前,也许我真看错大外甥媳妇啦,只看到了她心机过重的一面,却没想到真到了关键时刻,她不光能善下一条心,还能横下这条心来做事。一家三兄妹,实际长嫂已当家呀!姐姐说,这一家,三双儿女六个人,最可我心的还得是老大媳妇,没有秉玉的勤快俭简,一手撑持,我也不敢撒开手另扑了一户人家,就是只为着那个憨儿子,我不是也得将就着过不是?秉玉的心思确是重,可乡下来的孩子,穷怕了,又独力撑着那个家,难免就使出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邪招子,不这样,又让她怎样呢?
那天分手的时候,姐姐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的东西,交给我,说:“这个。看来眼下只能交你替姐保存了。”我打开纸口袋,里面装着的正是那个大红的塑料皮笔记本,“一片红”单夹一页,赫然其中。姐姐抹着眼角说:“再进了一家门,不管两人嘴上说的怎么好,也难比你死去的姐夫啊。许多事,不能不想在前头,防在前头。你替姐姐操着这份心吧。”
我掂着那个愈觉沉重的笔记本,问:“这个,那兄妹三个知道吗?”
姐姐说:“既说丢了,那就是丢了,还让他们知道干什么?还没看够家里的这八出戏呀?”
是的,家家都有八出戏。清苦寒门里酌焦大、刘姥姥们的故事,未必就没有大观园里宝哥哥林妹妹的来得精彩。那一刻,我远望着渐渐消失在城市人流中的老姐姐,设想着尚家未来可能发生的故事,只觉心中一片茫然。
责任编辑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