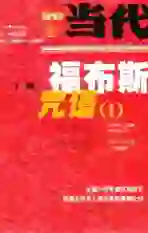香木镇的梆子响了
2009-03-21白天光
白天光
1.匣子匠让香木镇的街上重又有了牌匾
香木镇的匠人不少。但香木镇的匠人很抱团儿,懂得香木镇的规矩,不做偷食他人饭碗的勾当。香木镇几百丈石头长街,街的两旁排满了匠人的手艺家什。香木镇人难见得有读书的,铺子都没牌匾。
当年这里有过一家私塾,教书先生叫窦守德,还有字号叫卧柳居士。但窦守德白天教学子们三从四德,晚上却跟香木镇的银匠的小夫人小芍药在他的私塾学堂里做那档子事儿。窦守德对女人缺少专心致志,跟了小芍药半年,又跟烙烧饼的媳妇儿到他的私塾学堂,重复做那档子事儿。
后来窦守德终于被人逮了正着,香木镇的匠人是有组织的,叫梆子会(匠人们听到梆子便都聚在一起开会),梆子会决定把窦守德给阉了。当晚,窦守德扔下私塾学堂,兜里揣着不足十两银子,就逃出了香木镇,到哪儿去活命,没人知道。这样,香木镇的匠人们便有了忌讳,商铺一概不挂匾,不吊幌,因为当初香木镇的牌匾和幌子都是窦守德写的。
但香木镇的匠人们吊在商铺前的物件儿,让外地人看了便也一下子就能知晓是怎样的行当。裁缝店会悬起一件长袍马褂,一把剪子缝在裆上。炸炸糕的会炸出碗大的炸糕,插在竹竿子的顶端。剃头的门口悬着一条用马尾巴编成的大辫子……香木镇的匠人们都活得滋润,见不得这镇上的匠人们有多少发大财的,但这些匠人们也都相互走动,梆子一响就聚到一块儿。梆子每个铺子都有,拎起来就敲,一般都是谁有事儿,谁就敲。
匠人们之间的来往,不唤其名,只叫外号,这些外号只有香木镇的匠人之间知晓,外人却听不懂。裁缝的脑袋很大,应该叫大脑袋才合适,但匠人们却叫他粉子,原是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陪过一个叫粉子的戏子睡觉,粉子比他大十六岁。炸炸糕的是个驼背,本该叫罗锅子才合适,但匠人们却叫他后鞧,因为他能生吃猪肉,却只能吃后鞧。还有卖杂粮的吊眼梢子,吊眼梢子姓陈,眼皮总跳,上眼皮总粘着芦苇膜。剃头的莲花指姓张,说话粗声大嗓,但手指又细又长。膏药铺的老狗,做过坐堂医,中医的望闻问切他用得不拿手,他给别人诊病靠鼻子嗅。说书的花蚂蚱姓边,嘴皮子很溜,但他说书不光靠说,在一丈长宽的台子上又蹦又跳。在香木镇的匠人里,外号最出奇的叫活尸。活尸应该是个木匠,但他不干正宗的木匠活儿,只做匣子。他为啥叫活尸,因为他有绝活儿,他做出的匣子,把盖儿盖严,一袋烟的工夫就能把人憋死,而活尸钻进他做的匣子里,睡一宿觉都不带憋死的。
活尸的生意不错,在他的手工铺子里摆放着上百个匣子。这些个匣子都有来处,大的能装绫罗绸缎,小的能装金银细软。这些个匣子也有名号,最大的那个匣子四角包铜,三层锁,匣子上是烙画。活尸烙画不烙花鸟鱼虫,不烙梅兰松竹,大多烙兽头,有虎头,龙头,狮子头。烙虎头的叫虎藏,烙狮子头的叫狮镇,烙龙头的叫龙吼。活尸还能做暗匣子,在匣子里有暗处,一般人看不出来。这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镇上的匠人们虽然相互之间都叫外号,但真正的名号也都知道。活尸来香木镇十多年,人们却没有问出他姓甚名谁来。有一回,梆子会特意给大伙儿建个防匪竹签档案,问活尸的来历,活尸终于说了,但大伙儿不知道活尸的名字为啥这么长:公吉喇特龚吉尔·阿兰肩甲。后鞧是有些见识的,他在京城待过,就惊讶着说,公吉喇特龚吉尔是满族的姓氏,阿兰肩甲是桦树皮的意思。哎呀活尸,你,你,你肯定是在旗的,朝廷当大官的肯定有你亲戚。
活尸一声长叹,什么也不说。
人们知道了活尸是满人,又是朝廷有亲戚的人,是不宜叫活尸的,此后便叫他桦树皮。
来找桦树皮做活儿的有平民百姓,也有富豪,平民较少,富豪较多。原是富豪家里边的东西都值钱,当放金贵的匣子里。富豪们送礼也讲究用匣子。距这里几百里的哈尔滨有家元泰果子,是哈尔滨财东们送礼最喜欢的东西,用的果匣子都是桦树皮做的。哈尔滨的秦庄酱菜的酱菜匣子也是桦树皮做的,秦庄酱菜是贡品,进了京城,朝廷是要过目的。
桦树皮给别人做匣子,一般不论价儿,凭赏,这比讨价还价还要赚钱。凡来订做匣子的,如果满意。多少银子都认掏。这年夏天,香木镇西的香木河发了大水,淹了香木镇的石板路。香木镇的石板路通官道,官道通奉天,也通京城。河发了大水,来这香木镇的人便少了,生意就显得冷清。这天一个人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溅着石板路的雨水停在了桦树皮匣子铺的门前。一般谈生意,桦树皮是不进屋的,见这骑枣红马的人来头不简单,就将这人请进铺子里。这人看不出年龄,唇上有一抹很齐整的胡子,面皮儿却很嫩。他穿着鹿皮裤子,鹿皮鞋,腰间扎着虎尾巴腰带,上身穿着杭缎马褂,头戴一顶藤须子编的遮阳帽,嘴里还叼着一柞长的银烟袋。
桦树皮急忙哈腰,问道,这位爷想要什么匣子?
来者坐下,将银烟袋握在手里,说道,给我做两只暗匣子,明处放人参,暗处放大烟膏子。收多少钱手工,说个数儿就行。不过我不能来取货,你得给我送到山上去……
桦树皮已经知道来者是山上的胡子,就用黑话问,这位爷在哪个筏子?山上的公蝶还是母蝶?
来者说,你不用跟我说黑话。我跟你实说,我是山上槽子沟的军师,我叫梁厚哲,也叫铁嘴梁。最近绿营军要到山上清理胡子,可能先要朝我们开刀。护国军的军长是北辰大帅,这家伙不认钱,只认大烟膏子。但下山以后,有两股绺子跟我们过不去,我们用你这匣子,就过关了。
桦树皮说,明白了。早知道梁军师的大名,你们大当家的梁载江对香木镇不薄,没到这里劫过财物,绑过肉票。就凭这个,我桦树皮也得为大当家的效劳。
梁厚哲说,大当家的是我二叔,对香木镇不薄是有道理的。当年我二叔领我上山立竿子,路过香木镇,那时候我们手里没有一块大洋,就在这儿讨吃的。我们吃过香木镇的黏糕、煎饼,还有狍子肉包子,你说我们爷儿俩能忘记这个恩情吗。
桦树皮说,啥也别说了,就当是家里人。啥时候要这匣子,我就啥时候给你们送到山上去,保准这暗匣子做得奇绝,让您和大当家的满意。
梁厚哲说,那就五天以后吧。
梁厚哲走了,桦树皮不敢耽搁,就从炕上拽出几块梨木板子,黑天白日地做细活儿,四天头上,两个暗匣子就做好了。桦树皮怕匣子生虫子,又用野猪油炸红山椒,给这匣子刷了色。
桦树皮做完匣子,又歇上一天。这时后鞧悄悄地摸到他的屋里,小声问,前几天的来者可是山上的梁军师?这小子不太仁义,不如他二叔。你可对他加点小心。
桦树皮说,我一个匣子匠,有啥担心的,我给他做的两只匣子,也没要钱。
后鞧问,这梁军师要暗匣子干啥用?
桦树皮说,这你就别多嘴了。他干啥用是人家的事儿,咱要是多嘴多舌,那才叫惹是生非。
后鞧说,你这俩匣子做的可够精致的了。
桦树皮说,山上的梁大当家的这些年也没祸害咱们香木镇,我这两只匣子就算是咱们香木镇给他的贡品了。
后鞧说,那是,那是。不过你得让他帮你报个仇。这对山上的绺子们来说是小事儿,对你来
说可是大事儿。
桦树皮问,啥仇,我桦树皮一辈子没仇人。
后鞧说,咋没仇人,你家嫂子小刺梅果儿让谁祸害了。
桦树皮说,窦守德已经离开香木镇六七年了。上哪儿找他去。再说女人跟上了别的男人,那是她中了邪。我总觉得窦守德能勾女人是他的本事,你没看好自己的女人,那是你没本事。我也不佩服小刺梅果儿,要是跟人家好,就投奔人家去,干啥到山坡上吊死了呢。
后鞧说,我知道了窦守德的下落。江北七十里有个三岔河集镇,窦守德在镇上的邱家皮货行做事,是账房先生。你要是请山上的绺子去三岔河杀了窦守德,这香木镇的人都会说你的好儿,香木镇的老爷们儿将来也会把你供起来。桦树皮,这可是个好机会。
桦树皮说,到山上以后再说。
第二天,桦树皮套了一挂二马篷车,装上做好的暗匣子,出了香木镇的东出口,拐过山道,进了山上的壕沟。壕沟向东再走三十里,就是槽子沟了。走出十几里,壕沟突然出现了横七竖八的树根子,桦树皮下车一看,便知道是绺子们干的,便喊着黑话,山上沟,九十九,横是木头,竖也是木头。哪是梢儿,哪是头儿……
一棵大树的背后出来两个背着月牙大刀的汉子。一个汉子问,你可是香木镇的匣子匠?
桦树皮说,正是。
另一个汉子问,是梁军师让你上山来的?
桦树皮说,不是。我是过槽子沟下平村道,去三桥集镇办货。
一个汉子便抽出了月牙大刀,说道,别撒谎了。
桦树皮问,你们可是梁大当家的人?
另一个汉子说,我们都是梁大当家的人。我们奉大当家之命接你来的。
桦树皮想了想,说,我上山,得和梁军师和梁大当家的见一面。
一个汉子说,放心,到了山上就见到军师了,大当家的也会和你见面的。
桦树皮说,那我就等大当家的跟我见面后再把匣子给他。
另一个汉子举起月牙大刀,说,大哥,你可熟悉上山的路?
桦树皮说,没去过梁大当家的山头儿。
那汉子问,梁军师说,没说在山口接你。
桦树皮说,你们不是来了吗。
两个汉子小声说了些什么,桦树皮觉得不对劲儿,趁他们不注意,转了车辕子就往山下逃。
第二天中午,梁厚哲又骑着枣红马来到了香木镇。他走进桦树皮的匣子铺,脸色很不好看,说道,你咋没给我送去?
桦树皮说,我昨天真的给您送去了,在山里的壕沟,险些没丧了命。有两个别着月牙大刀的汉子把我的匣子劫了,我桦树皮一辈子没撒过谎,这两个人都长得很膀,身后背的月牙大刀锃亮。他们不像你派出去接我的人,还劫了匣子。
梁厚哲说道,我不怪你,今天我亲自来接你。
桦树皮说,下山是逃下来的,匣子坏了,得重做。
梁厚哲说,那好,三天之后我和我二叔一块儿来。
梁厚哲走后,后鞧又来了。他对桦树皮说,我总觉得你要出事儿,对付山上的绺子,只好逃了。
桦树皮说,我怎么能逃。我十六岁就来香木镇,在这儿我过得不富,但也不穷。我不愿离开这里,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生意好做,而是我舍不得你们这些梆子会的老哥们儿啊。
后鞧说,一会儿开个梆子会,让老哥儿几个给你出出主意吧。
下半晌,天晴了,日头也热了,地上冒着热气。满街筒子开始响起了梆子。这次梆子会是在桦树皮的铺子里开的。其实这些日子,桦树皮的铺子发生了什么,梆子会的老哥们儿也都知道了。粉子先说,依我看,来的这个梁军师并不是山上的人,我总看他的面相像军人。会不会是护国军的人?
卖杂粮的吊眼梢子说,一定是北辰大帅派过来的,在打探去槽子沟的线路。
后鞧问,那半路咋会出现两个刀客?
粉子说,这刀客也是护国军的人。他们在摆放树根子的地方其实就已经迷了路。
桦树皮说,想起来了,他们还问我去没去过大当家的山头。看来粉子说对了。
后鞧说,既然你已经和绿营军的人见面了。为了灭你的口,他们肯定还会来找你。
桦树皮说,那我该咋办。
粉子说,躲出去。西走五十里就不是北辰大帅的地界儿了。
桦树皮说,我倒想去一个地方,更安全。
后鞧说,啥地方。
桦树皮说,江北三岔河集镇,邱家皮货行。窦守德在那儿当账房,他应该能帮我一把,他和我老婆在私塾学堂里那啥了我都没追究。
粉子说,还别说,窦守德还真能帮你。
香木镇梆子会没有自开。他们估算的事情很准确。护国军最终没有上山去围剿槽子沟,这个无能的北辰大帅后来被调防去了墨尔根(齐齐哈尔)。
北辰大帅的护国军撤防了,桦树皮也没回来。有一天,他鼻青脸肿地被一挂二马篷车拉了回来,一下车,就被后鞧发现了。后鞧就问,桦树皮,你咋的了?被绿营军抓起来了?
桦树皮是不撒谎的,说道,在邱家皮货行,让窦守德给我揍了。窦守德现在的老婆是邱掌柜的老闺女,有一天窦守德到山上买雪貂皮,我就把他的媳妇给睡了。我在睡窦守德媳妇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舒坦过。我一直把这女子当成小刺梅果儿。这娘们儿有点傻,我回香木镇,走到半道儿,她追上我了,要跟我到这儿来过日子,窦守德就把我揍了一顿,把她的媳妇领回去了。临分手的时候,窦守德还和我抱拳,说道,大哥,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就这么回事儿。
后鞧拍着桦树皮的肩膀说,我的哥,你做的很对呀,你是为咱们香木镇的老爷们儿们出了口气啊。
桦树皮回到了香木镇,又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天,从香木镇的东头奔过来两匹青鬃马。马背上坐着一老一少,他们一进香木镇就打听桦树皮的匣子铺。香木镇人的眼睛不揉沙子,能断定出这一老一少不是坏人。到了铺子前,一老一少下了马,老的冲桦树皮抱拳说道,桦树皮大哥,你救了我们山上的人。北辰这个杂种要清剿我们,想在香木镇找个识路的,你没有领他们上山,我梁载江来向你道谢。少的下马,扔过一条皮袋子,说道,大叔,我叫梁厚哲。我是我叔的军师,这一袋子大洋是山上兄弟们对您的酬谢。香木镇是我们爷儿俩当年落难的必经之路,往后香木镇就是我们山上的一座大门,各位叔叔要是有求于我们山上的人,只管说话。
香木镇的爷们儿们感到很自豪。十几年了,才看到梁家叔侄俩的真面目。后鞧炸了一筐炸糕送给梁家叔侄俩,粉子抱拳说道,山上的兄弟们缺衣少穿的,就到香木镇找我粉子。梁家叔侄俩要回去,又被后鞧拦住了,后鞧小声对梁大当家的说,我们香木镇人为人实在,这些年来也没有个仇人,只是八年以前有个仇人离开了这里,如果能够帮我们除掉这一害……
梁大当家的说,好说。
桦树皮也走过来,拉过后鞧。对梁大当家的说,大哥,别听他乱说。香木镇已经没仇人了。
梁家叔侄俩笑了笑,掉过马头就进了山。
粉子埋怨后鞧,桦树皮已经替咱们出了气,你咋还找人家动杀机呢。
后鞧说,这个茬儿我给忘了。细想起来,这窦守德也不算是太坏的人。他又对桦树皮说,如果方便,你再去三岔河集镇,让窦守德过来住几天。
若干年(大约是民国六年),窦守德在三岔河集镇遇到了麻烦,又来香木镇避难。香木镇人
接纳了他。窦守德在梆子会上,跪在地上发言,往后,我再也不碰女人了。因为我下边让我媳妇,那个叫邱桂花的女人给那啥了。往后,我给大家帮忙,只要大家管我吃的就行。
香木镇又活泛起来,家家的铺子都挂上了牌匾和幌子。字写得很俊,但不那么苍劲有力了。有魏体,有小楷,没有狂草。落款是:卧柳居士。
窦守德白天帮别人干活,晚上就在桦树皮家住。那天两个人喝了一瓶酒,互相抱着头又哭又笑。
窦守德说,桦树皮,你真是大善人哪。
桦树皮笑了,窦先生,善到极处便是恶,恶到极处也是善。
窦守德问,谁说的?
桦树皮说,你离开香木镇的时候,你私塾学堂的黑板上就写着这么几个字。
2.梆子会攒了三百大洋发给年度大善人
粉子给人裁剪衣服,不用尺量尺寸。他用大拇指中指拉成柞,按柞量尺寸,给老爷们儿裁衣服从前胸一直摸到胯下,就省去了量尺寸。给女人裁衣服,他让女人靠墙,有一面墙挂着粉面子,女人在墙上一贴,肥瘦就出来了。粉子的作坊人手不多,他老婆是哈尔滨人,炕上地下的活儿都不会干,针线活儿也不会做,她天天只会在作坊里骂人。作坊里有两个给粉子打下手儿的,一个是陈妈,领口上得齐整,能用布条编扣子,当地人俗称叫蒜皮疙瘩。陈妈的手脚慢,但活儿做得细,她已经给粉子打下手六年多了。还有一个叫小荷叶的姑娘,手脚快,眼睛也亮堂,她擅做男服。粉子的作坊还有一个宝贝。是一台洋缝纫机,上边有很多洋文,多少年他都不认识。后来窦守德帮他认出来了,说这机器是德国产的,叫象头缝纫机,这宝贝是粉子在哈尔滨高加索大街的估物市场用一匹杭州绸子换的。粉子脑子活,这洋宝贝他用了几天就熟了。用这洋机器做男装,一天可以做上一件,针线码儿均匀,不起褶儿。粉子的作坊墙上挂的都是物件,有三只俄国产的铜熨斗,还有一只日本产的喷雾皮囊。墙根儿下放着火盆,火盆总有文火燃着,烧的是椴木白炭,炭火上压着一块铝板,铝板上放着一把烙铁和一只锡酒壶,粉子在做衣服的时候,做出激情来便喝一口。
粉子的老婆叫德娴,比粉子大将近十岁,长得不算难看,一身白肉,嗓门儿却高。德娴胆子很大,裁缝店出个什么大事儿,粉子就躲起来。由德娴出面应对。镇南财主何三老爷做一件长袍,前襟鼓包,便领着两个家丁,来找粉子,让粉子重做一件,粉子知道不是他的错。这何三老爷常年蹲在自家后院看几匹公马和母马交媾,何三老爷所有的长袍前襟的膝盖处都有包。粉子坚守和气生财,便答应给他做一件,哪知德娴就揭了他的短,谁不知道你何三老爷常年在后院蹲着,尽看一些下三滥的景儿,哪有膝盖不出包的道理。何三老爷就来横的,我看牲口交配,你咋知道,你是不是看我。德娴也不示弱,你家三个儿媳妇,两个儿媳妇说你的闲话,愿意问就问她们去。何三老爷就把屋子里的火盆踢翻了,火盆上的酒呼地着了起来。德娴就把何三老爷的长袍扒下来,扔进水缸里,又拽出来盖在火盆上。何三老爷走了,粉子吓得躲在了门后,德娴把剩下的半壶酒拎起来,拽着粉子说,当家的。把它喝了,往后胆子大点儿。粉子就把酒喝了,喝完就跑出门外,对着快没影儿的何三老爷骂道,奶奶的,有能耐你他妈再来!
德娴常骂陈妈的手脚慢,耽误活儿,也常骂小荷叶手脚太快,干活马虎。陈妈和小荷叶都不吱声儿,因为德娴每天都在骂,听见她的骂声就像听外面刮风一样,溜着耳边儿就过去了。但陈妈和小荷叶都知道德娴的嘴损,但心地很善。逢年过节德娴就让粉子给陈妈和小荷叶多发点工钱,这一老一少在作坊里给自己做衣服,也不收钱。德娴的做派有些像男人,一街的男人媳妇当年都被窦守德撩过,但窦守德不敢碰德娴。有一回德娴在门口儿看见了窦守德,她就把剪子拿出来,看着窦守德乐,然后又把兜里揣着的一根胡萝卜掏出来,三下两下将胡萝卜铰得稀碎。窦守德脸吓得煞白,还忘不了跟她寒暄几句,嫂子,你忙呢。
香木镇没出过大事儿,但香木镇的老爷们儿都担心,怕粉子的老婆将来会给香木镇惹祸。这个担心终于来了。
这天,一挂二马篷子大车停在裁缝店门前,篷子车上的布是碎花绸子,车前车后绣着凤舞。香木镇的人虽然没出镇上几十里,但见识也能在千里之外。一看这车,就知道是女人坐的。果然,从车上下来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都半老徐娘了,长着滚圆的身子,脸上挂着洋粉脂,很远就能闻到刺鼻子的古怪气味。两个半老徐娘进了成衣铺。就让粉子出来。粉子正在做活儿,将洋机器停下来,问,两位太太让本裁缝怎样效劳?
一个半老徐娘说道,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凤兰,这是我妹妹许凤仙。去过兰县的天香楼吗。
粉子直摇头,没去过。
那个叫许凤仙的女人一努嘴,你这个老爷们儿,白活。在咱们关东活着,男人哪有不进天香楼的。许凤仙在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知道屋子里的炕上还半躺着粉子的老婆德娴。德娴听见这话就从屋里走出来,说道,我爷们儿没去过天香楼,我去过。
许风兰就笑,你个女人?
德娴说,哈尔滨我二哥宋德峰,也就是哈尔滨烟厂的镖头,在哈尔滨排行老三。当年有个叫霍大脑袋的大盗逃到了你们天香楼,是我二哥领着他的兄弟把他的脑袋砍了。我跟我三哥宋德礼去你那儿看过热闹。
许凤仙说道,你说的是五年以前的事儿,那时候天香楼的掌柜是刘翰轩。现在换人了,掌柜的是许俊才。也是我老兄弟。哈尔滨地面上的黑道儿也重新排行了,大哥是黄大蝎子,二哥是白进斗,三哥是朱续良……这位姐姐多少年没回娘家了?
粉子就给德娴使眼色,不让她说话。他哈着腰说。二位姐姐有什么吩咐只管说。
许凤兰说,做十套女旗袍。这十个姑娘出不来,但每个姑娘身高多少,肥瘦怎样,我们都用线头儿量了。
许凤仙说,十套女旗袍,要在十天内做出。下个月的十六,督军北辰大帅要领几个兄弟到我那儿玩儿去,这十个姑娘是给北辰大帅预备的,她们不能穿得太土。我车上料子已经拉来了,都是苏州安字号布庄的进贡绸子。袁大帅登基用的就是这料子。
许凤兰说,把这十套衣服做好,我不会少给你银子。
粉子要出去抱布料,却被德娴拦住了。德娴对两个女人说,我家掌柜是布衣百姓的裁缝,这旗袍是要用能工巧匠缝纫。哈尔滨到处都是大裁缝,两位姐姐怎么能舍近求远呢。
许凤仙说,不是舍近求远,而是看好了你家掌柜的手艺。听说你家掌柜给哈尔滨的牧师做过洋服,这旗袍又算得了什么。
粉子说,能做,能做。
许凤仙就让赶车的马夫把苏州绸子卸了下来。
德娴就一脚把粉子踹了个跟头,对两个女人说,我掌柜的啥手艺我知道,他做不了。如果这旗袍做得不合体,既对不住二位姐姐,更对不住北辰大帅。
许风兰说。算了,不在你这儿做了,这江北的裁缝也不只你一家。你这成衣铺没把我天香楼放在眼里,是成心要跟我们过不去,那咱们就等着以后慢慢儿处吧。说完,两个女人让马夫把绸子重又装到车上,她们上了篷布大车。车挑了
头。马车夫甩了声鞭子,这篷布大车就撒欢儿地出了香木镇。
大车走没影儿了,粉子就坐在门口号啕大哭,德娴,德娴,我的祖奶奶,你这是要毁了我这成衣铺啊。粉子哭完了,进屋又找酒喝,德娴这时有点后悔了,觉得得罪了天香楼的两个老鸨,怕是要招来横祸,就走出成衣铺,跟香木镇上的爷们儿央求,我德娴这回给粉子惹了祸,怕是要也给诸位添麻烦,哥儿几个替嫂子想想辙……
后鞧就扯开脖子喊,敲梆子,开会!
太阳下山,香木镇的店铺都关了,街上就响起了梆子声。梆子会的人都集中在粉子的院里,商议如何才能平息即将落下的横祸。
桦树皮说,天香楼倒是没多大势头,可这北辰大帅可是惹不起的主儿。
后鞧说。那就只好到山上求梁大当家的了。
桦树皮说,这不行,梁大当家的也不会干这等蠢事。梁氏叔侄也常年下山,在天香楼里也有女相好儿,他们不会到天香楼给自个儿找麻烦。
粉子说,这可咋办。
窦守德说,我倒想起一辙来。天香楼的人怕北辰大帅,但北辰大帅也有怕的人。他怕洋人。我们可以求洋人帮助。
老狗说,镇南十五里有个教堂,牧师瓦德里是个人物。他来过咱们香木镇,可以求他帮忙。瓦德里的靠山是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这可是民国政府都不敢惹的洋衙门。
粉子说,咱中国人自己出事儿,自己摆平。找老毛子帮忙,有点儿石可碜。要不我明天就亲自去天香楼,给两个老鸨道歉,再把活儿接下。
后鞧说,给妓女做旗袍,让北辰大帅逛窑子,都是作损的事儿,就不该干。既然已经出事儿了,那咱们就得豁出去了,等着天香楼的人来,到你的成衣铺,要砸就砸,要抢就抢,认了就是。
粉子就一跺脚,我认了。但跺完脚,又冲大伙儿横起了眼睛,那我请你们梆子会的哥儿几个来,就是为了让我忍一忍,认倒霉?
正在大伙儿僵持的时候,在屋里做活儿的陈妈慢吞吞地走了出来,说道,这事儿我来办吧。
粉子说,你能咋办?
陈妈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果然,十几天以后,许凤仙引路领来了一支队伍,是护国军,他们把香木镇的路口都封住了。一个大胖子骑着马,和许凤仙到了粉子的成衣铺门前,下了马。大胖子穿一身护国军军服,唇上留着齐整的中山胡,叉着腰冲铺子里喊,粉子,他奶奶的给我出来!
粉子和德娴没敢出屋,倒是陈妈出去了。她揉了揉眼睛,把大胖子看了个仔细,说,你是邵旋吧。
大胖子说,我是邵旋,你是谁?
陈妈说,我是郑俭良的妈。
邵旋急忙哈腰,是郑大妈,失敬失敬。
陈妈说,俭良常说起你。当年护防双城堡,是你们两个大冬天的在那儿守着,我和俭良他爹给你们送豆包。
邵旋说,现在俭良大哥可不得了,在张大帅手底下当差,和少帅在一起喝过酒。我们北辰大帅要想见少帅,得求俭良大哥……大妈您在这儿……
陈妈说,是我外甥在这儿开了成衣铺,没事儿我总愿意在这儿坐坐。你们也进屋歇歇吧。
邵旋说,不进屋了,我们在这一带巡防,说不定就闯到哪家铺子里。要知道是您外甥开的这成衣铺,我们说啥也不敢惊动您外甥。
粉子这才出来,说,都进屋坐会儿喝点水吧。
邵旋说,看这年龄我该叫你大哥。大哥,往后有事儿你就到护国军找我,我是北辰大帅的副官。
邵旋和许凤仙走了,香木镇又恢复了平静。
粉子的成衣铺也恢复了平静。
粉子的成衣铺虽然恢复了平静,德娴的骂声还是不断。只是她不再骂陈妈了,还叫陈妈为干妈。
梆子会几天以后又敲起了梆子,这次梆子会的成员在后鞧家集会,粉子也去了。走在半路上他在想,后鞧这么鬼机灵的家伙,整天炸炸糕,能出啥事儿?
梆子会开会了,由后鞧主持。后鞧说,咱们香木镇看着平安,却也有不平安的时候,一不平安,除了我们梆子会的这些人能出谋划策之外,也出了许多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我想每个会员要出资十两银子,加在一起也有三百两。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要把全年的事情放在良心的这杆秤上称一称,善和恶就出来了。做出大善的,这三百两银子就该归他。我的意见,不知道大伙儿同不同意。
莲花指马上就说,同意,同意。出银两的事儿也是积大德,我愿意出二十两。
大伙儿都没意见,这银子就算是攒成了份子。
后鞧说,眼见得到了年底,今年这银子该给谁。
粉子说,那还用说,给陈妈呗。
桦树皮说,也不能都给她,也该给窦先生几十两。
后鞧说,瞎扯淡。他把咱们的娘们儿都睡了,咱还给他钱。
粉子说,桦树皮,你是占了便宜。愿意出钱,你就给窦守德出,说不定窦守德还能帮你找个相好儿的呢。
梆子会的哥们儿就乐。
……
陈妈收了三百两银子,但她给小荷叶了,对小荷叶说,把钱交给你爹,快塌了的房子翻个新。你娘想肉吃,一年多了都没吃到嘴,你割一条子肉,让你娘吃个够。
小荷叶就哭了。
德娴有一天走了,留下几个字。粉子识字,见那上面写着——
粉子:
我不生育。跟你结婚十一年,你得有个后。我回哈尔滨了。你再续个弦吧,让陈妈帮你张罗。等你结婚生了子,如果让我回去,我再回去。
陈妈说,粉子,这事儿不能干。把德娴叫回来。日子该咋过还咋过。
粉子喝了一口酒,说,陈妈,我听你的。
3.小豆荚儿和炸糕
镇南财主何三老爷有个老闺女,叫小豆荚儿,常到香木镇来,到香木镇上她也不瞎逛,直奔后鞧的炸糕铺子。她拎着柳条梗儿编的冬瓜状小扁筐,筐底下垫着两片粽叶子,买完了炸糕就放在筐里,再用粽叶子盖上。后鞧的炸糕只两种馅儿,一种是芝麻盐儿,一种是红糖小豆。小豆荚儿来买炸糕是自带馅儿来的,让后鞧现包现炸。小豆荚儿的豆馅儿很精致,有核桃仁、山楂、白糖捣成的馅儿,叫元宝馅儿,有芝麻酱、红糖、胡萝卜丝捣成的馅儿,叫红宝馅儿,还有猪肉、蛋黄、红糖捣成的馅儿,叫状元馅儿……每次小豆荚儿来,后鞧就觉得心里头舒坦,他看出来这何三老爷的老闺女会吃。给小豆荚儿炸完炸糕,满锅里都有特殊的香味儿,这香味儿漫着,一街都能闻着。小豆荚儿会吃,可她不胖,中溜儿的个儿,有腰有臀,她不裹脚,走道儿却也婀娜着。后鞧在给小豆荚儿炸炸糕的时候,总要讨教,何小姐,这馅儿都是啥做的。
小豆荚儿不温不火地说,你是炸糕匠,还不识得这馅儿吗。
小豆荚儿有时候也没鼻子带脸地训他,你是手艺人,但你也是二五眼的手艺人。你这黏米面筋道。炸的时候文火把握得相当,你的炸糕靠的是筋道和颜色,口味太差,就两种馅儿,除了糖馅儿就是椒盐儿,凭这手艺你也只能在香木镇混日子了,进了省城,你就是个要饭的。
后鞧也不生气,说,小姐是将我看扁了。我是京城人,省城是没去过,但我在京城可待了十几年。炸糕不是我们家族的手艺,我父亲当年在地安门后边的御膳楼做过御厨,大清改朝换代了,我们才变成了下人,炸糕是街头的手艺。开始我不是做炸糕的,我是做月饼的,当年我刻的
月饼模子上百套,我做出的月饼馅儿都是照着御膳楼的食谱做的。
小豆荚儿就睁大了眼睛。又慢慢地半眯缝着,说,我看着不像。
小豆荚儿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香木镇买炸糕,可是最近有几个月没来了,就让后鞧觉得有些心慌。后鞧姓赵,叫赵登科,来香木镇十几年,也有好人缘儿,一街铺子的掌柜都白吃过他的炸糕。当年赵登科来香木镇,背驼得很重,在道边上支起的大锅,他有点够不着,就踩着一只木墩儿,每天脸都被烤得通红。街上的人都可怜他。便张罗着给他娶一房媳妇,粉子家的女帮工陈妈给他提了个亲,是她们陈家堡子的人,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腰很直溜,但腿弯弯。后鞧没相中。说,我是有媳妇的,闯关东的时候过了热河,我这媳妇儿就走丢了,我估摸着她早晚能找到我。香木镇的哥们儿以为后鞧是在说大话,或者是不同意陈妈领来的老姑娘的托辞,就都一笑,不再管他了。不料几年以后,还真有一个富态的女人领着个八岁的儿子来找他。这时人们才信后鞧的话不是撒谎。这女人命不太好,和后鞧过了几年,就得病死了,给他扔下了儿子。这儿子像水葱儿似的蹭蹭地长,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比他爹高出一头。又几年,这小子和卖杂粮的吊眼梢子的儿子齐了肩。吊眼梢子的儿子伸手能摸到房檐瓦。
孩子大了,香木镇上的人家看好后鞧儿子的不少。这小子叫赵英俊,也确实是英俊的样子。但赵英俊不急着娶亲,在窦守德的私塾学堂读了几年书,便去江北的兰县读上了国立高中。
小豆荚儿来买炸糕,让后鞧动了心思。他觉得小豆荚儿要是嫁给了英俊,那是太般配了。儿子儿媳能把炸糕的铺面儿撑大,小豆荚儿做馅儿,他炸。给儿子拴一挂篷布大车,可以把炸糕拉到省城去卖,或者把这炸糕拉到兰县、三岔河的集市,到时候他后鞧的炸糕铺子可以请窦守德重新给起个店号……
小豆荚儿几个月没来。后鞧就觉得有些不舒坦。和他相邻的成衣铺掌柜粉子也问,这何三老爷的老闺女咋没来买炸糕呢?
后鞧叹一口气,咳,富人家,吃啥都有够。
粉子就凑到后鞧跟前说道,你知道小豆荚儿为啥几个月没来,她订亲了,男人是兰县的巡警队长,也是何家屯人。这巡警队长叫齐殿臣,外号叫齐麻子,他爹是跳大神的,原来挺穷,这齐殿臣当了巡警队长以后,全家都搬到兰县去了,住着深宅大院。齐队长的老婆死了一年多,这小豆荚儿是给他续弦……
后鞧有些气愤,这何三老爷真他妈不是人。这么好的姑娘嫁给了臭巡警,这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粉子说,开始齐队长还不同意呢。是何三老爷主动送上门的,说是还陪送了两石白米和三匹好马。
后鞧说,这何三老爷不他妈得好死。
眼见得又过了一个月,小豆荚儿突然又来了,这让后鞧感到很意外。这次小豆荚儿来香木镇不是买炸糕的,而是躲到了卖杂粮的吊眼梢子家。吊眼梢子的儿子叫陈学谦,也在兰县县城当巡警,是齐队长手下的小队长。可能和陈学谦是相好儿的。小豆荚儿进了杂粮店就没出来。吊眼梢子就找后鞧、粉子,还有香木镇的其他伙计,他要求梆子会开会。梆子会凡遇到大事儿,是随时都可以开会的,吊眼梢子心急,就自己敲梆子。梆子会的成员没在杂粮铺开会,都聚到了炸糕铺子后院的作坊里。梆子会的成员听见梆子声,从不耽搁,各自将铺面关了板儿,急着开会。
后鞧问,吊眼梢子,啥事儿这么火燎屁股?
吊眼梢子说,镇南何三老爷的老闺女给我家找了麻烦。她在兰县巡警队原本是要跟齐队长结婚的,她却相中了我们家学谦。这是不可能的。谁都可以得罪,怎么可以得罪巡警队的齐队长,小豆荚儿逃到我这儿来,要是让齐队长知道了,过了江就能把我抓去。
粉子问,你家学谦呢?
吊眼梢子说,学谦还在巡警队呢。学谦没相中小豆荚儿,是小豆荚儿硬要嫁给我们家学谦的。
后鞧说,这事儿好办。把小豆荚儿送回江北,或者把小豆荚儿送到何三老爷那儿。
吊眼梢子说,这样怕不行,小豆荚儿现在怀里揣着一把剪子,说谁要把她送回江北或者送回她娘家,她就把自个儿捅死。我现在都不敢碰她,她要是死了,齐队长和何三老爷都得把我当成歹人。
一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后鞧想了想,说道,把她送到我这儿来吧。你们家学谦没相中小豆荚儿,我们家英俊相中了。江北的巡警要是过来,你就说没看见小豆荚儿。
吊眼梢子说,小豆荚儿这孩子虎。逃出来的时候还跟齐队长说了,要逃到香木镇去。
后鞧说,那你就把事儿都推到我身上。
粉子就给他一脚,你就不怕齐队长剁了你的脑袋。
后鞧说,现在是民国了,他齐队长也不能滥杀无辜。
桦树皮说,后鞧这么仗义,那就得让他仗义一回。没啥事儿就散会吧,我还得赶制两个匣子,后天送到哈尔滨去。
吊眼梢子叹了一口气,说,后鞧大哥,那你就受委屈了。
吊眼梢子把小豆荚儿送到了后鞧的炸糕铺子,说让她在这儿躲些日子,比在他那儿强。
小豆荚儿被送到了炸糕铺子。后鞧就到桦树皮那儿朝他借一只藏假匣子。并叮嘱,一定要在匣子上留出几个孔儿来,人在里边躺着憋不死。
桦树皮就把他铺子里最大的一只藏假的匣子搬到了炸糕铺子。这藏假匣子被埋在了面穴子里,匣子的两个孔儿塞进去两节竹子通到穴子外面,小豆荚儿藏在里面,出气很匀。
香木镇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人们等着看兰县的齐队长来香木镇如何闹腾,同时也为后鞧捏着一把汗。
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有肘候也能发生。这齐队长竟然没来香木镇,陈学谦也没回来。每天很寂寞的窦守德过江北兰县打听事情的根梢儿,回来的时候就进了粉子的成衣铺,进屋就使劲儿拍着粉子,你说这后鞧的命咋这么好呢,白白地捡来了一个儿媳妇。
粉子就问,咋回事儿?
窦守德说,齐队长的新媳妇小豆荚儿跑了以后,齐队长就直接奔了何家屯,让何三老爷交人。何三老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媳妇儿给你送去了,你没看住是你的事儿。两个人就你一嘴我一嘴地吵了起来,后来又动起了手儿,齐队长用洋枪断了何三老爷的一条腿。何三老爷的家丁见齐队长断了何三老爷的腿,就点了洋炮轰了齐队长,齐队长的一只眼睛被崩瞎了……现在这事儿江北兰县那儿的百姓都知道。兰县县长把齐队长给撸了,现在吊眼梢子的儿子学谦当上了巡警队长。
粉子就说,那陈学谦不得管后鞧要人?
窦守德笑了,热闹就在这儿。
粉子说,看来又得开梆子会了。
后鞧知道了江北发生的事儿,就把小豆荚儿从藏假匣子里搀了出来。小豆荚儿也真是好体力,在藏假匣子里躺了九天九夜,出来的时候腿脚还很利索,一气儿吃了十几个炸糕,吃完了抿着嘴说,你这两种馅儿吃着真没味道。
后鞧怕得罪何三老爷,就对小豆荚儿说,事儿已经平息下来了,我是不是该把你送回家了。
小豆荚儿说,还没算平息。我还得在你这儿待上一段日子。
这天,吊眼梢子的儿子陈学谦回来了。到了晚上又走了。香木镇上的铺子都关了板儿,吊眼梢子就敲后鞧炸糕铺子的门,后鞧把门推开,让
吊眼梢子进来。吊眼梢子一进来就看见了小豆荚儿,小豆荚儿知道吊眼梢子来和她有关,就躲到后屋去了。
后鞧问,来接小豆荚儿去你家?
吊眼梢子说,大哥真是明白人。今天学谦回来了,我见了他面儿才知道,学谦和小豆荚儿真是恩爱。学谦让我把小豆荚儿接到我家,到年底的时候把他们的婚事儿办了。你救了小豆荚儿,咱也不能白让你救,学谦说了,要给你三百块大洋。
后鞧说,不少。
这时小豆荚儿出来了,说,现在我才看出来,你家学谦做人很刁猾,够坏的。女人要是嫁了他,也不会有啥好日子。你转告学谦,我不嫁给他了。要嫁,我就嫁登科大叔的儿子英俊。
吊眼梢子想了想,说,我跟你爹打了照面儿,他同意你和我家学谦结婚。
小豆荚儿说,我不能听他的。要是听他的,我都死好几回了。您如果能见到我爹,您就告诉他,我小豆荚儿怀里有一把剪子,只要他来找我,我就把我自个儿捅了。
吊眼梢子站起来,拍着屁股说,咱不娶了,咱不娶了!
小豆荚儿后来没有成为后鞧的儿媳。年底的时候,英俊从国立高中回来,刚过正月初五就走了。这回他走得很远,是去日本公费留学。
后鞧感到很惊喜,我儿子要是留了洋,那可是祖坟上冒了青气,留洋回来,那就是京城的人了。我可以回到阔别十多年的京城了。
小豆荚儿不嫁人,在后鞧的炸糕铺子里打短工,给后鞧的炸糕做馅儿。香木镇上的人说,这小豆荚儿啥时候能离开香木镇呢。
4.小坠子
剃头铺的莲花指叫张座山,一嘴的山东话,嘴还挺痨。香木镇的上百颗脑袋都归他管,大清没了以后,他一气儿剪掉了一百多根辫子,这是民国县长吴乾鹄下的旨,兰县凡是躲躲藏藏不削辫子的,都被县衙抓去,在兰县的城西修一天的路,然后过江到香木镇,让莲花指剪辫子。现在莲花指屋后的仓房里还装着几麻袋的大辫子。莲花指不光能剪掉辫子,还能剃出新式的头来,莲花指管这些新发式叫老毛子式(俄罗斯人的背头),东洋式(日本人的三七开分头),还有民国政府式(汪精卫的五五开分头)。莲花指剪头的家伙什儿齐全,他有一把英国产的推子,中指大拇指一使劲儿,头发就咔喳咔喳地往下掉,被推过的地方像毡子一样平。莲花指还有几把好梳子,有银梳子,牛角梳子,鱼骨梳子,玛瑙梳子,还有一把象牙梳子。据说这些梳子都是莲花指媳妇嫁给他时的陪嫁。莲花指原是在哈尔滨高加索大街学徒的,他的岳父就是他的师父,他岳父是个二窜子(混血儿),爹是俄罗斯人,娘是中国人。莲花指的岳父还有洋名字,叫谢尔盖。在哈尔滨高加索大街,一提起谢尔盖,都知道。他常去俄罗斯驻哈尔滨领事馆,给俄罗斯人剃头,有钱有势的人也找他剃头。后来谢尔盖惹了祸,给一日本人刮胡子,把日本人人中上的一抹胡子给刮掉了,日本人把人中胡子看得很重要,就把他的理发馆砸了。谢尔盖胆小,被日本人吓出了毛病,不出半年就死了。莲花指娶了谢尔盖的闺女,投奔了莲花指媳妇的舅舅,就去了香木镇。莲花指来香木镇的时间并不长,还不到十年。但他跟大伙儿厮混得比当地人还活泛,靠的是他嘴痨。
其实莲花指剃头,剃男发式并不是他的绝活儿,他修理女发有绝活儿。当年谢尔盖在哈尔滨发馆给人理发,也给女人修理发式,给女人修理发式不在于刀子和剪子,而在于手指头上的活儿。莲花指的手指头又细又长,在女人的头上抓几把,女人的头上就会膨起莲花,弯成麦穗儿,捋成荷叶……香木镇是一个闭塞的小镇,人都很土,尤其是女人,很少在大街上闲逛,莲花指的剃头铺就根本没有女人来修理头发。有一回,何三老爷的三太太领着表妹到他这儿修头,莲花指没敢伸手,让媳妇安娜给修的。安娜也会修女发,但她很少上铺子做活儿,她怕败了丈夫莲花指的手艺。
这年秋天,两乘轿子抬到了莲花指的剃头铺子门前。前边的轿子里下来两个又粗又壮的女人,腰间还别着大刀,后面的轿子里下来一位娇小的女人,和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妈子。老妈子搀着娇小的女人进了剃头铺子,见有一张闲椅子,就搬了过来,老妈子腰间还夹着一块雪白的羊绒垫子,铺在椅子上,让娇小的女人坐下。这时候莲花指正在给粉子的表弟剃秃瓢,刚剃到一半就停下了,知道这来者不是善茬子。
老妈子粗门儿大嗓地说道,剃头匠莲花指,我知道你,当年我丈夫的大辫子就是你给割下来的,又给他剃了洋人的头,我丈夫总夸你的手艺好……今儿个我给你带来一位贵客,她是江北护国军程司令的三姨太,是苏州美女。明儿个程司令过生日,三姨太得在前场应酬,你得给她好好地把头发修理修理。
老妈子又对两个带刀的女人说,你们到门口把守着,谁也不准进这剃头铺子,谁进砍谁脑袋。
老妈子又笑着对莲花指说,是三姨太的两个保镖。
粉子的表弟捂着半拉秃瓢吓得跑了。
莲花指吓得有些发抖,说,我……我不会做女发。
老妈子脸上的横肉一颤,说道,你会。这香木镇方圆百里,有我不知道的吗。你岳父叫谢尔盖,也是你师父,在哈尔滨常做女发,你要说不会,那你就别在香木镇待了,护国军三天就把你赶走。
三姨太站起来,对老妈子说,鞠妈,别粗门儿大嗓的,吓着人家师傅。又对莲花指说,师傅,我盼侍女没文化,有点粗俗,您担谅。今天请您为我做头,您就大胆地做,做好了我常上您这儿来,做不好我也不怪您。
莲花指这才有些放松,问道,小姐想做个什么发式?
三姨太就让鞠妈到轿子里搬来一只水牛皮烙花兜子,她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画片,递给莲花指,说道,这是美耕火柴的广告画,这女人是仿京都赛金花的发式画的。我看挺好。
莲花指看了看,笑了,是荷叶式。我能做。不过……
三姨太说,师傅请讲。
莲花指说,我就不给您做了,让我媳妇给您做。她的手艺得到过我师父的真传。
三姨太说,那就更好了。
莲花指就到里屋叫她媳妇。
莲花指的媳妇安娜也有点洋人血统,举止做派也不土,她一出来就客气地对三姨太说,小姐能从江北到我们这土地方来做头,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一定给小姐做好。
安娜开始给三姨太洗头,莲花指打下手儿,从一只檀木箱子里找出了一瓶法国产的洗头露,三姨太的头发被洗得又黑又亮,散发着香气。擦干了头发,三姨太就把那法国产的洗头露拿过来,看着,也叹着,真是好东西。
安娜给三姨太做头,做了两个多时辰。三姨太头上的荷叶层次分明,柔润光亮。鞠妈举着镜子让三姨太看,三姨太非常满意地说,我这头发一拾掇,就变得这么洋气。程司令看了,会非常满意。
三姨太起身要回江北,回头又看着那瓶法国产的洗头露。莲花指显得很木讷,安娜就给莲花指使了个颜色,莲花指就拿起了那半瓶子洗头露递给三姨太,小姐,您喜欢就拿去用吧。
三姨太掏出了二十块大洋给安娜,安娜故作推辞,最后还是收下了。这是莲花指的剃头铺子的最高收入,就是在哈尔滨,修理女发也只两块大洋,而这三姨太却如此大方。三姨太不光掏
了大洋。还对安娜说,你给我这法国洗头露,我是不能白要的,容我几天后打发人,也给你送件礼物来,到时候你可不能不收。
莲花指说,小姐太客气了。
两乘轿子慢悠悠地离开了香木镇。一街的香味几天不散。
果然,几天以后,三姨太派鞠妈和两个护国军。给安娜送来了一件裘皮大衣。安娜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
鞠妈也不粗门儿大嗓了,也变得很客气地说道,妹子,你得收下。如果你不收,我家女主人该骂我没用了。
莲花指就替安娜收下了这件裘皮大衣。
江北护国军司令的三姨太和莲花指的剃头铺子有了走动,这让香木镇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很眼红,都说莲花指撞了好运。
粉子说,依我看,莲花指撞上的并不一定是好运。
半个月以后,鞠妈又跟着两个女保镖来到了香木镇。鞠妈进了剃头铺子,就像到了亲戚家一样,见到莲花指就问,我的妹夫,妹妹干啥去了?
莲花指放下手中的活儿,说,在后院给我做晌午饭呢。
鞠妈说,做啥好吃的?
莲花指说,擀面条儿。我得意水捞面,酱牛肉和红皮辣椒打卤。
鞠妈说,我也得意这一口儿。
安娜见鞠妈来了,表面装着很高兴,其实她从心里挺烦这鞠妈的。但她还是让鞠妈和两个保镖在剃头铺子的后院吃了面条。吃完了一碗面条儿,鞠妈说,安娜妹子,你和我们家三姨太可是有缘分,这些日子她想你了,想让你过江北陪她待几天。
安娜说,难得三姨太这么瞧得起我,她可是司令的太太,而我只是个剃头匠的老婆,怎么能跟她拉近乎。我真是怕给三姨太丢脸面。
鞠妈小声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三姨太可不是那种娇贵的人。上次到你这儿来修发,你也看出来了,她做人比我温和。三姨太并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她父母是做香油生意的,一次失火,烧光了家产,父亲一股火儿就生了病,生了病就没好。她父亲死了以后,她妈领着她到哈尔滨投奔她的二姨,她二姨很刁蛮,容不下她们娘儿俩,就把她们撵了出去。那时候三姨太才十六岁,就和她妈在哈尔滨的老徐酒楼干活儿。老徐酒楼是山东人开的,江北的程司令是山东人,总上老徐酒楼摆宴席,他看好了三姨太,就把三姨太娶了。其实三姨太是个苦孩子,也没见过啥大世面,在江北的护国军兵营里,除了我这个女人跟她好以外,大太太和二太太一块儿欺负她。好在程司令护着她,去年把大太太打跑了。三太太很孤单,她也想跟外边有个来往,谁知一见到了你,她就觉得和你对上了脾气……
安娜说,这三姨太也是够可怜的,我是得看看她去。不过我得跟我当家的商量商量。
这时莲花指给人剃完了头,正回后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道,去吧去吧,三姨太这个人不错。再说护国军的程司令可是咱们这一带的大人物,也是保咱们一方平安的,能为程司令效劳,也是咱们香木镇人的荣幸。
下午,安娜就随鞠妈坐着轿子去了江北。
谁知道,三天以后,安娜哭丧着脸回来了,头发很乱,眼睛也红了。一进屋她就抱着莲花指的大腿哭了,当家的,谁知道我进了狼窝,好悬没被狼咬了。
莲花指把她扶起来问,咋的了?慢慢说。
安娜就哭着说,我去江北头一天,给三姨太做头发,我们姐儿俩很对脾气。晚上程司令招待我们吃饭,谁知在吃饭的时候,程司令摸我的大腿,说他就喜欢二毛子。晚上他就要睡我,是三姨太把我藏了起来。第二天,我要逃出来,可护国军的兵营把守严密,出不去。今天早晨,三姨太也抱着我哭,说,姐姐,我对不住你。不该让你到护国军的兵营里来,谁知道老程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你动了心思。她又对我说,老程是一个做事情必须要做到底的人,他要娶你,你要不从,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三姨太还劝我,回去和姐夫商量商量,不行就从了吧……当家的,你说我可咋办。
莲花指也感到很意外,说道,你都三十七八了,这程司令咋能看上你。
安娜说,程司令他跟我说,他四十七八,娶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可以直接晋升大太太。还说我长得年轻,面皮也白……
没等安娜说完,莲花指就给了安娜一嘴巴,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些!
安娜说,我知道我从了程司令是不可能的,就特意回来看看你。咱家的儿子在哈尔滨当药铺盼伙计,将来也能养活自己。这些年你积攒了一些钱,也够后半生用的了。我想看完了你。再去哈尔滨看看儿子,然后我就一头扎进松花江里……
莲花指说,孩儿他妈,咱没权没势。可也不能等着受辱。容我让梆子会的哥们儿们替我想想法儿。如果有法儿更好,没法儿咱们就把东西拾掇拾掇,离开香木镇,逃到关里去……说完,莲花指就到粉子家,拿起了梆子会的梆子,满大街地敲着。
这次梆子会在桦树皮的匣子铺里召开。这也是为了脸面,毕竟这年梆子会还没有商量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莲花指从头到尾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就听大家的意见。
后鞧说,要不就从了吧。就是从了你也不吃亏,可以管程司令要钱,有了钱,你可以再娶更年轻的女人。
吊眼梢子说,从了还有好处。你可以离开香木镇,把你的剃头铺子兑出去,朝程司令要个官儿当。要个团长旅长的,比江北县长吴乾鹄的官儿还大,还牛气。
桦树皮小声说,女人这东西,就像木匠的刨花子,割出一茬还有一茬。原来香木镇的铁匠洪老大说过,女人乃锐器,打磨者生硬,搁置者生锈。你媳妇当年不是也被窦先生睡过一回……
莲花指就急了眼,你放屁!说的是人话吗!
后鞧说,如果你是一条汉子,就过江北直接跟程司令见个面,和他说理。护国军是新政府的军队,他要欺男霸女,你就到京城去告他。
莲花指咬着牙说,就照着你后鞧说的办了。
第二天,莲花指把铺子关了,自个儿收拾收拾了头型,梳的是民国政府式,头上又抹了发蜡。他又到粉子的成衣铺里找了件中山装,又朝窦守德借了一管自来水笔,别在了上衣兜上,和媳妇安娜坐着马车去江北。原本莲花指是要自己去的,安娜却要和他一块儿去,如果程司令动武了,她就死在兵营里。
香木镇梆子会的人们盼着莲花指早点回来,更盼着他能带回好消息来。谁知道莲花指去了五天也没回来。
粉子说,完了,这莲花指肯定是让程司令断了脑袋。可惜了我那件中山装了,是东洋礼服呢做的。
第六天的时候,莲花指回来了,但他媳妇却没回来。他也领回来一个女人,人们见到这个女人都愣了,这个女人竟是程司令的三姨太!
莲花指没有感到悲伤,继续开他的剃头铺子。三姨太成了他的媳妇。莲花指已经知道了这三姨太的小名儿,叫小坠子,他在剃头铺里喊,小坠子,烧壶水!小坠子,该做午饭了!香木镇上的人都能听见。
后鞧有一天把莲花指拉到他的炸糕铺子,让他吃了两个炸糕,问他,程司令咋能用他的三姨太换你的糟糠呢。
莲花指摇摇头,说,我也整不明白。
5.嗅出大美不易
老狗是当地人,祖宗几代都在香木镇,香木镇的老人说,老狗的祖宗是香木镇最早圈地盖房子的人,没有老狗的祖宗,就没有香木镇。据
说有考证,在官书《清史稗抄》上有过记载:康熙二年,直隶人北迁徙,囤四方,乃直隶总督之兵变,官者逃亡,皇族旁支受康熙白眼者,分四屯。农耕者屯于墨尔根,种麦。兵者散于兴安岭,屯于山中,多为匪。读书者屯于晒网场(哈尔滨)。商者屯于卜奎(齐齐哈尔的又一别称),延寿(现延寿县)之香木镇。老狗的祖宗是直隶的坐堂医,家传拔毒化淤膏药。老狗姓叶赫,后来不知为啥就单姓了叶。老狗的父亲叫叶寿都,老狗叫叶延林。老叶家人都长着肥硕的蒜头鼻子,所以江南江北的人都管叶家的膏药叫大鼻子膏药。老狗的膏药铺是有名号的,叫回天大膏药。老狗的膏药确实神奇,啥病贴上都好,牙疼,烂眼边子,原本是不能用膏药的,但老狗就能用膏药把这杂症扳过来,牙疼往后背上贴膏药,烂眼边子往脚心上贴膏药,让人疑惑。江北有个老中医,也很有名,叫郭一鳞,他差人去买老狗家的膏药,叹道,乃是龙王爷的粪便,天外之物。叶家人熬膏药大都在后半夜,把窗户门都用棉褥子捂严,外边拴着一条狗给他看门户,这狗起码也有将近二十岁,香木镇如果有狗叫,就是从膏药铺传来的。膏药铺的狗不叫,别家的狗是不敢叫的。当地人有老话,吃谁像谁,养活谁像谁,仔细端详,膏药铺的这条老狗和叶延林长得很连像。有一年,看门护院的老狗死了,但老狗的名字没死,让叶延林顶替了。香木镇人叫叶延林老狗,叶延林一点儿都不生气,他觉得他也是老狗。狗的鼻子是最灵的,叶延林的鼻子不比死去的老狗的鼻子差。他给病家看病,先扶脉,然后就用鼻子嗅。老狗能嗅出阴虚火旺,干经湿热,肺络滞阻,这就是绝活儿。
老狗的膏药确实治病,但谁贴了老狗的膏药,得有忍受力。老狗的膏药贴到身上以后,先热后奇痒难忍,又后钻心疼。尤其是把膏药揭掉的时候,那更需要病家有忍力,老狗的膏药被撕掉的时候,膏药上准粘着一块黑肉,但被揭去黑肉的伤口有新肉芽,带血丝,老狗就用田七粉涂平,三天后病家就痊愈了。老狗的媳妇是个小个子,长得精瘦,外号叫顶针儿。别看顶针儿小,本事很大,膏药铺都由她打点,老狗只管熬膏药。顶针生了一对儿双胞胎儿子,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比爹妈高出半头。哥儿俩精明得很,他们不愿意守在香木镇,十六岁的时候就去了卜奎。在卜奎的正街上开了膏药铺,生意做得比他们父母的好。两个孩子生意做得好,除了他们的聪明,也是靠了他们的母亲顶针儿。顶针儿当初领着双胞胎儿子在卜奎闯荡一年,就赚了一个当街的铺子,顶针儿从香木镇到卜奎,又从卜奎到香木镇两下跑,一点儿不觉得疲惫。顶针儿能制服老狗,顶针儿比老狗矮一头,有一天香木镇的人看见顶针儿站在凳子上扇老狗的嘴巴,老狗不还手,还哈着腰使老婆的嘴巴打得更准。
这一天,顶针儿从卜奎风风火火地回来了,一进膏药铺就坐在了地上。老狗把她抱到炕上,问,咋的了?
顶针儿说,卜奎的膏药铺快要让人给挤兑黄了。从京都来了一个黄一帖,也是卖膏药的,他说他是朝廷御医的后代,他的膏药不是他熬制的,他是从京都买来的,到卜奎加价坑百姓。卜奎的百姓都很愚,还真认他的账。原本买卖上的事儿可以各显其能,但这黄掌柜糟践咱们叶家膏药,说咱们的膏药里掺了羊粪,分明是想一脚把我们踩死。当家的,我回来就是和你商量……
老狗说,商量啥,花钱上东山的槽子沟找梁大爷,一股绺子过去就平了他。
顶针儿说,这么做不行,卜奎有护国军,土匪不敢靠近他们。我有一个好办法,你看如何。
老狗说,啥办法。
顶针儿说,咱不用刀杀他,咱用权和势压他。护国军师长钮祜禄·阿克敦有个儿子,腿上总生疮,有名的中医都给他看过,都不见好。我想试试。
老狗说,这可试不得。治好了,咱们算是交下了师长,治坏了可是要杀头的。
顶针儿说,我看可以试试,治好了咱交下了师长,治不好也不能把人治死。我就想向你讨个底,咱这膏药到底有没有把握。你到卜奎师长那里,给他儿子用鼻子闻闻……
老狗说,这是大事儿,得让梆子会来定。
顶针儿就找梆子,交给老狗。在晌午人们正吃饭的时候,他把梆子敲响了。
按照梆子会的顺序,这次的梆子会在花蚂蚱的说书馆召开。花蚂蚱说的都是旧书,香木镇十里八村的人听得有些腻了,他就常过江北去说书。这几天嗓子干疼,就回来歇息,哪知刚回来,街上的梆子就响了,就要在他家开梆子会。花蚂蚱仁义,守规矩,放下碗筷就把摆着十几张桌子的说书馆打扫干净,等人们吃完了午饭,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就聚到了花蚂蚱的说书馆。花蚂蚱这才端起饭碗,坐在长凳子上跟大伙儿说话。听花蚂蚱的嗓子嘶哑,老狗说,把饭吃完,我好好给你闻闻,一会儿给你拿帖膏药贴上,保你三天后就能说书。
花蚂蚱笑了,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你这膏药。
一会儿人聚齐了,后鞧问老狗,人齐了,啥事儿,说吧。
老狗鼻子灵嘴笨,就叫老婆顶针儿来跟大伙儿说卜奎的事儿。顶针儿爆豆儿似的一口气把事儿说完了。
桦树皮说,这事儿看起来简单,定起来却难。护国军的师长比县长还大,怎能靠得近?再说,又怎能进得兵营?进得兵营师长又怎能信得过咱这民间的大膏药?
莲花指说,护国军当官儿的我领教了,也是长着一只鼻子两只眼睛,到澡堂子一泡,都是他妈一样的人。我看只有人的胆子大,才能干大事儿。你看我……
吊眼梢子说,人可以先不去,想法儿把膏药传进去。
顶针儿说,师长不信。街道上的土中医他都不放在眼里,他认准的是京都御医。但我能进去。给师长做饭的厨娘,他老妈生过蛇盘疮,就是用我们老叶家的膏药治好的。
粉子说,成了。你就把牌押在师长的厨娘身上吧,先给厨娘送点礼,送点啥呢?
后鞧说,我给她炸十块五仁馅儿的炸糕,再让粉子给厨娘做件杭缎子的大衫,装在桦树皮打的礼品匣子里,就齐了。
老狗就点头,行,真行。
花蚂蚱唱——
用银子搭桥
用金子挡道
我看你这官家哪里跑
顶针儿听了梆子会的意见,第二天就拎着礼品匣子去了卜奎。
香木镇梆子会的哥们儿们每次开完梆子会,都盼着梆子会研究出的结果,多少年来,梆子会哥们拿出的智谋,远远超过了三个臭皮匠,每一个人都有成就感。
老狗盼着老婆把卜奎的事情办得利落,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到西路口望着。十几天过去了,顶针儿没有消息。老狗有点坐不住了,就在这天把店关了,准备收拾收拾去卜奎。他没有跟梆子会的哥们儿们打招呼,因为他知道顶针儿处理事情稳妥,不会出什么差错,可能是在等时间,或者是在和那个兵营里的厨娘周旋。
谁知他刚要出门,就有一个人把他拦住了。这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绅士打扮。长袍马褂,戴一顶水牛皮礼帽,一手拎着皮匣子,一手拄着龙头杖,他见到老狗,便哈腰问道,请问大哥可是叶延林先生?
老狗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点着头,我是。你……
来人说道,鄙人黄乃勋,卜奎黄氏膏药铺的掌柜。今日登门造访。
老狗一怔,不知如何面对这个黄一帖。这时粉子路过,他就叫粉子过来,和黄一帖一块儿进了院子,却没请到屋里去坐。
老狗问道,黄先生来我这里有何贵干?我老婆在卜奎,有啥大事儿怎么不找她商量?
粉子听出了这话是说给他听的。让他知道来人就是黄一帖。老狗见黄一帖这龙杖的底部是锃亮的铁器,他怕这黄一帖和他动怒。粉子见院里有一把劈柴的大斧,就拎了过来,拄着,对老狗说,你让我来帮你劈柴,我一会儿就帮你劈。
黄一帖看着乱糟糟的院子,说道,叶先生生活寡淡,你这么有本事,竟然不露锋芒,真让鄙人佩服。
老狗不会客气,说道,你也别跟我绕弯子了,有啥话就跟我说。
黄一帖说道,我到你这儿来是想跟你说,我和你们是一场误会。我黄某人本事不大,也没有祖传的制膏药的秘笈,我只能算是一个商贩,把别人的膏药买到手,再转卖给他人,这种生意在我们老家叫作圈子生意。何谓圈子,五年就是一圈。到了六年,这圈儿就变成了扁的。你夫人误以为我会夺她的生意,就费了很大的周折,竟然还去找护国军的师长,这是劳民伤财的事儿,不能干。我见那天夫人拎了一个很贵重的匣子,就知道这礼不薄。我就去了你们在卜奎的膏药铺,把话跟你夫人和儿子全都说清楚了,可你夫人不信,还要让你的两个儿子打我。恕我直言,你夫人很蛮横,这是商人的大忌,不和气怎么能生财。我见和她说不清,就特地来拜访你……
老狗问。我不知道黄先生这个圈儿画了有多大了?
黄一帖说,就要封口了。仨月的时间。
老狗想了想,说,仨月的时间不长。你就画吧。
黄一帖说,我的圈子生意严守规矩。既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一天。我准备十月初六离开卜奎,不过,我到你这儿来,还有大事儿商量。
老狗说,咱香木镇人实在,有啥事儿你就说。
黄一帖说,我十月初六离开卜奎,十月初七准备到你这儿来。我要在你这儿买走六百帖膏药,重新到牡丹江一带画圈儿。在这五年里,你要满足我的膏药,我一手钱一手货。不过,你给我膏药的价格得让我能赚一半的利。
老狗说,那行。十月初七我把六百帖膏药给你备好。
黄一帖抱拳说道,叶先生,那就告辞了。走了两步又回身,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没办,就把皮匣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匣子来,说道,这是九帖膏药,是关里关外九家膏药铺里的膏药。这些膏药我在后面都写上了字,从2一直写到10,因为我还没有见到过疗效数第一的膏药。我希望你的膏药能写上1字。
说完,就把这九帖膏药送给了老狗。
黄一帖走了,走了几步远,又被老狗叫住了,黄先生,吃完午饭再走吧。
粉子也说,咱这香木镇的炸糕好吃的很哩。
黄一帖回头,说道,等我下次来再吃吧。
几天以后,老狗的老婆顶针儿回来了,又是哭丧着脸。老狗问她,还有仨月就等不了了?是不是那黄一帖耍了咱们?
顶针说,钮祜禄师长开始不信咱的膏药,是他的厨娘帮着引荐了咱大儿子大双,大双看了师长儿子腿上的毒疮,认定是能治好的。几天的工夫,真就治好了。
老狗说,这是好事儿啊。
顶针儿说,好事儿也变成了坏事儿。他把大双二双都拉到护国军里去了,让他们两个当军医。大双同意了,二双不同意,昨天二双从兵营里逃了。至今下落不明。这就惹怒了钮祜禄师长,说如果抓回二双,就砍他的脑袋。
老狗说。这二双也真不知好歹。在钮祜禄师长手下当差,等着的是高官厚禄……你这当娘的也没好好说教说教。
顶针儿说,二双打小儿就是一个犟种,我咋能说得了他。
老狗一声长叹,任他去吧。
老狗的老婆从卜奎回到了香木镇,她一下子变得有些呆傻了,整天惦记两个儿子。
转眼间就过了仨月。黄一帖是守信用的人,十月初七准时来香木镇老狗那里取膏药。老狗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兵营,一个下落不明,老狗的心思也就不在膏药铺里了,黄一帖这天来取膏药,他把这个茬儿给忘了。黄一帖没怪罪他,就问,叶先生有何难处,我黄某人肯定能帮你。
老狗不作声,顶针儿在炕上哇哇地哭。哭完了就骂黄一帖,你这晦气的东西,让我们老叶家今年倒了霉。
黄一帖也不怒,笑着说,大嫂,我知道你们两口子为啥闹心,我来了,你就不用闹心了。你二儿子没走远,他在牡丹江呢,这孩子看人准,从兵营里逃出来,就投奔我去了。听说钮祜禄师长明年开春儿换防,到时候我就把他给你们送回来。你大儿子听说在兵营里混得不错,他既是钮枯禄师长的军医,又是侍卫官,这小子将来能有出息。
顶针儿瞪了黄一帖一眼,不说话。
老狗说,黄先生是个贵人。你在我这儿待。一天,我连夜把膏药给你熬成……这膏药钱你就不用付了。
黄一帖说,钱是要给的。如果能在香木镇待一天,可是一件好事儿。松花江沿岸好东西都集中在香木镇,好人也都在香木镇,我得见识见识。
黄一帖就出了膏药铺,在街上闲散地逛着。
老狗让顶针儿准备饭菜,顶针儿在炕上不动窝儿,老狗就给了她一嘴巴,我爹活着的时候说过,泱泱人世,美丑难辨,嗅出大美不易。怕的是把丑当美,把美当丑。人啊!
6.水浒人物武三郎
花蚂蚱有许多名儿,不知道哪个名儿是准的。粉子听说花蚂蚱叫边鸿宇,自称湖畔先生。后鞧听说花蚂蚱叫边鸿贵,艺名稗草先生。花蚂蚱的名字跟他说书的内容没个准儿,可以任意添加。花蚂蚱一辈子只讲两部书,一部《封神榜》,一部《水浒传》。《水浒传》对天下人来说都不陌生。连香木镇的孩子都知道《水浒传》里有一百单八将,他在说书时竟然添加了一将,这一将叫武三郎,就是硬给武松加了个弟弟。这弟弟叫武柳,不会蒸炊饼也不会打虎,却能勾女人。花蚂蚱在说书的时候,说道——
话说这武柳一出世,裆里夹着硕大的玩意儿,不哭不闹,也不看他的爹妈,却直勾勾地看着接生婆。这接生婆叫潘银花,是潘金莲的表妹,十八岁就能接生。这武柳看见潘银花,竟然哈哈大笑,把一屋子的人都吓跑了。武柳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一脚能把武大踹到沟里去。他打不过武二郎,却也有损招儿,用手抠二哥的胳肢窝,二哥怕这一招儿,吓得直跑。武柳还去潘银花那里,偷看潘银花洗澡,让潘银花拽进屋里,灌了两口洗澡水。武柳的父母见武柳从小就拈花惹草,怕给武家将来招惹麻烦,便把他送人了。武柳来到这家,不想爹不想娘,也不想哥哥,在这人家待得舒坦,整天蹦蹦跳跳,因为他的养母是孙二娘。孙二娘惯着这个武柳,武柳越出去拈花惹草她越高兴。话说大宋皇帝徽宗到泰安府微服私访,带了两个妃子,一天,忽然一个妃子失踪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天分解。
花蚂蚱在讲这段书的时候,在不足一丈宽窄的说书台子上能做出各种动作,引得台下的说书人都乐得前仰后合。
花蚂蚱嗓子疼,从江北回来了,贴了老狗的膏药,三天也不见效,又自己煎润喉方:胖大海三钱,金银花各三钱,山菊花两钱,覆盆子、菟丝子各三钱。喝了几剂,仍不见效。花蚂蚱的人缘儿很
好,香木镇的哥们儿只要他在家,就都来看他,不听他说书,听他讲话,也能让他听得上瘾。这天,粉子来他的说书馆看他,给他出了一方,红菇娘儿三枚,冰片一钱,龟板一钱,水煎服。花蚂蚱就笑了,这是滋阴润喉方,对我已经不见效了。
粉子就劝他,够吃够喝就算了,在香木镇就是不干活儿,这些老哥们儿也不会眼见你饿着冻着。
花蚂蚱就拉着粉子的手说,粉子兄弟,在香木镇,咱们都是好哥们儿,但要说最对脾气的,还得数你粉子……这次大哥嗓子疼,不是累的,是在青岗县惹了麻烦,大哥一股火儿,前几天嗓子都说不出话了,这才回咱这香木镇来躲躲。
粉子问,啥麻烦,让梆子会的人给你出点子,还有平不了的事儿?
花蚂蚱说,青冈县的县长是个祸害女人的县长。青岗县长看见俊俏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他都划拉。但这小子说他坏,还能说出他的好处来。凡是跟他睡过的女人,都不白睡。小媳妇儿的男人都在他手下当差,大姑娘被他睡的,都给上好的杭州绢子,有时候还给她们首饰。这小子才华横溢,口才也好,长得也英俊。大高个儿,白面皮儿,一头乌发三七开,是洋学生的发式,穿的衣服你都没看过,是东洋的礼服呢剪的中山装,缝的双线,纽扣儿是紫玛瑙的。他还戴着一块怀表,是洋玩意儿,报时的时候怀表里就有蛐蛐儿叫。这县长也是真招女人喜欢……
粉子说,这是好事儿啊,咱们江北要是出这么个县长,那江北的兰县也就出了名儿了。
花蚂蚱说,其实我也不烦这县长,我刚到青岗的时候,还见他在县衙门口向庶民百姓训话。他的话非常中听,他说,青岗乃北疆之福地,陆路水路畅通,可招各路商人在此集贸,吾子民焉能缺吃少穿。然吾子民缺的是民国之文明,吾福地理应多出秀才……青岗县县衙对外来的商人从不挤兑,收的课税也少。我是打算在那里待下去的,谁知说了一天书,就闯了大祸……我讲的是《水浒传》,讲到武柳时,听书的都哈哈大笑,原来此地的县长便叫武柳。第二天,我就被县衙抓去了,被县警事局的人打得鼻孔蹿血。县长武柳没出面,副县长见的我,问,你为何如此侮辱我们县长?你得说清楚,是哪个小媳妇儿的丈夫唆使你这么干的?我说,我讲《水浒》已经讲了半辈子,这武柳是我爷爷那辈儿就添加的,县长受辱,不是我的故意,也没人唆使我。我被关进大牢,有个狱警听过我说书,很敬重我,就让我逃了。我能躲得了今天,可躲不了明天。粉子,你说我能不上火吗。
粉子说,这事儿可不小。大哥,敲梆子吧。
花蚂蚱无力敲梆子,粉子就替他敲。晚上掌灯的时候,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就聚到了后鞧的炸糕作坊里。
花蚂蚱把他在青岗县惹的祸从根到梢地说了一遍,然后听大家出主意。
吊眼梢子说,既然武县长穿戴那么讲究,又说出了大民国的文明,那一定是个开明的县长,搞破鞋那还能算事儿吗。要是在大清国,这么英俊有才华的县长,娶他十个八个的都应该。
桦树皮说,吊眼梢子,你把话说歪了。不是让你夸这县长的好,而是让你给花蚂蚱出点子。
吊眼梢子说,这点子就算我出了。花蚂蚱,你不该逃,也不该回来躲,这一逃一躲反倒让这武县长认为你心里有鬼。你该跟他见上一面。
后鞧说,人看外表是看不出什么的,别看他武县长长得英俊,说不准就是个衣冠禽兽,咬人不露齿的狗。最好的办法是找人帮你说说话。
花蚂蚱问,找谁?
后鞧说,江北护国军的程司令。连省长都惧他三分,跟武县长说句话,那还不是高看了他武县长。让莲花指出面。
莲花指说,自从安娜嫁给程司令以后,我一直也没去护国军那里。这小子如果要见着我,可能要剁我的脑袋。花蚂蚱大哥,你得体谅我,我不能帮你这个忙。
桦树皮说,那就让粉子家的陈妈出面吧。陈妈的儿子郑俭良是东北军的团长,他跟护国军的关系也能不错。
粉子说,我看就别麻烦陈妈了。陈妈年岁大了,不宜走动。她儿子郑俭良在奉天,坐车还得一天多……
后鞧说,依我看,这事儿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就凭你花蚂蚱的口才,还不能跟武县长对话?
花蚂蚱就站起来,我听后鞧的。明天我就回去,我要亲自见见这个武县长,大不了我这几斤重的脑袋落地。我都六十岁的人了,还怕啥生死。我这次没白回来,你们的主意好,就看我的运气了。
……
花蚂蚱又去青岗了。这一去就是半年。快过年的时候,花蚂蚱回来了,他的嗓子不再嘶哑了,脸色红润,好像比以前胖了。他的衣服也换了,一身紫色的长袍马褂,头上还带了顶鹿皮礼帽。
花蚂蚱一回香木镇,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就问他,你因祸得福了?说说,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儿?
花蚂蚱说,晚上诸位兄弟到我的说书馆,我给大家说段书,就不用给你们说事情的原委了。
晚上,大伙儿吃完了饭,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就聚到了花蚂蚱的说书馆。花蚂蚱雇了两个乡下大嫂,把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长条桌子上摆了许多盘子,盘子里有瓜子儿,还有纸包的洋糖球儿。说书馆的一角生了炉子,炉子里放了能散发出香味的香槐木炭,炭火上烧着葫芦形的大铜茶壶。凡是进说书馆听书的人,今天一律免费,白吃糖,白嗑瓜子儿,白喝茶水。见人满了,花蚂蚱就开始说书——
话说这武家有三个儿子,各怀绝技。大儿子武大会蒸炊饼。二儿子武松棍棒耍得灵活,十五岁时就在北山打死了两条狼。三儿子武柳可是个人物,这孩子一出生,竟看见一只鸭子在门口走,就呀呀地哭,但脸上没有痛苦,细听原是一首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武柳七岁进了私塾学堂,十六岁时乡试进了秀才,原本是要进京殿试的,孰知他没去,他说,大清黄龙残喘,小民红面朝天。原来武柳已经看破红尘,知道民国才是吾庶民百姓的天日。武三郎胸怀大志;三次进京,深得大总统袁世凯的赏识,见一面便赐县令,来到了边疆。武柳为民造福,乃是吉星高照,容我一唱——
武县长身高八尺君王相
又有一副慈善心肠
百姓疾苦看得清
与人为善德无疆
……
武县长不媚朝官不在乎痛痒
有人说他见了女人眼睛发亮
其实是对县长大人的诽谤
叫一声武大人
民国蒸蒸日上
你定能步步高升步入高官殿堂
……
这原本是一段枯燥无味韵演唱,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听了却哈哈大笑。为啥笑,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心里清楚。
花蚂蚱是好兴致,唱了大半宿,见人慢慢地散了,而梆子会的哥们儿们却没有走。后鞧说,蚂蚱大哥,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们来段原来的武三郎吧。
花蚂蚱摇摇头,说,后鞧兄弟,时间也太长了,哥都忘了。
后半夜的时候,人都散了,花蚂蚱吃了两块后鞧的五仁炸糕,就躺下了。要睡没睡的时候,忽然梆子响了。花蚂蚱就坐起来,自言自语,香木镇又发生了啥事儿了?
责任编辑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