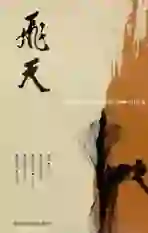《红线》与《聂隐娘传》比较研究
2009-03-15王森林
《红线》与《聂隐娘传》都是唐传奇名篇,讲述的都是神奇女侠的传奇故事。《红线》讲的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侍女红线,明音律,善阮咸,通经史。当薛嵩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吞并潞州的野心忧闷不堪时,红线主动请缨为薛嵩解忧。她当天夜初装束前去魏州,半夜而返,盗回田承嗣金盒。又叫薛嵩派人快马送回魏州,并附书信一封,以示恐吓。田承嗣一见,果然惊慌失措,立即送礼求情示弱。不久,红线辞别薛嵩,归隐山林,不知所踪。《聂隐娘传》也是晚唐作家的作品,作者是裴■,讲述的是魏博大将之女聂隐娘十岁为一尼姑看中窃去,教给她剑术,专取恶人首级。五年后还家,自择夫婿嫁之。元和年间,魏博节度使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睦,让她暗杀刘,隐娘因佩服刘公神明,弃暗投明,反为刘昌裔击毙了魏博派来的刺客精精儿,接着又用计避开了魏博刺客妙手空空儿的搏击。后亦不知所踪。
这两篇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为迅速平定安史之乱,唐王朝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分封安史旧部,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这就是河北三镇。另一降将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三镇中田承嗣势力最大,也最为跋扈,是唐代藩镇中第一个表现出半独立野心的人。
然而,薛嵩对朝廷的态度,与田承嗣有天壤之别。降唐后,“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他所镇守的相、卫,正隔在河北三镇与朝廷所控制的宣武镇之间,起着屏障汴州和东都的作用。而田承嗣要扩充实力,第一个目标就是相卫镇。《聂隐娘传》中和刘昌裔发生矛盾纠葛的是田承嗣之子田季安,史称田季安极为残暴,恶名远播。田氏盘踞魏博四十九年不入朝廷,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而据韩愈《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将军刘公墓志铭》记载,刘昌裔在召还京师的途中发病,左右劝其休息,他说:“吾恐不得生谢天子。”对朝廷相当恭敬和忠心。在一些生活小节上,刘昌裔也相当的谨慎和节制。韩愈《刘公墓志铭》云:“公少好学问。始为儿时,重迟不戏,恒若有思念计画”;“公不好音声,不大为居宅,于诸帅中独然。”
明白了以上事实,就可以知道当时薛嵩和田承嗣、刘昌裔和田季安之间的矛盾斗争就不仅仅是藩镇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维护国家一统与分裂割据之间的斗争。因此,对双方当事人的态度就有了是非之分,就有了区别人格高下的标准。
《红线》和《聂隐娘传》就是把人物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叙述的。这就框定了一个非是即非的故事发展走向,结果自然是故事的主人公红线和聂隐娘都是站在正义的方面来和魏博节度使斗争,并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这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态度,也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愿望。这是两篇传奇一致的地方。
但仅仅具有同一的故事框架并不表示叙事线索的一致。红线是薛嵩的家生婢,和薛嵩是主奴关系,奴才对主子的忠心是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违此即属不义。红线帮助薛嵩制服田承嗣,首先是奴报主的行为。红线的出发点是减主忧,这是符合封建社会主忧臣辱,主危臣死的伦理道德的,是义的体现。但这种义行只有在其主子的行为是正当的时候才具有超越的意义。
聂隐娘与红线不同。聂隐娘是魏博大将的女儿。魏帅又常赐以金帛,并让她做随从左右的军吏,可谓宠任有加。但她由于“服刘公之神明”,转而投奔刘公。这似乎有违于“不既信,不倍(背)言”的侠义道精神。其实并非如此,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聂隐娘既不与魏帅同是非,自也不会与他相与信。这就是所谓的“立气齐”。就这一点来说,聂隐娘的“背叛”和红线的“报恩”具有同等的光辉。
《红线》的作者给故事的叙述设置了一个正义的空间,红线在其中只要不违背这个设定,她的一切行为就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而聂隐娘的作者给她设定的是一个非正义的空间,这就决定作者的故事叙述过程就是聂隐娘不断突破既定设置空间的过程:作者让聂隐娘出生在魏博大将聂锋的家中,如果按这个设定去发展,就可能是和红线完全相反的命运。所以作者先叙述了她的第一次突破:在她十岁的时候,一个尼姑把她偷走带到山中,教她各种神奇的武功;然后把她带到都市,向她指出一些人的恶行,让她刺杀这些人。有一次,聂隐娘在刺杀一个罪恶深重的大官时,由于这个大官正和他的儿子在一起嬉闹,聂隐娘不忍下手,所以回来较迟,遭到了尼姑的叱责:“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
在这次突破中,聂隐娘懂得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和判断,也明白了面对罪恶目标时应该怎么做, “断其所爱”的真实含义不仅仅是杀掉目标所爱,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不能以小仁而宽大恶。
聂隐娘艺成后归家,得到魏帅的喜爱重用,这是聂隐娘向既定设置的回归。表面看这是倒退,实际上却是作者叙事技巧的高度艺术化。一般读者往往忽略这个情节,于是就看不到前后事件的紧密关系。聂隐娘离家时年仅十岁,不会懂得人间的是非曲直和处置应对。学艺五年,尼姑不仅教会了她高超的武功,更教会了她为人为侠的准则。作者有意安排她在魏帅身边,是让她近距离的看清魏帅的真实面目,不露声色的为她对既定设置的最后突破安排好关榫。
《红线》的作者没有把这个女侠的高超武功哪里来的做任何交代。据红线自述,她的前生本是男子,游学江湖间,学神龙药书,只因用错了药,死了三人,阴功得诛,才被降为女子。似乎她的绝世神奇是前生带来的。由于没有制定人物性格转变的叙事策略,人物性格就显得缺少发展。
小说中对武功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但很注意根据故事的情节而采取不同的叙述视角。同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在《红线》中,由于盗取田承嗣金盒是红线独自一人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作者采取了让红线亲口叙述的方式,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聂隐娘传》使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因为隐娘和刺客的搏斗是在刘昌裔的眼前完成的,有他人的参与。全知和限知视角的不同,不仅切合两人当时的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小说意境的创造。
《红线》的作者追求的是诗的意境,他努力使小说充满诗的优美,空灵,具有诗性特征。本来是危险丛生,让人魂魄俱惊的盗盒行动,在作者的笔下却是诗意盎然的探险旅行,在带给读者多姿的审美想象和空阔的审美空间的同时,会产生强烈的审美共鸣。
对武技剑术和格斗场面的描写,极富传奇性,这已突破了《红线》等作品的重在写意,而具有了极强的写实效果。这标志着唐人豪侠小说渐趋成熟。
人们往往把中唐的社会现实和小说的创作背景联系起来,游国恩说:“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蓄养刺客以牵制和威慑对方,而神仙方术之盛,又赋予了这些剑侠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民,也希望有这样一些人来仗义除奸。”但却非本文讨论的内容了。
【参考文献】
[1]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王森林,黄淮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