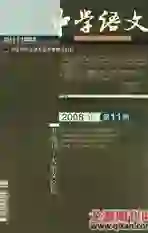一条幸福不归路
2008-12-18卢文锋朱秋清
卢文锋 朱秋清
【摘要】鲁迅小说《药》里有一条“灰白的路”,它“愈走愈分明”,是“一条大道”,“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庾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这一条路,对小说里的华老栓和革命者夏瑜来说,是一条幸福的但又是一条没有归宿的路。
【关键词】药 幸福 革命者 人民群众
小说关于“路”的第一次描写,是在华老栓准备去买药的时候。小说写“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由于是在晚上,路的颜色“只有”“灰白”一种颜色,显得单调,加上“阴沉沉的”“一无所有”,这就渲染了一种孤寂、阴森的氛围。而一般来说,一有动静,狗就会叫,而这时革命者夏瑜将要被杀,应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是很轰动的事,可那“几只狗”竟“一只也没有叫”,“街上(路)”也是“黑沉沉的一无所有”,连狗都不叫了,何况于人。可见,当时杀人(对革命者的镇压)是何等平常的事,平常到连狗都习以为常了。人们对革命者的被杀没有任何的反应,暗示出当时人对革命者的被杀是冷漠的,对革命是不了解的;同时又暗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残酷,革命者的死对人(狗)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是无谓的死,是无谓的牺牲。华老栓希望能用蘸有革命者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在他脚下的“路(街上)”是“一无所有”,暗示了他想用人血馒头治好他儿子的病的希望(靠走这条路)必然破灭。可华老栓却“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跨步格外高远”“路”在他脚下“也愈走愈分明”,他明明知道馒头上蘸的是夏瑜(革命者)的鲜血,但他却深信这样的“药”(这条路)能治好他儿子的病,为能得到这种神奇的“药”而深感“爽快”,却不管杀的是谁(革命者),可见他的愚昧和落后。
“路”的第二次描写是在华老栓买了“药”之后。“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大道”(路)呢?“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的家里,收获许多幸福。”显然,华老栓对这“药”很重视,得到后很高兴,极其兴奋、自信,充满幸福感。他从“药”上看到了希望,这对他及他全家来说,是一条能治好病的幸福之道。有意思的是,小说是把这条“大道(路)”与后面的“古口亭口”对照着写的。这“古口亭口”可念作“古某亭口”。“口”,是文章里表示缺文的记号,作者是有意这样写的。浙江绍兴城内的古轩亭口有一牌楼,匾上题有“古轩亭口”四个字,清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于1907年在这里就义。《药》里夏瑜这个人物,一般认为是作者以秋瑾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经历为素材而创造出来的。革命者被杀的地方,在华老栓来说,却是一条通往他家中的幸福“大道”。很显然,这里一边描写着愚昧群众的“幸福”,一边暗示着革命者的悲哀;一边描写着革命者的被杀,一边暗示着革命脱离群众。
第三次关于“路”的描写是在后来华大妈上坟之时,“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庾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很显然,这路自然成了两边的分界线。左边埋的是死刑的人,夏瑜则是被当局判了死刑的人,当然也是埋在左边的人了。更重要的,这“路”也是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分界线。夏瑜生前所从事的革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拥护,即使死后,也不能与一般的群众归为一类,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有一条鸿沟,这鸿沟就是群众对革命的不理解,以致于革命者死后都不能被自己解救的对象所理解、所容纳。确实,直至后来无论是华大妈还是夏奶奶,都没有理解夏瑜。因此,对夏瑜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来说,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所走的“路”,从以解救民众,结束黑暗社会为目的的角度讲,他们为这个奋斗牺牲,是幸福的,是“幸福者”(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注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们所走的这样一条“路”是不通的,是一条没有归宿的“路”,因此,他们又是“哀痛者”(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小说里的这条“路”,一边是愚昧落后,一边是单枪匹马的奋斗。“路”的两边,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种方向、两种不同的人,是平行地前进着的。要想融合交叉,革命就必须发动群众,“疗救”“愚弱的国民”(鲁迅《〈呐喊〉自序》,彻底进行新的革命,也是真正革命的必走之路,这就是小说《药》的深刻含义。
这条“路”,对华老栓和夏瑜来说,都是一条幸福的不归路,乃至于对所有如华老栓一样的愚昧落后的人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条“幸福”的不归“路”。“路”在小说里的描写,看是闲笔,实是不闲。它体现人物性格,蕴含主题。
★作者简介:卢文锋,广西贺州昭平中学教师;朱秋清,广西贺州昭平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