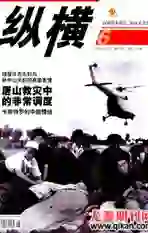两代人的回忆
2008-09-02阎阳生
恢复高考二十多年后,在“八八”会议故址,两代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伟人已去,音容犹在。小平那句“……二十年见大效”的预言恍若昨日,那个在高考作文中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婴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
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以他独特的眼光,一锤定音恢复了停滞11年的高考。570万满怀惊喜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形成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进京赶考”。
二十多年后,依旧在北京饭店那间中式会客厅里,当年参会的学界泰斗吴文俊、王大珩、王守武、黄秉维、叶笃正,教育部负责人李琦、何东昌又聚在一起,彼此已是鬓发银白。当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把我和人大教授周效正、央视高级记者钟里满作为当年的考生代表介绍给他们时,吴老看着这些虽学有所成,但也年过半百的后进无限感慨:当年小平同志就在这里提了—个希望,希望从恢复高考起,“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二十年见大效”。转眼就是二十多年了,小平的话恍若昨日。
王老问起我当年那篇被民间传为“不称职的父亲”的状元作文,我告诉他,那个在作文中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婴儿”也已经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这又是新一代人了。我告诉女儿,你们的高考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我们的高考就是由在座的前辈和小平同志一起央策的。我们到这里,首先就是要表达我们这些老三届的感激之情”。
二十多年前的1977年8月,33位专家也是从四面八方,从劳动的牛棚,从尘封的实验室,从拦羊的荒坡,从停滞的大学来到北京饭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找到的33位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没有一位社会科学家。虽然大家并不知道会议的主题,但都预感到—个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到来。
如今这其中的六位专家、教授和两位部长故地重逢,与当年参加高考的受益者一起围坐在这间古旧的客厅里回忆往事,小平同志那句“我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今天来听听大家意见”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当邓小平一锤定音“今年就恢复高考”时。我正在污水井取水样,觉得我们这些年过三十的老三届只是一个陪衬……
李琦回忆,在太原招生会议上仍延续“文革”中“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老办法。邓小平在无奈中也划了圈。现在要让第一线的教授专家来推动一下这些保守的各级领导干部。刘西尧部长也说,报告今天已经送上去了。查全性急着说,今年还来得及:第一,今年还没有正式招生,第二报告也未送到。耽误一年就是十几万青年的问题。邓小平问刘西尧还来得及追回来吗?刘西尧说还来得及,但高考就要推迟了。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追回来”。随着他“即使推迟半年,也要改,今年就要恢复高考!”的一锤定音,全场响起第一次热烈的掌声。王大珩说,小平同志的果断,那个时候我们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而这时,我正用捡来的废砖头和防震棚旧木料,在租住的农民房旁为怀孕的妻子搭厨房,并不指望有什么不同的梦……
由于在部队那次的经历,对于只有靠走后门推荐上大学早就绝望了。我在部队时既是笔杆子又是军事尖子,能把大号手榴弹扔到60米开外。虽然我父亲被关押审查,但首长惜才尚武,只是让我下炊事班做饭。1973年夏天,突然调我到高考复习班,真是喜从天降。但去了以后才知道是给—个领导的后代补课改作文,那种失落可想而知。其实当时发生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考试成绩不算数了,出身和门路是首要条件。
从部队复员后,我到环保所当了个化验工,每天怀里揣着两个馒头夹桃酥,四处抽取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每天下班都用自行车“顺”几块砖头回来。有时我爱人也挺着个大肚子捡几块回来,谁会想到她曾是个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啊,为跟我到北京才对调到地铁当工人。我们在贫民区终于把厨房的四墙垒起来,坐在中间看着天上的星星算着孩子的出生日期,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所以当1977年秋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觉得我们这些30岁的老三届只不过是个陪衬,考分要比常人高出一大节。要知道那是11年的考生堆积在一起、竞争残酷的高考,录取比例是57:1!没有教材,以前的书抄家时早没了。碰巧有个同学盛家驷收藏了包括旧考卷的各种课本,我和宋柏林是连看书带蹭饭。后来他成了著名收藏家。
但当我填写志愿表选择报考学校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考上了以后怎么办?清华大学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她曾是那样近在咫尺。尽管妻子全力支持我,但孩子冬天即将在这小屋中出生。我每天得搬运蜂窝煤劈柴生火,大杂院里的水龙头冻了,我得到对面工地去提水。京郊著名的八大学院来回也要两个小时的路程,但我要保证这小屋水缸是满的,火炉是热的,奶瓶是温的……我拿出圆规,选择半径最小的学校,三个志愿都写了建工学院。它离这里骑车用不了10分钟,我们这个小家是圆心。
邓小平真的发了脾气。断然划掉招生的“出身”条款,从根本上动摇了极“左”的传统根基。高考作文前夜,老鼠在床下冻得乱窜,我却格外清醒……
尽管小平在“八八”会议敲定当年恢复高考,但是事情一进入极“左”的思维定式和传统的审议程序,便又一次进入胶着状态。李琦回忆,面对拖了40天议而不决的招生会议,邓小平发了脾气。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找来教育部的负责人,批评他们办事太慢,政审条件太繁琐,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不敢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将来要摔跟头的!”并亲自在1977年招生方案中删除了政审中唯成分论的“出身”条款,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为,“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看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当时就包括薄一波等受冲击的老干部的孩子得以冲破非议参加高考。这使干百万考生实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几乎每年高考,人们都要提起那篇引起轰动的作文。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前几门数理化考题太容易了,根本拉不开分数以填补年龄差距,成败都在这最后一门的作文上。那天夜里,隔着贴在斑驳窗棱上的旧片基,大杂院里已飘下最初的雪花。我没有时间点燃炉火,生产的妻子被送回柳州娘家。我压上了全家的棉被,任凭饥饿的老鼠在床下乱窜。寒冷却使幻觉格外清晰起来:身后慈爱的母亲,眼前宽容的妻子、脑海中女儿的第一声啼哭……
第二天的作文题目颇具时代特色:《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看着考卷心里非常矛盾,写一篇“抓纲治国”的应景文章并不难,但大家都会写,分数根本拉不开。但发出内心郁积了10年的感受,在当时尚未解冻的政治气候下必定凶多吉少。这时我耳边响起了女儿出生时的哭声,它仿佛是一声命运的呼唤,我终于写下了第一句叹息,“再也没有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然后笔就再也没有停
下来。
北京电视台《真实档案》帮我找到了1977年12月11日当晚的日记:
下午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从产房女儿写到实验室,报考大学,又回到病房,这平凡的学习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回青春的战斗吗?
估计如果碰上有想象力的老师,可以拿下85分以上,如果碰上教条的中学教师,可能只有60分了。这门考得有点冒险。
……我完全信服上帝的公平了,我等待和服从他的裁判。
后来事情竟戏剧般的相似!那篇作文还没最后判定就被传出,就以《不称职的父亲》的题目在民间广为传抄,听说当时对是得最高分还是最低分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后代无法理解,一篇作文怎么能传抄成了社会的焦点。一个美女作家在网上说,阎阳生在那个年代振聋发聩的作文,在今天看来实在不算什么。网络上任何一篇点击5次以下的作文,抖出的料都要比他精彩。
面对动辄点击率上百万的美女作家,我常常毛骨悚然:一片眼球翻动的海洋。但我也知足,时隔30年,还有人点击我。不知再过30年,还会有人记起那篇古董吗?鲁豫说:会的,因为它折射了那个时代。
高考并没有使我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它在一代人的心中鲜明地印上了两个前所未有的词汇:“公平”和“竞争”,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现在人们有一种说法,好像当时考上大学的老三届都自然地成了党政高官。而我从建工学院毕业后,人生并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一度还被分配单位拒之门外。最终仍是去取污水搞化验,只是头衔从工人变为助工,工资由40.5元升为56元。
但是我们渴望的不正是公平的竞争吗?况且10年一届的状元头衔也并不是御赐,而是来自民间,正如他们在传抄时给它的昵称“不称职的父亲”。如果那时被戴上一顶乌纱,我就不会横心出国留学,并由此走遍陌生的世界;也不会毅然辞职下海,感受市场大潮的初起。
对于高考的关注成为我难以舍弃的一个学术课题。我把登在《人民论坛》的论文《我国高考史上的两次重大变革》向“八八”会议的前辈汇报。当570万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时,他们心中的旗帜上鲜明地印着两个前所未有的词汇:“公平”和“竞争”。这是“八八”会议留给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遗产。
在会下,和当时清华大学的领导何东昌的交谈对我有特殊的意义。1966年,我18岁,继两年前我考上当时北京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后,又在第二年被选入清华预科。预科班的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前途一片光明。我的理想是工程物理系,地点是遥远的西北戈壁核基地,目标是美帝苏修。当时何东昌不仅是抓试点的大学领导,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但青春的活力使我依然觉得太漫长,我和几个密友决定跳级提前参加高考。但第二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突然转向。当宣布暂停高考时,我们竟有一种压力骤然释放的解放感!
当我们意识到运动的荒唐时已经太晚了,接着毛主席一挥手,一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被送往农村。父亲被关押后,我揣着一封信投奔三十八军。取消高考造成了10年的文化荒漠,我们遭遇到人生的第二次饥荒:继“三年灾害”中对食物饥饿后,“文革”中对知识的饥渴。
我告诉何老,当时没敢报考清华大学的一个原因是内心对清华的负罪感。我后来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也是一种自我反思。令我十分感动的是,何校长和所有到会的“八八”会议的学者一一在我的文章上签名,成为我珍贵的纪念。这次会见也成为中央电视台文献纪录片《千秋基业》的重要内容。
1977年,我和弟弟从一南一北分别考上大学,80年代又分别考上德、法留学生。当我们在欧洲相遇时,回想起小平同志当年恢复高考的政治眼光和果敢决断,不禁感慨万千。
责任编辑王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