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政治”
2008-05-14黄艾禾韩永何忠洲
黄艾禾 韩 永 何忠洲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当我们面对同一条江的时候,能否站在整个流域系统的高度,还来认识水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从1949年到2005年的55年间,用水结构发生了变化。在2005年全国的总用水量中,农业仍是用水大户,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但工业用水从1949年的占总量2.3%增到22.8%;城镇生活用水从由原来占总量的0.6%,变成8.4%。
也就是说,从前,水主要用来发展农业,而现在,工业和城镇居民用水在急剧增加。
从1980年到2006年,湖南省的用水总量从277.1亿立方米增加到327.7亿立方米,这一增长看起来并不显著,但据湖南省水利厅教授级高工聂芳容透露的信息,增长主要集中在省内几个大型城市。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同一条江时,用水的主体是分为城镇居民用水、农业、工业、生态环境和航运等各方面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一条中,对这些主体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序表述:“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需要”。
面对同一条江
在四川省,人们在开始讨论,把水都用在农业上,值不值?成都市水务局高级工程师陈渭忠告诉记者,在四川,原本有很多冬水田(靠天下雨,筑埂留水),但后来都被改成两季的水稻田。水稻田的大面积扩张,使得袁隆平的水稻优种技术得到充分展示。但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水稻都是以耗水为前提的。
在反对者看来,水稻的大量发展,固然有利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上升,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的政绩,但却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消耗。“更何况现在种粮基本上没什么钱可挣。”陈渭忠说。
在湖南,专家也提到这样一个数字:该省的农业用水的途中损耗率高达50%。
而“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反对毗河引水工程的《官方规划》的理由之一,就是该规划把农业灌溉置于首位,而把城镇供水置于“综合利用”的次要地位,显然不符合《水法》的精神。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对四川的各级水电站也颇有微词。他们说,水电站们在搞一场“圈水运动”,是在用公共河流资源来为小圈子、部门的少部分人牟利。比如柏条河上的水电站,这个一度是国人瞩目的争执焦点。反对者们指责说:层层级级的水库、水电站,不仅未能起到积极的蓄水排洪的作用,相反在利益的诱使下,更多的偏向于把水更多用于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地区和行业。
记者了解到,每当冬天的枯水季节,各级水库都倾向于蓄水发电,因为到了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是用电的高峰。而这时,其他方面如工业、生态环境和航运,也都急需用水。
比如在湖南,当去年11月10日,湘江长沙段的水位跌破历史最低水位时,湘江上游的东江水库接到下泻命令,以阻止长沙段水位滑向灾难性的25米以下。因为如果水位降到25米以下,大量的污染物将难以得到有效的稀释,水质可能受到的破坏难以想象。与东江水库一起充当救命角色的还有江垭水库。
但东江水库在库水无私下泻,缓解下游引水困难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隐忧。湖南省防指办副主任肖坤桃分析,按照当时的下泻流量,东江水库还保证可以一两个月,但如果过度下泻,水位降得太低会影响自己的正常发电,尤其是春节前后正值用电高峰,如果电力不足将会带来更多的不便。
有消息说,湖南省在去年的大旱中,因缺水,企业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产能未能释放出来。但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又造成江河大量污染,使得本来就紧张的水更加不够用。仅湖南省水利厅公布的检测数据就显示,在大部分年份,湘江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河长达不到三类水质。
四川的长年监测也表明:岷江中游大部分河段为五类及劣五类水质,沱江干流大部分河段为四类至五类水质。成都市内“二江”锦江和沙河基本为劣五类水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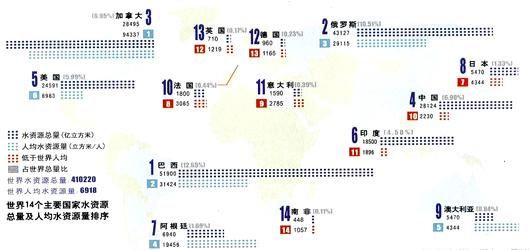
“水的问题,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说到底它是政治问题”
夏军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在前几年承担过一个海河流域的“生态修复的水资源保障规划”。这个规划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先进的理念:生态承载。
夏军说:“一条河,它的沿途各个地方都要用水的,这里其实是水与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发展,其承载力要有一个度。比如说,它有污染,这样有一个水环境的承载力问题;土地有限要种粮食,有土地承载力的问题。人的生活要用水,工厂的排污、经济发展要水,种种相关的因素,加在一起应该是一个综合系统。这样,一个流域应该有一个综合承载力。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承载力,对不起,你这个工厂不能建。不能去用这个水。一条河流的开发要有一个度。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开发和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夏军介绍说,他们正在淮河流域做这种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在海河流域,这个研究至少几年前就开始了。过去水资源只是计算水量,现在就要考虑,还有污染,算不算水量?要把和水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水与气候,水与生态,水与社会,水与经济。从前人们做水资源方面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做:土地部门做一个土地的承载力规划;环保部门做纳污能力的规划,水电部门做水资源承载力规划,等等。但是,水的问题不是靠一个个分隔的部门能够管理好的。“单个的计划是没有用的”,所以,夏军他们做的水资源规划,从一开始,就要考虑一个全盘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综合模型。這在国外已经非常通行。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副局长杨永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从另一个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是缺乏统一调度。长江流域实行的是流域机构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体制,大的工程基本上都是电站,它们多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很少从面上来考虑问题,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是:上游有那么多水利工程,如果统一调度,还会出现下游这么干枯的状况?
“现在的问题是,各个方面都在谈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人站在整个流域系统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这就是体制上的问题。所以水的问题,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说到底它是政治问题。”夏军说。
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昌明是从人与自然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如果1998年的洪水发生在远古时候,那还叫水灾吗?那时,今天的灾区根本没人住啊。现在,你把太湖也围起来了,要种地,那对不起,洪水就没地方去了。所以说到底,就是人水的和谐关系问题。要辩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