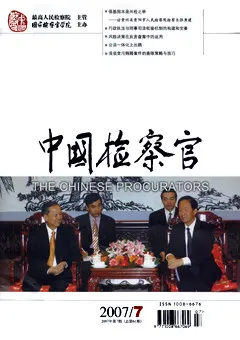论损失最小化原则在司法中的应用
2007-12-29朱全景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07年7期
内容摘要:损失最小化原则是司法效率的一项重要原则。传统的法经济学理论缺乏对损失最小化原则的探讨和研究。理论研究上的缺乏和空白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损失最小化原则的忽视和某些领域中的司法实践的被动局面。改变这些被动局面必须重视损失最小化原则在司法中的应用。
关键词:损失最小化 收益最大化 司法 效率
追求司法效率已成为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共识。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对于司法效率的追求通常集中于司法收益最大化,而司法效率的另外一个视角———司法损失最小化却没有被理论所认识。理论认识的缺乏又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司法损失最小化作用的忽视和某些领域中的司法实践的被动局面。
一、收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古典经济学的开山巨著《国富论》,书中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假设,提出了斯密定理,即在经济运行中,许许多多经济主体独立的追求收益最大化能够天然地促进经济的繁荣,使经济达到最优,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经历二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斯密定理在数学上得到完美的证明,经济学形成了新古典的理论体系。以研究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以收益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即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厂商追求生产利润的最大化。所以,没有收益最大化的前提假设,就不会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理论体系。在美国,“一大批法律经济学学者已经进入了从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法律经济学早已从纯学术研究进入了司法实践。”[1]根据成本收益方法,司法效率主义者认为,“第一,经济思考总是在司法裁决的决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不太明确甚至是鲜为人知;第二,法院和立法机关更明确地运用经济理论会使法律制度得到改善。”[2]至此,收益最大化成了司法效率的基本原则。
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工具的司法效率主义者忽视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益最大化原则,只是符合“积极的经济学”或“‘正的’的经济学”[3]。对于业已发生的灾害,这种“积极的经济学”或“‘正’的经济学”不能充分地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研究灾害的“消极的经济学”或“‘副’的经济学”必须建立在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损失最小化是指在业已发生灾害的前提假设下,人总是追求自身损失的最小化。虽然“消极与积极,负与正两者之间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收益和损失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损失可以视作负的收益,损失最小化也可以视作收益最大化延续,“但是负与正、积极与消极的界限,破坏与建设之间的界限毕竟不容混淆,”[4]损失最小化原则标志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发生了转变。收益最大化在实际上主要意指人们对于积极事情的预期和面对积极事情的行为选择。而损失最小化意味着如何最大的减少无可挽回、不可避免的负面事件造成的破坏和损害,如何在损害发生之后努力去改变现状,使损害的程度降到最低。如果在损害发生之后,还一味的坚持收益最大化原则,期许损害不发生前的状态,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在损害面前更加被动,只有坚持损失最小化原则才能主动应对从而把业已发生损失降到最低。在司法领域,损失最小化原则意味着损害司法效率的事件发生后,司法行为选择不应该再机械地坚持收益最大化,而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损害,扭转损害造成的被动局面。
二、赖昌星遣返一案中体现的司法损失最小化原则
1999年8月福建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携家人逃至加拿大。2000年3月,赖昌星旅游签证到期,加拿大发出有条件离境令。11月23日,加拿大移民部以非法移民罪将赖昌星夫妇拘捕。2002年6月21日,加拿大难民事务委员会裁判法庭驳回赖昌星及其家人的难民资格申请。2004年2月3日、2005年4月14日加拿大联邦法院、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先后驳回了赖昌星“难民申请”的上诉。2005年9月,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赖昌星寻求政治庇护的上诉。
赖昌星出逃加拿大后,中国大陆一直在争取将赖昌星从加方遣返回国进行审判。但引渡或遣返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死刑不引渡”原则。按照这条规则当被请求国有理由认为被引渡或遣返人在引渡或遣返后可能被判处死刑时,可以拒绝引渡的请求。加拿大是废除死刑并且实行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国家,即使遣返的其它条件具备,如果被遣返分子可能会判处死刑,也会导致遣返的搁置和失败。而“远华”案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00亿美元,涉案非主犯有的尚被判处死刑,作为主犯的赖昌星根据中国的法律极有可能判处死刑。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承诺,对遣返归来的赖昌星不判处死刑。随之,引发了国内对于赖昌星遣返问题的争论。质疑和反对的观点主要加集中在法学家所指出的“死刑犯不引渡的条款会不会成为外逃贪官的‘免死金牌’,对惩治贪官不利,并且极有可能导致‘同罪不同刑’的问题。”[5]
从司法效率的角度来看,质疑和反对的观点还是坚持收益最大化的观点。根据罪行法定原则,适用国内的《刑法》和其它法律对赖昌星进行刑罚判决,从而对犯罪分子达到最大的威摄力。但是,在赖昌星出逃已经发生,加方坚持死刑不引渡的前提下,收益最大化的司法效率原则不能再主导司法实践。同没有出逃相比,赖昌星的出逃已经对中国司法效率造成挑战和损失。此种情形之下,中国司法实践的主导原则应该实现从收益最大化到损失最小化的转变,力争将赖昌星出逃对中国司法效率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正是从司法损失的最小化原则出发,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与不作承诺,放弃遣返相比较,我们作出承诺以争取实现遣返,这是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6]再坚持司法收益最大化原则不仅毫无现实意义,而且还会因赖昌星得不到任何刑罚而加剧犯罪分子的出逃。虽然对死刑不引渡的承诺有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出现“同罪不同刑”,“但如果引渡无法实现,就会使外逃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根本得不到任何惩处,也就更谈不上司法公正。”所以,承诺死刑不引渡“这方面的意义远大于对某个人判处的具体刑罚”,“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做法。”[7]
三、司法损失最小化原则在司法中的应用
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掀起第二次废除死刑浪潮,由此引致的死刑变革问题在各国《刑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相联系,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国际司法合作领域开始得到确立。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英国1967年逃犯法》、1981年《瑞士联邦国际刑事协助法》、1982年《联邦德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都贯彻了死刑不引渡原则。2002年12月18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没有明确坚持这一原则,在某些条款,尤其是中国作为请求国的条款中“中国〈引渡法〉还是十分有限地、间接地接受了死刑不引渡原则。”[8]但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在经济犯罪领域还保留大量死刑罪名,当中国做为引渡请求国时,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对不量死刑做出承诺,无疑会跟国内的《刑法》和其它法律在实际上相抵触,损害罪行法定和司法主权。这又使得中国在死刑不引渡问题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不承诺不判处死刑,外国就不会引渡过来;如果承诺不判处死刑,又与我国的《刑法》规定不相符合。”[9]从而在实际上使绝大多数的遣返或引渡不能实现。
在中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贪污贿赂分子外逃逐年增多,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国外。截至到2004年,我国资本外逃已达700多亿美元[10],其中贪污贿赂分子外逃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犯罪分子在国外肆无忌惮地挥霍携逃的国有资产,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挑战国家的司法主权和尊严。开展国际司法合作,断绝贪污贿赂分子的出逃之路,成为中国司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在引渡问题变司法收益最大化原则为司法损失最小原则,从而打破引渡问题的困境,承诺“死刑不引渡”。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在引渡问题上坚持司法损失的最小化承诺“死刑不引渡”是国际的通例。在世界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最强大的美国是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但其在引渡问题上也必须坚持死刑不引渡原则。与泰国签订的《美泰引渡条约》明确规定“如果根据请求国的法律请求引渡所依据的犯罪可以判处死刑,而根据被请求国的法律此种犯罪不判处死刑,被请求国主管机关可以拒绝引渡。”[11]坚持损失最小化原则,承诺死刑不引渡,看似使司法效率遭受损失,但同不引渡相比却能使司法损失降到最小,维护司法的尊严。在我国已经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