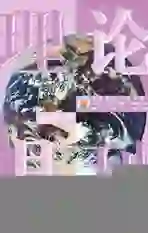论党内和谐的“六有”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2007-12-20张扣林
张扣林
摘要:十七大报告指出:“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经。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党内民主是增进党内和谐的根本路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那样,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在党内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局面”。
关键词:党内民主; 党内和谐; 民主集中制; “四个服从”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11-0012-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经。这一科学论断,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党内民主与党内和谐、人民民主与社会和谐等关系进行了科学的阐释,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增进党内和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发展党内民主是增进党内和谐的根本路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在党内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局面”。
一、 “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在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地方(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之间的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是权力授受关系。党内这种权力授受关系的状况反映着党内和谐的程度,因此,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一方面必须坚持“四个服从”的原则,努力在党内形成“有集中”的和谐局面,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努力在党内形成“有民主”的和谐局面。
1. “有集中”。无产阶级政党不是松散的联盟,不是许多党员数字的简单总和,也不是各个地方组织的联合会,而是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运作机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有机体。这种运作机制,就是民主集中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时候,就把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作为同盟和国际的组织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的历史上,列宁首先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党的建设中,后又推广运用于共产国际各国党的建设中,并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会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结成工人阶级大军。”[1]“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所以特别强调“集中”对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是因为,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只有坚持党内集中,才能解决党内权力结构问题,即党组织的分层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划分问题。在党的组织结构中,党的组织分层、分级和设置大致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党中央对地方(基层)党组织具有领导关系,地方(基层)党组织对党中央处于服从地位。党的组织结构只有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直线垂直(纵向)关系,而在各地方组织之间或各基层组织之间并没有横向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由一个中心层层向外辐射的网络结构。党中央与地方(基层)党组织具有不同的权力。中央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处于最高层次,地方次之,基层再次之。各地方组织之间或各基层组织之间要发生组织关系,必须上行到领导他们的上级组织,再从上而下下达指令,才能发生关系,其它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中央之上或与之平行的权力。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只有坚持党内集中的原则,才能规范党中央与地方(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做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才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领导体制,维护中央的权威即列宁所说的“权力威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所以特别强调“集中”对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还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组成的统一体。它不仅必须有自己统一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章程,藉以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还需要在组织上一致,而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是党成为统一整体的物质保证。正如列宁所讲,只有经过组织,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只有坚持党内集中,才能建立起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完整组织系统,形成党“组织的物质统一”。
2. “有民主”。代议制是现代民主的基本特征。自从代议制产生以来,选举一直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和实行代议制的途径。对国家民主来说是这样,对党内民主来说也是如此。正如列宁所讲,“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3]党员是党的主人,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党员。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怎样才能获得权力,或党员是怎样把自己民主权利转化为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力呢?这就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的方式,党员将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力委托给自己信任的代表或党的各级组织。或党员通过党内民主选举的方式,把自己的民主权利转化为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力。恩格斯在总结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同盟历史的时候就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4]列宁指出:“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就在于“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5]党员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各地方(基层)组织,党的各地方(基层)组织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中央组织。无论是党的中央组织还是地方组织或基层组织,都是党员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如果离开了党内民主选举,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权力,不仅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会失去代表性和合法性。因此,党内民主选举是党的各级组织得以产生和拥有相应权力的深厚基础,也是党的各级组织产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如果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那么可以说,体现选举人意志的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的生命。体现选举人意志的选举是党内民主的基础,也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标志。尽管目前党内选举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存在着许多不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只有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深化改革和不断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使党内选举充分反映党员的意志,如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完善选举程序等,才能使党的各级组织赢得党员和群众的合法性认同,才能不断地拓展党的生存空间。十六大以来,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通过党员直接选举的试点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建设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作为党领导下有序进行的体现党内民主的选举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机制,实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和群众公认原则的结合,切实保障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有利于防止腐败,有利于实现领导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结合,有利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激发党员干部和广大党员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积极性。这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总结党内选举试点改革的经验,明确提出“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求“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这就明确肯定非党员群众具有参与推荐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的权利。
二、 “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特征及其实现途径
党是一个全体成员在信仰一致基础上组成的自愿联合体,但信仰一致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存在矛盾。如在组织关系上,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之间的矛盾、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的矛盾。在工作问题上,存在着党委领导成员之间以及普通党员之间的矛盾;在思想问题上,存在着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观念方面的矛盾等。由于这些矛盾处理的状况反映着党内和谐的程度,因此,在党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完善并严格遵守党的各项制度,努力在党内形成“有纪律”的和谐局面,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各项民主权利, 努力在党内形成“有自由”的和谐局面。
1. “有纪律”。“有纪律”是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有序化的根本保证。由于民主是承认和保证一定范围内所有人的参与权和决定权,所以民主的实现过程必须依循人们所共同约定的规矩,使民主制度化、程序化。任何个人的意志都必须服从制度和程序的约束,使这种制度和程序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把民主引入党内生活中,创建了党内民主制度。马克思强调只有把党内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个人的意志服从党内制度的权威,才能克服党内生活中的人治现象,实现党内生活的正常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制度建党”的思想,标志着我党治党模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换。人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治党需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还是法的作用,而在于人的地位与法的地位的高低。在党内生活中,如果人高于法,权大于法,法屈从于个人的权威之下,这是人治在党内生活中的表现。如果法高于人,法大于权,人服从于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得到确认,这是法治在党内生活中的表现。总之,区分人治和法治,就是看法律在党内生活中能不能至上,凡是法律至上的就是法治,否则就是人治。这里所讲的“人”不是泛指,而是专指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借用托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就是“在专制制度下,国王就是法律,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就是国王”。要实现党內生活正常化,必须依靠法治,依靠党的制度。这不仅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而且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不仅如此,“有纪律”还是实现党内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毫无疑问,在党内存在着多层次和多种类的矛盾,如在组织关系上,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之间的矛盾、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的矛盾;如在工作问题上,存在着党委领导成员之间以及普通党员之间的矛盾;又如在思想问题上,存在着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观念方面的矛盾等。如果这些矛盾处理得不好,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精力就会在无穷无尽的内部纠纷中消耗殆尽,党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这些矛盾处理得不好,党就无法实现在思想政治,组织行动上团结统一。那么,怎样才能调节党内各种关系,实现党内生活的正常化、秩序化呢?只有依靠党的纪律,特别是依靠以“四个服从”为主要内容的组织纪律。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7]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结成工人阶级大军。”[8]邓小平说:“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9]“四个服从”,是调整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关系,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关系,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关系的根本准则。如果离开或丢弃“四个服从”这一党的根本组织纪律,党不仅会变成四分五裂,而且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很难设想,一个松散的没有纪律的不定型的团体能够维持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具有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他建立了一个有严明纪律的政党。而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从分裂走向毁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放弃党的组织纪律。
2. “有自由”。在党内生活中,纪律和自由是党内民主的两个相反相成方面。纪律是对全体党员而言的,自由是对党员个体而言的。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特别遵守党内“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并不是对党员个人自由的否认,相反,是党员个人自由的保障。“有自由”是党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人的一切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基于人的主体地位产生的。在党内,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自己当家作主。党员的主体地位不仅是党员的一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源泉,而且是党的活力的源泉。那么,怎样才能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呢?最根本的是发展党内民主,让党员真正成为党的主人,自己当家作主。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的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10]人的积极性都源于人们利益的满足。人们的利益可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没有前者,后者是虚幻的;没有后者,前者是平庸的。因此,精神利益的满足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党内民主,虽然不能给党员直接的物质利益,但是它为党员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所提供的自由空间却直接满足了人们的精神利益的要求。在党组织的自由空间中,党员可以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获得人格独立和精神平等的精神抚慰,从而树立“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意识。“有自由”是党员民主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仅仅是一种权利,即“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党内自由就是可以做法纪没有禁止的任何事情。党章不仅规定党员享有八项民主权利,而且规定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都不得侵犯,充分表明党员行使民主权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有纪律保障的。江泽民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思想。他说,“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从改革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等。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氛围。“党员主体地位”这一重大概念的提出,为努力促进党内“有自由”和谐局面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 “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特征及其实现途径
在党内决策过程中,党内存在着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由于多数人与少数人关系的状况反映着党内和谐的程度,因此,在党内决策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坚持“尊重多数”的原则,努力在党内形成“有统一意志”的和谐局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保护少数”的原则,努力在党内形成“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和谐局面。
1. “有统一意志”。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对党内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列宁曾指出,整个党组织按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重要标志,就是“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立党组织的策略方针。”“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11]党章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我们说党员对党内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不是说人人决定党内事务的“满堂言”,更不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决定党的事务的“个人专断”,“一言堂”,而且。因此,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既是党内民主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内民主的根本要求。正如列宁所讲:“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12]在党内决策过程中,只有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党内多数人的意志确认为党的意志,才能使党内生活具“有统一意志”,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或“个人专断”。虽然民主并非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政治活动的机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做出的决定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发表意见和实际讨论后决策的结果容易接近真理,即使出现了错误也能得到比较及时的纠正。在党内,党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有时出现相反的意见,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行动上每个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则就违反了党的纪律。因为,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已包含着少数人的意志向多数人作出让步,因此,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基础上作出的决定,并且上升为党的统一意志(制度和纪律)之后,少数人必须遵守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只有这样,党才能保持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那种只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的做法,是错误的。
2. “有个人心情舒畅”。在党内决策过程中,如果多数人决定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多数人无权作出决定并去实现这些决定,那么,党内就无法让多数人“心情舒畅”。同样,如果少数人陈述和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他们的正当利益可以随意受到侵害,那么,党内就无法让少数人“心情舒畅”。如果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甚至全党,那么,党内必然是死气沉沉,充满压抑,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活力。因此,在党内决策过程中能否实现“有个人心情舒畅”局面,是检验党内是否和谐的标尺。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党内决策过程中“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呢?这就是在贯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时,不仅要“尊重多数”,更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少数”。西方一位政治学家说过,民主不能保证最好的,只能防止最坏的。在党内决策过程中,“尊重多数”体现按照大多数人意见办事,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民主价值,但“尊重多数”决不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更不是剥夺少数人参与党内决策的民主权利,相反,要求“尊重和保护少数”。这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今天只是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还因为,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多数人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客观真理,而真理有时恰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怎样才能“尊重和保护少数”呢?我们认为必须做到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对某个事项作出决定之前,应当使少数人同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该认真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尽可能地吸取这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对不同意见采取一种“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虚心、审慎、妥协、兼容的态度;其二,对该事项经过充分讨论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正式决定之后,多数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不能歧视少数,更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另外,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就对公共问题作出决定而言。至于与公共无关也对公共无妨的个人私事,应该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不能将多数人的观点强加给少数人。只有这样,才能让少数人也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党内主人的地位,调动少数人参与党内民主决策的积极性,在党内形成“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
参考文献:
[1][8]列宁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0、526.
[2]列宁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312.
[3]列宁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0.
[5]列宁集(第1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49.
[6][9]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27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529.
[11]列宁集(第1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1-192.
[12]列宁集(第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
责任编辑 张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