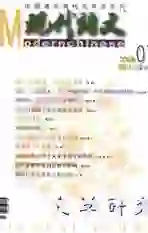简论《在一个地铁车站》的意象并置手法
2006-05-20崔玉香
英美意象派创始人、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又译《地铁车站》或《巴黎某地铁车站上》)是一首只有短短两行的现代诗歌,但它不仅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赞誉和阅读认同,而且历经近一个世纪岁月风尘的磨洗至今仍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迷人的光彩。这首诗纯以意象并置的手法营造了一个开放性的意义空间,给人们以解读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并且在人们的阅读中不断实现其意义的“增殖”,这无疑也是一首具有经典品格的诗。
大凡论及英美意象主义,都少不了提到《在一个地铁车站》,庞德本人也曾以此诗的创作为例来说明“单一意象的诗”,可见他对这首诗是颇为得意的。这首诗不仅被视为他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成了意象派的旗帜性作品。
意象派所提倡的“意象”(image),是指运用想象、幻想、比喻等手法构成各种具体可感的鲜明的形象,并将自己的情感渗透其中,暗示给读者。庞德曾为之下过一个定义:“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它有内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内层是“意”,即诗人主体理性与感情的复合,特别强调情感的表现;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的“呈现”,对于“象”,庞德提倡要精确描写。其实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立象尽意”,即准确地呈现物象并在物象中寄寓作者的主观情感的创作原则是颇为相近的。
在表现手法上,《在一个地铁车站》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类诗歌颇为相似,这就是直接采用意象的并置与意象的叠加手法含蓄地表达思想情感。中国古典诗词为避免主客关系过分明确,经常省略连接词及明确语法关系的介词,甚至在诗句中不用或少用动词,仅靠名词的排列组合就营造出一种含蓄幽远、情景交融的境界来。这样的诗歌在古典诗歌中并不少见,如我们所熟知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诗的前三句就是完全采用名词并列的方式,即我们所说的意象的直接并置,营造出一种孤独、凄凉和忧伤的氛围,有力地烘托了下文“断肠人在天涯”这一点题之句。此外,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仅用了三个意象,就传达出行为主体与情人别后的孤独、落寞与伤感的意绪。因为在古诗中,“杨柳”是表达“分别”的特定意象;“月”这一意象表团圆,而“残月”则是不能团聚的象征。在这里,“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意象,既是客观的描写,也是主观情绪的表达。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也是仅靠了两个有内在“比兴”关系的意象,就巧妙地实现了情与境谐,使读者从鲜明的意象中品味出人至晚景的凄凉、萧索和伤感的内在意蕴。
再如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贺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均是以最简约的语言方式将创作主体的“意中之象”清晰、鲜明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同时,又含蓄地传达了主体者深沉的情感。
当然,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的并置不仅仅是指名词的单纯罗列。首先,它要求语言的高度凝炼、简约;其次,作者所选取的意象也必须具体、鲜明,同时又与创作主体所寄寓的情感和谐一致;再次,并置的意象之间或者直接有“比兴”关系,或者是意象与隐逸在文本之外的诗人的形象、情感之间暗含“比兴”关系。这样才能做到虚实相生、言近旨远,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收到情景交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功效。
庞德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的爱好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丰富、简约含蓄极为推崇,他还曾译介和仿作过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在翻译过程中,他发现汉字这种表意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意象,并且意象之间联系词的省略即意象的直接并置,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他把这种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地铁车站》就是运用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并置的方法创作的一首诗歌。全诗只有短短两行,十四个单词: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ed)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整首诗仅有两个意象——“面孔”和“花瓣”,但一个意象就是一个色彩鲜明的画面,有着强烈的视觉效果。虽没有任何有助于逻辑推理的关联词以及明确语法关系的介词,但并置的意象之间却产生了奇妙的比兴效果,使读者能够自然而然地将“面孔”与“花瓣”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和想象。
这首诗中,庞德准确描述了自己在巴黎地铁车站时瞬间的印象。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幽暗的地铁车站内来往的人群不断闪现的“面孔”这一客观物象,并将之转化为私人化的、即时性的对世界的感知。这时,客观物象已成为了诗人的“意中之象”,这主观之“意”是通过“幽灵”、“湿漉漉”、“黑色”这些表达感觉的词语和“花瓣”这一色彩鲜明的喻体传达出来的。在这里,“幽灵”一词并无贬义,而是表达客观物象“面孔”在诗人眼中飘忽、迅疾闪现的主观感觉;“湿漉漉”则是指黑色的钢轨、幽暗的站台在灯下泛着亮光,有一种仿佛被雨水淋湿了的感觉;而钢轨与站台伸向远方的线条在诗人眼中就幻化成了极富创意的 “黑色枝条”;相映之下,在其中来往的人们的面孔,则格外明亮、鲜润,自然就是“黑色枝条上”所绽放的鲜艳、明丽的“花瓣”了,它映亮了灰暗的地铁车站,令人赏心悦目。
同样是运用意象的并置手法,以鲜明的意象来表达感情,但我们仍可发现庞德的《地铁车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明显区别,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意在运用意象营造出一种氛围、一种意境,做到情景交融,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取得一种心理上的叠加效应。它强调的是“象”中之“意”,即作者的思想情感。如前述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三个并置的意象所构成的画面是统一在“忧伤”的情绪和“凄清旷远”的氛围之下,这样,即使没有下文的“断肠人在天涯”一句,我们也可体味到主体者孤旅天涯的感伤和凄清。也许对具体词句的解读可能各人有所不同,但对这首诗的整体情绪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古典诗歌的意象与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情感、意向和谐一致,给意义的阐释以明确的定向。
庞德的《地铁车站》虽然意象构成的画面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并置的意象间也有“比兴”关系,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想象与联想,但整首诗似乎未能体现出“比兴” 的真正含义,“比而不兴”。因为它过分强调“意中之象”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情感及诗的意向的隐含;同时,过简的诗句导致诗章缺乏关于自身阐释的定向性提示,使读者难以破译和阐释其意义。
我们知道,就诗歌的阅读来说,读者所重视的不是作者创造或描绘了什么“意象”,而是想知道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要表达什么。庞德本人也曾说过,“诗歌是极大感情价值的表述”,意象是“理性与感情的复合体”,即情与景的统一。以此来反观《地铁车站》,我觉得这首诗并没有真正实现他自己的这一创作原则。由于他过于强调“意象”本身而忽视情感的灌注,使得他对地铁车站的这一瞬间印象的意义语焉不详、暧昧不明。在我看来,《在一个地铁车站》读起来更像一首未完成的残篇,须待作者进一步补笔才能完整、明确。
(崔玉香,烟台教育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