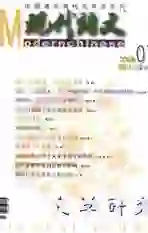简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将的民族特征
2006-05-20毛成坤李芳
毛成坤 李 芳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问世于十四世纪的元末明初,以宏伟的篇章描写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逐鹿中原的近一个世纪的军事、政治斗争。《三国演义》刊印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为中国小说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平家物语》是日本“军记物语”这一文学样式的巅峰之作,大约成书于镰仓时代(1192-1333)中期,比《三国演义》约早一百多年。其作者一说是“民部少辅时长”(《醍醐杂抄》),一说是“信浓前司行长”(《徒然草》)。全书共十三卷192节,以铿锵有力的语言艺术再现了平安时代(794-1191)末期,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争夺权力的兴衰始末。它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日本文学家、学者对该书的评价之高,不亚于中国学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两书描绘的都是各自民族历史上最富于风云变幻的时代,三国鼎立、源平争霸,在那剑戟相向、杀声震天的年代里,武将们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向历史的前台,成为文学家们着力刻画的对象,就个体而言,两书塑造的英雄人物无论主次均各有一番情貌,或急躁鲁莽,或稳重谨慎,或粗中有细,或刚中带柔,而这鲜明的个性特征却是以强烈的民族色彩和社会性格为底色的,正是这强烈的民族色彩和社会性格,孕育出截然不同的英雄群像,成为昭示各自民族精神的丰碑。
在冷兵器时代,骁勇善战、万夫莫当的武将对战争的胜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这样的人物也是《三国演义》和《平家物语》所共同矜夸的。但重“武勇”的同时,两部书也将“文”看作是成为优秀军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所不同的是《三国演义》的“文”指的是“谋略”;《平家物语》的“文”指的是“风雅”,即艺术品位和生活情趣。
《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可见中国历来就不赞成“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而尊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三国演义》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作。吕布虎牢关下战三英,濮阳城大破曹操,“天下英雄谁敌手”,是何其的英勇,当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他有勇无谋、目光短浅、自以为能“匹马纵横天下”,有恃无恐,却接连中陈登之计,失了徐州、小沛,又不用陈宫之谋,终落了个被曹操生擒命殒白门楼的下场。与此相反,关羽温酒斩华雄、刺颜良、诛文丑,是其武功盖世;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是其勇气过人;水淹七军、生擒庞德,则又是他善于谋略。像这样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尊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在这里,“武勇”与“谋略”相辅相成,它们共同作用于军事、政治斗争,并保证其成功。
日本武士的“风雅”,正如中国武将的“谋略”,是日本优秀军人必不可少的修养。起兵讨伐平氏的源赖政兵败后,在战场上请求他的属下割下他的头,属下不忍心下手,源赖政只得自杀。在自杀前,他做了一首和歌:“叹我如草木,永年土中埋,今生长已矣,花苞终不开。”然后“以刀尖刺入腹部,伏下身去,穿透而死。”作者接着写道:“这种情况那是作歌的时候,因他自幼酷爱此道,所以到了最后关头仍不忘作歌。”平家武士平忠度在源氏军队眼看要杀进京城之际却不急于逃命,而是向歌人藤原俊成交了一本自己的和歌草稿,求他把自己的和歌收在敕选和歌集中。他说:“即使收录一首,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藤原俊成则为平忠度的“风雅之情”“禁不住感动得流泪了”。后来平忠度在战场上被取了首级,作者赞叹地写道:“真可怜呀,这位精通武艺又擅长诗歌的人,了不起的大将军。”而如果缺乏这种风雅之情,即使是勇冠三军、战无不胜的将军也要遭到无情的嘲笑。源平二氏争战,木曾义仲一马当先,通过几场战役将平氏赶出关西,统帅军队直逼京师。但他自小在信浓国山村长大,不曾见识过京都的浮华和礼节,因此书上说:“兵卫佐中原泰定到底气度不凡,不像木曾那样当上左马头,担任京师的守备,而举止言谈还是那么粗俗。”“木曾自从晋封为朝廷高官,便认为不宜穿直裰入朝,开始换上布制的狩衣,头戴立乌帽子,下穿带纽结的长统裤,从上到下实在难看。但是,他倒很喜欢坐车,可还穿着铠甲,插着箭,挽着弓,完全没有骑马时那种威风了。……及至来到法皇的宫里,把牛从车上卸下来,他就从后面下车。在城里长大的仆从告诉他:‘这车子要从后边上,从前边下。‘管它什么车,那头不能上下!他仍然坚持从后面下车。类似这样可笑的事还有不少。”作者并没有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宽宥他。源义经是源氏家族的“白眉”,其武勇与木曾义仲不相上下,在智谋、文雅上较之又更胜一筹。志度浦之战、坛浦之战中,源义经以少胜多,最终歼灭平氏有生力量,为镰仓幕府的开创立下汗马功劳。而当他主持公众禊祓大典时,书上却写道:“且说宫中准备举行大尝会,所以天皇先进行禊祓行幸,德大寺的左大将实定公当时是内大臣,故由他主持典礼。前年先帝举行禊祓行幸时,由平家的内大臣宗盛公在节旗之下主持典礼,当时他就席于节旗的帷幄之中,前面竖着龙旗,风采焕发,那峨冠、袖筒以至裙裤的下摆,都显得仪范超群。同时,一门之中还有三位中将知盛、头中将重衡,以及近卫司的人们,共挽天皇所乘的凤辇,那潇洒的风度是无与伦比的。今天,九郎判官义经主持典礼,他虽与木曾义仲不同,熟悉宫廷规矩,但那仪表连平家最末流的人尤且不如。”平家把持中央政权二十余年,深深习得王朝贵族的艺术文化,并培养出超凡脱俗的气质,但“武勇”方面已大不如前,“富士川一战”被几只水鸟吓得落荒而逃。源氏发迹于关东偏远地区,均是以一当百的勇士,但文化修养不高。源平争权中,源氏是胜利者,作者褒扬他们的武勇,却讥笑他们的无知;平氏是失败者,作者欣赏他们的风雅,却慨叹他们的怯懦。可见,在这里“武勇”与“风雅”是并列的、互不相关的两方面,一位真正的武士则是这两者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名优秀的武将要内怀“忠义”,并排斥“匹夫之勇”与“妇人之仁”。吕布之所以命殒白门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留恋妻子,不依陈宫之谋,不忍外出屯军,致使属下萌生反心。刘表偏爱后妻,废长立幼,重用妻族,致使幼子刘琮在其身后不久将荆州拱手让于曹操。如果这些仅仅说明吕布、刘表等人分不清孰重孰轻,因小失大,那么张飞失落了徐州,甘糜二夫人落于吕布之手,受到关羽责备,张飞欲自刎谢罪,刘备阻拦时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则可足见三国武人对夫妻之情的淡薄。刘备丢失新野,携领万民逃往江陵,几度濒临险境却不肯弃民先走,看到百姓为之流离失所,遭受军火荼毒,心中愧疚难当,几欲投江自尽。甘糜二夫人及儿子阿斗与他途中失散,于敌军中生死未卜,但书中却只字未提刘备对他们的挂念。甚至当赵子龙出生入死杀入长坂坡突破重围救出阿斗,将之递于刘备面前时,“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虽然意在收买人心,但也说明在三国武人的价值观中,不仅是夫妻之情,即使是父子之情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倒是对兄弟之情,也就是义,三国武人则看得重如泰山。关羽这个人物之所以备受称道,不仅在于他的智勇双全,更在于他对兄弟义气的重视。关羽被曹操的军队包围,无奈之下只好投降,却宣称“只降汉帝,不降曹操”,并事先声明“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关羽投降后,曹操给他的待遇非常优厚,先后送给她美女、锦袍、赤兔马等。但是关羽不为所动,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他就毅然决然辞别曹操,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地去投奔刘备,终于兄弟重聚。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关羽为“古今名将中第一奇人”,认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在《三国志演义》中,关羽除了有点刚强自恃外,按作者时代衡量标准,几乎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缺陷。古城会一节写得更是细腻曲折感人肺腑。
与《三国》武将相比,《平家物语》中的武士们则显得儿女情长得多。在“维盛出奔”一节里,源氏大军即刻就要攻入京师,作为平家嫡孙,平维盛不得不抛妻弃子,随家族一起逃往关西,他“平素就已料到会有和妻子儿女诀别的一天,可是事到临头,心里还是不免悲伤”,看着如花似玉的娇妻忍痛地说道:“正如我平时对你说的,我要同大家出奔到西国去。不管到哪里,都是大家一路同行,但因路上有敌人埋伏着,很难平安通过。万一听到我遇害的消息,你千万不要出家,可以另外找个人婚配,这样既可使你免于遭难,也可把孩子抚养成人。世上总还会有钟情的人。”……“当时你十三我十五,少年结发,伉俪情深,烈火我们可一同跳入,龙潭我们可携手沉沦,生不同时,但愿死无先后。可是,现在这样悲伤地奔赴战场,倘若带了你们同去,那正是前途渺茫,境遇可悲,实在不堪设想呀,而且这次毫无准备,将来在什么地方能够安心住下,再来迎接吧。”说罢便狠了狠心,准备离去,而儿子、女儿从房里跑了出来,拉住父亲铠甲的袖子和护腰软甲依恋地哭泣起来。他在这里百般地劝慰着,兄弟们过来催他,但看到这样的情景,“院子里的兄弟们也都湿了铠衣的袖子”。“敦盛之死”这一节,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篇章。一之谷之战源氏大军以奇袭制胜,平家节节败退,逃命的军卒纷纷奔向海边备好的船只。源氏军中的骁将熊谷直实穷追不舍,驱马来到须磨海滩。当他看到一个锦衣金鞍的平家武将时,就跃马上前将其打翻在地。本想一刀结果了对方的性命,不想揭开护面甲一看,却是一位用淡妆稍加修饰并涂了牙齿的美少年。熊谷直实这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小次郎,不由对刀下的少年产生了怜惜之情,于是迟迟不忍下手。心想:“杀了他一个人,该打败仗的也胜不了;不杀他,该胜的仗也败不了。自家的小次郎受了轻伤,我就心里难受,倘若杀了他,他的父母该多么悲伤啊。”可是源氏军中的其他将领已经曾后面赶了上来,熊谷只好含泪割下了少年的首级。事后才知道这位泰然而死的少年就是平中盛之孙,经盛之子,官任大夫的平敦盛。日后,熊谷削发出家追悼敦盛的亡灵。在《平家物语》里这样描绘武士们内心细腻的夫妻之情、父子之情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源氏军中的梶原平三景时,明明已经冲出重围,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自己的儿子景季。问道:“部曲们,景季呢?”部曲们回答说:“深入敌阵里去了,怕是遇难了吧!”梶原平三听了说道:“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孩子,景季被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返回去吧!”于是返身冲向敌阵,在数万骑敌军中,东奔西突,辗转厮杀,终于找到了景季。还有平家的武将濑尾兼康为了儿子小太郎放弃了战场逃生的机会,并且在自知无救的情况下,在敌军的重围中亲手割下儿子的首级后战死。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武将凸现的人格是“武勇”、“谋略”、“忠义”,这三者紧密结合,共同为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服务。而日本优秀武士凸现的人格是“武勇”、“风雅”、“人情”,这三者是泾渭分明的,各自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无论平维盛如何不舍,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无论熊谷直实多么不忍,他还是杀了平敦盛,以后又出家。正是这种各个领域的不能兼顾才造成了悲剧的美。“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似乎认为,‘人的义务的整体像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分为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菊与刀》)因此在《平家物语》中,文与武,柔与刚,残忍的屠杀与同情的眼泪往往奇怪地并列在一起。武士们一边举刀砍头,一边唏嘘感叹;一边舞刀弄剑,一边风花雪月;一边英勇无畏,一边凄凄惨惨。
(毛成坤 李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