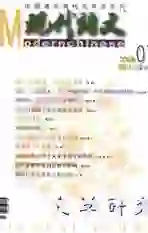游走与飞翔
2006-05-20倪文平赵志民
倪文平 赵志民
一
自德国哲学家尼采发出惊世骇俗之言:上帝死了之后,整个西方社会陷入价值瓦解、信仰崩溃的极大恐慌中。已经习惯和上帝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神的子民瞬间发现那个仁慈博爱的老人只是海市蜃楼般的一个幻影之际,巨大的愤怒和质疑镂刻在他们迷茫的额头:上帝如此仓皇地离去了,但人类的罪恶该让谁来救赎?精神的家园还有谁来守侯?既然上帝死了,天国的庭院必然会荒芜颓败,破败不堪,那么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理想又何处存身?这种骨子里的痛苦和凄惶折射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衰败。在新的价值体系确立之前,这种心理的痛楚不会泯灭——人类必须再造一个上帝!于是西方一代代文学巨匠用他们高贵的头颅和如椽巨笔从事一项不啻于建造一座埃及金字塔的复杂工程,试图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原则的努力注定充满着艰辛和失败。事实上,人类卑微可怜的存在状态、真实痛切的生存感受得到以前所未有的揭示和书写,空虚、无聊、孤独、痛苦成为此刻文学津津乐道的主题。很滑稽的是,试图为人类找到出路、拯救迷茫人群的大师巨匠们把人们引向一条黑暗恐怖的羊肠小道。大师沉重的影子压碎了人们关于当下和未来的种种美好和乐观的憧憬。在价值重构这一精神大势下,文学对以往的文学观念表达方法做了一次彻底、决绝的反叛和逃亡,这是破釜沉舟的、没有退路的一次叛乱,名目繁多、样式各异的现代主义流派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无一例外不再表达生存的荒谬,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难以沟通,人在荒谬的历史语境中尴尬无奈的生存状态,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扼杀以及人异化等存在的负面因素。
西方文学在向现代主义的整体迁移过程中带来的是艺术技巧的全面更新,为文学注入新的构成要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根本性变革直接影响了中国新文学,但中国新文学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也使其更为主动的、有选择的接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四十年代在中国诗坛卓有建树的九叶诗派正是建立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收改造和融化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民族的生存经验,试图为我国新诗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为新诗找到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
二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试验性的文学思潮,其先锋性、自足性、独立性不言而喻,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却远远没有为纯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壤和文化氛围,“20世纪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国共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使20世纪成为一个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
九叶诗派崛起在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所谓的民歌体、山歌体、街头诗等本难以在诗歌的圣殿中闪现的诗歌样式在中国诗坛上众声喧哗之际,九叶诗派的出现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无可否认,在整个民族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的现实语境中 ,文学作为宣传的工具、救亡图存的手段,甚至是政治的附庸、仆人并不应受到苛责,但站在新的时代高地审视这一时段的文学,艺术性、审美性的长久缺席毕竟是难以掩饰的缺陷。
穆旦、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九位诗人立足于本民族当下的苦难生存经验,积极汲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些许技巧和创作手法,创作出一篇篇无愧于伟大时代、作家良知,同时又能和世界诗歌潮流相对话、相交流的大气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资源的态度上,不是盲目地因袭,一味地模仿,而是努力融入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自觉体认和评判。所以 ,他们的诗作既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同时又有迥异于现代主义观念的独特发现 。这是九叶诗派对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整体性浅显、直白、滥情的一次有力反驳,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潮流的不自觉修补。对“自我”进行痛苦的审视、自我的分裂、对立、撕扯成为九叶诗派表达的主题和关注的重心,但他们更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大地,投向民族心灵的深处,自觉地叹服其历史和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近距离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融入生活,体现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
《中国新诗》第一集序《我们呼唤》可以视为九叶诗派对诗歌的主张:“到处是有历史的巨雷似的呼唤:到旷野去,到人民的搏斗里去,到诚挚的生活里去,它以它的光叫我们知道:只在历史的光耀里才有人的光耀,人的存在只因为他的严肃的工作,人的存在只因为他的自我的牺牲——在生活里也在文艺与诗的创作里。”又说:“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的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的思考一切,首先是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连。一片庞大的繁复的历史景色使我们不能不学习坚忍的挣扎,在中心坚持,也向前突破,对生活也对诗艺术作不断的搏斗。我们的工作要求一份真诚的原则,毅然不动似的塑像似的凝紧,也要求一个份量相当又准确无误的全局的把握。我们应该有一份浑然的人的时代的风格与历史的超越的眼光,也应该允许有各自贴切的个人的突出与沉潜的深切的个人的投掷。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个人光耀之上创造一片无我的光耀——一个真实世界处处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一个圣洁的大欢悦,一份严肃的工作。新人类早晨的辛勤的耕耘。”可以看出,九叶诗人自觉强调个人对历史的融入,具有阔大而深沉的历史感,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实现对历史的真实言说。但面对同时代淹没诗人个人声音、诗歌完全沦落为口号式的宣传的弊端,九叶诗人力求凸显诗人个人的风格、个人的独特表达,大时代的风云变迁、波澜云涌必须经由诗人的感性体验和智性思考来显现。同时,九叶派也力图用诗歌来复活历史的无限复杂性、生动性和真实性。九叶诗派善于用各种异己力量的同声喧哗,激烈碰撞,不同方向的拉扯,造成一种紧张感和急迫感,使诗歌富有张力。正如袁可嘉在《九叶集》序言中所言:“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执行和感性的溶合,注意运用象征和联想,让现实与理想相互渗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普遍地把诗歌关注的重点放在对自我的关注上,艾略特的《荒原》把整个的人类存在之境比作荒芜颓废没有希望的蛮荒之原。金斯伯格是在诗中被生存困扰而发出痛苦嚎叫的孤独者。
如果说浪漫主义唤起了人们被工业文明压抑许久的人类本性,呼唤人们关照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愫,达到心灵超迈的高远之境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在精神维度的追求上则使人未免绝望。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恰恰相反,他们有着更为卓越的精神风标,以至于无论人的如何努力,离那个目标总是可望而不可及,永远无法抵达。因为现代主义的此岸世界中人与人是隔绝的,沟通是难以实现的,存在是荒谬的。
九叶诗人是积极的为人生派,在艺术手法的采取上,他们更多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手法,但在艺术观念的价值体认和评判上,他们主动向现实主义靠拢,聚焦现实,关注本民族的苦难生存,对民族复兴充满信心的同时并不回避现实中的挫折和矛盾。穆旦的《赞美》正是体现九叶诗派这一创作趋势的代表性作品。穆旦是九叶诗派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这篇凝重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杰作中,诗人以真挚深沉的感情赞美伟大的祖国,它不是建立在盲目乐观之上的廉价的颂歌,而是正视民族苦难生存现实的悲壮之歌,诗中有着民族的血和泪,创伤和疼痛。密集的诗歌意象,浓郁激越的情感爆发,完美的诗歌形式,使诗歌蒙上雄浑壮阔的色调。它并不回避一个屈辱的民族为了自由独立所必然付出的血的代价,但面对沉甸甸的历史和现实,诗人始终用庄严神圣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陈敬容的《逻辑病人的春天》把目光转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幸的人生和徒劳的挣扎令人扼腕叹息。《冬日黄昏桥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生与死的界线显得如此模糊不明,谁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像尘土一样浮浮沉沉。九叶诗派的一些诗作甚至可以当作政治讽喻诗来读——《南京》:善良地看着你觉得心痛,精神病学家说你发疯,华盛顿摸摸口袋:好个无底洞!这类诗作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功利性,虽不免有些浅显直露,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一颗关心现实人生、民族命运的火热的心。
三
五四以来,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作为体现新诗实绩的重要一脉一直绵延不绝。中国白话新诗的开山鼻祖胡适的《尝试集》中大多篇章实际上是对西方正在风行的意象派的借鉴和模仿,胡适所倡导的“八不”主张,也与意象派的诗歌主张多有暗合之处,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白话诗人在意象派的山脚下艰难地攀登。但由于草创期的中国新诗缺乏必要的诗歌理论素养和创作实践的酝酿,多数新诗流于意象的碎片和情绪化的渲染。稍后的李金发对现代主义诗歌的陌生化效果、含混、矛盾等艺术手法深有领悟,其诗作颇有象征主义色彩,但其诗歌也难以摆脱生涩怪癖的怪圈。在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过程中,个人的声音最易埋没在形形色色、众生喧哗的文学主张中,不易形成较大的影响。九叶诗派以其对艺术的共同追求而走在一起,并形成自己的文学阵地,在肃穆的诗歌圣殿中发出自己铿锵有力的声响。
西方现代主义从整体上颠覆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它以更激进的姿态强调主观,强调对自我心灵的审视,但这种审视是远距离的、冷漠的、客观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自我解剖,它反对浪漫主义的主观膨胀和由此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状况揭示的失真,在他们失去任何感情色彩的冷漠语调中,牵引着的实际上是作者对人类可怜的生存状况的痛苦发现,西弗弗斯在滚动石块的重复无聊繁重的肉体惩罚中发现了幸福快乐的秘密,面对苦难的人生处境,文学不应当加重从山顶滚滚而落的石头的重量和力度。
九叶诗派在对西方现代派借鉴吸收的同时又不失警惕,自觉加大了诗歌对现实人生诗意关照和世俗关怀,他们并不排斥情感在诗歌中的功能,相反,他们大大的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陈敬容早期的诗集《盈盈集》、《交响集》深受何其芳的影响,唐祈早期以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杭约赫的早期诗篇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热情,这些早期浪漫主义的因子并没有因为他们后期现代主义的艺术选择而泯灭,而借现代主义的躯体还魂,渗透到他们颇具现代主义气质的诗歌中。杭约赫的《跨出门去的》是为纪念民主斗士李公朴殉难而作的:你曾经譬如自己是座桥,/一群群的年轻人经过你走向/耶路撒冷;现在你横下了/身体,更像一座桥,迎来/人的觉醒,和一个丰收的世界。在平实缓和的语调中汹涌澎湃的是作者对烈士伟岸人格和崇高品质的敬仰之情。唐祈的《圣者》是纪念继李公仆先生之后牺牲的闻一多先生的名作,与杭约赫的《跨出门去》可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每个人死时,/决定/一生匆促的行踪,有的缩小,灰尘般虚渺....../有的却在这一秒钟/从容地爆裂,世界忽然显得震动。朴素的语词因为有强烈的情感作支撑而显得很有力度。穆旦的诗作充满了诗人灵魂搏斗的痕迹,无羁的想象,喷薄而出的激情,圆润成熟的诗艺,使他的诗歌显得厚实深沉。蓝天下,为永远的谜困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生,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青春生命涌动的欲望和焦灼,敞开与封闭的迷惑和希翼,残缺与完整的挣扎与融合,使这首诗充满了张力,而其间迸涌的是穆旦对青春生命的积极体认,有着穆旦健康率真的情感投射。
激情和想象在九叶诗人中得以大面积的复活和跃动,更难能可贵的是,九叶诗派的诗大多抒发一种健康向上的情感因素,充满明朗和明丽的色调。对恶的憎恶与反讽,对真与光明的渴求和拥抱有着诗人最真诚的艺术良知关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拳拳赤子之心,他们是积极的现实派,即便是书写心灵苦闷与忧郁的诗作也充满了健康清新的气息,而滤除了现代派诗歌通常难以摆脱的颓废、空虚、阴冷的情感氛围与艺术格调。无论是宏大的国家、集体、民族等主题的尝试,还是对微妙曲折的心灵的深沉开掘,九叶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溶化为个人心灵的秘密,在艰辛的思考中寻觅最完美的诗歌表达方式,体味破茧成蝶的诗歌生成喜悦。剔除各种大而无当的主义、学说、主张对诗歌自由精神的过度的侵扰、阉割和挤占,九叶诗人以独立的姿态宣告着个人声音的在场。
四
当我们把对历史的长距离眺望的目光抽回到现实,打量当下诗坛的整体性生态环境时,我们会发现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进入新世纪的今天,现代、后现代成为当下诗坛的时髦用语和诗人们趋之若鹜的争夺的魔杖。解构深度消解意义,宣告着思想的执著、认真和质问已成为明日黄花,历史难逃被“大话”“戏说”的劫难,诗人更强调对世俗社会的迎合和认同,诗歌实现整体性的迁移之后,整体趋向世俗化、粗鄙化,世俗欲望如巨兽猛禽吞噬着一切所谓的崇高神圣的坚守。中国的当下诗歌并不缺乏所谓的技巧和手法,事实上,中国当下诗歌中以几乎可以找到一切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影子,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诗歌传统,一种诗歌精神。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是以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技巧来为中国新诗注入新的血液和力量,但他们始终不曾背弃诗歌对当下存在的关注,在坚守诗歌理想和诗人主体性的前提下始终不曾放弃诗人对沉重的历史语境中人的命运的思考和关怀,以积极健康的情感力量实现诗歌对历史民族个人的担当。诗歌之魂在临空高蹈之际,始终没有忘却大地的引力和呼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一切的外来诗歌资源都必须融入中国的现实经验。
无法否认,四十年代特殊的时代氛围,包括译著的稀少,东西方诗学沟通的滞涩,特殊的战争心理状态对文学的急功近利的影响等,使九叶诗人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和不足,但其对西方现代主义改造和超越的气魄和努力,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考和实践,对当下诗歌也许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诗歌资源吧!
(倪文平 赵志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