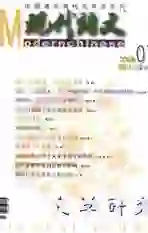权和性捆绑下女性的生存处境
2006-05-20赵新亚
阎连科在文坛上一路走来,从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载满了一种“乌托邦”情结。追求理想是因为现实的苦难。贫穷的生活,多舛的命运,把人们紧紧地拧成了一股绳子,为了共同的生存而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我们看到了《情感狱》中连科的乡亲们为了连科的出息,舍弃了自己的返销粮;《年月日》中先爷为了全村人的种子,用自己的精血滋养玉蜀黍;《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男人们去教火场卖皮子等等绞人心肠的图景。这都是与苦难和命运作斗争的牺牲。阎连科把这些牺牲用宏大的场面推到叙事的前台的时候,一群女性在权力和性欲的紧紧追逼下更为凄惨的生存状况在叙述的缝隙(虽然有时也被推置到前台,但总体上来讲前台的叙述是属于集体属于男性的)中时时闪现,撞击着读者的眼球。在这里,女性什么都是,除了不是她们自己。
权力与女性
阎连科的小说世界是典型的男权世界,到处是晃动着的男人的身影,到处是男人们为了权力的明争暗斗。“村长”这个词是许多小说故事得以完成的中心词。这样的世界中,村长和父亲发挥着主宰功能。“中国古代的家庭不仅仅是个体依据社会分工而结合的社会生产单位,也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繁衍扩大的单位,它更是一种统治单位,它对于女性发挥着父权国家机器的功能。”虽然这不是中国古代的家庭,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村落依然发挥着这样的功能。村长或者是爷爷或者是父亲这样的掌权者操纵着女性一生的命运。《情感狱》中村长三姑女和连科的婚事告吹,和副乡长孩娃定亲,全都是村长和支书的决定。虽然三姑女不在场,但她的命运已经被几句话改变了。她根本就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个人自由的机会。在《寨子沟乱石盘》中,小蛾的婚事也是有爷爷敲定的。虽然她的心里恋着城里收购站的小伙子,爷爷还是把她给了三豹,并在结婚前成为三豹夺走小蛾清白的帮凶。传统的家长制,以及传宗接代、把根留住的腐朽观念葬送了小蛾的幸福。虽然小蛾走了,离开了闭塞的山沟,但她已经是个受害者了。
女性不仅仅受到男权社会中权力的拥有者的主宰,还受到男权社会中权力的觊觎者的利用。传统社会把权力赋予男性,权力成为男性的社会化特征。男性为了得到权力而不择手段,女人常常成为他们谋取权力的工具。在《情感狱》中,连科对副乡长姑女的纠缠,只因为她是副乡长的女儿。他还想方设法打动红玲的心,甚至丧失良心地制造红玲从崖上摔下来而英雄救美的事件。这也全然不是爱情,只是因为红玲他爹是支书。而红玲是一个被双重利用的角色,不但是连科利用他向上爬,他爹也利用她向上爬,最终把她嫁给了在县委坐办公室的人的瘸腿儿子。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哀。甚至于《受活》中的茅枝婆,不也是被权力玩弄的对象吗?她的被玩弄是因为她是受活庄的领袖,控制了她,柳鹰雀就可以利用受活庄的残疾人们来满足他的权利欲望,完成他永垂不朽的愿望。《最后一名女知青》中娅梅被骗走的是感情和金钱,男人想得到的只是金钱,而在这样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金钱就意味着地位,就意味着某些方面的特殊的权力。女人在阎连科的叙述中只能是权力的牺牲品。
性与女性
性不可否认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原始冲动,自然而然发生的性是美好的。劳伦斯说过“性意识本身没有什么错,只要它们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确形式的性刺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被称为“人本心理学之父”的马斯洛也详尽地描述了“高峰体验”的状态和意义,将此看作是人生最灿烂、最完美、最幸福、且富有个性的时刻。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性失去了它美好的意义,如果说男人们在非“正确形式的性刺激”中也得到了性的满足,那么只有那些女人成了性的牺牲品。她们没有体验到性的快乐,性成为她们被压迫、被物化、工具化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较之于权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权的压迫只能来自于某些男人的话,那么性的压迫则可以来自于一切有性能力的男人。由于男女在性方面具有区别,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描述的一样“男性……他的兴趣始终关注于性的生理方面……女性不同,她感兴趣于传奇的爱情,注重她与丈夫间的情感交流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关系。”所以在非正常情况下,女性除了承受性所带来的痛苦外,没有任何欢乐可言。在男人眼里,她们是被用来传宗接代的,是被用来泄欲的,是用来转嫁郁积的情感的,是用来抚慰创伤的。当男人贪恋性爱时,他们渴望妖艳、妩媚、放浪形骸的“妓女型”女子,当他们需要家庭样的温暖和踏实时,他们又渴望忠贞不渝、痴情专一的贤妻良母样的“母亲型”女子(采用蔡翔在评述《白涡》时的说法)。女人在男人的对象化中获得的是歪曲的所指意义,在苦难与夹缝中生存。
在阎连科的成名作《两程故里》中,喜梅在十七岁时即被程天青的父亲强暴,而又宿命般的被程天青求着结婚,最后在乱伦的耻辱感中悬梁自尽。在《日光流年》中第一代村长杜桑为了村子不断子绝孙,让女人加快生产而置女人死活于不顾。一生没有爱过竹翠的司马蓝只因为对竹翠的恨就在自家的院子中痛快淋漓的完成了男女之事。三豹糟践了小蛾之后,丢下了“怪不得寨子沟的男人女人们乱干这号事……真舒服!” 这样的话。在《金莲,你好》中,老二在社会上混,憋了一肚子苦水,想在家里从嫂子那里得到安慰,他说:“金莲嫂,我的亲嫂子,我心里不平哩,想到天东地西都不能平衡哩,我求你让我在这住一夜,住一夜我的心里也就平衡了……”甚至于《最后一名女知青》中,天元因为娅梅在外面又结过婚而没有告诉他,就不愿意和娅梅复婚。他们只容许自己在外面沾花惹草,而不许女人不忠于自己,不容许女人有一点过错,要求女人在性上完全归他所有。女人就这样在男人的定义和要求中,丧失了性的乐趣,同时也丧失了自己。
权、性的胶合与女性
权力和性的胶合自古以来就存在。我在前面把权和性分开来论述,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女性受男权的压迫时,施压的主体或受益者,有时只占有权,有时只占有性。而在权和性的胶合下,压迫被套上了合法、合理、甚至正义的外衣。这样,女性的牺牲就被遮蔽了,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残酷。古代的诸如“昭君出塞”等和亲政策,其实正是权性胶合对女性的蹂躏。对于献出女人的一方来说,它只失去了一个女人而保全了国家,对女人的损害在国家权利和利益的名义下正义化了。对于得到女人的一方来说,它避免了战争而获得了地位的巩固和提高,权、性双赢,何乐而不为?而对于女人来说呢?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礼品,是一个物。她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和快乐,成为男人处在弱势地位时的挡箭牌,成为男人淫乐的工具和对象。在阎连科的笔下,这样的古代和亲政策原型一再出现。且不说《情感狱》中那一系列带有政治意义的婚嫁事件或多或少都带有和亲政策的影子,最为突出和明显的就是在《日光流年》中,为了留住带人修梯田的卢主任蓝四十的出场,《金莲,你好》中为了刘街改镇金莲的出场。
在《日光流年》中,当村人们为谁去侍奉卢主任陷入僵局时,和司马蓝订过亲的蓝四十主动提出自己去侍奉卢主任。司马蓝也发誓即使如此,它一样要娶蓝四十为妻。蓝四十跪下给司马蓝磕了一个头后,就不言不语,脚步飘飘,要倒不倒地走了。那是一个庄严、情绪高涨而又不能爆发的沉闷的场面。我们丝毫不能怀疑这次献身所具有的巨大意义。然而,事情过后,蓝四十却是背着“破鞋”“肉王”的臭名声走过了孤独的一生,这对那个已逝的庄严的场面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在《金莲,你好》中,金莲进城侍奉李主任的时候“村长……扭过头望着金莲说,金莲,拜托了,我代表咱刘街几万人口拜托了。说着他弯了一下身,朝金莲鞠了一个躬。跟着,老二、月和村委会的干部们都弯腰朝金莲鞠了一个躬。接下来,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一层层,一圈圈,受了传染又如事先安排好了样齐哗哗地都向金莲弯了腰。金莲看见他们直腰后,所有地目光都祈求地望着她,金莲的眼睛就湿润了。”这是刘街人为他们的恩人金莲送别的场面。我们看不到鄙视,此刻的金莲高高在上,是人们理想和幸福的女神。然而等到半年后,金莲迫不得已回到西门镇时,没有一个人来接她,除了郓儿哥,一个小孩子。而村长开着小车见了金莲却躲似的开走了。如果说历史上那些和亲的女人们还在历史上留下了虚名,那么篮四十和金莲呢?当她们作为工具的作用发挥完后,她们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了。没有人因为她们曾是为大家才去走那条出卖色相的路,她们只是人人唾弃的妓女型人物了。这就是女性在权性胶合中男权社会的悲惨的生存处境。
女性主义在路上
通读完所有能找到的阎连科的小说,看到阎连科笔下的女性人物,她们的处境比同在苦难中的男性人物更为凄惨。他们被苦难所包围的时候,也同样被男权社会中的权利和性所包围着、所折磨着而不得发出喘息的声音。曾经有评论者这样评论阎连科的小说“对女性持有一种忽视或者歧视的态度”。我认为与其说是作者在忽视或歧视女性,倒不如说是作者所写的那个社会在忽视或歧视女性。正如苦难并不是我们社会唯一的特征,而阎连科恰恰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写了苦难,从而写出了他的深刻,他的独到之处,使我们更深入的体会到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女性也不完全是阎连科笔下那样的生存状况,但阎连科就写了这些,这些也是我们女性生存的一种图景。即使是在女性主义风行了几十年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能够从男权社会权力和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
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基本理清了女性今天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原因。这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种族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女性自我的等等一系列。只要你读一读女性主义文论就不会对此感到陌生。女性主义一直在解构和颠覆之中,否定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否定曾经肯定过的女强人型的女性,也否定对自然母性的追寻,提倡建立“双性文化特征”的理想社会。女性主义者们也一直在做着争取经济、政治等各种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权利,争取和男人处于平等的地位,批判文学中的男权主义倾向,寻找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创作女性自己的文学作品,写女人独特的经验,从而使女性一步步浮出历史地表。然而在这些工作轰轰烈烈、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时候,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处境的凄惨,比之阎连科笔下的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为触目的社会现象即是卖淫、嫖娼的泛滥,“包二奶”的风行。而在边远地区的落后山村,谁又能否定有阎连科笔下的三姑女们的存在呢?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已经日趋成熟了,但她好像是扎了翅膀高高地飞在天上,当面对广大女性的生存处境时,我们又希望女性主义长出双脚坚定的站在地上。女性要达到和男性和谐相处,从理论上来讲是要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体制的转变,意识形态的转变,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等等。然而怎样做才是有效的方式呢?在我看来,女性主义的路还很长。
(赵新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