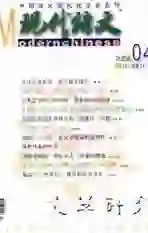讽刺喜剧里渗透着悲剧情思
2006-03-03付煜
付 煜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作过这样的概括:“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就是说悲剧是一种有价值的事物的毁灭,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残酷命运的无情演绎,但它能激励着人们的记忆,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净化。”而喜剧则是一种笑的艺术,是以笑为手段通过能引起笑声的故事来反映现实生活,揭露旧的、丑恶的事物,或者歌颂新的、美好的事物。讽刺喜剧是喜剧多重性表现形态中的一种,所反映的对象是生活中要否定的现象,它以辛辣的笔锋嘲笑和鞭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的、阴险的事物和现象。
一般情况下,喜和悲是对立的,但也不是绝然相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互相渗透。笑着向昨天告别,就是由悲转到喜的过程,乐极生悲,就是由喜转到悲的过程。在喜剧里渗透悲剧因素,往往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生活的本质。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鲁迅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范进中举》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当然堪称讽刺喜剧的代表作,本文试图初步探析《范进中举》的美学风格——讽刺喜剧里渗透着悲剧情思。
一、“范进中举”是喜剧
喜剧性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寓庄于谐”。“庄”是指喜剧的主题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谐”是指主题思想的表现形式是诙谐可笑的,“谐”与“庄”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寓庄于谐”就是在诙谐可笑的形式中表现深邃的社会思想内涵的审美形态。“范进中举”是一个喜剧性故事,它所揭示社会主题的“庄”主要在于鞭挞了科举制度,而体现表现形式的“谐”主要在于喜剧的情节、喜剧的人物、喜剧的环境。
喜剧的情节。在戏剧作品中,情节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间相互关系的系列事件的发展过程。《范进中举》虽是长篇的节选,但它有自己完整的故事情节,完全可以当作一个短篇来读。情节的序幕是范进进学,岳丈祝贺。进学使范进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但胡屠户的贺词却是挖苦、讽刺兼责骂,而范进只能低声下气,还要“千恩万谢”。情节的开端是借钱遭骂,范进偷试。借钱触及到岳丈的经济利益,故而遭到岳丈的几乎用尽所有刻毒词语的肆意辱骂,骂得范进屁都不敢放一个,但他不顾一切,硬是应举而去,就充分表现了他对功名利禄的苦苦追寻。情节的发展是范进卖鸡,捷报到家。这一情节,既表现了范进中举前拮据的生活,又显示了他屡试不中,闻喜而不敢相信的复杂心情。情节的高潮是范进发疯,屠户治病。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一疯一打,真是洋相出尽,令人捧腹。情节的结局是乡绅造访,馈银赠房。张、范的交结,演出了一幕地位迅变的幽默剧,使我们既认识到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地位、金钱为转移,又深刻地认识封建科举的实质。情节的尾声是范进送银,屠户回家。这个势利小人的见钱眼开、虚情假意的嘴脸让人们啼笑皆非。总的来说,《范进中举》的故事情节虽着眼于平凡小事,但由于作者巧妙的安排,也平中现奇,具有一波三折的特点,而且,人物性格也随着情节的发展变化逐步体现出来,所以,平凡的小事也能引人深思顿悟,曲折的情节更让我们看清社会的本质,真有曲径通幽之妙。
喜剧的人物。范进中举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范进、胡屠户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典型。范进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中举前地位卑微,穷愁潦倒,邻居不理,岳父辱骂,而他逆来顺受,甘受屈辱,只是想到“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追求功名如痴如醉。中举以后,他竟欢喜得发了疯癫,丑态百出。当张乡绅拜访拉拢时,他明知张乡绅所言是无稽的攀附之词,却连称“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以欣喜”,又显出他的心灵熏染着世故圆滑的恶浊之气。这些都讽刺了一个热衷功名、猥琐懦弱而又圆滑世故的知识分子中的丑类形象。胡屠户是一个庸俗不堪、令人作呕的势利小人,是整段故事中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人物。他虚伪,却也诚实。“言为心声”,他说的、骂的、训斥的、夸口的、恭维的无一不是他的心里话。他毫不掩饰、老老实实地讲出了他对于功名富贵崇拜向往的由衷之情,这是他的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空气的毒化。张静斋是作者刻画的次要人物之一,具体描写了“张老爷拜会新贵范老爷”的场面,着墨不多,却足以揭露他虚伪矫情、世故奸滑的丑恶灵魂。同时,作者还善于三笔两笔地把其他次要人物(如众邻居、老太太、娘子胡氏等)勾勒得神态栩然。范进疯后,众人与家人心情不同,众人比较冷静理智,能判断事实,帮想办法,家人则是担忧恐惧。作为家人,老太太和胡氏的表情语言又有差异,老太太是“哭道”,而胡氏在众人面前则比较克制,她们说话的内容也有不同,老太太只是悲叹命苦,而胡氏考虑的是怎样治病。还有众邻居,一边劝说,一边主动拿出鸡蛋酒米,露出趋炎附势之心态。总之,这些人物的举手投足、喜笑怒骂集中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使我们能够在审美愉悦中审视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
喜剧的环境。典型的环境更能揭示人物的性格。小说首先展示了决定范进辛酸悲苦命运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范进热衷功名富贵的心理和行为都是不由自主的,是受恶浊的社会环境所支配的,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言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胡屠户更是典型的代表,他由嘲笑女婿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到在他的眼里变成“文曲星”下凡,这一切皆因为“姑老爷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四个字写出了功名富贵在当时所有人心目中的分量,可以说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功名富贵热”,就像病毒一样在整个社会上扩散,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其次,小说描写了范进的家庭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简直是由困境直奔小康。中举前,家境贫寒,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吃的是“每日小菜饭”,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直裰。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中举后,马上一切都变了,人们贺喜、送礼、巴结逢迎,什么东西都送上门来,顷刻间,钱、米、房屋、细瓷碗盏、绫罗绸缎,乃至奴仆、丫鬟等等,凡是富贵人家有的东西,几乎都应有尽有了。我们不禁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就是在为社会选拔人才吗?
二、“范进中举”又是悲剧
喜剧的情节、喜剧的人物、喜剧的环境是一幕幕丑剧,又是一幕幕闹剧,是引人发笑的,但掩卷深思,可笑的背后是深刻的可悲,不仅悲在个人,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个人的悲剧。范进中举后就发疯了,为什么会发疯呢?原来是喜极而疯,因为他盼望的中举这一天对他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间,整整35年过去了,到第36个年头才盼到,此时,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有的只是原来的一次次考不上的心理准备,考不上再考,一旦他考上了,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经受巨大的欢喜,所以他是喜极而狂,喜极而疯。旁
人也说:“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从这儿可以看出,科举取仕对读书人来说的确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同时对他们的身心也是一种巨大的摧残,是长年累月人性的摧残,摧残到什么程度呢?摧残到了人不知羞耻,丧失了人格,散着头发,满身满脸的污泥,鞋也跑掉了一只,还跑到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在那儿当众宣布:“我中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甚至都不相信自己中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描写里自然透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凉。
时代的悲剧。范进是可笑可悲的,但这种悲不是范进一个人的,在当时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的,他们在科举制度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一年又一年地跋涉在赶考的漫漫长途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灵、人格受到巨大的扭曲,但他们没有能力跳出这个罗网,只能在这样的罗网中挣扎。所以由范进这样一个个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很多文人的共同命运,但他们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个人在科举罗网中挣扎的命运悲剧,更可悲的是像范进那样发疯醒来,便时来运转,得到众人的簇拥,得到张乡绅的亲近,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这才是最荒谬的。所以说,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制度、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民族心态,不是单个的读书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的灵魂被窒息被扼杀,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了生机和希望。
社会的悲剧。当范进经过了艰苦的科举道路的跋涉而终于做官以后,他会不会做一个清官呢?不会,相反,经过这么多年的寒窗苦熬,一旦当了官,他必定要找补回来,补偿他30多年失去的一切,所以,他整个人的性格也完全发生了变化。中举之前,他是个唯唯诺诺、老实巴交的人,小说中描写“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有点钱还想到救济邻居,见到平头百姓还和他们拱手作揖,和他们平起平坐,因为他本身是个平民百姓。中举之后呢,他就完全不一样了,连对丈人的称呼都发生了变化,原来他称胡屠户是“岳丈”,是尊称,现在称他的岳父为“老爹”了,虽然是长辈,但自己的地位已经高于对方,就丝毫没有了尊敬的意识。可见,他的人格已被扭曲了,这种扭曲意味着他当官后必将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昏官。事实上,出仕之前,他就与张乡绅互相勾结,使他既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方势力,拉帮结派,官官相护,那么他出仕后能指望为百姓和社会做点什么好事吗?恐怕他只会变本加厉地去搜刮民脂民膏。这些就让我们就看清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之荒谬,所以,范进中举,并不能代表他得到学识上的进步,而只能表明他更进一步地套入在封建专制的枷锁中,于国于民没有丝毫利益。试想:用此类人治国平天下,可治乎?可平乎?
三、用讽刺手法表现喜剧里的悲剧情思
鲁迅评说《儒林外史》“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谐”是谐趣,指喜剧性的成分,“戚”是悲剧性的哭泣,就是说悲剧性的哭泣与喜剧性的成分是融为一体的,作者是如何表现喜剧性情节里的悲剧性哭泣呢?是讽刺艺术,是运用了夸张、对比、倒错等多种表现手法来体现的讽刺艺术。
“夸张”突出讽刺。夸张是喜剧常用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它是在符合生活本质的基础上,将事物故意夸大、扭曲、变形,以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一文用夸张手法的地方比较多,最典型的是范进发疯、屠户治病这一情节。这是用夸张的手法虚构出来的,这看来似乎离奇得很,却如鲁迅所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为,中举的喜报,是范进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这喜报表明他从此就将身价百倍,富贵荣华,他一时竟不能相信这样天大的喜讯能与自己联得起来,如在梦幻中一般,报帖又分明就在眼前,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才确信这是真的。几十年来的苦水闷气一吐而光,他狂喜得完全忘形了,竟致旁若无人,“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这意味着他己因承受不了失常变态了。“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往门外飞跑”,意味着他的疯狂,疯劲十足。“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一直走到集上去了”,又意味着他疯得不知东西南北,神智不清,丑态百出。中举而发疯,这个夸张的故事及其夸张的过程描写本身已经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更何况这个疯病偏要用他的岳父的巴掌这样一个变态的方法来治疗:“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居然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这一疯一打相映成趣,更是无情的嘲讽、辛辣的鞭笞。总之,中举,对范进来说自然是荣耀之至,但挨巴掌却是受辱,荣而后辱,令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深感他的可怜、可悲、可鄙。
“对比”强化讽刺。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了讽刺效果。可以说《范进中举》一文多处运用了对比手法,最突出的是描写胡屠户两次“贺喜”。第一次“贺喜”是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是“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岳丈今日却犯难害怕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他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两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说穿了,就是因为“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市侩嘴脸。
“倒错”表现讽刺。倒错也是喜剧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指的是形式与内容的自相矛盾,即用伪装的外在形式的美来表现内在内容上的空虚与丑恶,就像《史记·滑稽列传》司马贞《索引》里所说的“言非若是,说是若非”,结果是欲盖弥彰,这样就取得了诙谐的效果。《范进中举》一文中描写的人物的言行前后矛盾处颇多,因而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和讽刺效果。如描写范进的疯态就生动地揭示了范进内心和外形的矛盾:就内心而言,他是个胜利者,他感到扬眉吐气,因而拍着手大笑,他要向周围的人宣布自己的宿愿已经实现,所以往门外飞跑,跑到集市上;但在外形上他却是个失败者,头发跌散,两手黄泥,遍身是水,如同落汤鸡一样。这就是强烈的讽刺。再如写胡屠户的贪婪相,胡屠户一边“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一边假意推辞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并不等范进说完话,“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之后,“低着头,笑眯眯地去了。”这一细节揭示的是胡屠户言语和动作的矛盾,银子已经紧紧地攥在手里了,嘴里还偏说不要,暴露了这个市侩嗜钱如命的本性。又如写张乡绅造访这一情节,张乡绅开口一个“世先生”,闭口一个“亲切的世弟兄”,而且“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又送银子,又送房子。既然如此亲近,那么当初范进“家里饿了两三天”“抱着鸡”“寻人买”时,这位“至亲骨肉般”的世弟兄到哪里去了呢?可见,人物的言词与事实的矛盾揭示了这个肮脏丑恶的灵魂。
当然,作者也能恰到好处地掌握讽刺的分寸,能随着人物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行讽刺,如范进在中举前生活艰难,处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作了一定的讽刺,但更多的是同情,中举后,做了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作者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采取的是辛辣的嘲讽。
总而言之,范进最终还是科举制度的幸运儿,毕竟高中了,然而,当他中举发狂大笑时,我们却想哭:读书人的人格哪里去了?掩卷而思,这种疯疯癫癫的闹剧表演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悲剧底蕴,而且入木三分地揭示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即科举选拔制对读书人的毒害深入到了骨髓。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人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型的散文家廖燕也说:“明巧而秦拙”。“明巧”就巧在用功名富贵作诱饵,诱使天下人读书,但是只允许读朝廷规定的“圣贤书”,这就使读书变成了“愚民术”,让天下的读书人长年累月、无休无止乃至疯疯癫癫地困在书山题海里,从而达到了“不焚而自焚”的效果,这样,多少人的青春、才华及其宝贵的智慧都被埋葬在科举制度里。
(付煜,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