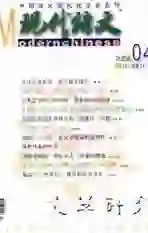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
2006-03-03廖淙
廖 淙
关于汉末诗歌(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的研究历时久远,前贤已从很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本文试结合汉末时代特征,考察汉末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歌,从文化心理角度来论述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及影响。
时代界定及背景
据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东汉中期指汉和帝永元元年(89)至汉质帝本初元年(146);东汉后期指汉桓帝建和元年(147)至汉献帝兴平二年(195)。东汉王朝实际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元年)才正式结束。不过在文学史上,通常建安二十五年问的文学归为魏晋文学的范围。活动于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交替时期的作家,按照习惯,有的划入汉代,有的划入魏晋,而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交错的。”本文涉及的诗歌主要在东汉中后期,但是《古诗十九首》至今学术界尚未明确是属于汉代文学还是魏晋文学的范畴。所以,为了论述的方便,故在本文中提出一个“汉末”的概念,起自东汉中期,终结大致到建安时期。
汉末是一个乱极的时代。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日益庞大,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力。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相互兼并奏响了汉政权彻底崩溃的序曲。战乱极大破坏了生产,给百姓带来灾难,并将他们卷入战争的漩涡。乐府诗《战城南》及《十五从军征》、《妇病行》等作品充分揭露了当时战争的残酷、旷日持久,导致社会民不聊生。战乱宣告着汉政权即将终结,随之也让深固于百姓心中的儒家信仰、观念崩溃。讲求大一统,尊卑有序,倡导礼乐的儒家思想作为汉朝统治思想现在已不再神圣唯一。道家思想重新抬头,先秦流传的其他门派思想也重获市场,东汉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逐渐盛行。乱世的颠沛流离,社会思想的多元化,让文人也从多视角审视自身和社会,叛离体现为一种觉醒。
汉末诗歌对传统的叛离
儒家思想中对政治生活、政治理想极为重视。自孔子以来,历代名儒都在构建着和谐政治生活的蓝图。在此过程中,他们将礼乐、文教(自《诗经》时代到唐代,中国文学都以诗歌为正宗,所以文教即是本文所指的诗教)作为一种有效手段,来辅以政化。孔子编定《诗经》,著《春秋》便奠定了几千年“文以载道”的基调。孔子关于《诗经·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成为历代文学品评的重要尺度。“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成为儒家诗教的重要依据。在西汉文学标志性体裁赋中,由于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对政权劝讽匡谏,对秩序的讲求,及积极用世的诗教成为传统。这种传统在东汉末年被打破了。
东汉末年,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汉政权梁柱俱毁,彻底的倾坍只是时间的问题。几百年雄视八方的政权变得气息奄奄。这使得社会文化心理发生巨大变化。那种“世纪末”的恐惧、失落和与盛时相比的强烈反差,使得士民开始对儒家思想的神圣权威产生怀疑。本土宗教道家在沉寂于“独尊儒术”几百年后复苏,东汉传入的佛家思想也开始传播。加之“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及“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动荡不定的社会状况,战乱不断,人的命运生死无常,及时行乐、趋利轻义的思想也在抬头。这些使得社会文化心理变得复杂多元。中国文学、文化心理在经过极度膨胀、张扬的西汉“少年期”后,此时在朝代更迭和战争洗礼下历经沧桑,逐渐走向成熟。在汉末诗歌里,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变迁痕迹。
1.直露的情爱
《诗经》中有很多作品涉及到男女情爱。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情感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尺度不远。就是《诗经·国风》里被孔子所批评的“郑卫之音”对于后世来说,其实也仍摇曳含蓄。
《诗经》以降,爱情诗歌几乎成为空白,直到东汉。除了在《楚辞》中的一些作品里出现情爱话题外,非常罕见。张衡的《四愁诗》可被看作是爱情话题的抬头,但仍然含蓄蕴藉,并有他指。随之出现的其他民歌、文人作品里,对爱情的追求,对男女欢爱(侧重于情欲追求,床第之欢)的赞美直露无遗。如《上邪》里以热恋女子口吻喊出的爱情誓言足可惊天地、泣鬼神,给人的心灵震撼无与伦比。张衡《同声歌》应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女欢爱的五言诗歌。里面所写“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思为菀弱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以大量的细节铺写房帏生活,大胆地赞美为传统所讳言的男欢女爱之乐。在《古诗十九首》中,虽然很多爱情诗歌温婉地表现男女恋情,但在《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里仍唱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声音。这些作品肯定着男女床第之欢,在当时社会还有儒家思想影响的余威下,这是在思想上解脱桎梏,给儒家定义的爱情表达尺度的重创,充满了对传统诗教的叛逆精神。
2.义、利的取舍
儒家所推崇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准绳随其在汉末的式微而消解。出自一种“文化逆反心理”,汉末文人看出儒家道德光环的虚伪和脆弱。于是,行为取舍上力倡义的薄弱,利的实惠。更何况在极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奢谈仁义道德显得苍白无力而滑稽。所以,在《东门行》中,那位贫士本已出门,却又折回(此时折回应不排除心中残余道德影响的因素),然而看“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在妻子牵衣泣劝时,断然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该诗能被保存及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出,就算一些儒家正统卫道士,对于离乱时代道德衰颓时,人在义、利间取舍的态度无可奈何的理解和默认。此外,《孤儿行》反映出兄、嫂薄情,失骨肉同胞之义气;《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反映出同窗朋友之义的淡薄。《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中更是直接喊出“人生守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常苦辛。”提倡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的儒家在汉末若听此言说,不知做如何想。
3.惜时以行乐
儒家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积极入世的精神也被及时行乐的思想所替代。汉末时代,儒家思想削弱,道家思想重新抬头,佛家思想开始传播。道家思想里本就提及去名务实。佛家思想又以“空”“寂灭”来冲击汉末乱世人的价值观念。于是,惜时以行乐的观念影响很广。在《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反映了宛、洛间从权贵到下层的宴乐自娱,毫无忧国忧时之想,诗末“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既有对权贵们千钟厚禄却无所事事的愤激之意,也有大厦将倾,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及时宴乐来麻醉自己的颓然。在《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先铺写一片荒凉之景。物人皆非,于是感慨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在短暂的人生中,追名逐利、荣耀优游,其出发点决非儒家的“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了。在《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和《去者日以疏》里,作者又提出了“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否定了当时已在流行的修道成仙,感到人生如寄,昼短夜长的悲哀和空幻。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叛离之影响
从文化心理角度考察,西汉文学可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少年期。汉大赋的恣肆纵横、华丽博采体现着少年般初涉人世的自信和外向张扬。至汉末,似进入了成长的青年期,一个心理断乳期。四百年汉祚将尽,儒家已先期沦落,社会文化心理受到极大挫伤。汉末诗歌对传统儒家诗教的叛离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创痛。在这创痛期,文人开始自省,以多文化视角来审视社会,审视自身,更多地开始了对生命、命运、道德等的思考。这是每个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唯其如此,才能成熟。唯其如此,才有随之后继的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的魏晋时期。魏晋时期的文学真正自觉应直接归功于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这种叛离宣告了文人从政治、道德的附庸地位走出,文人个性开始觉醒。这种叛离也有过激之处,体现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否定和颠覆,产生消极厌离的思想心态。但将在后世经过多次的打磨、调适,文人文化心理最终沉淀为成熟,从而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笔者有志于此道,以此小文抛砖迎玉,愿与各位方家继续勉力探讨。
(廖淙,四川省江油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