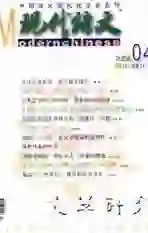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鬼魅世界及其现实基础
2006-03-03张华艳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魏晋南北朝时期鬼故事如雨后春笋,成为当时小说的主流。从量的统计来看,魏晋六朝鬼故事的可观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虽然许多志怪散佚,使后人难窥全貌,但尚存的佚文仍有助于我们作出上述结论。署名魏文帝曹丕的《列异传》今存佚文五十条,取材鬼事的达十四条之多;成书于西晋的《异林》今存佚文一条,亦为鬼事;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当属魏晋六朝志怪之代表,其中五分之一专属鬼故事;东晋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凡一百六十条,鬼故事占了三分之一;东晋孔约《志怪》存佚文十条,鬼故事有两条;东晋祖台之《灵鬼志》存佚文二十四条,提及鬼事者九条;东晋戴祚《甄异传》存佚文十七条,鬼故事则占十一条;六朝虽多“释氏辅教之书”,但承魏晋遗风,鬼故事亦为数众多;刘义庆的《幽明录》存佚文二百六十五条,鬼故事足有四分之一;刘敬叔《异苑》多达三百八十二条,鬼故事凡四十一条;祖冲之的《述异记》存佚文九十条,鬼事近三分之一;魏晋志怪有几十种,以上不过择其典范,约举几例,已足见其盛。
这种现象与远古的鬼神崇拜是分不开的,远古的鬼神信仰是鬼魅小说孕育的沃土,然而它的出现正如植物的春花秋实需要季节的变化一样,它也需要外界的社会环境,以“鬼魅”为主体的小说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说明这一时期的外界环境对于鬼魅小说的出现不无促进作用。而事实正是如此,魏晋志怪小说中所描绘的鬼世界不再是单调的片断的和模糊的,它已经是一个多彩、完整而又清晰的虚幻世界,是人们在古代迷信观念的基础上按现实社会的模样,根据世代积淀的人生经验加以构建的。它实质是现实的一种变形的投影与折射,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其深刻性和广泛性是当时其他文体的作品无法比拟的。本文将从人鬼婚恋、亡灵现形、幽界官吏、鬼魂秉性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论述。
(一)
人鬼婚恋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流传久远而又常见的题材,据小说家考索,魏文帝曹丕《列异传》中的《谈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的一篇写人鬼相恋的作品。随后出现的《搜神记》中的《紫玉》、《驸马都尉》、《崔少府墓》、《钟繇》;《甄异传》中的《秦树》;《搜神后记》中的《李仲文女》等都是人鬼之恋的作品。《谈生》叙谈生年已四十,尚未娶妻,常常是一个人孤独地却有感情地诵读《诗经》。某天夜半,一位少女出现在他面前,少女姿容美丽,服饰漂亮,自荐与谈生结为夫妻,并告诫他说:“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身。”二人恩爱相处,生下一儿已经两岁了。谈生忍不住好奇之心,等妻子熟睡后用灯照了她,发现她腰部以上生肉如人,腰部以下却是枯骨。妻子醒来深责谈生辜负了她,如果再等一年就可以复活了。人鬼不得不从此分离,后来谈生变卖鬼妻临别前赠给他的珠袍时,被鬼妻娘家发现,这才知道鬼妻是雎阳王的亡女。《紫玉》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原与韩重私定终生,但王不允,紫玉遂郁郁而死。三年后韩重游学归来,方知紫玉已死,便到紫玉墓前倾诉衷情。这时紫玉的魂魄从墓中出来与他相会,并赋诗表达她郁结于胸的哀怨。随后邀韩重到她的墓冢,在墓冢过了三天三夜的夫妻生活。临别时紫玉以径尺明珠相赠,并请他转致吴王。吴王以韩重捏造谎言,将其逮捕。紫玉的鬼魂于是向父母诉说原委,母亲想要拥抱女儿,紫玉却像青烟一样消逝了。《驸马都尉》叙书生辛道度游学途中到一家大宅求食,主人小姐以礼相迎,治办饮馔款待,并坦言自己是秦闵王女,无夫而亡有二十三年,愿和他结为夫妻。三天三夜后不得不分离,临别赠金枕一枚。辛道度后来卖这金枕被秦妃发现,查之情实,遂封辛道度为驸马都尉。《崔少府墓》中卢充也因和崔氏鬼女结合而得子,并子孙冠盖,相承至今;《钟繇》中叙述钟繇迷恋女子后,朋友告诉他女子可能是鬼魅,钟繇虽不忍伤害她,却还是用刀砍伤了其大腿,钟繇循血而寻,于墓中发现女子。《秦树》中秦树夜行迷路,来到了一个人家求宿,一女子接待入室,言谈甚恰,遂结为夫妇,第二天清晨,女子泪眼相别,秦树走出数十步,回望宿处,却是一座坟墓,女子赠送的一双指环亦消失无踪。《李仲文女》叙张子长与前府君李仲文死去的女儿结为夫妻,后被发现,李家发墓见女体已生肉,而因为发墓女体己长成的肉也腐烂了,二人不再能为夫妻。
这类作品的故事情节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人鬼的角色分派不同,人是男子,鬼是女子。在魏晋志怪中尚未发现有男鬼和女人幽婚的作品,这些故事中的女鬼都是温柔多情的美女,而且出生名门,况且还都是王公贵族显宦之女。其实这类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寒士庶民在门第婚姻制度压抑下的心理和欲望。自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社会等级极其森严,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现实,就是在同一阶级内部也非常讲究门第高下,据《世说新语》载,桓温为其子求婚于长史王坦之之女,王坦之为此请示其父王蓝田,王蓝田以“兵,哪可嫁女与之”为由而拒绝,当时桓温权势炙手可热,但仅仅因为出身军人而遭自己属下拒婚,这除了说明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权势并不等于门第,有了权势并不能使自己的门第高贵之外,更说明了当时门第等级之雷池不可逾越。这一点在《搜神记》中《申翼之》(引自: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25,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有反映:“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讬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乡严斋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之气,举门户以相讬,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慌愧。”贵族世家为维护高贵血统,严禁与庶族通婚,这种风气至六朝愈演愈烈,贵族与庶族之间通婚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庶族男士们备受压抑,因此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清流男士们坐在一起说民间琐事,道陋巷微语之时,谈论最多的应该是俊男怨女之类的绯闻及人鬼之恋故事,况且在他们谈论的人鬼之恋故事中,男主人多为落魄文人,生活窘迫,境遇堪怜。他们存在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强烈向往。飘然而至的女鬼姿色绝美,温婉可人而令人心旌摇荡,使得那些单身男子长期受压抑地人性逐渐萌动,美满的生活倏然而至,足以令人羡慕。更令男主人公惊羡的是女鬼多是豪门贵族甚或帝王之后,而且往往自荐枕席,以身相许。于是,一个落魄文人在现实中的对高门望族的不满和失落,对豪门世族的艳羡和向往,一起尽情地倾注在描绘人鬼婚恋故事中了,并在这唯我、虚幻的世界中获得自身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欲望,并改换门庭,显亲扬名,在一种近乎白日梦中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和象征的满足。
其次,女鬼一般是未婚而死的少女,有的已有恋人,有的虽没有,却是怀着少女的幽怨而死,她们对爱情幸福都有一种炽热的渴求,是磨灭不了的情爱使她们从坟墓走出来主动投入她们所爱男子的怀抱。这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婚姻“必由父母,须用媒妁”的礼教来说无疑是一种叛逆,在现实人生中几乎没有一个女子敢违背封建礼教而主动追求爱情,然而幽明殊途,鬼的主动大胆
或是因为鬼的身份做了掩护。但女鬼的所作所为也有其社会的因素存在。古代文人们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奉“修治齐平”为己任,以远女色为君子,因而在对待爱情上总处于被动地位,表现在人鬼婚恋故事中,便是女鬼主动委身男子,而且好像越是把女性写的主动、轻佻越衬托出文人的高贵。这实际上是男性语权下对女性主动献情的心理期待的反映,而这种期待在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于是只能在文学创作中将女性写得比男性大胆主动、真挚热情,以此作为他们感情空虚的补偿。
(二)
除人鬼婚恋外,魏晋谈鬼小说中叙述亡灵现形的作品也有相当比例。《异苑·桓杌》(引自:宋,李防《太平广记》卷318上海古籍出版社)写桓妻乳母陈氏的儿子道生淹死了,忽然归家,说在河伯身边当差,告假二十日探家,其母十分悲伤,啼哭不已。桓家有一黑乌鸦,用翅膀遮掩母亲的口,舌上便长了个瘤,其母从此不再哭泣。《述异记·王肇宗》写王肇宗死后现形回家与母亲妻子共话家常,《述异记·朱泰》写朱病亡后未安葬,现形还家安慰妻母。《冥祥记·庾绍之》写绍病亡后不忘亲朋挚友,忽然现形与朋友高谈阔论。《幽明录·王明儿》则叙亡灵对邻里故乡的眷恋,王明死后忽然现形还家:“命召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同观乡间,……”这里表现了亡灵对故乡对家人对现实生活的刻骨铭心的爱慕与眷恋。《幽明录·王彪之》写其母现形让他去躲灾。《幽明录·王志都》写王死也不忘给朋友娶妻等等。这些亡灵现形的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亡去的人对家人的依恋及关爱,我们在体味亡灵与他们亲人之间浓浓亲情之外,不自觉地也体会到了幽明殊途的凄切与悲凉。
而这一点正是这一时期人民生命意识的最真实的反映。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上人民蒙受深重灾难的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交错,封建割据势力为一己之利,不仅把屠刀指向平民百姓,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杀个昏天黑地。诚如鲁迅所言,这是个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战乱、灾荒、瘟疫、暴力频仍,生灵涂炭,人民危险,朝不保夕。死亡的威胁时时困扰着士大夫文人,对生命价值可贵的体认,使他们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伤感,请看下面的诗句:
曹植:“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自顾非金石,咄令人悲”。
陆机:“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陶渊明:“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们像这样敏锐地感受到生与死的问题。李泽厚先生说:“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思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面对生死,知识分子阶层中有的人大作玄言诗,希望在老庄哲学中寻找“避难所”。有的则在山水田园中显示旷达,纵浪大化超然物外,而普通百姓没有那么多闲情逸志,面对无休止的灾难和亲友的亡故,他们往往幻想死去的亲人能突然回到家门,或者自己能与长逝者短暂相聚,于是亡灵再现鬼话大盛,而这些故事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
(三)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王朝更替频繁,士大夫们往往一生经历数朝,仕进不断,荣宠不衰。士大夫传统的品德节操在当时的达官贵人身上是难以找到踪影的。“政失准的”与“士无节操”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干宝在《晋纪·总论》“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的概括,正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集团的本质。整个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无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地方属员,大都只顾自己中饱私囊,惟利是图。一时贿赂公行,贪赃枉法,无法无天。这样的黑暗现实在当时文人的其他作品中是很少见到反映的,而在志怪小说的鬼故事中却有着多方面的揭示。《搜神记》中的《徐泰梦》、《黑衣客》与《甄异传》中的《张闿》三则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鬼吏在执差中可以随心所欲,徇私舞弊,草菅人命,张冠李戴,赦免“应死者”,随便抓一个与“应死者”面目相似或同名的无辜者去顶数。前两则由“应死者”自身或家人对鬼吏哀求得免,似乎充满了“人情味”,但是于彼有“情”于此却无“情”。而且是祸及无辜,使人感到鬼神世界实在是混乱不堪。后一则旨在宣扬善有善报,在人心不古,寡情不义已经成为时代通病的当时,这则故事的产生自然有其现实意义。故事中的鬼吏似乎也有“人情味”,但其“人情味”并非来自“应死者”的哀求,而是来自“应死者”的宽厚。鬼吏赦免“应死者”也并非完全出于“人情味”,如果没有“该死者”毫无吝啬的款待,鬼吏便借口说自己是奉命而来,说了不算,但毕竟吃人嘴软,一番酹享之后,鬼吏便改口让随便找一个替身,回去竟然也能交差。这哪里是写鬼世界,这分明是现实世界的大写真。
相对于前三则故事而言,《异苑》中的《乐安章沈》与《搜神后记》中的《李除》对鬼世界吏治腐败的揭露则更为深刻。如果前三则故事中还有一丁点儿“人情味”的话,这两则故事中就全是索贿徇私与受贿舞弊了。章沈命数已尽,已死数天,却死而复生,因为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所以得免死,由此可见,只要朝中有人,即使犯了死罪最终也可逍遥法外。如果朝中无人,也不必惊慌,只要家中有钱就行。与章沈同被捕的还有一名女子,这女子名秋英,聪明伶俐,见章沈得免,便将手腕上的金钏取下,托章沈送给主事者,结果也得免了。更可笑的是:《襄阳李除》中的李除被天曹抓去时身上不曾准备,但他却懂得怎样使自己起死回生,于是便向鬼吏许下金钏,鬼吏居然也同意让他回取,这样就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妻子守在灵前,忽然见李除突然坐起,摘下妻子手腕上的金钏便又死了。鬼吏得到了财赂,便免了李除。这岂不是公然徇私舞弊与招财纳贿吗?从身居深闺的富家少女与平民百姓也眼见心知,可看出这种风气在当时蔓延范围很广。《搜神记》中的《蒋济亡儿》反映的又是另外的情形,没有亲属,无需钱财,只要有权势,事情依然好办。蒋济亡儿生时为卿相子孙,托父母的福荫,享尽了富贵荣华。死后因生死异路,成了憔悴困苦的泰山伍佰。后借迎新君上任之际,托梦于其母,泄露了“地机”,让他父亲帮忙给自己尚在人世的“新君——孙阿”打通关节,孙阿当然照办了。蒋济亡儿虽在阴间,却能够继续安逸享乐。由此可以看出,鬼世界与人世界原来是相通的,权势显赫者不但可以在阳世横行不法,还可以将手伸到阴间去干预,官僚的腐败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四)
将鬼魅人情化人格化是魏晋志怪的一个显著特点。魏晋志怪所描写的鬼魅多具人形,其形可以是鬼魅生前的形貌,也可以随意变换面孔。有面目狰狞为恶的恶鬼,有面目可亲的善鬼。正如人群有善人好人,坏人恶人一样,作为一类精神幻想的鬼魂群像也可以分为善鬼和恶鬼,同时,鬼也有衣
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有七情六欲的精神需要。在此,关于鬼魅的秉性与特征则也是对现实人性的反映。
恶鬼害人,如《搜神记》中《秦巨伯》:“琅琊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彭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捉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孙警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圻。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刀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之,伯竟刺杀之。”两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在鬼的戏弄下被祖父亲手杀死。这还不够残忍,这其中掺杂着闹剧的成分,出自《搜神记》的另一篇鬼害人的故事《釜中白头公》则让人不寒而栗: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卜,卜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盖来叩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慌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十口,取以当之。后十日,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恶鬼就如同世间的邪恶势力一样,凶狠残暴,杀人不眨眼,但邪不压正,面对邪恶势力,人只要表现出无惧无畏,鬼魅便会像纸老虎一样不战而亡。《幽明录》中《嘲鬼》叙述阮德如在厕所中见一丑鬼,而德如心安气定,说:“人都说鬼可憎,果然如此”,鬼便害羞地退出了。而鬼对阮德如秋毫无犯。可见,这其中的各种恶鬼形象就是各种丑恶人物的再版。
相对恶鬼而言,善鬼则表现了人性善的一面。魏晋志怪中有的鬼知恩图报,《拾遗记》中的《糜竺》篇中糜竺把女鬼的墓移到干燥处,女鬼便救了糜竺家的火灾,保住了糜竺家的财产。《幽明录》中的《桓恭》因桓恭经常向住处一个墓穴中投食,得到了墓主人的相助,位至刺吏。有的鬼见人有困难则主动帮助人,《幽明录》中《鬼赡人》阮瑜之家贫,有鬼来给他衣食所用,日子达到小康。《齐谐记》中《朱子之》朱子之得儿子患心痛,鬼为他寻来了药方……。各种各样的善鬼在冥冥之中关注着世间生人的衣食住行,并在人们有困难时竭力相助,和恶鬼的所作所为相比,则会让人感到温情脉脉,感到世间的温暖。在那个战乱频仍,荼毒生灵的年代,这或许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寄托,从侧面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深厚的人文精神的关怀。
魏晋六朝时的人们相信“鬼乃皆实有”,况且干宝在收集《搜神记》时有“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声明,所以后世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把魏晋志怪小说中的鬼故事当作宣扬鬼迷信的封建糟粕来看待,很少有人敢涉足于这一“禁区”。但如果我们揭开这层封建迷信糟粕的面纱,对这类作品做一番深入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鬼魅的世界中隐含着人世间的真情、欢乐、痛苦与不幸,都是人世问真实的投影。发掘这些作品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现实意蕴,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了解,这才是这类小说存在的价值。
(张华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