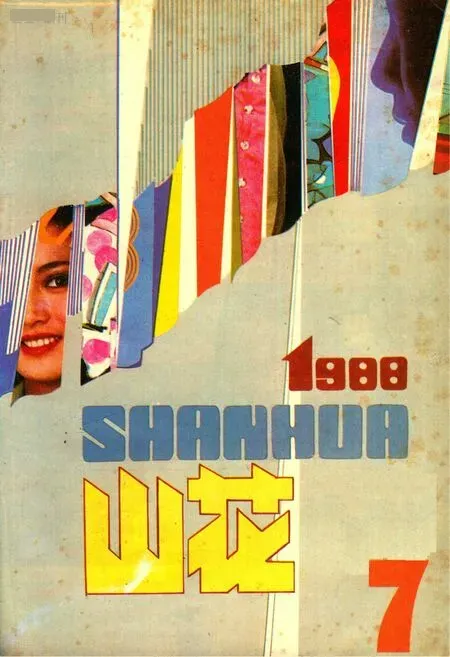网络诗歌对人文精神的解构
2005-04-29任毅蒋登科
任 毅 蒋登科
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诗歌总能较其它的文学门类率先嗅到时代环境瞬息万变的气息,及时作出反应,并对自身的发展方式作出矫正。网络诗歌应运而生。它依赖网络技术而存在,和其他的技术媒介的发展一样,离不开人文的动机和目的,必然地负载着一定的人文价值和人性底蕴。从十多年我国大陆网络诗歌的发展来看,相对于平媒诗歌,它却更多地体现了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解构。
国际互联网1994年落户中国大陆,1995年大陆即有了文学网站。网络文学和作为网络文学重要一翼的网络诗歌在网罗天下的Internet上很快演出了人间的千姿百态。2000年至2001年,是网路诗歌成长最为迅速的一年,大约近二十种诗歌站点和论坛开通,各种综合网站和专门的诗歌网站搭乘“信息高速公路”遍地开花。“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灵石岛”、“界限”、“终点”、“守望者”、“蒲公英”、“锋刃”论坛逐步成长为影响较大的纯涛歌网站,而以综合栏目出现的著名的有“北大在线·文学大讲堂”、“榕树下”、“橄榄树”、“橡皮”等。它们—般都由一个或几个著名诗人牵头,以自身的特色和个性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网络世界中,网站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网站互相链结,携手言欢,资源共享,人员流动,网络写手 (又称“土著”诗人)可以在这充满声光电色、透明而敞亮的虚拟时空中像银鱼般自由穿行,不受拘束,悠悠乎诗哉!网络的这个快乐时空很快也引来“境外”传统诗人的频频光顾。现在,出没于各种大小网站的诗人正日益增多,网络诗歌在一个多元的文化时空中展开,隐约已经对主流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优秀电子刊物俨然有与传统诗歌刊物分庭抗礼之势。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的诗歌网站除了少数运作规范、质量较高的以外,整体水平还并不太好,一些网站更像人来客往、搬货卸货的诗歌“转运站”或人声鼎沸、招帖挥舞的诗歌“茶座”。
诗人杨晓民以敏锐的理论前瞻,率先将“网络诗歌”这一命题推到了大陆文学评论的前沿。他提出“网络世界的普及,特别是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交互性,又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为现行诗歌的转换提供了可能,为大众阅读、写作、批评诗歌开辟了无限的前景。”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正在经历的一次空前的革命,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它不仅会极大地改变诗歌传统的书写和传播方式,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改变诗歌自身的形态。杨晓民又将网络上即将出现的诗歌样式称为“超文本诗歌”,并且清晰、缜密地发掘出它的革命性意义:“网络诗歌”修复了诗歌与现实的关联,拆除了诗歌通向大众的屏障;巨大的交互性,取消了诗人和大众的界限;语言游戏的狂欢庆典;语言的平面化和公共性;平等原则,确立了诗歌新的游戏规则。对网络诗歌的发展前景,诗人也难以抹去心头的隐忧,“网络诗歌的崛起……最终意味着现行诗歌的全军覆没还是泛诗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诗歌的死亡还是全面复兴?”大众传播的全球化形式的确深刻地改变了诗人和读者的书写、阅读方式,认知结构及审美心理,然而,把诗歌的复兴仅仅寄希望于创作媒介的崛起和转换,而不是创作主体精神上的复兴,恐怕也是不可靠的。
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学者、诗人杜国清提出:“由于最近开始席卷全球的国际网络(internet)势将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国际网路诗学。”在中国诗史主题变迁和表现技巧“通变”的诗史发展规律中,考察诗的艺术创造、意象生成、审美想象和象征这些诗学中重要的命题和国际网路的本质、构成之间的关系,寻找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网络诗学的框架。他为我们勾勒了未来诗人“在线”创作的图景:“利用电脑掌握天下资料,再进而运思谋篇,将是今后诗人写诗的创造方式。”“……诗人的想象操作与电脑回应的双向互动中,产生出各种繁复多样的艺术造境,而使电脑网路的创作发挥象征表现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创作成为诗人与电脑对话互动,而在自由自在的电脑操作发挥最大限度的想象力。”网络世界固然可以让诗人享受到言论自由的最大快感和声光无穷变幻的乐趣,可是“极尽声色的耳愉目悦”并不能和“神与物游”、“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艺术运思的美妙等量齐观。即使网络像佛教的“因陀罗网”一样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天下大同、资源共享的“极乐世界”,能够鼠标所向“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但是“信息”不等于艺术创作的才情、知识、想象力和良好的艺术直觉,更不等于“人生智慧”和“生命境界”。技术的进步,信息资源的占有,并不能保证现代人能创作出比前代人更优秀的诗。电脑网络对诗创造的影响是要通过诗人、诗歌发表的场域——诗网站等诸多中间环节达成。夸大网络对艺术灵感的激发、拓展艺术想象力空间的作用,构筑艺术疆域里新的“技术神话”使我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技术文明崇拜和迷恋的气息。
由于诗歌本身的特性和诗歌网站制作者水平或现有网络技术条件的限制,在网络诗歌中表现得并不充分,上面提到的诗歌网站,以多媒体技术和超级链接方式制作诗歌作品的并不多见,在人们理想中充满声光变幻,融音乐性、绘画性和高度艺术性为一体的网络诗并没有出现,杨晓民预言的“具有互文性质的、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超诗歌文本”更鲜有面世,现在人们看到最多的还只是一个平媒诗歌的网络化形态。《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诗歌》(桑克:《诗探索》 2001年第1--2辑)、《鱼戏莲叶间》(马策:《诗生活月刊》 2001年第3期)、《透视网络诗歌》(小引:《界限》诗月刊第3期)、《网络诗歌的虚假繁荣(一))》(尚冰雪:《诗江湖》月刊2002年第1期)、《需要在黑暗中呆多久》(朵渔:《诗江湖》月刊2002年第1期)、《向虚拟空间绽放的“诗之花”——“网络诗歌”理论研究现状的考察和刍议》湖慧翼:《界限》诗月刊第8期)等,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评述“网络诗歌”文学现象的随笔和理论文章,大多是网界同人的“现身说法”,不成系统,难成阵势,整体上缺乏对于网络诗歌的自觉的理论建构。
“网络诗歌”并不意味着它相对传统的平媒诗歌有着独立的写作方式、审美趣味和评判标准,网络诗歌不是独立于原有的文本诗歌存在的,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诗歌的最为内在的本质未变,它只是融入全球化大众传媒背景之中的新的传播方式和诗歌样式。换句话说,网络诗歌是运用网络这个新的媒介和载体,来创作、传播、存储和阅读的新的诗歌样式,它不仅指运用网络的多媒体技术和超文本链接手段创作的诗歌,而且也包括文本诗歌的网络化形态,也就是在网上传播的平媒诗歌。如果用“网络诗歌”挑战已有的传统诗歌的价值标准,甚至干脆拒绝“诗歌”的、“艺术”的批评,像某些前卫的网络“土著”诗人做得那样,就会悖离“网络诗歌”本身的精神要旨。
当然,网络又绝不是仅仅构成了当代诗歌和诗人写作的一个外部环境,促成了一个新的诗坛地貌的形成,也不能把它与传统文本诗歌的区别圈定在诗歌生存环境的好坏,发表的难易,受众的多寡,传播速度快慢等等表象上。“网络”不是加在“诗歌”头衔前面的简单的附加值。当代西方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二十世纪文化传播学上一个划时代的命题——“媒介即是讯息”。习惯的思维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可是麦氏却洞察到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积极、能动地对讯息产生重大的影响。“媒介是人的延伸”,麦氏认为媒介对人的感知有强烈的作用,并且区分了两种媒介和人的感知结构、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呈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呈三维结构。机械媒介优其是线性结构的印刷品)是“分裂切割、线性思维、偏重视觉、强调专门化的”,使人用分析切割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在过去机械时代里,人成为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畸形人。“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到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网络时代的人是感知整合的人,是能整体思维、整体把握世界的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全面发展的人”。由此,网络媒介对诗歌创作也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能动作用。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哪一次书写和阅读方式的改变,不同时又是一次文化的重新定位和价值标准的一次(或大或小的)重新选择呢?用不同媒介手段阅读和创作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物质的性质会直接影响到所表现的内容。电子媒介可以能动地“参与”诗歌的书写、传播,并且深刻影响着诗人的主体精神结构和感知、审美心理。
可是,与传统平媒诗歌相比,网络诗歌却更多地表现出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解构。
网络诗歌的匿名创作放弃了诗人对创作主体角色的承担。网络诗歌的写作往往是匿名的,网络诗人处于一种“三无”状态,即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所有网民在同一个平台上自由嬉戏,相互交流却又各自独立,这使得网络写作可以摆脱物欲功利的诱惑,实现艺术创作的心灵自由;又可以褪去涛歌以外的因素强加给诗歌的负载,保持诗歌的独立品格。随着作者虚拟和主体性缺位,诗歌写作的责任和良知、诗人的使命感和作品的意义链也就无根无依或无足轻重,诗歌的价值依凭和审美承担成了被遗忘的理念或不合时宜的信念。
法国当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经从“知识与权力”的转换机制上研究创作主体的地位和功能问题,他说:“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话语是一种社会权力,诗人对话语的介入,不在于如何将意义赋予诗歌文本以及诗人如何从内部调动话语的规则来完成构思,而是在话语中诗人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遵循一些什么规则?表现出什么功能?网络诗歌写作对主体承担的卸落,正是在人文本体的意义上,用主观代替了艺术主体,又用主观化的客观代替了艺术客体,最终它放弃的不仅是主体承担,还有承担背后的艺术责任和社会权力。
网络诗歌颠覆了传统平媒诗中的人文价值观。网络诗歌大多是从聊天室起家的,“灌水区”里的众声喧哗,图的就是言说自由和消愁解闷。人网者多是怀着好奇、休闲、交友、打发无聊、派遣孤独等游戏性的心情发育的,这种“亚健康”精神状态摆脱了名利等社会束缚,撕开了虚与逶迤、道貌岸然的生存面具,回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网者只需按虚拟牡区的游戏规则扮演好自己的网络角色,而无须承担其他责任。以这样一种心理定势进入网络诗歌创作,便是以类似巴赫金的“狂欢化”方式规避传统观念,鄙视主流文化,清除本质主义,直至嘲讽或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而采用非正统的、前卫的、后现代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社会、生命和生活。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从网上红到网下,说到底是在用一种土得掉渣的言辞将生活的酸楚化作一缕无奈的笑谈和稀松,“翠花,上酸菜”一时间脍炙人口的背后,是对典雅、高贵、仰慕等价值观的生动抛弃。对于网络诗人来说烟消云散的还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人文传统、道德范式和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有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体现意义深度的历史记忆。网络诗歌创作不设防地任由颠覆的价值观对传统实施矫枉过正,以之充塞艺术的精神,其实是把自己的主体立场不负责任地交给了反叛和前卫姿态,从而以一种自蹈幻觉的方式满足那已被架空了的诗歌价值选择。
网络诗歌的读屏模式消解了平媒诗歌阅读时的诗性体验。网络诗歌提供给人们的是屏显电子诗歌文本,而不是纸介印刷的作品,以“读屏”替代了“读书”,“阅读”变成了“观看”,“想象”变成了“直观”,印刷文化演变为视觉文化,是网络带来的诗歌媒介革命,也是后现代社会“视觉消费”对读者诗性体验的拆解。
读者从互联网上读到的诗歌作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屏幕上显示的文字符号,即把传统的平媒诗歌经过电子化处理后送进网络供网民点击和浏览,或者绕开纸质传媒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创作,然后发送到某一网站首发,我们称这样的作品为“网络原创诗歌”。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诗歌,即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文字、声音、图片、图象动画,乃至影视剪辑等融合起来组成的网络诗歌作品,这类网络诗歌没法转换为纸介质作品,离开了计算机网络就不能存在。不过这两种网络诗歌都会造成对诗性精神的漠视、对诗歌审美体验的淡化。就文字读屏模式来说,为迅速吸引网民眼球,一般网络原创诗歌都要设法“让文字动起来”。网络诗人全凭兴致,顾不上精细打磨,甚至压根儿就不具备精细打磨的艺术素养和耐心。网上充斥着的“口水诗”和“平面化写作”就是明证。网民在欣赏时则由于节省时间和上网费的需要,一般都是快速浏览,甚至一目十行,来不及细细体味,领悟不了诗歌语言内部的蕴味(假如作品中有韵味的话)。这对于以表意为主的汉语诗歌来说,是审美阅读的大忌。语言的审美在于一个“审”字,即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仔细端详、把玩和品评。诗歌艺术的诗性魅力是间接的、渐进的和想象的,要通过对语言形象的经验还原、想象填充和韵味品咂才能把握其美感和意蕴,即所谓“辨于味而后可以育诗”(司空图)。钟嵘评价诗歌时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论及诗之意境时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蕴藉深厚的诗歌煮象往往迷离恍惚,超出语表,寄于言外,其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常常是空灵深婉、超乎象外,要靠读者在“收视反听”、“绝虑凝神”中心领神会,达成“神遇而迹化”、“目击而道存”。然而,网上阅读追求的是畅神和逸趣、自适而快心,往往是走马观花,大都省略了诗性体验、审美品味和艺术感悟等重要环节,任由文字和影像从眼前飘过,却不容去作悠悠的品咂和舒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更谈不上追求艺术的精神内核和形式之美。的确,上网读屏少有韵味,只有影像;没有体验,只有速度。诗歌内在的诗性被速度蒸发了,“字立纸上”的诗化平台被声光电屏有效地拆解了。
黑格尔说过,艺术像科学一样也表达着理智透过现象对对象本质的认识,艺术品总要通过精神的浸润而后进行感性的直观,他说:“艺术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把真实的东西,按照它在精神里的样子,按照它的整体,拿来和客观感性事物调和(统一)起来,以供感性观照。”网络艺术作为人的一种认知实在的感性直观,自然会有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应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自我理解方式,诗歌归根到底是高度个人化的创新性劳动,媒介技术手段的更新,对诗歌写作者审美心理结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能代替诗人融入深邃,隋感的智性思考,和诗人深入生命本体和艺术本体的灵魂跋涉。思想家克罗齐曾指出:艺术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不是一种物理的事实,真正的艺术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心灵之中,而物质形式只是真正艺术品的摹本。网络为诗人俯仰天地、放眼古今、精神解放、张扬个性提供了一个平台,却不是力挽诗歌“颓势”狂澜的灵丹妙药。网络上红旗招展、山头林立、人多势众并不一定会产生大作家、大作品。诗歌进步,述需从荡涤诗人和“诗坛”自身开始,伟大的作品的产生,最终还是要植根诗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依赖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伟大人格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重塑网络诗歌的人文关怀、凝聚新的文化精神,引导驾驭网络这匹野马,使它朝向复兴新诗、朝向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精神指向上发展。电子媒体的崛起,把诗歌置于全球大众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新诗应该可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和契机,实现它在艺术领域的再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