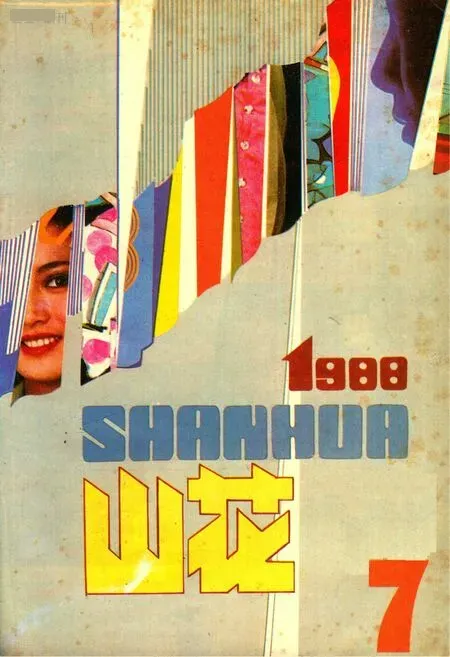精神如何对现实发言
2005-04-29赖洪波
赖洪波
2005年伊始至今,一篇强烈抨击中国当下文化与思想状况的“战斗檄文”(涨炜:《精神的背景》,《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以下简称“张文”)在互联网上引发的激烈论争仍然余音缭绕。其中,作家李锐对张文的批评尤其引人注目。在张文中,把中国从四十年末到现在的思想文化划分为两大时期:即“精神平均化时朗”(或称之为“精神板结期”)和“精神沙化时期”。前一时期的时间段大致为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末;后者则指向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化的逐渐被市场主导的文化状况。论者认为,与“精神沙化”的文化状况相比,“精神平均化时期”的文学和思想虽然“过分简单化和幼稚化”、在艺术创作上也存在“平庸单调”,但这一时期的文化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因为它“尚有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内容,有探索的生气,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运行了几百年的商业化秩序一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精神的平均化”和“精神的沙化”相比,“精神的平均化”由于对商业化的反抗意识而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和更高的等级。李锐的尖锐批评正是因此而起。他的批评矛头显然同时指向“精神平均化时期”的“专制权力和“沙化时期”的市场与消费,并且认为当前中国文化正处于“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张文也就成为只说出“一半事实”的“谎言”。在“拥张派”与“拥李派”的之间,一场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状况的激烈论争由此在网络上迅速展开。
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张李”二人的相同点却也是明显的,即他们都对当下中国文化状况表示极为不满,对之做出了极度阴郁的判断。无论是“精神的沙化”的总结,还是“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的论断,其攻击的矛头都指向严肃文化失去中心位置逐渐边缘化和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文化现状。这种文化状况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由文化界对这场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引发的。可以说,“张李”之争,实际上是对一个老命题的重新提出。这一命题的核心,仍然是在90年代的讨论中就已经触及的:即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逐渐完成市场化转型的社会中的边缘化、严肃文学的边缘化,同时伴随着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转换自身角色的思考。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向则是对大众文化的崛起的普遍忧虑。关于这—问题,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一些对抽象玄奥的“人文精神”表示质疑同时对大众文化的崛起持理解态度的学者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如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事实上,人文关怀、终极价值等等,不过是知识分子讲述的一种话语,与其说这是出于对现实的特别关切或勇于承担文化的道义责任,不如说是他倾向于讲述这种话语,倾向于认同这种知识。在这里,知识谱系本身被人们遗忘,说话的‘人被认为是起决定支配作用的主体。…在中国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的语境中来谈论问题,毫无疑问会触及‘人文关怀这种元理论命题,甚至可以说这种知识构型就包含着这个思想内核。”山这些批评对新世纪“张李”的论争同样有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姿态和立场的“超验道德”,同样也必须历史化,才能使我们得以观察和分析其得以产生的话语机制背后的权力运作。而在新世纪的中国,随着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成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已经具备了一些新的现实因素。而由这些现实因素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新的表征。
在这些现实因素中,我们首先不能忽视的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上的紧密咬合已经使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发生改变。作为全球吸引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经济的腾飞成为带动世界资本流动和增殖的强有力的火车头之一。这一现实因素,标志着中国由自现代历史开始的反抗世界秩序到今天的加入和参与世界秩序的巨大转变。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在上一世纪90年代完成的“惊人的一跃”。在新世纪,我们不可忽视的另一个现实因素是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在此前所不断预言的“崩溃”并未来临。相反,中国却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逐渐迈向“和平崛起”的进程。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从由五四新文化开创的以反抗世界秩序来实现强国梦的文化架构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框架。新世纪的社会现实使我们开启新的思索。
这些新的现实因素构成“新世纪文化”产生的现实土壤,也使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知识分子所争论的命题的阐释具备了更为清晰的现实轮廓。如何阐释新世纪的现实发展带来的新的文化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精神/文化”对现实的思考力度和对现实发言的针对性。在这一问题上,仅仅做出精神和道德上的高姿态是不够的——“知识分子紧紧抵住崇高纯洁性的时候比堕落时更加危险。”以简单的道德姿态对现实表示弃绝,只会使精神/文化在现实变化面前失去应有的理性分析,变成道德家充满悲情和绝望的叫战。伴随着中国现实的发展,“新世纪文化”的一些特征进一步凸显出来。首先,严肃文学的中心地位进一步丧失,“纯文学”获得自身高度发展的同时付出了缩小文化空间的代价。进入现代以来,从五四“遵将令”的新文学开始,无论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还是奶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作为“启蒙与救亡”的工具,文学在文化空间中都居于核心的位置。50年代至 70年代的文学,更是社会聚焦的中心。由此,才产生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的说法。到了80年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倾向就是要摆脱“阶级斗争的工具”地位,成为没有政治束缚的“纯文学”。但是一直到 80年代中期,文学由于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一直是引发社会轰动效应的主要话题。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文学才“失去”百年来的“轰动效应”。现代性话语赋予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启蒙角色因此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知识分子一向以一种双重性的角色出现。他首先是为民众说出真理的人,他掌握语言并成为没有表达权力与能力的代言人,他受民众的委托来表达民众的意志。其次,他从民众身上获得启悟与力量,民众给他激情和灵感。他不一定处于社会地位的中心,却始终处于话语的中心。他是洞察文化历史/语言的人,他提供终极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崛起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新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失落感更为强烈。随着中国全面加入全球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成功,现代性开启的“我启你蒙”的话语秩序的现实基础已经改变。全身心寻找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人机遇、依靠个人奋斗,追求个人成功和财富的世俗梦想营绕在“大众”心头,刺激他们以惊人的勤奋劳作投入到庸俗的具体而微的世俗生活。在一个醉心于依靠个人奋斗追求成功与财富的消费时代,启蒙者的尴尬在于,整天忙碌的人群/大众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来等待“被启”。然而正是这些大众,在改变自身境遇的同时,造就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梦想。中国的现实和“大众”正在以惊人地速度脱离现代性话语所设定的历史框架,唯有启蒙者仍然在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中徘徊。可是祥林嫂们已经进城打工,充当着勤劳而廉价的劳动力。她们一天劳累下来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看《刘老根》与《马大帅》给农民创造的新的改变自身境遇的文化想象,而不是去向知识分子询问“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相关问题。这一次,历史并不需要知识分子面对祥林嫂提问后的匆忙逃离,而是“被启蒙者”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主动选择了放弃“被启”的地位,转而投身于新的文化空间,以新的文化形态去更新关于自身的文化想象。
“新世纪文化”的另一表征正是大众文化的全面崛起。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新文学”的许多社会功能成为中国社会影响力最大和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化形态。由于大众文化与市场化商品化的紧密联系,它的繁荣在一些“启蒙者”的眼里往往就成为一个社会堕落的标志,被称之为没有任何主体性存在的“沙化时期”。但大众文化的繁荣其实已经在这样两个维度提示我们的思考路向。首先,大众文化的繁荣建立在中国社会的逐渐繁荣和崛起之上的。这一现实基础为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大众文化开始承担新世纪文化想象的重要方面。其次,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研究理论告诉我们:“……大众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它既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领域。”可见,大众文化的形态和意义是繁复多重的,是多种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领域。而简单把大众文化看作是由无生命力无主体性“沙粒”构成的堕落的文化形态的观点无疑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简单的道德表态也无助于我们在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有意思的是,由《精神的背景》及其引发的论争本身也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一个表征。一方面,“张李”之争显示出自“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知识分子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这一次,分化在90年代反对和斥责市场化商品化的同盟的内部产生。这一文化现象表征了“新世纪文化”超越现代性框架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新的焦虑。它更清晰地表明:无论是对“精神平均化时期”的“浪漫憧憬”,还是对“板结”与“沙化”的双重攻击,都远离了中国飞速发展的现实。因此它再度昭示了“新世纪文化”本身的复杂性给“精神”提出的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在“新世纪文化”的新的文化空间—互联网上吸引更多的网民地参与,“论争”显然掀起新一轮的话语生产,并且由此带动一些网站点击率和一些人知名度的攀升。话语生产直接带动了经济利益的增长。在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消费文化的批评在新世纪已经以最快捷的速度变成文化消费链条上的一环。一位批评家的追问显然是有道理的:“‘卖掉的一切都是坏东西吗,包括不包括《精神的背景》本身?”看来回答是肯定的。《精神的背景》“卖”得相当不错。它崇高的道德悲情和拒绝进入当下的决绝姿态都已被多元化的消费文化吸纳,使它的消费者在充满道德崇高感的自我想象的中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这恐怕也是这一场“论争”引发的又一个颇为吊诡的文化征候。
从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今日的网络论争,10年来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沧桑巨变,精神该如何来对这些现实发言呢?是躲在同一个命题下无视现实继续自顾盲说,还是迎接现实的挑战开启新的思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正如有人在回顾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总结的:“对于一个社会的一定阶段的各种现象的分析,一定要同其物质基础相联系,没有物质基础的意识不过只是一种观念,同能改变社会的动力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如果没有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加以分析,而只把这种心理作为批判对象,那么这种批判只能带来空虚的道德审判的回应。这种分析可以提醒我们警惕一种对理解现实无益的道德表态,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性的思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