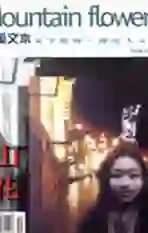阳光下的葬礼
2004-04-29晏子非
三月十五日事件
三月十五的月光汪汪流淌,从窗口飘进又飘出。黔芳与光伟就是在农历三月十五日的月光中走进他们的爱情生活的。
黄昏,黔芳正在凉台上搓洗她的红裤头,光伟看见她背上的小背心随着双手的搓动在腰间一上一下地跳动。黔芳听到光伟的目光穿过来的声音,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呼叫。大林听了,问黔芳在叫什么,黔芳愣了一下,说:今晚有事。大林惊愕地仰头望去,只见黔芳那湿淋淋的红裤头在风中飘呀飘。大林想黔芳怎么知道今晚上有事呢?大林的目光向隔壁的凉台望去,他总觉得隔壁那女人实在是太美了,美得如同冰天雪地中—朵艳丽的花。大林每次看见女人就感到有一股清凛凛的寒风吹拂,让他神清气爽。年复一年,那纤纤素雅的身姿使他总是挥之不去地联想到什么花。是什么花呢?他又—时说不上来。许多个失眠之夜,一次又一次,那花的模样眼看着就要在脑海中清晰起来时,突然“咚”的一声又四散开了。大林经常被这莫名其妙的花搞得头昏脑胀神经衰弱。
黔芳出门后,大林就壮着胆子走进了隔壁那间充满诱惑的房间。他顿时感到做贼样的惊慌,心咚咚咚地往喉咙上撞。房屋光线很暗,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靠墙而立,另一间小屋四壁除了门和窗,全是书。大林见了这些书一下就迷失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书,他顶替他父亲进了水泥厂后,才觉得小学课本上那仅有的几个汉字怎么也用不过来。从此,他就对书充满了敬畏,特别是那些大部头书。大林见了这些书,才觉得屋主的神秘与伟大。他想起了女人的丈夫,那个整天低头沉思着的蔫吧啦叽的男人,他不知那男人整天在想些什么。大林四下张望,才发现那男人此时不在家,他顿时从迷失中清醒过来,一股热气贯注了他的全身,让他狂想。虽然这狂想翻扛倒海地存在着,却像水汽—样让他抓不到实质。他朝着那房间深处走去,有意将脚步落得很重,以掩盖着自己的恐慌,同时想用脚步声提示女人的注意。女人毫无知觉,仍就安然地躺着,丝毫都没有发现大林的到来。大林见了女人全身又是一阵寒颤。他两只脚在幽暗的房间里一前一后地迈着,脚步声在房间里空洞地回响,有几分恐怖,像电影中的某个谋杀镜头。大林来到女人的床头,见女人正眯着双眼,甜甜地笑着。女人的笑使她更是增添了几分秀色。大林从来没有这么近地靠拢这个女人,此时他更强烈地感觉这女人像一种花。大林生出一种欲望,想摸—摸女人的脸。他这样想着,手就随着欲望伸出去了,他摸到女人那洁滑如玉的脸时,那花的形象一下子就在他脑子里绽开了,他清晰地记起了童年时常把玩的一种生长在悬崖上质地生脆的岩百花。
三月十五的月亮,在夜空中汪汪地流淌。黔芳望着圆圆的月亮泪水就一串串地往下掉。
我真的老了吗?
谁说你老了。光伟用手抹去了黔芳眼角的泪水。月光下,黔芳的脸像抹了一层厚厚的粉,让光伟想起了日本的舞女。黔芳软软地偎在光伟的怀里,光伟感觉到一股迷魂的气息扑来,直沁他的心底,使他一阵阵发昏,觉着身体的某些部位在迅速地膨胀,像被孩童呼呼吹大的猪尿泡,他感到黔芳的声音遥遥远远地飘来:跟我走吧。光伟就恍恍惚惚地跟了黔芳来到土产公司那栋废弃的砖木结构仓库,从残破的门洞中钻了进去。黔芳说这是她侦察了许久,是个万无一失的地方。
事后,光伟感到背后痒痒的,像有千百条虫子在上面爬动。他将身子移动到窗下的一片月光里,说你看看我背上好像有虫子,给找捉捉。黔芳借着从门洞中淌进来的月光看见了一片美丽的景致:你背上怎么落满了一片片梅花?黔芳不解地问。她用食指沾住一朵,移到眼前,惊呼道:血——,红艳艳的血。此时,他们才觉出空气中迷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他们气吁吁地跑到派出所报案时,见大林也在派出所。大林正惊惊诧诧地向警察大声说道:太恐怖了,太恐怖了。黔芳扑向大林的怀里。大林紧紧地拥着黔芳,不解地问道,你也看见了?真是太恐怖了。黔芳没有接大林的话茬,脑子里全是那一片片血汪汪的梅花:是从哪里落下来的呢?黔芳暗暗想着,嘴里仍不停地说:死人了,杀人了。大林抱紧发抖的黔芳,责怪道: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什么呀?
你不是说今晚有事吗?
黔芳不解地看着大林,两眼就死鱼一般直了。
值班民警从现场回来后,向局长汇报了这案情,并在当天的记录中写道:
案一
报案人:刘大林。报案时间:某年4月12日22时42分。(农历三月十五日。)案发地点:水泥厂职工宿舍三楼5号。死者姓名:紫烟。姓别:女。年龄:28岁。职业:无业。死亡原因:从现场情况,死者安静地躺在床上,面带笑容,身体表面没有伤痕,无任何暴力和挣扎迹象,可能是自杀。(据悉:死者生前患了15年的忧郁症。)死亡时间:4月12日上午4时许
案二
报案人:朱黔芳,杨光伟。报案时间:某年4月12日10时正(农业三月十五日)。案发地点:县土产公司废弃的仓库。死者姓名:寒隐。性别:男。年龄:30岁左右。职业:水泥厂下岗职工,业余作家。死亡原因:自杀。割破手腕失血过多而死。现场无任何暴力迹象,地上散落一些无页码手稿。据考证为死者生前所写。死亡时间:4月12日下午10时许
备注:据田振副县长说,两案死者是一对夫妻。
散页一
[……我绝望地想着。空气在交头接耳地传递着小话。一双双溜溜转动的眼里藏着一个个鬼胎,世界充满了鬼胎。
银色的铱金钢笔独自悲凉,像一个懦弱者无奈的叹息。笔是什么?我再没有理由和勇气握住它。一个个灵魂在阳光下怆然倒下,笔作为精神的拐杖,在偌大的世界找不到一个支点,任何语言都如暗河之水,任你没完没了地呐喊与咆哮。世界麻木于咆哮,麻木于惊诧与呐喊,像松树皲裂的皮,找不到深埋其中的脉动。这将是我最后的声音了,是我向这世界作出的最后的交待。我别无选择,像落荒而逃的人忘了带上回家的钥匙。我没了退路,没了诉说的语言,那怕只是……]
青春
田振用诗人的想象和浪漫与紫烟邂逅在小城黄昏的老街。
田振从省城的建材学校毕业分到水泥厂,就开始了寻找小城诗人寒隐的历程。田振走在小城老街的青石板街道上,前边是紫烟婀娜多姿的身影。
十八岁的紫烟以无比绚丽的青春照亮小城时,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孤独与美丽注定只是一颗相思的种子,让小城的男人们愁肠百结而又欲罢不能,浮躁的心情黑压压地罩着了小城的大街小巷。男人们整日梦游、狂呼、争风吃醋和打驾斗殴、鼻青脸肿地在大街上展示自己的英雄行径成为那一年小城男人的流行时尚。紫烟每天从街上走过,留给人们的是林黛玉似的冷艳和孤清。紫烟认识自己美丽的同时,也深刻地体味了红颜薄命这一宿命。那时,她已病人膏肓。男人们—个个向她走近,又一个个离她而去。
认识诗人寒隐吗?
诗人?!寒隐?不知道。人们一脸迷茫地摇了摇头。
认识诗人寒隐吗?
哪样人?诗人?你是在说梦话哟?诗人是多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在我们这小城!一个中年男人自以为是地反讥道。
认识诗人寒隐吗?
田振与紫烟走在小城黄昏中的青石板老街上,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从这长长的影子里,人们看到了不远处那个凄美的故事。田振是紫烟经历的男人中最优秀的男人,他以诗人的想象和激情把他们的爱情之路铺展得绚丽多彩。当田振决定与紫烟将爱情进行到底时,紫烟并没有迷醉于风和日丽的爱抚中,她不是不相信田振的一片真心,而是一次次的爱情遭遇使她的理智的光辉从青春的幻想中一层层地剥裸出来,让她经受着未老先衰的心路历程。
田振与紫烟每天像蜜蜂寻找花朵一样寻访诗人寒隐。太阳正从头顶上照下来,田振不时看看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影子,不时看看阳光下闪着幽幽蓝光的青石板路,街道两旁的青砖黑瓦的筒子楼房和木质发黑的吊脚楼,把老街拥挤得幽深而又狭长。临街的门口坐着一些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的老太太,檐下的长木凳上四仰八叉地躺着醉熏熏的男人。田振仍然固执地把目光贴在那一张张茫然的脸上:
你们认识诗人寒隐吗?
不认识。
你们知道诗人寒隐吗?
不知道!
听说诗人寒隐就住在这条街上呀?
不晓得!不晓得!你还要问多少遍?真是一个疯子。
……
田振与紫烟走在这老街上,与黄昏构成一幅情景交融的美丽风景。当时诗人寒隐正趴在老街旁的一栋欲倾还立的吊脚楼的角楼窗口,继续着他夕阳中千年不绝的胡思乱想。他看到田振与紫烟从街上相伴而过时,就感到这两个孤独的身影与自己多少有些关联。田振和紫烟不知道诗人寒隐此时就在自己的头顶上。寒隐的目光还没有在田振身上停稳,就被紫烟那款款而行的步态掠走。紫烟的身旁是深红色的木屋,背后有隐隐的远山,这一景致在木框窗口的剪辑装饰下,成了一幅精美的图画。
……
如果奋举的双臂是因痛苦而张满的弓弦
我将以心为镞
射向那苍老的太阳
人们从楼门里伸出头来,看见吊脚楼的二楼窗口里伸出的一条长长的脖子上,吊着一个葫芦一样的脑袋,正张着嘴巴大声朗颂。人们惊愕地望着那张苍白的脸因激动而涨满了悲切,愤愤地骂道:
又是—个疯子。
田振听见了寒隐的朗诵,旋风似的转过身来,奔向寒隐租住的角楼。
寒隐警觉地注视着站在门口的田振,眼中充满了敌意。田振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他才似曾相识地慢慢缓过神来。寒隐的神情让田振不寒而栗。田振站在寒隐那一片狼籍的屋子里,不知所措:这就是享誉不小的诗人寒隐?这就是高山一样让他仰望的诗人寒隐?田振的思绪中闪现出了“衣已宽”这个词。确切地说,寒隐是“衣已宽”了,像插在玉米地里的稻草人,长过膝盖的黑色春秋衫空空荡荡地挂在肩膀上,一头蓬蓬勃勃的长发扎成马尾拖在后背,只有那双眼睛启明星一样透出寒光。他想起了两年前读到寒隐的一首名为《诗人》的诗:“笔食桑般啃着纸称毒蛇般啃着思想/笔越啃越饿你越啃越瘦/笔啃完纸时/你却瘦成了一首诗。”田振突然看到了寒隐眼中跃动着热烈的火光。他顺着寒隐的眼光看去,紫烟优雅地靠在门框上。四目相对中,寒隐一步一步地走向紫烟,口中喃喃地说:
真是你么?
不,你认错人了。
没有错,你是我冥冥中千百次的臆想,一次次的描摹,已在我的想象中绘成了一幅逼真的油画。
紫烟感到寒隐的目光真诚得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她心中的怯弱与自悲。她不敢抬头直视那目光,只有一股暖流在全身游走,一点点地溶解她心中的绝望,拥抱着她孤独的灵魂。她正沉迷于一个遥远的声音的呼唤。理智的光芒再次照亮了紫烟的记忆时,那两道目光像火龙一样点燃了她心底的希望,也烤煳了她心底的希望。
哈哈哈哈哈哈——。紫烟含着眼泪大笑着奔出了巷道,逃避着寒隐目光的追逐。虽然她从田振的感情中多少看到了一点世俗的虚伪与轻浮,但她不想把自己真正地漩人寒隐爱的漩涡,不愿将自己的感情沉得太深,更不敢企望两人感情的血水相溶,因为寒隐不是田振,寒隐的目光太真诚了,真诚得如一朵冰花,稍有不慎就会悔恨终身。
望着紫烟远去的身影,寒隐顿时感到自己如花残叶落枝断般脆弱。他无奈地看见紫烟的身影如风中旋转的落叶向街口飘去。
交谈中,田振才得知寒隐与自己同在水泥厂,并且,同样在车间轮着三班倒。
你为什么不去浪迹天涯?
因为我母亲。
你需要母爱。
不,我诅咒母爱,母爱是一条蛇,缠着我的日日夜夜。
……
认识了寒隐,田振更深透地认识了诗歌。站在诗歌的面前,他再没了往日的自信。诗歌起码不能改变诗人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的一日三班倒的现实。田振厌恶这样的现实,他心灰意冷地想,生命将在这轰轰机声中一天天灰飞烟灭,一股悲怆的情愫骤然升起。也许这个世界不需要诗人,生活不需要诗歌,但是田振从寒隐的眼中,仍然看到诗歌的根深蒂固。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秋天,田振犹豫着敲开了厂长办公室的门。田振被厂长那惊愕的眼神笼罩得阵阵窒息。厂长是一个胖子,是一个蛮横而高傲的男人。田振惶惶地走进厂长的办公室,手脚无措地在厂长指定的位子上坐下,目光不停地转动。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坐在桌子对面的厂长显得有些至高无上,他干咳了两声后,甩过一支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悠悠地吸起来。田振也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思绪仍是飘飘浮浮的,没有从半空中沉落下来。
我想跟你谈谈。田振嘴唇嚅动了半天,才颤抖地说,心中更是慌乱。
厂长显得有些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面对一个下属,厂长很难敞开他的心扉,何况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下属。
田振也干咳了一下,才稳住飘飞的思絮,开始了他的话题。他们的谈话显得艰涩而又曲折。田振犹豫了一阵,壮着胆子亮出最后一张牌时,他看见厂长矜持的眼神闪烁着如北方解冻的冰河缓缓地流动起来。
那次交谈改变了田振一生的命运。当他那篇关于厂子改革经验介绍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发后,厂长的脸像盛开的牡丹花一样灿烂。田振随之从车间调到了厂长办公室。在小城,一个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青年无疑是前程远大的。
田振刚实践拓开了一个写作者的光明大道。春风得意的田振带着晴空万里的心情去找紫烟时,紫烟正躺在床上双手紧紧抓住床架痛苦地呼喊道:救救我呀,田振。田振奔过去捉住紫烟的手,见她青紫的脸上因痛苦而扭曲的表情,心情顿时晴转多云。以后的日子里一想到紫烟,田振就是愁眉不解。看见田振度日如年地煎熬,紫烟坦然地向田振挥挥手,以友好的方式让田振走出痛苦。当爱情再—次如空中的彩虹远去时,紫烟只是摇了摇头。
田振希望自己的成功能让寒隐觉悟些什么。他兴致勃勃地拍开了寒隐的门,刚一落座,便急切地与他交谈,像在朗颂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歌。田振太得意了,他只顾自己不停地讲,没有注意寒隐表情的变化。寒隐的目光里渐渐充满了鄙夷的神情。田振最终感到寒隐的目光如数九寒天的霜风一刀一刀地割着他的心,他的讲述才一声比一声低了下来,最后,他突然改变了语调,争辩道:我也是多么地热爱诗歌啊,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诗人。寒隐无力地摇了摇头,喘着粗气扑向窗口,仰天长啸道:
多么地悲哀啊!圣洁的诗歌,你为什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势利人们猥亵!
寒隐实在是容不下一点儿虚伪。他总是时时将真诚裸露出来,最后却又被现实撕得遍体鳞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独自落泪。一个又一个夜晚,田振徘徊在寒隐的窗外,见寒隐的屋里一直没有开灯。黑暗中,只见烟蒂一闪一闪地照亮着寒隐满是泪水的脸。然而在这片诗歌的沙漠上,田振是寒隐望眼欲穿的唯一绿洲。一天,寒隐终于打开了门,以诗歌的真诚和青春的热情拥住了田振。一个农民的儿子就这样以自己艰辛苦难的历程原谅了另一个农民的儿子无奈的追求与选择。他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只是相互道了一声珍重。
一路的风尘与艰辛,田振忘了诗歌如同遗忘了诗人寒隐,只有在孤独的时候,寒隐才像冬天萧瑟林丛里的一片耀跟的红叶,在他意识的深处飘摇闪耀,像一个惊世的感叹,让田振怦然心动。
散页二
[……是真实的,奔腾的血啊!奋勇地向前方,我看到了死亡的海岸,原来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收留着那些奔逃而疲惫的灵魂,让它们真实地躺下。
沿着那束阳光的方向,我看见了紫烟,紫烟安详地躺在床上,死亡把紫烟妆扮得那么甜美。我惊叹着紫烟的甜美,死亡的甜美。甜美是期待。紫烟在期待什么?等我去继续着我们的情缘?那关于爱情的寓言。紫烟是这么说的,她说完这句话后,灿烂的笑就凝结在脸上了。我看见了她的笑就热泪盈眶。我惊奇着这灿烂地笑着的紫烟的美,一种旷世的美,清雅中的热烈……]
电话
一个电话使田振想起久违的诗人朋友寒隐。
自从与诗歌分手后,田振在这条路上,一路埋头疾走。他没有回头顾望一下,他不是不想回望那段消魂的青春时光,而是怕自己的灵魂受到诗歌的鞭打。他像疯狂的扑食者,加速地远离了过去。
长久以来,电话铃声整日像发情的猫,时时向人们提示它的存在。田振习惯在这电话铃声中接待一个又一个来访者,习惯于人群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像空中的氧气,让他无法躲避。如果某一天,人们不再来访,电话铃声也不再响起,他真难想象那样的日子是多么的空寂。置身于这样的气氛中,他感到自己有着高瞻远瞩的灵动,视野广阔得像如来佛伸出的两支手臂,就是那本领超群的孙悟空那十万八千里的跟斗也只不过是在他五指间的戏耍的游戏。田振常常生出一种错觉,感到自己与电话是连接着一张密集的大网的网绳,被他紧紧握在手中,网的所及之处就是他打捞权力的水域。在这片水域中,鱼群的走向尽收眼底。这超然的眼力来自他静观八面来风,锁定四方云动的能力。
寒隐的电话是在一个午后打来的,当时,田振正在与工业局长密谈着一件重要的事情。整个房间候满了云吞雾吐的人,一个个神情紧张地候在外厅,怯怯地小声议论着。这时,电话铃声像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聚然高声大叫起米,使表情严肃面孔僵直的人们一下子活跃起来。田振的妻子像一股可爱的小旋风,从人群中飘过来,抓住电话,接着又将话筒捂着递给田振,并轻声说道:一个叫寒隐的。田振见这名字一时没有照亮自己的记忆,手一挥,像挥去一个烟圈。妻子对着话筒说了一声:“他不在家。”就挂了。
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起来,田振无奈地从妻子的手中接过话筒,还没有移近耳旁,就听到那边大声骂道:
怎么了,县老爷,真的很忙吗?忙得连当年的烂哥们的电话都不接了?田振愣了一下,想能跟他如此说话的人实在少有。他皱了皱眉头,静心地辨认对方的声音,当他听到是老叟的声音时,心中的怒火就一扫而光了。
你看你,又犯牛性子啦?我不是正在听你骂人吗?
我是说刚才,刚才寒隐的电话。
哪个?寒隐!此时寒隐的身影才一下跃进他的想象中。
久违了,我的朋友!田振暗自叹息道。
寒隐在电话里说他下岗了,希望他这个县长能用手中的权力为他谋一份工作。田振心情一下子就暗淡下来了。他感觉一阵悲凉,为寒隐而悲凉,他想寒隐实在不该落到如此地步。
知道了寒隐的处境,田振再也控制不住了自己,任表情阴云暗淡,明察秋毫的工业局长忙问道:
铁哥们?
当年在水泥厂的文学难友。
搞文学的?到我那里去吧,我那儿正差一个写写画画的人。
那太好了,王局长,我代表我的朋友谢谢你。
没什么,既是你的朋友,就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两天后,寒隐就到工业局去上班去了。
田振在官场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日子里,寒隐在他的记忆中渐渐退隐。一天,老叟来到田振的办公室,一本厚厚的小说集子递到他眼前,他才惊叹着寒隐的毅力的坚韧和思想的深沉。那本《奔逃与固守》的小说集子在当年获得了全省的一个大奖,这给寒隐在文坛上奠定了基础。他想寒隐这么多年的努力也该有所回报了,生活应该给那些苦苦耕耘的人一份收获的希望。老叟还告诉田振说,寒隐与紫烟结婚五年了,至今没有生育。田振听后,心里一阵痉挛:他在心里为寒隐的高尚品格敬礼!
寒隐到工业局上班还没到一月,王局长就来向田振诉苦了:
田县长,您那朋友我再不敢用了。
怎么了?
他太死心眼,我让他写一个报告,到地区争取全县各工厂的技改资金,他却把全县工业的亏损情况如实地写进报告里,并将亏损的原因归罪于种种人为的管理不善。我说这样不行,让他改改,他还理直气壮地与我争论什么实事求是,说我是欺骗,不吸取历史教训。你说,这样写上去,上边能批吗?
田振听后,也是非常气愤,心想你寒隐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见回头。
第二天,田振把寒隐叫来狠狠地训了一顿。在他大声吼骂中,寒隐竟没有像他想象那样针锋相对,而是勾着头,让他把气出完了,才嚅嚅地说:
对不起了。
这样吧,我再给你联系一下那些私营企业。
算了吧!我是没救了,我总是不能容下一点虚伪,明知那样做的后果,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我还是静下心来写我的小说吧!
可是你总得找个工作维持生计呀!
我与紫烟不是还有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吗?艰苦点,也许还是能撑下去的。
紫烟怎样?田振感到心中一阵绞痛。
还不是老样子,天天吃药。我怀疑她的血管里流的不再是红色的血了,而是黑色的中药汁。从此,寒隐和紫烟的处境一直是田振的一个心病,他时时留意,想为寒隐找一份工作,可这小城因企业单位都不景气,正在裁员;而县财政困难,事业单位又进不去。
几天之后,田振又接到寒隐的电话,寒隐在电话里急切地说:
田振,快救救我呀!
怎么了,你!
我完了,当我坦然地静下心来写作时,我再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文字了。
怎么会这样呢,先别浮躁,好好地调节一下心态。
你能给我找—个空闲的房间吗,我想换个环境看看。
好!你耐心等着吧!我给你看看。
散页三
[……自言自语,语言像风雨来临前的星星,怆惶逃遁,失语是一种境界,这并非我空前绝后的顿悟。
我睁开眼睛的刹那,阳光就明晃晃地挤满了一屋。一缕缕阳光荡漾着,洗涤着我的一些私心杂念,使我头脑玻璃般透亮起来。
世界死静,被丝丝的虫鸣奋力撕开了一条窄窄的缝隙,随后,又严严实实地弹了回去,严密如初。心间如挂在钟乳石上的水珠,“叮咚——”一声坠下,在空寂中激起一声回响,随后,就凝结了。
生存的全部过程就是逃遁,从希望到失望,从残缺到圆满。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如一条忠实的狗,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为了这一职责,耗尽了我全部的智慧,信心与意志。然而,世界恰恰是忠实的刑台,是灵魂的地狱,是爱恨交织的网。
血终于涌出来了,像黎明前的鸡啼,黄昏里的晚霞,清新婉转如小桥流水。
红艳艳的血啊!奔腾着,沿着蓝色的脉管……]
阳光下的葬礼
寒隐与紫烟的丧事是由田振主持举办的,灵堂设在水泥厂的院子里。因为田振的关系,县里各单位都送来了花圈。田振此仁义之举成了人们一时间广为传颂的佳话。也有人说,田振这是机关算尽,苍天助他。这几天县里正在开人代会,副县长田振是县长候选人之一。他这样做无疑给这次县长竞选增添了筹码。可悲的是,洁身自好清高一生的寒隐最终还是成为他人仕途上的垫脚石。田振很忙,但他每天再晚也要来灵堂里坐一会儿,他每次来都是前呼后拥的,就是在灵堂停留的那短暂几十分钟里,仍是一边接电话—边与人交谈。一会儿,有人前来与他耳语一阵,他起身向寒隐的父亲母亲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匆匆地走了。田振—走,跟随的人也散去了,灵堂顿时冷清下来,只有政府办的一个办事员守在灵堂。这时,寒隐母亲那一声声悲切的呼号与阴阳先生的傩堂戏交叉着进行,给这灵堂带来些哀伤的氛围。寒隐母亲那哀哀凄凄的哭号足以使每一个在场的人落泪:我苦命的儿呀!你怎么就走了呀?丢下你的娘在后面怎么办呀?我——的——儿——啦——。你——等等我——呀——。寒隐的母亲哭着哭着,哭到伤心处时就向棺木撞去,但每次都被寒隐的父亲拖住了。寒隐父亲一直表情木然地坐在灵堂边的一个角落,想着他永远解不开的一桩心事,只有老伴哭到伤心处时,才走过来双手拥着老伴的肩膀劝说—阵,好似他从十里之外的乡下赶来不是参加儿子的葬礼,而是专门来看护他的老伴。寒隐的兄弟姐妹们都没有来。在他们兄妹五人中,只有寒隐一人在外工作,余下的四人都在乡下老家,整日在土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跳出了龙门的寒隐无疑是他们的希望与骄傲,但他们说寒隐是个窝囊废,工作多年从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儿实惠。听寒隐的母亲如此说,在场的人都感到心酸。不知寒隐听了此话有何感想,只见松枝白花丛中寒隐的遗像表情恬静,似乎把世间的一切恩怨全抛在了脑后。
三月的阳光中迷漫着浓浓的淡黄花粉气息,香飘阵阵,使人感到一股绵绵不绝的醉意,像农人犁完松软的土地后端着的一碗老酒。这天,完成选举任务的人大代表们走出会场时,见一黄烟里走着一路送葬的队伍,在这小城三月的春光里,成为一道风景。那一路的黄烟、麻布、唢喇纷乱了天空,纷乱了人们的思绪。两坟棺木在黄烟中游动。沿街的人们看着两坟棺木,交头接耳地风传着死者生前的种种传奇,斜视的目光穿越滚滚黄烟,似乎看见了死者不屈的灵魂在舞蹈。
那辆红旗轿车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边,田振表情凝重地坐在车里,人们分不清这位新当选的县长脸上的表情是悲还是喜。
两天前,人们还不知道小城中住着一个名叫寒隐的作家,他为文一生,却默默无闻,最终,是他的死亡方式让他在这小城—鸣惊人。人们在传言中张着惊愕的嘴,久久不能合拢。一位在乡村当了二十多年教师的人大代表听到这些传言后,沿着那传言四处奔走,寻找作家的著作。乡村教师终于在县文联的一个集满灰尘的厨柜顶上找到那本《奔逃与固守》的小说集子。他回到宾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细细品读,寒隐的形象才通过他的作品在乡村教师的想象中支离破碎地活跃起来。乡村教师通宵达旦地读着这些艰涩如天书般的文字,却总找不着文字的精髓。此时,窗外传来了雄鸡的第一声啼叫。乡村教师合上书,关了灯,闭目思索良久。突然,他拍案而起,仰头长叹,似乎一个顿悟,照亮了全书。他拉亮电灯,准备再次细读,刚打开书,见一路彩蝶从书页中鱼贯飞出,在乡村教师的头上绕了三圈,从窗口飞出。乡村教师追到宾馆外,见灰麻麻的天空中,只有东边的启明星闪着清冷的光辉,那一路彩蝶在这光辉的衬映下,飘飘渺渺地向天边飞去,乡村教师仰头凝望了良久,直至那彩蝶飞出他的视野,才一步一回头地返回房间,拿起书再看时,书中已空无一字了。
作者简介:
晏子非,原名晏武方,生于1968年。本文为作者小说处女作。